- +1
美軍祁觀︱告別后冷戰:大國競爭軍事準備
冷戰勝利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紅利,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得到鞏固,政治上定于一尊,軍事上獨孤求敗。
單極時代的美國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與許多敵人交過手,而這些對手的體量、技術及組織能力都與美國不在一個“位面”。后冷戰時代美國的多次主要軍事干預與戰爭均發生在歐亞大陸或歐洲腹地,這些對手雖處在地理上的腹地,卻是地緣上的“帝國”邊緣。
當前,美國開始以“大國競爭”的回歸作為自身全球戰略的基調,其焦點又回到了如何在東半球、歐亞大陸及其周邊域內(如近海、遠洋)預防和阻止“新王登基”。在西太、東歐這兩個潛在的新戰線上(特別是前者),美國所要面對的是技術能力、裝備質量與數量、訓練水平、作戰思想、后勤動員等方面均在提高的對手。
當美國的對手在閱兵場上、訓練場上一次次檢驗、打磨和展示新質戰斗力時,美國開始了告別后冷戰時代的軍事安全戰略大調整。在新興大國奮力爭取機會窗口的同時,美國也在強調面對軍事大國時如何確保戰略和戰術上的“優勢窗口”。
大戰略回歸
大國軍事競爭定位的確立,標志著地緣政治“大戰略”的回歸。相較后冷戰時代和后9·11時代在“帝國邊緣”地帶的軍事介入及長期的治安戰,回歸的大國競爭“大戰略”要求美國從全球、跨地區、跨領域的層面進行軍事安全準備,而非聚焦于單一地區、國家或領域。
這種回歸相承于美國自參加一戰以來對歐亞大陸的戰略認知。在某種意義上,歐亞大陸之于美國類似于歐陸之于英國。任何一個有可能大范圍集中歐亞大陸資源和力量的國家都會成為美國的離岸平衡對象。
麥金德與馬漢的結合,或明或暗地主導了美國的大戰略思維。確保美國能夠相對自由和低成本地獲取東半球的資源與將東半球納入其全球經濟版圖,是美國大戰略的長期主題,無論美國政客與政策決策者是否如此明確表態。聽其言,在官方戰略中,如最近的重返亞太、印太戰略,都表明了這一定位。觀其行,美國過去一個世紀的戰爭經歷、軍力發展重點、結盟策略等等,無不指向這一戰略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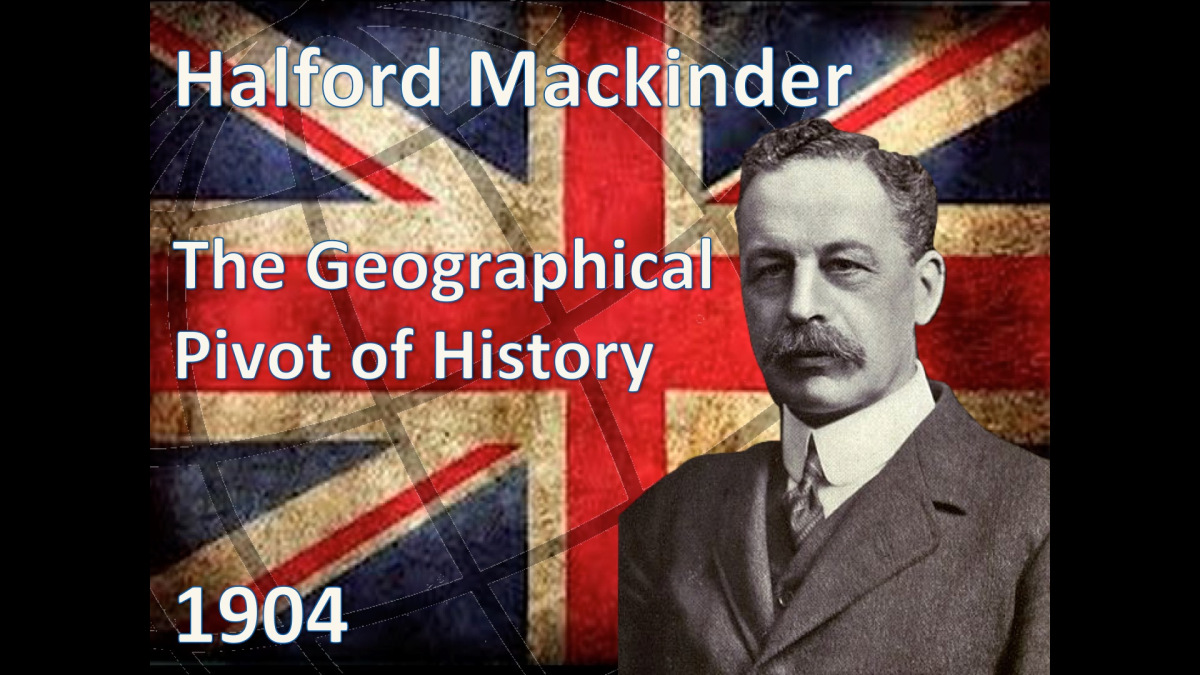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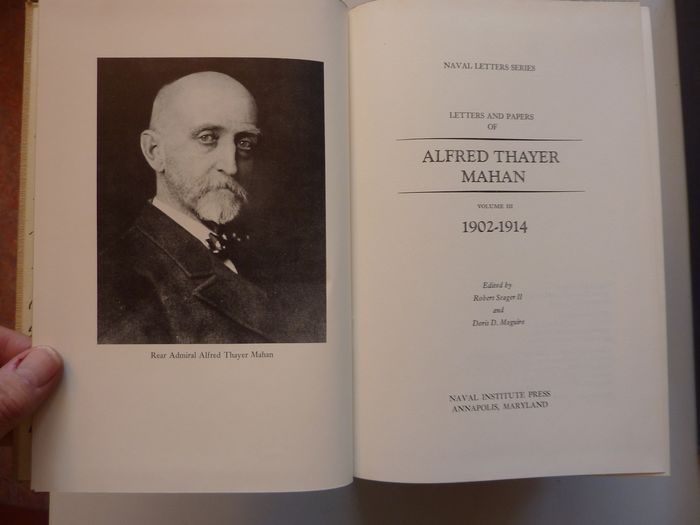
基于這一定位,美軍始終是一支進攻型的外線作戰軍隊,擁有最強的遠程力量和火力投送能力,擁有遍布歐亞大陸關鍵節點的基地、補給、預置力量、情報監控網絡。
在大國競爭思路下,歐亞大陸出現以下兩種情況的任一一種或同時出現,美國便會做出軍事上的準備:一個或多個大國可能在歐亞大陸及其周邊各域(近海、遠洋、電磁、太空等)獲取壓倒性戰略優勢;歐亞大陸的美國盟友及伙伴國家無力對這一新興大國進行遏制。
威懾與戰爭準備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大國競爭成為美國軍事戰略基調后,迅速成為美國軍費政治的主要元素。無論是軍費鷹派,財政問題上較為保守的共和黨人,還是堅持國防與非國防開支掛鉤的民主黨,在大國競爭需要也應該花更多錢的觀點上是一致的。從奧巴馬執政后期到特朗普上臺這幾年,這種意見一直是主流。
如果參照美國自身的高標,由于整體財政狀況、赤字壓力、兩黨政治和程序成本掣肘,現在的軍費局面并未達到大國競爭旗手們的理想狀況,或者說單靠大國競爭的定位無法支撐高標的軍費增長與擴軍、換代,但不斷攀升是事實。
大國競爭給了美國過去幾年軍費持續增長、創新高的原動力。
目前美國的軍事準備在戰略與常規力量、威懾與作戰思想、重要資源的使用、軍事動員能力幾個方面都有所展開。戰略力量方面,五角大樓做出了幾年內戰略威懾能力現代化的數十億計劃;未來將裝備新型戰略導彈核潛艇、新型隱身轟炸機;不斷提高多層導彈防御網的建設,從偵察探測能力、指控系統到殺傷載具,升級工作全面鋪開;退出《中導條約》,加強陸基中遠程火力建設,提高對軍事大國的區域威懾能力、對時間敏感目標的打擊能力。
常規力量方面,美國的軍事準備重新回到針對同級別能力和體量的對手,將作戰能力聚焦于規模相對大的高強度、高技術常規軍事沖突。這與過去幾十年在歐亞大陸腹地與中小國家及非國家行為體作戰是完全不同的。
為此,美軍加速空中力量的隱身化;在海上重新強調制海權的爭奪與掌控,由后冷戰時代的由海向陸與近岸作戰能力建設重新轉向艦隊防空與反艦能力;加強各軍種遠程打擊能力;提升本已獨步全球的情報、監視與偵察能力,包括太空軍事能力;強化電子戰與賽博空間的攻防能力,特別開始著重攻的環節;多管齊下開發高超聲速武器,提升對時間敏感目標的快速反應能力;將無人化與人工智能技術引入指揮和殺傷鏈條,從情報收集與分析、目標甄別到任務規劃,在“人在回路”的前提下縮短殺傷鏈,提高大國競爭中對稍縱即逝機會的把握能力,維持并盡可能重新擴大“優勢窗口”。
作戰思想方面,美國對于亞歐大陸新興軍事強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力量擔憂已久,即便反介入與區域拒止不是這些國家的官方戰略,其軍事力量發展也并非單純以反制美國為目標。美軍以此為假想作戰環境,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如陸軍與空軍的“多域作戰”、陸戰隊的“遠征前進基地作戰”、海軍的“分布式海上作戰”。
這些新方案雖都處在不成熟的發展階段,且各有側重,但在戰爭規律演變的大方向上,體現了一些共同特點。它們都強調:進一步深度融合;多個域的打通(陸、海、空、天、電、網);戰場密度進一步降低,即每一級作戰單元的責任區范圍繼續上升;在提升單一平臺能力的基礎上同時弱化平臺作用,更加側重平臺間網絡的作用;提高新概念、新技術的開發和使用,如無人化和人工智能。
能力建設方面,由于對手逐漸縮小了與美的軍事能力代差,五角大樓內外開始更加嚴肅地看待美國國防技術與裝備的開發與采購效率,核心目標是提速,連帶目標也包括減緩成本攀升。這些目標的達成無法單獨依靠五角大樓自身的改革與合理化流程實現,也不僅僅是政-軍-工互動的結果,而涉及到更大范圍的國民經濟調整,如從奧巴馬到特朗普政府都一再強調的產業回流和再工業化。不過開發流程的合理化非常必要,如新的“804條款”,將產業和產品開發的優先級別重新置于五角大樓冗繁的辦公室、案牘工作之上,在武器系統開發流程節點之間形成優化和必要的重疊,給予軍方特別是作戰部隊更大的發言權。
同樣在能力建設方面,為了應對大國競爭,美國開始重新關注國家動員能力與潛力的建設、戰備水平的維持與提高。在這方面,經歷過世界大戰與冷戰對抗的美國并不陌生,也并未自廢武功。但是在與類似體量與質量的對手交鋒時,在高技術、高強度、高烈度沖突中,如何確保后勤、人員、彈藥、信息等方面的持續保障,對于當前的美國來說仍是個相對新的問題,如其關鍵軍兵種的戰備水平便是一個問題(相對美軍自身高標而言)。不同于對付那些“我家大門常打開”的中小對手,美國將無法自由、安全地確保戰場單向透明,無法將彈藥消耗視為“去庫存”而開始大規模提高關鍵裝備(如防區外導彈)的儲備,無法維持絕對的制空、制海權,無法以相對低的成本自由進出作戰區域。
總之,美軍將不再是那支擁有“上帝視角”和動輒“開掛”的軍隊。在大國之間即便是短周期的沖突中,美軍乃至美國如何保證可持續的戰斗力輸出,都會是一個新挑戰。
長期斗爭準備與韌性
美國政界與軍方認為大國競爭與“帝國”邊緣地帶最大的不同是長期存在的斗爭灰色地帶與所謂的“混合戰爭”。情報、賽博攻防、輿論戰等領域的交鋒將長期存在。
“多域作戰”概念便不再把大國競爭和軍事沖突簡單理解為交火,而是在沖突光譜的左右兩側均做了延展,“沖突左”包括政治影響、顛覆活動、網絡攻擊、信息輿論戰等,沖突過程包括各個域能力的綜合使用,強調一體化、融合、遠程打擊,沖突右則是重新進入威懾與僵持狀態或更理想的在戰略態勢上成功削弱競爭對手,完成對東半球崛起大國的壓制。
為了在這條延長了的沖突光譜上取得優勢,美國不僅在做著前述調整,也擁有很好的基礎。對于美國所認定的戰略競爭對手來說,今天的美國依然是太過強大的存在。在硬件上,美國有全球基地網、質與量皆超班的航母體系、最好的攻擊和導彈核潛艇、隱身化程度最高的空軍機隊、遍布全球的海底聲納陣、最為完善的衛星網絡等等。在軟件上,美國在過去百年經歷了世界大戰的洗禮、兩極對抗的考驗、單極世界的紅利收割,在資源動員和整合、訓練和作戰思想創新等各方面都擁有最為豐富的經驗。

此外,美國擁有堅厚的技術等能力積累,并在此基礎上擁有很強的糾錯能力。在后冷戰時代的“誤判”坐實后,便展現了很強的調整能力,如從裝備到思想重新對制海權的重視、在平臺代差優勢逐漸被縮小后重網絡輕平臺的轉向等等,無論是“第三次抵消”思路還是空海陸軍的“穿透型制空”、“分布式殺傷”、“多域作戰”,以及特朗普政府通過建立“太空軍”對于太空資產整合的特別強調,從歷史尺度來看都是在極短時間內做出的反應。落實過程中雖有軍費水平不盡理想、國民經濟去工業化后的質量和成本控制問題等困難,但對于美國這種體量的霸權國來說,能夠在沉重的“帝國包袱”下做出戰略和行動層面的迅速調整,不能不說是體現了其軍事安全機器的強大、彈性和韌性。
面對這樣一個從質到量都依然優勢明顯、且頗具彈性韌性的美國,對于被其所認定的軍事競爭對手來說,過去幾十年的成就巨大而令人鼓舞,但前路依舊坎坷,唯有俯首砥礪,與時間賽跑,與自己賽跑。
----
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