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普通人的自然|穿行汗馬:在自然保護(hù)區(qū),它們發(fā)現(xiàn)了我們
一路向北四千公里,轉(zhuǎn)機(jī)、驅(qū)車、長(zhǎng)途奔襲的過(guò)程中,目睹著山河地貌的變化,雪也層層遞增,漸漸顯像。冬雪漫漫,隨著時(shí)間推移,一切消隱其中,城市的輪廓如同謎題,只能等到春日才能拆解。

汗馬自然保護(hù)區(qū)的森林。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今年冬天,東北成為一片令人趨之若鶩的土地,除了雪的魅力,更多是由熱梗頻出的文旅營(yíng)銷帶動(dòng)的。與催生出流量人格的“爾濱”相比,同樣地處東北的“興安嶺”,更像一種來(lái)自語(yǔ)文課本的復(fù)古記憶。有趣的是,追溯課文的本源,上世紀(jì)60年代的課本里寫的是大興安嶺冬日林區(qū)緊張的伐木作業(yè),而當(dāng)下的課本里則是描摹小興安嶺中紫貂、黑熊與松鼠的蹤跡。這也恰恰說(shuō)明中國(guó)林區(qū)的時(shí)代變化。
林中激流:何為自然的原真面目
大興安嶺擁有大片寒溫帶森林、自然奔騰的河流和廣闊的濕地,8萬(wàn)平方公里的林區(qū)被稱為是中國(guó)最北生態(tài)安全防護(hù)屏障。自1964年開(kāi)發(fā)建設(shè)以來(lái),大興安嶺地區(qū)累計(jì)為中國(guó)提供商品材1.26億立方米;但2014年開(kāi)始,大興安嶺地區(qū)全面停止天然林商業(yè)性采伐,正式進(jìn)入轉(zhuǎn)型。

汗馬自然保護(hù)區(qū)的牌子。
而我此行要進(jìn)入的汗馬自然保護(hù)區(qū)(后簡(jiǎn)稱“汗馬”),位于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倫貝爾市根河市金河鎮(zhèn)境內(nèi),地處大興安嶺北段西北坡原始森林腹地,這也是中國(guó)保存最為完整最為原始寒溫帶明亮針葉林區(qū)。“汗馬” 在鄂溫克語(yǔ)中有“源頭”之意,即激流河的源頭。激流河是額爾古納河重要支流之一。在地圖上看,額爾古納河的眾多支流水系猶如蔓延舒展的葉脈,沿著大興安嶺的主脊通向大地的心臟。因汗馬從未曾受到人為干擾,這里也是野生動(dòng)物重要棲息地。汗馬自1954年被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政府批準(zhǔn)為“禁伐禁獵區(qū)”,1996年成為國(guó)家級(jí)自然保護(hù)區(qū),2015年被正式指定為“世界生物圈保護(hù)區(qū)”。

塔里亞河,額爾古納河的一級(jí)支流激流河的源頭。
對(duì)我而言,也因這次參與青野生態(tài)的行程,才開(kāi)始深入了解自然保護(hù)區(qū)的概念。青野生態(tài)立足于四川唐家河自然保護(hù)區(qū),由最初白熊坪保護(hù)站的站長(zhǎng)刁鯤鵬創(chuàng)立——“刁站”也是這次行程的領(lǐng)路人之一。
更奇妙的是,在我的家鄉(xiāng)肇慶市18公里外,地處珠江三角洲平原邊緣的鼎湖山,實(shí)際就是新中國(guó)第一個(gè)自然保護(hù)區(qū)。這里有近400年記錄歷史的地帶性原始森林──南亞熱帶季風(fēng)常綠闊葉林和其他多種森林類型。當(dāng)然,如果說(shuō)對(duì)自然保護(hù)區(qū)的認(rèn)定,是從“禁伐禁獵區(qū)”的標(biāo)志開(kāi)始,那么這個(gè)“第一”到底歸屬何方,在汗馬也時(shí)有爭(zhēng)論。在我的記憶中,鼎湖山更多是作為休閑旅游景區(qū)呈現(xiàn):童年時(shí)與爺爺奶奶住進(jìn)山中的療養(yǎng)招待所,因蚊蟲而徹夜難眠;剛學(xué)會(huì)游泳時(shí),也斗膽在馳飛的瀑布間暢泳;再長(zhǎng)大后,與同學(xué)赤足溯溪而上,登頂后在慶云寺外吃一碗豆花;這些山中記憶都長(zhǎng)存在我的心底。唯一對(duì)于原真自然的敬畏,也來(lái)自一則都市傳說(shuō):本地人將自然保護(hù)區(qū)內(nèi)的森林腹地稱為“老鼎”,認(rèn)為那里險(xiǎn)象橫生,想要入內(nèi)的登山者需先到派出所報(bào)備。直到近年來(lái),經(jīng)由自然教育而開(kāi)展的各類活動(dòng),終于讓我了解鼎湖山在旅游景觀之外的另一種面目。

根河小鎮(zhèn)。
回到汗馬,這里顯然不是一個(gè)易于和日常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區(qū)域。當(dāng)下即便擁有現(xiàn)代的交通工具,一路跋涉也并不從容。從海拉爾機(jī)場(chǎng)落地后,驅(qū)車三小時(shí)才到根河市,還需輾轉(zhuǎn)三小時(shí)才能抵達(dá)保護(hù)區(qū)的管理站,步行進(jìn)入保護(hù)區(qū)的緩沖區(qū)域。冬季晝短夜長(zhǎng),下午四點(diǎn)前,大家就要開(kāi)始返程,再經(jīng)歷三小時(shí)奔波,回到根河市。因?yàn)榈蜏兀麄€(gè)車身都在掛霜,窗外的風(fēng)景猶如一團(tuán)濃霧,盤旋不散。也因?yàn)閮鐾粒吠绢嶔ぃ尿?qū)車像一團(tuán)奔馳的火種,向著林深沖刺。

進(jìn)入保護(hù)區(qū)的管護(hù)站。
汗馬的冬日最低溫度可達(dá)零下五十度,但被積雪覆蓋的汗馬卻正值野生動(dòng)物調(diào)查的最好時(shí)間。落葉泰加林已然撤走了防護(hù)色,林間成為最大的曝光區(qū),大雪正正是動(dòng)物的顯影劑。如今,保護(hù)區(qū)內(nèi)已布設(shè)紅外相機(jī)84臺(tái),可監(jiān)測(cè)到駝鹿、猞猁、棕熊、黑嘴松雞、紫貂等珍稀瀕危的野生動(dòng)物影像。除了動(dòng)物方面,氣候變暖對(duì)凍土的影響、老頭林的生長(zhǎng)速度監(jiān)測(cè)等工作、火燒跡地植被恢復(fù)的調(diào)查等,都在自然保護(hù)區(qū)內(nèi)進(jìn)行。
此次作為領(lǐng)路人之一的馬健,是汗馬自然保護(hù)區(qū)生態(tài)科普宣教的干事之一,他與工作伙伴一年大部分時(shí)間,都在林間穿梭,監(jiān)測(cè)、記錄、統(tǒng)計(jì)。當(dāng)然,最令人興奮的時(shí)刻,必然是發(fā)現(xiàn)。在我們進(jìn)入保護(hù)區(qū)的前一周,他們就通過(guò)駝鹿與狍的尸體,發(fā)現(xiàn)是猞猁將其獵殺,從而架設(shè)紅外相機(jī)蹲守拍攝。大自然里,孤寂與獎(jiǎng)賞,似乎永遠(yuǎn)都是等價(jià)交換。
雪嶺逐鹿:是它們發(fā)現(xiàn)了我們
因文旅營(yíng)銷,今年?yáng)|北亞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也紛紛在聚光燈下“營(yíng)業(yè)”。鄂溫克本意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們”,原始獵民保持“逐鹿而居”的生活習(xí)慣。但1965年開(kāi)始,鄂溫克人結(jié)束游牧和狩獵生產(chǎn),開(kāi)始了定居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2003年8月,首批使鹿鄂溫克人和他們的馴鹿從大興安嶺腹地搬遷至位于根河市郊的敖魯古雅,敖魯古雅意為“楊樹(shù)林茂盛的地方”。為保證馴鹿的覓食,鄂溫克獵民迄今仍保持著頻繁遷徙,常以馴鹿食用的苔蘚豐富、群山環(huán)抱、河流分布的地區(qū)作為“獵民點(diǎn)”駐扎。我們到達(dá)其中一個(gè)獵民點(diǎn)時(shí),大部分馴鹿已外出覓食,剩下與蒙獒相處甚歡的那只一歲半的小鹿,實(shí)際是一只母鹿的棄子,被鄂溫克人用牛奶養(yǎng)大。

鄂溫克族人養(yǎng)的馴鹿。
與性情溫順的馴鹿不同,駝鹿是野外的巨獸。在未正式進(jìn)入保護(hù)區(qū)內(nèi)的老頭林邊,我們其實(shí)已在雪地上發(fā)現(xiàn)了駝鹿的腳印蹤跡與糞便。即便未見(jiàn)其真身,但已然能想象出它們奔襲的場(chǎng)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動(dòng)物,滿語(yǔ)被稱為“堪達(dá)罕”的駝鹿,肢長(zhǎng)、頭大、面長(zhǎng)、鼻形如駝。駝鹿是典型的泰加林居民,棲息于亞寒帶的原始針葉林或針闊混交林中,中國(guó)的駝鹿目前僅分布于東北地區(qū)的大興安嶺、小興安嶺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的阿爾泰山一帶,其中,大、小興安嶺分布區(qū)的駝鹿,不僅是亞洲駝鹿分布的最南部邊緣種群,也是世界駝鹿最南分布的種群之一。2016年,汗馬保護(hù)區(qū)設(shè)置的紅外相機(jī)同時(shí)監(jiān)測(cè)到6只駝鹿,在中國(guó)尚屬首次。
如果放眼全球,駝鹿在不同地區(qū)不僅有不同的名字(北美洲稱為“moose”; 歐洲稱為“elk”),也有著全然不同的生存境地。挪威經(jīng)典的三角警示標(biāo)志正是提醒司機(jī),駝鹿作為“馬路殺手”的存在。據(jù)統(tǒng)計(jì),2003年至2017年間,美國(guó)緬因州發(fā)生了7,062 起與駝鹿的碰撞事件。打開(kāi)一位加拿大獵人創(chuàng)建的網(wǎng)站“All about moose”時(shí),不僅可以看到與駝鹿息息相關(guān)的信息,甚至還有他編撰的一本捕獵駝鹿的技巧指南與食譜。

雪地上的動(dòng)物腳印。
與此同時(shí),頒布于1989年的《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名錄》,時(shí)隔32年后于2021年進(jìn)行首次更新調(diào)整,在這次更新中,駝鹿從國(guó)家二級(jí)保護(hù)動(dòng)物升級(jí)為國(guó)家一級(jí)。對(duì)野生動(dòng)物而言,它們的名字是否進(jìn)入名錄、在名錄的等級(jí)都會(huì)直接影響其種群的發(fā)展命運(yùn)。但如何定義其“稀缺”與“珍貴”,則始終在爭(zhēng)論之中。如因民間認(rèn)為藥用價(jià)值高而被大量捕殺的黃胸鹀(俗稱“黃花雀”),被污名化的蝙蝠等,是否值得關(guān)注,都一再成為議題。
在《動(dòng)物社群》一書中,兩位加拿大動(dòng)物權(quán)利家提供了一種主權(quán)思路:野生動(dòng)物易受人類活動(dòng)影響,其形式不僅有直接的暴力、破壞棲息地與無(wú)意的傷害,同時(shí)還有積極的干預(yù)。書中強(qiáng)調(diào)動(dòng)物的自主權(quán)利。這要求我們思考,對(duì)野生動(dòng)物的積極干預(yù)義務(wù)需要在一個(gè)合適的框架內(nèi)進(jìn)行,“并非為了倡導(dǎo)建立某種制度性機(jī)制,而是闡明那種會(huì)在背后推動(dòng)制度變革的人類-動(dòng)物關(guān)系圖景。”

保護(hù)區(qū)內(nèi)被廢棄的站點(diǎn)。
雖然只能在林間短暫停留幾個(gè)小時(shí),但鼠兔隱匿在灌叢中的干草窩,在厚雪中修筑的交錯(cuò)隧道;紫貂與狍子在林間雪地上的跳躍痕跡;被壓彎但實(shí)則伺機(jī)行動(dòng)的偃松;五十年樹(shù)齡才生長(zhǎng)到一米七的老頭林;從中都能感受這座森林之間的暗藏的生命搏動(dòng)。一切像是沒(méi)有發(fā)生,但一切已盡然發(fā)生。回程的路上,天色漸暗,車窗外灰蒙蒙,大家也昏昏沉沉睡去。司機(jī)一個(gè)急停,驚呼了一聲,發(fā)現(xiàn)了早上駝鹿蹤跡的來(lái)路,幾只巨大的黑影在林邊停駐,我們靜默相望,試圖理解地球上屬于他者的種群。車輛再次輕輕啟動(dòng)時(shí),黑影敏銳地消隱于林中。
事實(shí)上,是我們闖進(jìn)了它們的領(lǐng)地,被它們生活的世界所震懾。那個(gè)暮色將近的夜晚,是它們發(fā)現(xiàn)了我們。

保護(hù)區(qū)的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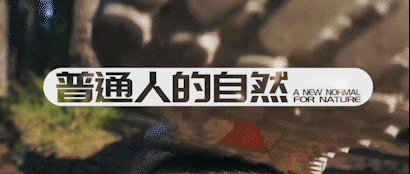
個(gè)人能為環(huán)境做什么?普通人如何在自然中自處?
“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專欄記錄普通人與自然相遇的故事。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