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黃燈《我的二本學(xué)生》:大學(xué)四年,他們從未停止內(nèi)卷
截至今年6月30日,全國共有3005所高等學(xué)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在這一千多所高校里,人們熟悉的“211”“985”不到十分之一。另一份數(shù)據(jù)表明,中國在校大學(xué)生里90%都在二本、三本及專科院校,一本院校只占全部高校的13%。
“在大眾化教育時代,越來越多年輕人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jī)會,但只有少數(shù)學(xué)生能進(jìn)入幾十所全國重點(diǎn)大學(xué),更多的人只能走進(jìn)數(shù)量龐大的普通二本院校。”在廣東一所二本院校從教14年之久的黃燈,發(fā)出了這樣的聲音。

黃燈(左)和她的學(xué)生們
黃燈是一名“70后”,1995年專科畢業(yè)于岳陽大學(xué)。岳陽大學(xué)隨后并入的學(xué)校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一所二本院校。大學(xué)畢業(yè)后的黃燈接受分配,在一家國營工廠干過文秘、會計、組織干事,1997年從機(jī)關(guān)下到車間成為一名擋車工。1998年工廠接單困難后,她決定考研,并于次年被武漢大學(xué)錄取,后來又考上了中山大學(xué)的博士。2005年黃燈博士畢業(yè),成為了一名大學(xué)老師。
在這里,黃燈教過2005級“80后”,也教過2015級“90后”。她目睹了高校擴(kuò)招,見證了大學(xué)生如何一步步擁抱市場,更思考了在短短二十年時間里,那些起點(diǎn)像她一樣的二本學(xué)生所面臨的境地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
她的花名冊上有4500多名學(xué)生,她從中選出100多名“80后”與“90后”寫成了《我的二本學(xué)生》。這份記錄從開學(xué)第一天開始寫,一直延續(xù)到學(xué)生們畢業(yè)、求職、買房、結(jié)婚。文稿完成于2018年下半年,曾在《人民文學(xué)》《十月》《天涯》《湖南文學(xué)》等刊物上發(fā)表,并于今年8月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
“作為老師,我對世界安全感邊界的認(rèn)定來源于對學(xué)生群體命運(yùn)的勘測。”黃燈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二本院校的學(xué)生折射出中國最為多數(shù)的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yùn)勾畫出中國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他們實(shí)現(xiàn)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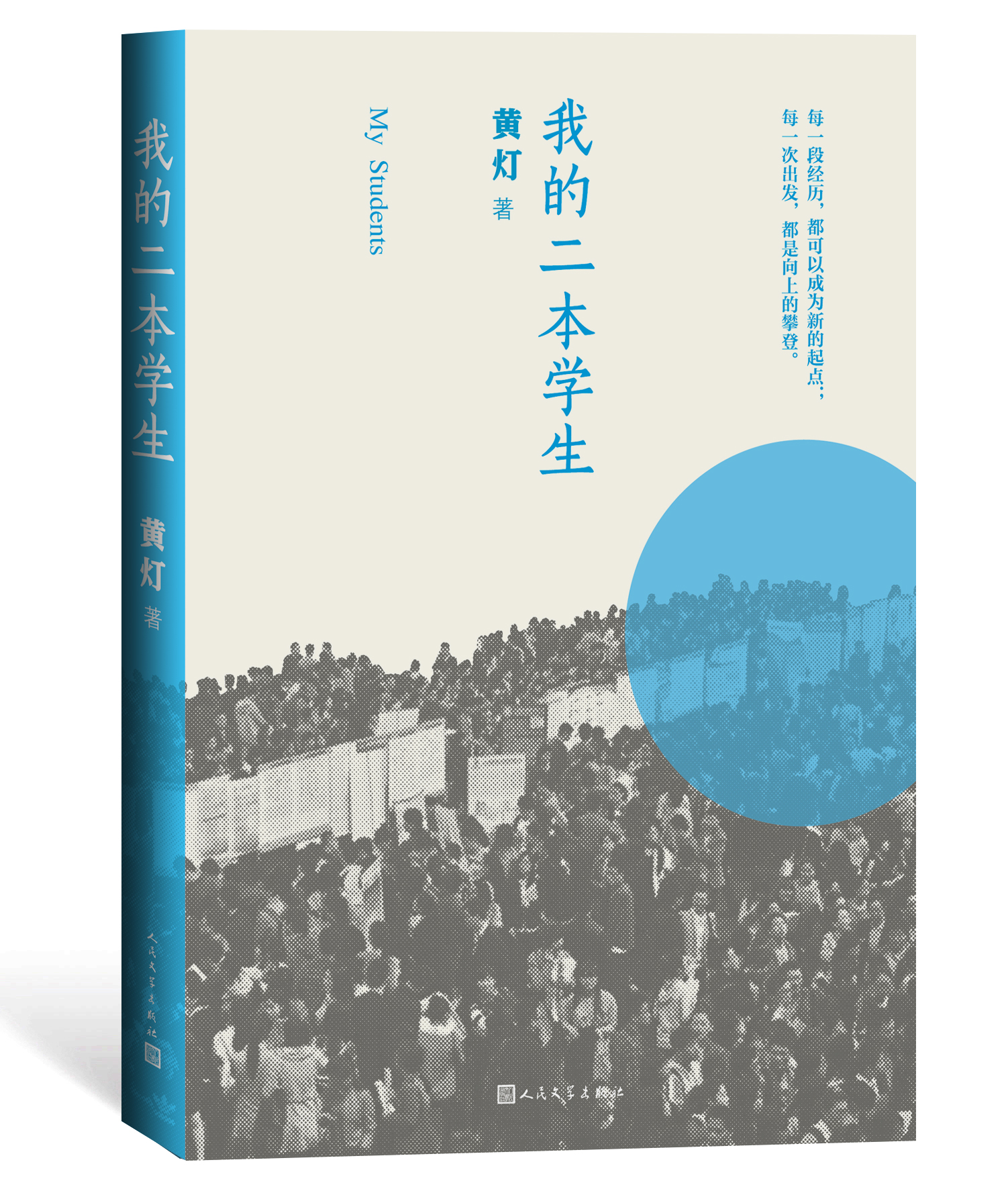
《我的二本學(xué)生》書影
近日,黃燈就《我的二本學(xué)生》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這段時間正好有很多關(guān)于“內(nèi)卷”的討論,“海淀媽媽”、“雞血爸爸”、“社畜”等皆是內(nèi)卷大隊的堅定分子。
“‘內(nèi)卷’的還有這群二本大學(xué)生啊,他們在四年大學(xué)時光里幾乎沒有放松過。”黃燈說。
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他們失去了什么?
高中老師喜歡和學(xué)生說:“等你們考上大學(xué)就解放了,到時候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黃燈發(fā)現(xiàn)這對現(xiàn)在的大學(xué)生而言根本是一句“假話”。“進(jìn)入大學(xué)校園第一天,我的學(xué)生們還來不及排解中學(xué)時代內(nèi)心的淤積,就被告知就業(yè)的壓力、考研的壓力、買房的壓力。他們很早就知道這份本科學(xué)歷無論在深造還是求職中,都是劣勢。”
對比自己念大學(xué)的經(jīng)歷和教學(xué)生的過程,黃燈能明顯感到中國大學(xué)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變化。在她的大學(xué)時代,哪怕是中專生、專科生也被視為“天之驕子”,大學(xué)教育注重學(xué)生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但現(xiàn)在的大學(xué)生變成了“找工作的主體”,按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溫鐵軍所言,“把人變成資本化的一個要素”。
“隨著社會發(fā)展,高等教育大眾化,文憑在客觀上也被稀釋了,這是不可否認(rèn)的。”但對于出身底層的年輕人,黃燈還是認(rèn)為讀書是性價比最高的一件事。她想補(bǔ)充的是,真正的教育不應(yīng)該只是讓年輕人“兌現(xiàn)”,還應(yīng)該為了完善一個人。最起碼,在綜合素質(zhì)被反復(fù)提及、強(qiáng)調(diào)的今天,一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是年輕人的心理素質(zhì)反而堪憂。他們走在畢業(yè)的關(guān)卡,“抑郁”“脆弱”“喪”……這些字眼如影隨形。
因?yàn)樯硖幬膶W(xué)圈,黃燈經(jīng)常聽到大家批評現(xiàn)在的大學(xué)生不讀書,哪怕是中文系出身也閱讀量極小。她對自己學(xué)生的閱讀情況也很不滿意,有一次她問班上多少人看過《紅樓夢》,結(jié)果舉手的五個人都不到。
和很多人一樣,她一度認(rèn)為問題就出在“學(xué)生懶惰”,還有“被手機(jī)、網(wǎng)絡(luò)分散了太多注意力”。但在多年的教學(xué)生活中,她越來越發(fā)現(xiàn)還有別的因素。比如,她的學(xué)生們除了要上中文專業(yè)的課,還要考高數(shù),上傳媒類甚至經(jīng)濟(jì)類、金融類的課。學(xué)生們上課壓力極大,但大部分課程只是蜻蜓點(diǎn)水,沒有太多專業(yè)含量。就算如此,還有好多學(xué)生要為“將來好就業(yè)”輔修雙學(xué)位,瘋狂考證,哪里還有時間和精力“好好讀一本書”?
在具體的課堂中,黃燈會感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癥,中小學(xué)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xué)時代終于結(jié)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果子。孩子們的面目越來越相似,就像是工廠里的標(biāo)準(zhǔn)化構(gòu)件。
“大學(xué)教育的質(zhì)量是值得我們反思的。”黃燈感慨道,這一段在人生中無比重要的時光若沒能沉淀到生命里,而像泡沫一樣浮在表面,是很可惜的。

黃燈與學(xué)生們合影
大學(xué)生就業(yè),和大學(xué)教育有多大關(guān)系?
黃燈一直在觀察學(xué)生們的畢業(yè)境況,她思考最多的是:孩子們的就業(yè)命運(yùn)究竟和大學(xué)教育有怎樣的關(guān)系?
她對比了自己兩次當(dāng)班主任的經(jīng)歷。一次在062111班,她面對的是2006級的大學(xué)生;一次在1516045班,她面對的是2015級的大學(xué)生。
062111班上有一個叫楊勝軒的學(xué)生,1987年生于廣州芳村,個人能力非常不錯。畢業(yè)后他去過淘寶網(wǎng)店,爭取過街道辦的民政專職。他每年都在工作之余準(zhǔn)備公務(wù)員考試,還始終保持著“兩年一證”的節(jié)奏,先后拿下會計從業(yè)證、證券從業(yè)資格證、社工證、駕駛證等等。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個周末,楊勝軒不是在上網(wǎng)絡(luò)課程,就是備考做題。
盡管楊勝軒的公務(wù)員考試名次逐年提高,但因?yàn)閳罂既藬?shù)漲幅更大,結(jié)果總是不盡人意。楊勝軒越來越認(rèn)為“關(guān)系太重要了,就算進(jìn)入面試,沒有關(guān)系也很難突破”,但依然會在年滿35歲之前把它看成一項“必須堅持的事業(yè)”。
楊勝軒在班上不是個例。黃燈發(fā)現(xiàn),062111的學(xué)生已將考公務(wù)員看作比考大學(xué)更重要的事。而且畢業(yè)多年后,這批“80后”同班同學(xué)的財富狀況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分化,分化的關(guān)鍵在于是否曾在某些時間點(diǎn)拿得出一筆房產(chǎn)首付。讓黃燈印象深刻的是,楊勝軒還說過這么一句話:大家更愿意關(guān)注鄉(xiāng)村的問題,而城市里家境一般的孩子沒人關(guān)心。
另一方面,相比062111的學(xué)生中還有三分之一留在深圳、廣州,1516045班上沒有一個“90后”學(xué)生敢理直氣壯地說出“我要待在大城市”,更沒有一個學(xué)生相信能憑借自己在大城市買得起一個安居之所。
比如1516045班上來自廣東湛江的秀珊,她是村里唯一的大學(xué)生。考上大學(xué)后,她被村里人問到畢業(yè)后分配哪里,秀珊說沒有分配,村里人一下覺得這所大學(xué)“有問題”。秀珊在大一時還充滿熱情,后來越來越消極,“我們很年輕,不想回家,但要留在廣州的話,可能一個月的工資付完房租都沒錢買衣服了。”
在畢業(yè)前夕,秀珊和同學(xué)們會用“咸魚”來形容自己的狀態(tài),用“上岸”來形容找到工作。這讓黃燈對當(dāng)下年輕人的生存處境充滿擔(dān)憂。她說,對她那時的普通大學(xué)生而言,無論出身如何,只要擁有一個共同的大學(xué)文憑,同窗的就業(yè)質(zhì)量就相差無幾。但從062111班到1516045班,學(xué)生們的去向越來越受制于個體背后掌握的資源,普通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
“我的學(xué)生90%來自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的廣東地區(qū),我任教的學(xué)校一直以就業(yè)優(yōu)勢著稱,生源也非常出色。盡管是一所二本學(xué)校,但70%的學(xué)生只有上了一本線才有機(jī)會招進(jìn)來,他們的境況尚且如此,而全國還有那么多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學(xué)生。”
黃燈想追問的是學(xué)生背后的社會關(guān)系、原生家庭、個人能力在就業(yè)質(zhì)量中所占的具體權(quán)重。“如果其權(quán)重越來越被個人實(shí)際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對大學(xué)教育的審視將來會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黃燈
記錄的局限,記錄的力量
在新書出版后,黃燈收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反饋”。
比如一位來自二本院校的工科生說,書里的那些二本學(xué)生之所以難找工作,是因?yàn)樽x了中文系,他們理工科生還是好找工作的。
“這個孩子說得有道理。但是我寫這份文本,從來就沒想過要代表所有的二本學(xué)生。書名叫《我的二本學(xué)生》,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份田野調(diào)查的場域,我的觀察對象是我的學(xué)生,甚至還有‘在場’的我自己。我是中文系出身,幾屆學(xué)生也都是。在對話之外,他們課上課下的發(fā)言、論文作業(yè)、郵件微信都是一手的鮮活的資料,通過這些‘抓手’,我想看見并記錄一部分被遮蔽的年輕人的生存境況,并通過間隔十年的對比了解他們命運(yùn)的變遷。”
上個月,她和賈樟柯在新世相有一場關(guān)于二本學(xué)生的對談,說到了記錄的力量。“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流失,它的場景、它的建筑、它的人物、它的聲音,都會在變化中流失掉。1998年賈樟柯拍了《小武》,他那時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試圖用影像記錄下這個時代真實(shí)的一面。這在我看來就是一種‘非虛構(gòu)的精神’。”
而她寫自己的二本學(xué)生,也是有意識地想為這個群體留下點(diǎn)什么,畢竟比起媒體爭相報道的“北大才子”“復(fù)旦新生”,占中國高校學(xué)子大多數(shù)的二本學(xué)生一直是“沉默”的。也有讀者留言說,那三本學(xué)生怎么辦,專科生怎么辦,一本學(xué)生群里的邊緣人又怎么辦。黃燈回:“那應(yīng)該由你們的老師來寫。”
可以看到,這本《我的二本學(xué)生》和《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diào)查》 在今年的非虛構(gòu)討論中常被提及,并由此展開非虛構(gòu)寫作倫理、“社會學(xué)熱”等引申話題。在《我的二本學(xué)生》之前,黃燈已有非虛構(gòu)作品《一個農(nóng)村兒媳眼中的鄉(xiāng)村圖景》、《大地上的親人》。
“我在寫作時并沒想到‘社會學(xué)熱’ ‘非虛構(gòu)熱’,我只堅信我所關(guān)注的問題非常重要。它是一份紀(jì)實(shí)性文本,除了對校名和人名做了處理,作者的能動性非常之少。”
紀(jì)實(shí)性文本的“靜止性”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一位被寫進(jìn)書里的女學(xué)生就告訴黃燈,自己這兩年日漸安穩(wěn),回頭再看2018年之前的記錄竟有些難以置信。“當(dāng)一個人的生活狀態(tài)和心態(tài)改變了,再回頭審視以前的生活,他/她會覺得‘這是我嗎’。生命總是開放的,動態(tài)的,它和相對靜止的文本會有碰撞,但這也是記錄有意思的地方。”
最讓她意想不到的是一些來自“211”“985”畢業(yè)生的反饋。往往在一次分享活動結(jié)束后,她會留下來和在場的主持人、媒體人多聊一會。
“這些孩子大多來自名校,也是‘80后’、‘90后’。有一個說,以前她看不到二本學(xué)生這一群體,以為一本學(xué)生已經(jīng)到處都是了,她突然發(fā)現(xiàn)同齡人還有另外的生活圖景。還有一個說,她總覺得上名校全靠自己努力,但現(xiàn)在感慨擁有經(jīng)濟(jì)穩(wěn)定的家庭和開明的父母是多大的幸運(yùn),她不再將一些人的失敗簡單粗暴地歸咎于‘不努力’。”
這些聲音是黃燈在寫《我的二本學(xué)生》時完全沒想到的。她驚喜的是,這些年輕人依然會自發(fā)地思考問題,依然有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他們眼里是有光的。”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