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國終于有犯罪片能和韓國抗衡了
原創(chuàng) 點擊右邊星標 一條 收錄于話題#一份值得收藏的片單54個
參與文末互動留言,贏《風平浪靜》電影票
11月6日,《風平浪靜》全國上映,
它被譽為“今年最值得期待的犯罪片”,
從上影節(jié)到平遙影展都一票難求。


這是一個“優(yōu)等生犯罪”的故事,
也是一出九十年代蕓蕓眾生像,
金錢、情欲、權力等議題在大銀幕上翻滾。
黃渤擔任監(jiān)制,主演都是實力派演員:
章宇、宋佳、李鴻其、王硯輝……
導演李霄峰非科班出身,
從影評人轉行拍電影,
《風平浪靜》是他執(zhí)導的第三部長片。

一條與李霄峰聊了聊,
他直言盡管自己獨立導演出身,
但特別重視電影制作的精良程度:
“電影本身就是一個技術產生的藝術,
我希望我拍的片子,
在全球最好的大銀幕上放也一點不丟人。”
撰文 宋遠程 責編 石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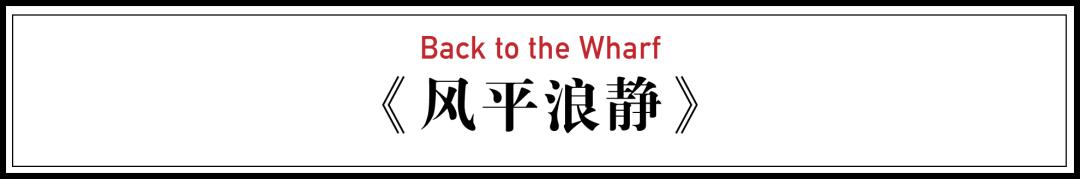

八月份《風平浪靜》在上影節(jié)首映后,很多人都想到了今年上半年上了好幾次熱搜的升學頂替事件。片子的主角宋浩本來是全校第一的優(yōu)等生,也是高考前被官二代同學搶走了保送的名額,但這只是他人生的悲劇的起點。為了報復,他誤闖民宅、捅了人,被迫離鄉(xiāng)逃難,一去十五年。

但在李霄峰看來,自己并非什么未卜先知,而只是在時代的浪潮中,“弱水三千,取一瓢飲”。
這是他的第三部電影,和前兩部作品一樣,片子延續(xù)了他對九十年代的著迷。他出生于1978年,九十年代是他的青年時代,也是他最熟悉的時代。在他看來,對于這個“表面風平浪靜,其實摧枯拉朽”的時代,中國電影還呈現得遠遠不夠。

首先是家里多了個弟弟。母親尸骨未寒,父親已經和年輕的情人打成一片。他質問父親,父親卻比他更加理直氣壯,“你別怪我,你媽都沒意見,你這個兒子養(yǎng)廢了,我怎么也得再續(xù)一個。”

九十年代,海外簽證和移民政策已經開放,父親開始著手為這個“更加有前途的”小兒子辦理移民澳洲的手續(xù)。
宋浩去找官二代同學李唐,想要為15年前的命案贖罪。借著房地產業(yè)的興起,李唐已經成為了當地一名賺得盆滿缽滿的地產開發(fā)商。他為宋浩現場表演如何處理一個釘子戶——解決不了問題,就解決有問題的人。

在回鄉(xiāng)路上的高速收費站,他偶遇了高中同學潘曉霜。后者曾無意目擊了他犯下命案的現場,卻不改學生時代就開始的對這位學霸的狂熱愛慕。重逢之后,她認定了他,毫不猶豫地按下了擋車桿,砸碎了宋浩的車玻璃窗。然后主動請他吃飯,借著酒勁順勢表白。


如果說宋浩和潘曉霜的愛情線是片中唯一的光亮的話,這線光也很快就被打斷了。宋浩再次被父親和李唐卷入當地權力集團的黑暗交易里。最終,他什么也沒有能夠挽回。15年前,他犧牲了自己的保送名額,這一次,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強拆、裸官、情欲、官商勾結、貧富差距……一個普通人的人生如此輕易地被摧毀了。這就是李霄峰鏡頭下九十年代的“滄桑巨變”,就像另一部“風雨云”。

那時互聯網剛剛興起,各種各樣的電影論壇開始涌現,北大新青年的“電影夜航船”、西祠胡同“后窗看電影”等等。電影人在論壇上形成了一個圈子,比如新浪“影行天下”的創(chuàng)辦人其實就是陸川,后來導演了《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第一代網絡影評人”的經歷給李霄峰積攢了入圈的第一批人脈資源。
李霄峰
2002年,李霄峰從國外留學回來,加入了陸川的劇組,一起籌備《可可西里》。
隨后十年,他過發(fā)行,寫過劇本,甚至在張元的《達達》里當主演,把行業(yè)的各個工種都體驗遍了。直到35歲時,他突然有了自己拍電影的沖動,“就是你要再不拍,估計以后也沒機會了。”

第二部作品《灰燼重生》(原名《追·蹤》),是一個“交換殺人”的故事:兩個陌路人,因為一本托爾斯泰的《復活》成為筆友,互相替對方解決深仇大恨后各奔東西。十年后,兩人再度重逢,不得不重新面對過去的罪惡。

《灰燼重生》讓李霄峰心力交瘁,但也孕育出了《風平浪靜》。他和制片人在一次聊天中提到,“成年人只講利弊,小孩子才看對錯”。這句話讓他非常憤怒,一個新的原創(chuàng)犯罪類型劇本開始成型。
《風平浪靜》是一個標準的中等體量的電影,最多的時候拍攝現場有200人在同時運轉,這是李霄峰迄今最大規(guī)模的制作。

“我的電影就是在全球最好的銀幕上放,也一點不丟人。就這個要求。”
以下是李霄峰的自述:
“風平浪靜”,里面卻是摧枯拉朽
和我的前兩部作品一樣,《風平浪靜》也是一個關于90年代的故事。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特別浪漫的時代,很熾熱,也很冰冷。在90年代,中國經濟開始騰飛。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還有金錢至上主義,各種各樣的思潮彼此映照,彼此沖刷,那個時代所產生的故事,看起來是風平浪靜,但其實里邊是摧枯拉朽。

首先是他的善良。善良的人往往軟弱、壓抑,不太容易去展現自己的內心。
宋浩離開西園之前并沒有接觸過社會,后來在廠里一干15年,正好錯過這期間社會變遷的洗禮,因此他回來的時候,是以少年一樣的精神狀態(tài),去經歷15年后人際關系的變化。

電影是在泉州拍的。我第一部電影里有河,第二部里有江,我就下意識覺得第三部應該有海。

到了泉州,看到那邊的海特別野,特別有力量,海邊則是大片的黑色礁石,我當即決定就這兒了。
我們知道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比如婁燁導演在那里拍《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其實福建也是,而泉州這個地方我覺得更有意思,因為它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八、九十年代,南方的沿海城市憑借得天獨厚的條件先富起來,人們的氣質總歸也是不一樣的。

《風平浪靜》最初是入圍了金馬創(chuàng)投,渤哥(黃渤)是評委之一。雖然最后獎沒有給我們,但也給他留下了一點印象。劇本出來以后,第一時間就給他看,他很喜歡,后來就做了這部片的監(jiān)制。

他對劇本有強大的平衡力,畢竟經驗比我豐富太多。在片場我們討論拍攝方案,他會停下來想一想,腦子一轉,就知道此時此刻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合適。
第一代“野生”影評人
小時候,我家離市里正規(guī)的電影院比較遠,就常常去附近工廠里的劇院。就像《灰燼重生》里的場景一樣,合唱團在寬敞的舞臺中心表演,觀眾席黑壓壓的全是大人。從小我就喜歡這種氣氛,這是看電影儀式感的一部分。

初中時我有一個本子,里面寫了很多文章。當時那個本子流傳在各個中學,有時出去轉一個多月才回到我手邊。各種我不認識的人在本子上寫滿批注和感想。那本子現在還在,但我不敢看,總覺得特別矯情。
后來我能夠有機會做電影,還是感謝兩件事,一個是盜版,一個是互聯網。
1999年的時候,大學BBS流傳一個片單,像伯格曼、安東尼奧尼,還有黑澤明、小津安二郎、今村昌平這些歐美以及日本的電影大師,順帶的是200多盤付費錄像帶。

那個時候我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電影叫大師電影。這些片子,有很多都是原來在電影學院才能看到的“內部參考片”,因為這些碟片,我們這種完全沒有科班背景的人,也有緣接觸到了,并且因為對這些電影的熱愛,一眼辨認出同類,聚集到一起。
我最欣賞的兩位導演,第一位是個日本人,黑澤明,對我來說他就是電影界的托爾斯泰。第二位是謝晉。這兩個人都特別全面,不拘泥于某一類型的電影,而且在刻畫人物上兩個人都是最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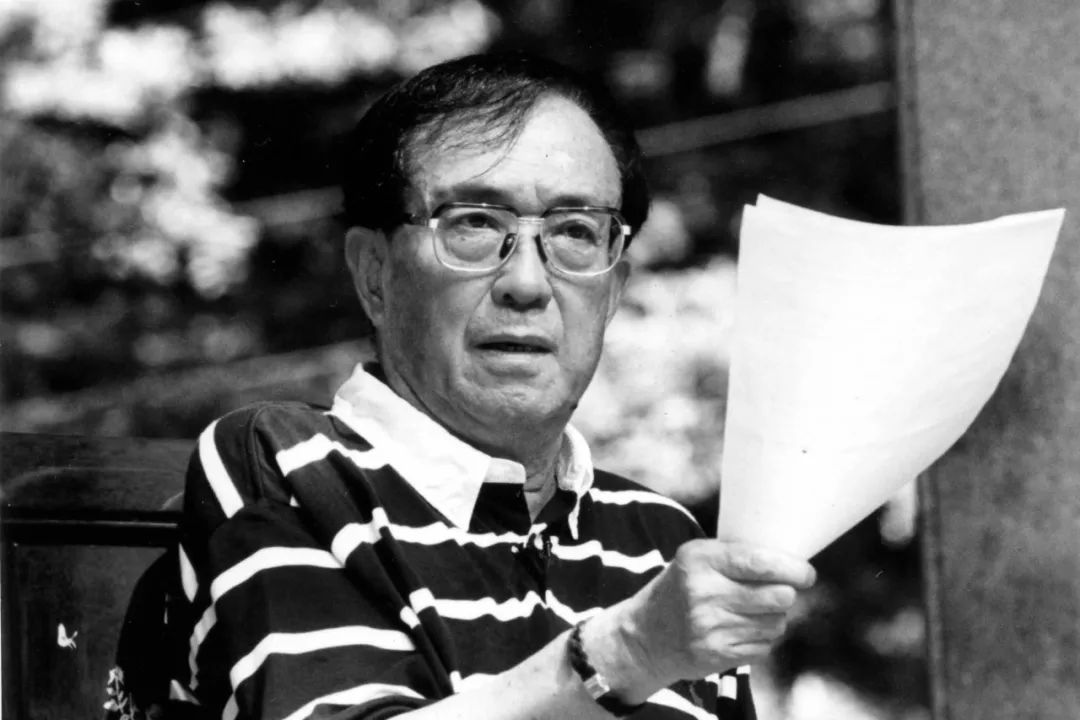
最早寫電影相關文字的時候,我完全沒想到“影評”后來會火成那樣,別人叫我影評人,我都覺得有點別扭。因為我覺得我當時還是個學生,好像不應該有什么標簽。但是后來我慢慢地才意識到,它可能是一個社會屬性,甚至會成為一個新的門類。
2000、2001年的時候,我拿著全中國影評人最高的稿費,一個月最多的時候拿過1萬塊。

那個時候是真的愉快,走到哪兒都有朋友吃吃喝喝,聊聊電影。寫東西也沒有限制,你想寫60年代電影,就寫60年代,你想借著電影發(fā)一篇自己的感慨,你就發(fā)感慨。我們自己買票去看某部電影的首映,看完不高興就寫文章罵它。

所以我拍完第一個電影之后,網上有不少人罵我。后來想想,出來混總得還,當年你也罵人家大導演是吧?現在剛出來被人罵,我覺得也是正常的。
要當導演就當專業(yè)的
去陸川那兒工作是我整個電影生涯的開始。
當時是給《可可西里》拍紀錄片。陸川是一個對制作要求特別嚴格的導演,在他底下工作壓力非常大,一年多時間里我們每天只能睡3~4個小時。

但當時還沒有想到自己去拍電影。之后的十年也都沒有什么沖動,做編劇、做海外發(fā)行、包括做演員,什么崗位都干過。到35歲的時候,突然有了那么一種時不我待的感覺,就是你要再不拍,估計以后也沒機會了。

可能因為年齡大,有了一些社會閱歷,而且對劇組的氣氛也早就熟悉了。所以我的第一部電影(《少女哪吒》)特別順利,所有人都很開心,本來是45天周期,35天基本上拍完了。第一部電影是最幸福的,因為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一部電影。
也許是因為入行在《可可西里》,我非常講究電影的制作意識。《少女哪吒》把90%的錢都用在了制作上。當時器材公司的人跟我們說,你們拿的是兩倍于預算的器材。

當時中國電影的氛圍是給演員很多錢,不太重視制作。但我覺得無論你想表達什么,你的劇組必須要正規(guī),必須是一個能打仗的劇組。我在細節(jié)方面,在器材的選擇、人員的配備上,都是一絲不茍,甚至有些折磨人。
當時《少女哪吒》報名金馬獎,我們是最后一個寄出去的,還是毛片,調色、聲效都還沒做。但它最后能入圍,就是因為在拍攝的時候精益求精,所以和成片的差距不是那么大。

第二部片《灰燼重生》的成本不低,但依然有3/4的投資花在了制作上。我花了大量精力去呈現夸張的光線和濃郁的色彩,因為那些視覺層面的要素,就是電影在自己領域要解決的問題。講故事當然重要,但是如果單單是為了故事,那為什么不看小說呢?
我始終覺得,電影是要放在電影院里看的。它有技術上的門檻,需要不同工種之間的配合,它有工業(yè)屬性。有的導演出道的時候,花個幾十萬就開始拍了,這當然是值得鼓勵的。但是不能因為這樣把電影拍出來了,就覺得電影的技術層面不值得重視。
我相信“實踐出真知”。所以,我鼓勵所有的影評人、媒體人或者電影愛好者,進片場實實在在地去感受一下。哪怕只是經歷了一部戲,出來以后對電影的看法可能就會有所不同。
近期報道:
▼

原標題:《中國終于有犯罪片能和韓國抗衡了》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