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丨演員章宇:我試著讓自己放松一點
“有一個斯巴達的男孩,他偷了一只狐貍,藏在衣服里。狐貍會瘋狂地啃咬他的肉,但因為這個狐貍是偷來的,他只能一言不發忍著,直到皮肉全部都被啃爛。但他不想暴露偷竊的這個行為。這個寓言的內核,跟宋浩是一樣的。”今年8月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章宇這樣介紹他即將要與觀眾見面的新角色。
《風平浪靜》11月6日全國公映。從今年亮相上影節金爵單元之后,這部電影一直備受期待。公映前嘗鮮看過電影的觀眾,不少人給予這部影片年度華語最佳的贊譽。關于整部電影,最大的夸贊都給了演員的表演。
在男主角章宇的好里面,有一如既往的穩和猛,也有給人新鮮感的部分,比如和女主角宋佳的愛情,一種瀕臨絕境里如詩如光的情感,浸潤在暗流洶涌的慘烈人生里,迸發出剎那的燦爛火光,灼熱而深邃。

《風平浪靜》劇照,章宇飾演宋浩
章宇說,宋浩是他演戲以來,演過的“最慘、最痛苦的人”,以至于拍戲過程中他常有演到崩潰的時候,指責導演“內心是住著怎樣的魔鬼才創造了一個這樣的人”。盡管盤盤他之前的角色,《我不是藥神》里的黃毛、《大象席地而坐》里的于城、《無名之輩》里的胡廣生,他飾演的人物從來都是悲劇性的。
而這一次,用“慘烈”這個詞形容《風平浪靜》里的宋浩應該很恰當——慘是人生里悲劇的際遇,烈是壓抑十多年后向著救贖拼死一掙。原本是三好學生的宋浩,在高考前夕,保送名額突然被頂替,權利交織之間,他也犯下無心過錯,最終背負殺人的罪孽遠走他鄉。隱姓埋名十余年后,因為母親去世,宋浩回到家鄉,原本已經平復的往事卻再起波瀾。
《風平浪靜》的導演李霄峰,之前有部長片處女作名叫《少女哪吒》,而在章宇看來,《風平浪靜》在本質上,是一個“少年哪吒”的故事。“哪吒”指向某種反骨和剔骨還父的古典主義情結,“少年”則是章宇所扮演的人物在停止成長后停滯的身心狀態。
所謂“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正是章宇想要去詮釋的人物的生命路徑。盡管拍攝時,他拒絕了從少年時代的宋浩開始演完整部電影,因為畢竟“年近四十”,他已經無法讓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演出那種“生理上年輕”,但是成年之后心性上的少年感,是他一直擅長且接近自我的東西。

《我不是藥神》劇照
時間倒回2018年,36歲的章宇,在《我不是藥神》里演了個像“喪家犬”一樣的黃毛,很多觀眾以為他就是個“小屁孩兒”。導演文牧野第一次見他的時候直接問的是“二十幾了?”即便得知實際年齡,也沒有影響文牧野用章宇的決定,因為章宇“有一雙沒有被娛樂圈干擾的非常干凈的眼神,用那個眼神來演二十歲綽綽有余”。
同一年末上映的《無名之輩》再度大爆,一直以來籍籍無名的演員章宇,就在那短短幾個月里被更多的人認識了。加上金馬獎最佳電影《大象席地而坐》,“章宇主演”成了文藝青年心目中某種蓋在好電影上的戳。
《風平浪靜》的制片人頓河透露,在最初和導演李霄峰討論演員人選時,女主角宋佳還因為氣場太大和太漂亮而經歷了一番爭議,而章宇是他們沒有任何猶豫的第一甚至是唯一選擇。“章宇有力量感、有攻擊性,但是這個攻擊性,是隱藏在日常的平和跟秩序之下的。”
而章宇也是宋佳堅持要來演這部電影的原因,她主動請纓,努力說服起初覺得她并不合適的導演,除了對劇本里人物的喜愛,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想來“會會章宇”。她對他的評價極高,她說,“我覺得《我不是藥神》這部戲,最大的意義,不在于它有多高的票房,它最大的意義,就是給中國影壇輸出了像章宇這樣的演員。”
章宇總是在演小人物,有人說他長了一張“底層臉”,也有人以為他是素人非職業演員出身。其實章宇是真正表演專業的科班畢業,在演電影之前,他早就是話劇舞臺上男一號挑大梁的“角兒”。
從事表演對章宇來說是陰差陽錯的意外。高中的時候他愛唱歌,但報考聲樂系沒考上,有人說你要不去試試旁邊的表演系,結果章宇居然考上了。不過說到愛唱歌的事,非常值得插播一句,去看《風平浪靜》的話,還能聽到章宇唱的片尾曲,真的好聽到洗腦。
畢業后,章宇考進貴州省話劇團,扎實的表演功力讓他一路演到男一號,演出的劇目還能拿下全國大獎。但“體制內”的生活,安逸到能逼瘋一個藝術家。同一出話劇反復演,他想變點花樣給出不一樣的處理,一起演出的搭檔,反而會責怪他沒事找事給人添麻煩。
北京舉辦奧運會的那一年,章宇翻出老早前寫的日記,上面記述著,“2008年,我應該在北京。”于是他迅速放下老家安逸的一切,成了一名北漂。他的辭職信是這么寫的:“由于本人對藝術事業的狂熱追求和對藝術實踐的極度渴望,以及自身的生存現狀,經思忖,決定去北京一邊掙錢,一邊學習。特此向團部申請辭職。”其實這封辭職信沒遞上去,團里當然也就沒批他的辭職申請,他是直接一走了之的。這是他出名前10年的事。

《無名之輩》劇照
2019年,是章宇沉寂的一年,其實《我不是藥神》和《無名之輩》之后,找他的戲很多,但他都推掉了。一方面自己需要適應“被看見”,在過往很長一段時間的認知里,這不算是什么好事。另一方面,他的確對劇本足夠挑剔,沒有足夠打動他的角色,他也不想過度消耗。
章宇也不喜歡采訪,“要不是這部電影要上映,我也不會接受你的采訪。”他這樣說著,打開手機放音樂,“我覺得我不太會說話,放點音樂能感覺自在一點。我們可以開始了。”

《風平浪靜》北京首映禮上的章宇。
【對話】
最痛苦的角色,是一個“黑洞”
澎湃新聞:這幾年,聽說找你的片子挺多的,你對劇本也挺挑剔的,所以《風平浪靜》打動你的地方是在哪里?
章宇:劇本的內核是一個非常古典的故事,是一個俄狄普斯情結的經典內核,一個關于弒父的東西,這個東西我喜歡。弒父這個情節,在我看來,是一個當代哪吒的故事。他的那種反叛,最后他剔骨還給父親是這個故事,讓我想到李霄峰第一部拍的不是《少女哪吒》嘛,我覺得《風平浪靜》,實際上是一個“少年哪吒”。雖然我演的這個角色,在生理上已經是完全的成年人,但這個人并沒有長大。在電影里面,有這個人物少年和成年的部分,少年部分是另外一個演員來演的,那種意氣風發的時候,他是生理年齡的少年。但我說我要演的才是真正的少年宋浩。離家15年,背負了15年的“原罪”和自己對自己的懲罰,再回到家鄉的這么一個人。他是真正的那種“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
澎湃新聞:這種成年之后還沒有長大心態,對你自己而言,是不是也能找到共鳴的地方?
章宇:我說我自己是“傻”,宋浩那種是“悲涼”,是“唏噓”。那種長不大,是因為他一直被某種原罪給拽住了,所以他沒有辦法成為世俗的成熟,他一直在那個東西里面,沒有繞開那個愧疚,一直在懲罰自己。

《風平浪靜》劇照
澎湃新聞:好像你一直演的人物內心都挺苦的,這次的苦和之前有什么不同?處理上需要找到一些怎樣新的方式?
章宇:其實像宋浩這種痛苦,我是沒有經歷過那么痛苦的事,我覺得這個人太痛苦了、太慘了,我看完劇本以后,太可憐這個角色了,我說心疼他。
比如“大象”那種痛苦,是有點存在主義的味道,實際上你可以說他起碼無病無災,你看到的是更形而上的那種虛無。《風平浪靜》就是形而下的,他就是實際的遭遇了,非常具體的全方面的打擊,要逃離、要逃亡,自己犯了極大的罪,這是非常實際,也非常世俗的那個東西,壓著他,不讓他能夠清理他的人生。從少年時他人生被偷走了,本來可以一片大好的前程、考上大學的那么一個人,陰差陽錯就這么荒謬地搭上了整個一生。
因為這次劇本這個角色太重了,我反而想盡量用一個可能有點冒險的方式去處理,我盡量會把它那些重的東西裹著,而不去外放著處理,把它們往內收斂,但這種包裹的過程,對自己的身心是一種巨大的內耗,就是你說的方式,我盡量讓他在表面上,看來像一個什么反應都沒有的人,一個極其麻木的人,他所有的內耗,就是在不停地折磨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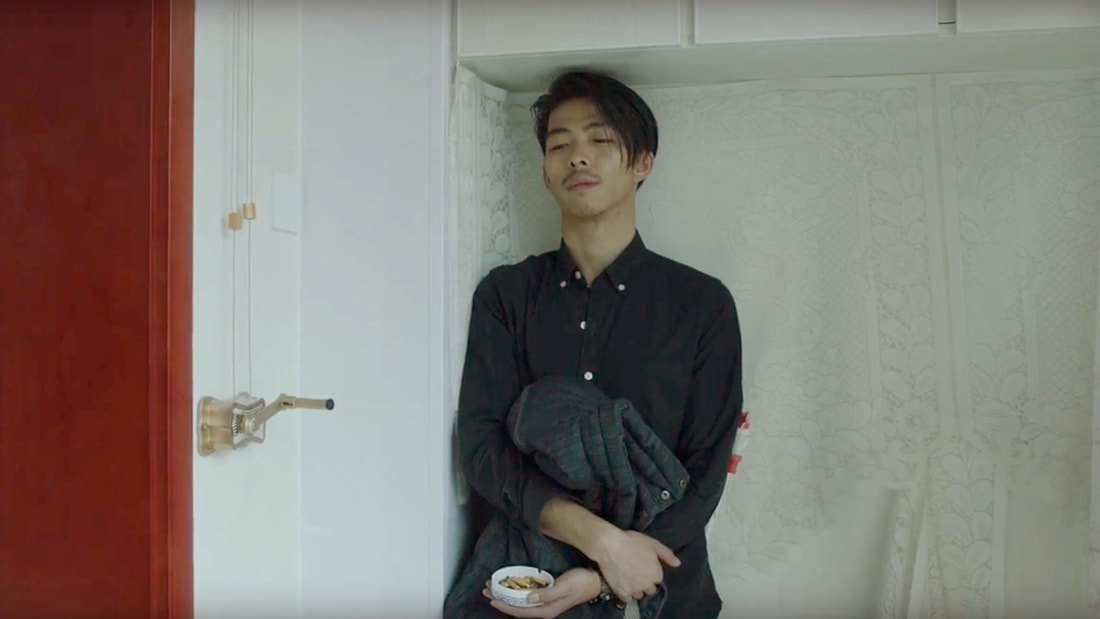
《大象席地而坐》劇照
澎湃新聞:演這么痛苦的人物,最后需要找什么方式,把那個情緒給卸掉嗎?
章宇:其實演完就好,演完就能舒服。趟過那些你在鏡頭前的每一場戲,每一個場景中的境遇,經歷完就會覺得我可以告別那一段經歷。
有一場戲是宋浩要埋人,我就在心里說“我總算可以告別了,太難受了”。演完那個真要緩好一會。我記得那天拍完我去質問李霄峰,我說你為什么要寫一個這么慘的人,你內心是住了什么魔鬼嗎?我想以后再也不要演這么慘的人了,真的太折磨了!所以拍戲的時候,我就總喜歡拖著他聊角色,這可能也是一種“疏解方式”,我不能自己一個人痛苦,我必須得拉著他一塊跳!
澎湃新聞:聽說你還是經常半夜拖著李霄峰聊,具體聊什么呢?
章宇:我大概是在告訴他,為什么很多東西他在劇本里寫出來了,但是我不演。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哪些東西盡量去弱化它。當時我就跟他說,我要把宋浩演成一個“黑洞”,什么反應、什么聲音、什么目光過去,都會被吸收掉,沒有任何反饋,麻木、不近人情,不諳世事,甚至反射弧都會比正常人要慢個三五拍。
我會聊這些。因為對人物的設計,實際上是一個整體的“工程”,但是我們在拍攝過程中,它的呈現是點狀的,我們在腦海和劇本上構建的那種線性的東西,它不是順著來的。所以我對人物的設計,是必須有我的整體的一個預想,在導演、攝影他們都看不到的時候,我會跟他們溝通我的想法。有些東西我也跟他們探討,更多的是希望他們不要擔心。我覺得只要能秉承下來,我相信是可以完成它的。

李霄峰、李鴻其、章宇
好的演員,能夠演出劇本的“外延”
澎湃新聞:但你這樣“任性”地改了導演原來對劇本人物的處理,就勢必牽涉到和你對手的演員,如果劇本上本來寫好的臺詞會有一些反應,但你變成一個“黑洞”,意味著其他人的反饋要跟著改變。
章宇:對,那就是相互像傳球一樣,大家相互地來回給球。一般傳球,是你打過來我打回去,宋浩的演法變成那邊打過來,球沒了。因為這次演員都非常好,所以大家在一塊這個不是問題,很快就能適應過來。
不管是小花(宋佳)也好、王硯輝老師也好,好的演員可以不預設對手會怎么演,我也不會預設他們。他們也給了我一些可能劇本上面沒有體現出來的驚喜,和他們的一些對人物的觸動。我覺得每個人都演出了劇本之外的那些“外延”。那個東西是很鮮活的,甚至是在劇本創作的時候,作者也無法設想的。它必須發生在某種“當下”,在一個真切的場景里,只有演員成為那個人物中的時候,他們對視、說話、交流的時候,才會激發出真切的東西來,尤其在導演給了很大的創作空間和自由度的時候,他不叫停,就會一直往外延伸。

《風平浪靜》劇照,章宇、宋佳
澎湃新聞:看過電影的觀眾都會覺得,愛情這條線索是非常動人的,談談你和宋佳之間的“火花”?
章宇:我跟宋佳一上來就很默契。我們第一天圍讀就很默契,兩個人湊一塊有種莫名的喜感,也不知道為啥,兩個人在一塊挺逗的。這個東西可能真是緣分,小花演的潘曉霜,你看過也知道,愛情段落是里邊非常搶眼的部分,就是好演員,戲確實是靠人演出來的。小花她帶來的那種生命力,無疑是給這個電影加分的。
宋浩太苦了,在宋佳來之前,在潘曉霜登場之前,他真的太苦了,只有潘曉霜給他帶來了那個溫度。然后他的臉都舒展開了,宋浩慢慢才會有笑容。你在前面沒有看他露出過一點明顯的情緒,只有潘曉霜來才激活了他。不管從拍攝過程中,還是從創作過程中的喜悅度,確實也是演到跟宋佳的戲的時候,心里邊就會舒服很多。
澎湃新聞:還有要說到和導演的合作,李霄峰其實是個挺“文人氣”的導演,過往的創作里還有很多的概念上的東西,實際你們在拍攝的時候,把導演概念性具象的那部分落到實處去,會是一種挑戰嗎?
章宇:李霄峰實際上是作者的意志很大很強的那種導演,在他的影片里邊,他作者的意志會非常突出來,我猜想這部電影,會是他的這部分意志最最往后退的一次,也是他最成熟的一次。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導演完全沒有把他的意志強加在我們身上,我們還是就人物和情境本身來探討。當然設計是一定要有的,他的設計已經都埋在劇作里了。當然視聽上的,你說的那種概念,或者說隱喻和象征的那些部分也有。所謂的具象化,確實一個靠表演,然后靠美術和和攝影。但是不是說要去“落實”那些概念,是要盡量要“化掉”它。讓那些能看得出來的人能讀到,但我們還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東西,它的分寸什么,實際上要靠觀眾來判斷。
演“黃毛”是“占便宜”
澎湃新聞:那說回表演這個更廣泛的議題,之前你自己會說自己不希望變得太出名,因為出名就會不利于“藏”在角色后面,但是《我不是藥神》和《無名之輩》給你帶來的認知度,是一個很大的提升,怎么消化這種變化,有沒有找到解決這種擔心的辦法?
章宇:這個其實真沒啥辦法。它就是一個硬幣的正反面,你演的角色被更多人看到和認可,那你這個人也就會被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以后我確實就不會像《我不是藥神》里演黃毛的時候那樣,能占那么大便宜。對,那就是“占便宜”,因為大家不知道你是誰,對你沒有期待。這張臉很陌生,就很容易就建立起那個角色的信服度。往后如果說確實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我,或者甚至人家會對你有一個預設或者期待,我覺得這個也無可厚非。這個有點像人家說,牌桌上說新手特別容易贏。但你贏了一次,你第二次就不是新手了。我也不能老想占便宜,實際情況也不允許,所以做好自己能做的那個部分,就OK了。

《我不是藥神》人物海報
澎湃新聞:除了形象上占不到便宜,比方說知名度帶來的生活上的影響,對于汲取養分的途徑會發生變化嗎?
章宇:多少會有些影響,但好在我起碼還不像我的名字那么大眾,長相其實也不打眼。我去年一年算淡出,沒有作品,然后你能感覺到慢慢在適應,所以一兩部作品帶來的影響,目前對我來說,還是一個短時的很快能夠過去的情況。現在我們都在這種互聯網時代,大家的興奮點和興趣點,很快就過去了。
澎湃新聞:像電影里面那種被一個突然的事件,改變了整個人生的轉折,你如果回你自己的人生,會有這種非常明確的轉折點嗎?
章宇:現在這么想的話,還真是當時誤打誤撞地選擇學表演這件事。我確實沒想到學這個專業真的改變了命運,當時是因為以前不知道自己喜歡啥,勁沒處使,然后無限地揮霍那種“利比多”。直到接觸到表演這個事情以后,你發現,你找到一個出口來揮霍你的精力和時間,你愿意為這個事情琢磨。又因為學表演,喜歡上電影,然后開始覺得,自己好像可以吃這碗飯,想要努力地去做這個事情,這是一個系列的遞進和改變。
澎湃新聞:有個說法是,你長了一張“底層臉”,你怎么看這個?
章宇:我也不知道“底層臉”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首先我確實長得“像素不太高”,大家看著可能沒有那么有距離感,會覺得這個人是我身邊的某個人,或者我以前就遇到這樣的問題。這也是我占便宜的地方,沒有什么。就是長得“像素不高”,但說“底層”其實可能也不準確,大家都差不多,誰也不是都含著金湯匙長大,可能大家看這個人長那么“寒磣”,還那么倒霉,也能挺開心的。
澎湃新聞:在你自己對表演還沒很多底氣的時候,作為一個不那么帥的人去學表演,外形有讓你不自信的時候嗎?應該那會兒學校表演系里還是帥哥美女多吧。
章宇:我一直都不太信那一套標準,因為我很早就發現,我自己喜歡的演員也都不好看,也是這個事情讓我覺得,好像我是OK的。而且拿 “好看”的一套標準,框在世俗的審美里去選人,但我們在銀幕上要塑造人,不是說是一個model,一個真的活生生的人的話,重要的一定不是好看和不好看,而是他是不是鮮活、生動、真切,這些都比好看要重要得多。

《風平浪靜》劇照
澎湃新聞:我看你之前有接受過一個采訪,當時說你自己不喜歡接受采訪,但理由是覺得“沒有資格”,我好奇你對“資格”這事怎么看的?
章宇:我確實不喜歡,要不是因為這個電影,我也不會接受采訪。我看過一些很好的訪談,那些學者或者說那些很厲害的藝術家,他們的訪談,真的有時候能給讀者醍醐灌頂的那種點撥。我沒到那種層面上,也沒有那種深度,所以泛泛的采訪,實際上我覺得對于我來說和讀采訪的人,可能也都沒啥意思。也聊不了多深,而且我自己經常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
澎湃新聞:但其實你是個有表達欲的人,你還寫詩什么的。
章宇:是,我只是不喜歡用這種說的方式。而且我應該說是以前挺想表達的,現在也不怎么表達了。我覺得放在作品里是最好的,音樂人就去做音樂,電影人用電影表達。我們說不好話,說的話也沒有什么營養,所以這是我不太喜歡做采訪的一個原因。
澎湃新聞:你前面說,你是那種需要投入很多精力把“利比多”卸掉的人,那除了表演,還有什么是你對這個世界比較有興趣的部分?
章宇:還是人性。雖然說你平時去觀察、去琢磨人,這是我們專業修養的一部分,但實際上我覺得對一個人活著,他怎么生活、怎么看待別的人,都是一個必要的修為,你怎么了解別人,怎么來看待自己,或者你有多了解自己,我覺得這是活著最重要的一個修為。
澎湃新聞:了解別人這件事情,在你塑造的那些人物上面可能去表達和體現了,你現在怎么了解自己呢?
章宇:你這個問題好難答,太大了。我只能說,現階段,我是一個非常走運的人。我自己其實一直挺擰巴。即便現在,我也一直在擰,我在做一些事情的選擇上面,在對劇本的要求上面,有點偏執。我也不覺得這個好,我也試著讓自己再放松一點,因為經過疫情,發現電影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這是自己一直珍視的事情,它也沒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也試著,想把這個東西,看得不要那么重,否則自己的傷害和失望就會更大。
澎湃新聞:小時候,想象過自己到現在這個歲數,應該是什么樣的嗎?
章宇:我記得我小時候設想,我30歲應該會有直升機了,小時候對于成功的定義是有錢,有錢就可以開直升機。對,這是曾經設想向往的一個很荒謬的、荒唐的、幼稚的想法。但是我快40了,我現在連摩托車都沒有。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