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對話】王清華:梯田、絲路及影視人類學研究的開拓者(下)
王清華,1979年考入云南大學歷史系,學習云南民族歷史專業。1983年畢業進入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從事民族學研究工作至今,曾任民族學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中國民族學會理事、中國影視人類學學會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民族學及影視人類學。著作有《梯田文化論——哈尼族生態農業》《南方陸上絲綢路》等多種,發表論文數十篇,參與拍攝《瀾滄江》等影片5部。
采訪者:王吉甫,云南省民族藝術研究院研究人員。
三、南方絲綢之路研究
王吉甫:王老師,昨天您提到您的研究方向里面有一項是關于南方絲綢之路的,那么現在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開展,對于絲綢之路的研究在全國是異常火爆,那么您在20多年前就研究了南方絲綢之路,可以說是在這個研究領域最早的開拓者,您是怎么發現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然后對它進行研究的?
王清華: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是非常偶然的。這項研究實際上是一段友誼的結晶。
我和我的朋友徐冶有一個共同的老師,他叫段鼎周(昆明市科協原副主席)。我們經常去他家,所談的多為學術問題。1984年底的一天,段老師說有一條古道從四川到云南,又從云南一直通往緬甸印度,這條古道對于云南來說太重要了,非常值得研究。
西南古道是中國最早連接世界兩大文明古國印度和中國的交通線,它的存在不僅使多民族云南的文化交流和融會加劇,而且帶來和傳播著中原和印度的文化,實際上這條古道很早就是東西方文化及南北文化交流的中間環節,起到了歷史文化的地理樞紐作用。研究這條古道,意義十分重大,不僅為了歷史,更是為了未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初,將為云南的發展提供歷史經驗和文化依據,對外開放提供借鑒。
那天的討論直到深夜,最后徐冶提出,課題的名稱可稱為“南方陸上絲綢路”。絲綢自古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東方文明的象征。古代中國的一切對外交通線,都被譽為“絲綢之路”。
我們三人就決定對這條古道進行研究,并進行了分工。當時我正在收集哈尼族的歷史文獻,就負責西南民族文獻;徐冶負責歷史文獻;段老師負責總體構架的設計。
王吉甫:因為南方絲綢之路形成的歷史年代跨度很大,這條路的分布區域也特別廣泛,你們當時對它的研究用的是什么研究方法?
王清華:我們三個分工以后對與這條路有關的歷史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研究,這是中國傳統的歷史文獻研究法,包括了資料的考證、訓詁;第二就是實地考察,真正的田野考察。由于我是學民族學的,對這個方法的掌握和應用比較得心應手,所以沿南方絲綢之路的田野考察也進行得比較順利,我們從成都開始一段一段一直考察到緬甸密支那,整個過程是感受很深,收獲很大的。今天這個資料還被人們廣泛運用。
經過兩年多的研究,1987年,“南方絲綢之路”課題結束,以《南方陸上絲綢路》為名出版,這是中國第一本關于南方古道的學術研究專著,是第一次以絲綢之路命名南方古道的專著。當然,它只是初步的研究。

田野工作照
王吉甫:重要的是你們最早開啟了這條路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你們將這條路命名為南方絲綢之路,在歷史上沒有人這么提出,之前說的都是唐蕃古道、川滇古道、蕃南古道、茶馬古道等,真正稱為南方絲綢之路就是你們提出來的。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在當時社會影響如何?
王清華:1987年,距今已30年了。當時,《南方陸上絲綢路》的出版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并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掀起了一股西南絲綢之路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云南日報》等媒體做了專題報道,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南方絲綢之路也名揚四海,不少人紛至沓來,意在探索這條鮮為人知的古道的底蘊與奧秘。此后,我和徐冶還有攝影師徐晉燕被《中國報道》這個雜志邀請實地考察南方絲綢之路,寫成報告,在《中國報道》上連載,一直連載了40多期。這個連載后來結集出版了《西南絲綢之路考察記》一書。這就是我們在30年前對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這個研究分為兩項工作,一個是歷史文獻資料的研究,另一個是沿這條路一直走到了緬甸,寫了這條路實地考察報告。此后,我又寫過《南方絲綢之路與中印文化交流》《大通道》等學術論文和影視人類學電視片。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如今國家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南方絲綢之路在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中間這么一個節點上,又被人們重新提起,目前它的研究顯得異常火爆。
說到當時的影響,最值得一提的是引動了四川省、貴州省還有云南曲靖地區對南方絲綢之路相關地方的研究。當時四川省博物館的館長童恩正教授就向四川省人民政府上書要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是以考古的方式對南方絲綢之路進行考古研究,被政府采納。但是遺憾的是不久童教授去美國并不幸去世,這項研究也就停止了。但是這項研究仍然造成了很深的影響,出現了一批繼續研究南方絲綢之路的四川學者,其中有著名學者段譽、石碩等,他們把南方絲綢之路的四川部分研究得非常好。不久前我們去四川考察,發現很多以前的考古發掘現場已經成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展示地,成了南方絲綢之路文化的旅游點。現在,南方絲綢之路在四川名氣很大,其研究和影響都遠遠超過我們云南。對于最先開展南方絲綢之路研究的云南,真是嚴重的挑戰。直到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以及云南被定位為面向東南亞南亞的輻射中心后,云南的南方絲綢之路研究才重新展開,這些都展示了當年南方絲綢之路研究的影響。

元陽:田野工作照
王吉甫:按照現在的情況來看,四川省對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比我們省做得好,我本人從事的是民族戲劇方面的研究,據我的觀察,云南的戲劇特別是花燈“窩子”都跟南方絲綢之路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那么站在您的角度,我們云南的學者有必要對南方絲綢之路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挖掘,讓其成為一個跨學科的更具體、更系統的研究嗎?您有什么樣的建議?
王清華:你說得非常非常重要。剛才我也說過,南方絲綢之路國內部分的研究,四川學者做得非常好也非常深入。四川成都是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他們的絲綢之路研究不僅對學術界,而且在整個文化界、旅游界,甚至企業界造成影響,很多領域的發展都與絲綢之路相聯系,很多產品都打著南方絲綢之路的牌子走向全國,走向東南亞地區和南亞地區。可以說四川掀起了南方絲綢之路研究的熱潮,這是國內。那么國外部分呢,我曾經到印度,在印度中國研究所講過中國絲綢之路研究的情況,并提出孟中印緬諸國聯合考察南方絲綢之路的建議,希望從南絲路的源頭四川經過云南再到緬甸再到印度的聯合考察,得到了絲路沿線國家學者相當的認可和響應。在印度訪問期間,我發現印度研究絲綢之路也很深入,范圍也很廣泛,涉及絲路貿易往來、絲路文化交流、絲路宗教傳播等,但印度學者(還有西方學者)研究的是印度境內的這一段絲綢之路,就是說,他們研究的是絲路的后半截。四川是南方絲綢之路的上段,緬甸、印度是下段,上下兩段都在進行著深入的研究,而最早研究南絲路的云南目前的研究卻落在后面,這是不應該的。自古以來,南方絲綢之路一直溝通著中原、東南亞、南亞的關系,是經濟文化交往交流的通道,云南的很多文化就是由這條古道輸入的,如你剛才所說的云南花燈,就是從中原沿這條路隨著移民輸入的,直到今天花燈仍在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繁榮發展,滿足著人們的精神文化及娛樂的需求。因此,我認為云南應該加大力度對絲綢之路及沿線經濟文化進行研究,并利用地理環境的優勢和面向東南亞南亞輻射中心的地位,把絲路研究延伸到緬甸、印度以及更遠的國度。還要聯合絲路沿線各國進行聯合考察,進行多學科的研究,結合今天的旅游業,結合云南今天的發展,我覺得對南方絲綢之路的系統考察和縱深研究是必要的。
四、影視人類學研究
王吉甫:影視人類學是一個新學科,是一門外來學科。這門學科和傳統的民族學人類學是什么樣的關系,您是如何與這門學問結緣并進行研究的?
王清華:說起來研究影視人類學又是很偶然的事情。也是20世紀80年代初,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的于小剛在泰國亞洲理工學院讀書,他回來后跟我說,西方有一門學科叫影視人類學,是用影視手段對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對象進行拍攝和研究的一門學問。當時聽他如此說就引起我的興趣。因為我是非常喜歡文學的一個人,在大學期間就寫過文學作品,做過很多文學夢。畢業分配進入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從事民族學哈尼族研究后,對文學仍是耿耿于懷,偶爾還是會寫上一點文學的東西。這個影視人類學,它與傳統的民族學人類學的最大不同就是,它也以人類的現實生活為研究對象,但它所獲取的資料是影視的,是活生生的形象資料,包括畫面、音響及同期錄音,這就具有了文學的色彩。我覺得這是一門老天賜予我的學問,它可以把我的文學愛好和民族學結合在一起。
于是,我找來了我的同學郝躍峻(他是搞影視的)與于小剛一起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發現影視人類學在西方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但我國還沒有這門學問。于是,我們野心勃勃地決心開展中國的影視人類學研究,促使這門新學科的建立。此后,于小剛收集并翻譯了一批國際影視人類學的文字資料和影視資料,我和郝躍駿則研究了中國20世紀50年代大調查時期的紀錄片,對影視人類學的性質、理論及方法論體系進行分析研究,對西方影視人類學的歷史及中國的影視現狀進行了考察研究。最后,我們寫出了中國第一篇影視人類學研究論文《影視人類學的歷史、現狀及理論框架》。
王吉甫:到現在為止學術界認為您是影視人類學最早的開拓者,現在也還在從事影視人類學的研究,關于這個新學科您做了些什么工作?
王清華:不是我開拓了這門學問,而是于小剛、郝躍峻和我一起最早研究了這個問題,當時確實想開啟中國的影視人類學研究、建立中國的影視人類學。
當我們的論文《影視人類學的歷史、現狀及理論框架》發表在《云南社會科學》(1988年第4期),當時就在學術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引起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的高度重視,影視人類學從那個時候開始在中國進行研究并得到了發展。
1994年,在北京,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成立了中國影視人類學學會,我擔任副秘書長后來又擔任副會長,這個學會直到今天還在非常蓬勃地發展,影視人類學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前景更是廣闊,不僅影響到了學術界,而且影響到了影視界、教育界,很多大學里面現在也開設了影視人類學專業。今天看來,當時這門學科引入中國是非常重要的。作為我個人來說,雖然是很偶然的機會讓我碰到了影視人類學,但正是這門學問將我的興趣愛好與我的民族學研究非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此,這門學問一直吸引著我讓我一直在做。

元陽:工作照
你問我在影視人類學這門新學科里我做過什么。我現在總結起來做過三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個方面是理論研究。對于這門新的學科,它的理論究竟怎樣,它的方法究竟怎樣,它的影響力究竟怎樣,這一系列的理論問題是我關注并研究的,曾發表過《影視人類學的歷史、現狀及理論框架》《影視人類學在我國的發展》《影視人類學與云南文化強省建設》等論文,完成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影視人類學在中國發展對策研究》,這個是理論方面的研究。
第二個方面是影片的拍攝。我們開啟了這門學問后得到了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的重視與支持,籌建了影視人類學研究攝制中心(1995年正式掛牌),由我來擔任中心主任。這個中心購置了完整的影視設備,配備了影視編攝人員,展開了影視人類學影片的攝制。到現在為止,我一共參與拍攝了40多部(集)電視片(有些是與其他單位合作)。這些片子當時在學術界和社會上都造成了很好的影響。例如《瀾滄江》,就是一部反映江河文化,反映瀾滄江沿岸20多個民族生活的電視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后,被人們稱為多元文化交織的大河云南的象征。再如,《珠江行》這部六集系列大片,深刻反映了珠江這條多民族大江的社會變遷,反映了這條大江穿越經濟比較滯后的云南到達經濟最發達的廣州的歷史反差和社會的大變革,揭示了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和經濟較落后地區巨大的中西部差別,這個片子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后也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響。這些片子我們稱為試驗性拍攝,所謂實驗性就是用人類學方法采用現代影視拍攝手段進行拍攝,它有別于一般的紀錄片,更有別于一般的專題片。我現在正在結集出版我的影視人類學影視腳本集,叫作《影視人類學田野紀實》。
第三個方面是建立機構。20世紀50年代,我國由于還沒有影視人類學學科,也沒有專門的研究拍攝機構,拍攝民族志電影的時候,采用的辦法是民族學學者和電影制片廠的攝影師合作來完成。
一門學科的發展需要研究平臺,需要專門的研究人員來進行,影視人類學學科發展則更須如此。由于影視人類學有別于傳統的人類學,它是綜合性學科。從事這門學科的研究者需要有人類學理論和人類學方法,與此同時還要有電影攝制的技術和影視理論方法,而且它的最終研究成果是影視人類學的影視片,因此影視人類學的發展更必須有專門性的研究機構平臺。
1987年我們在開始影視人類學研究的時候,在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的批準下開始籌建“影視人類學研究攝制中心”。
1994年,我參加了中國影視人類學學會的籌建。這個學術機構的建立對中國的影視人類學人才匯集和學科發展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它促使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影視人類學研究室的建立,云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的建立,蘭州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影視人類學教學研究機構的建立。這些研究機構不僅從事影視人類學的研究與拍攝,同時培養學生發展影視人類學。
1995年,我們籌建于1987年的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影視人類學研究攝制中心正式掛牌成立。“中心”長期致力于:1. 搶救拍攝正在逐步消失的各民族社會文化形象資料,制作影視人類學影視片;2. 建立影視人類學資料庫;3. 開展影視人類學理論研究;4. 促進影視界、學術界及影視人類學領域的國內外交流與合作。
總結起來說,在影視人類學這個領域我是獲益非常大的一個學者,正是影視人類學使我熟悉了整個電影的拍攝、制作,編輯及編導的過程,懂得了將人類學民族學的理論、方法與現代影視理論、方法結合起來,運用于影視人類學的研究、攝制和教學;而且影視人類學還對我的民族學研究有很大的補益。
所以,總的來說,我這一生應該說都在人類學民族學領域,從事過三個方面的研究:一是哈尼族及哈尼梯田文化研究;二是參與開展了南方絲綢之路研究;三是參與開啟了中國影視人類學。總的來說就是這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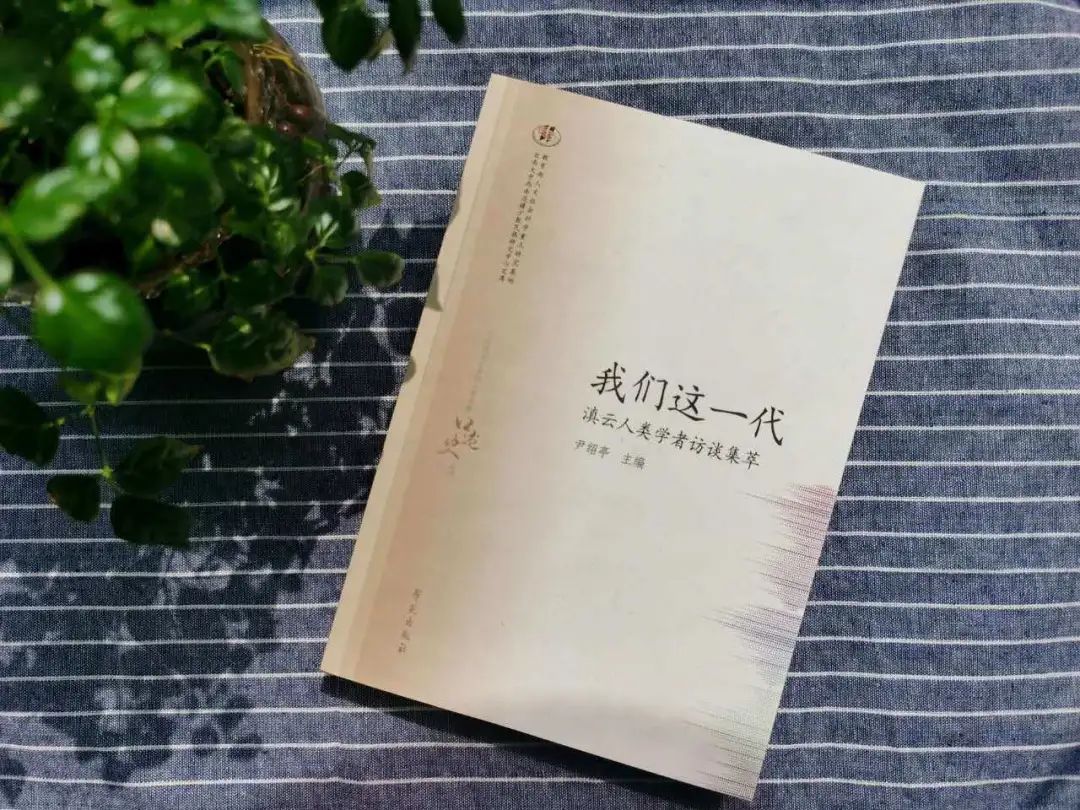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