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八佰》中的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復雜?
前段時間熱播的電影《八佰》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抗擊日寇的英雄們,還有一半天堂,一半地獄的魔幻現(xiàn)實場景:蘇州河一側的租界紙醉金迷,另一側的四行倉庫戰(zhàn)火紛飛,仿佛是兩個互不干涉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現(xiàn)象?真實的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復雜?
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復雜?
文 | 熊月之
來源 | 《12堂“四史”公開課》
從“華洋分處”到“國中之國”
我們常說,租界是國中之國,但是從歷史學的角度講,租界一開始不是國中之國。首先,最初租界只是將土地租給外國人,外國人在此居住,在此經(jīng)商,租金一畝地1500文。其次,這個土地的主權是我們國家的,因此租界絕不是殖民地。開始是嚴格規(guī)定華洋分處,外國人住在租界里面,中國人不能住在租界里。如果僅僅是外國人住,沒有中國人住,租界的范圍就很小,影響也就很小。從1843年開埠,1845年上海開始有租界,一直到1853年,上海都實行華洋分處,中國人可以進去掃馬路、賣菜,但不能住在里面。在這8—10年中,租界發(fā)展是緩慢的,如果一直像這樣發(fā)展下去,上海租界影響不會很大。
上海一開始是華洋分處,到1853年以后才華洋混雜,起因就是小刀會起義。小刀會起義一共持續(xù)了17個月多一點。1853年9月小刀會把上海縣城占了,然后清軍就打縣城,打小刀會,打來打去,打了17個月多,到1855年初才把小刀會鎮(zhèn)壓下去。小刀會起義發(fā)生時,縣城里外共有35萬人,到小刀會起義被鎮(zhèn)壓下去以后縣城還不到4萬人,90%的人都跑了、死了。死的當然是少數(shù),大多數(shù)人都跑了,一小部分跑到鄉(xiāng)下去,相當大一部分跑到租界里面去。最初的租界是今天外灘河南路以東、黃浦江邊、金陵東路那一帶,原來是華洋分處,不讓中國人進入。但戰(zhàn)爭發(fā)生了,難民涌來了,租界沒辦法,只好讓他們進來。那時英國政府和租界當局都是希望把這些人趕出去,戰(zhàn)亂結束以后也不希望這些人留在租界里。因為原來只有兩三千人、很容易管理的地方后來進來幾十萬人,要租房、要消費、要吃飯、要有垃圾出來,這些事情都必須由政府來管。

位于舊時法租界的上海武康大樓
租界當局和英國政府都不希望華洋分處變成混處,但租界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實行地方自治,權力是靠投票來決定的,靠有錢人投票決定。租界里的商人們覺得混處有好處,人多了,生意就來了,東西就好賣了,房地產(chǎn)就起來了,因此歡迎華洋混處。小刀會起義的時候,上海房地產(chǎn)的漲幅遠遠超過我們這些年上海房地產(chǎn)漲價的幅度。隨便什么地方蓋個房子,馬上就有人來住,最早一批老式石庫門房子就是這個時候開始建起來的。石庫門房子的容積率比較高,房子比較密集,在有限的面積里可以蓋更多的房子,容納更多的人。蓋房子的人和出租房子的人,也就能賺到更多的錢。因此商人投票的結果是歡迎華洋混處,接著修改章程,上海租界就變成了“國中之國”,變成了中國政府管不到的地方。
租界形成的歷史原因
那時候中國政府干什么去了,上海地方政府干什么去了?怎么不管國家的主權,不管地方的主權?怎么就讓外國人占領了呢?這就是因緣際會。1853—1854年,清朝正處在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太平天國把南京攻下變成了天京,清政府從各個地方調動軍隊來鎮(zhèn)壓太平軍,打不過,只好用曾國藩他們來打。那時候真的是很困難,清政府顧不過來。而上海地方政府更復雜!小刀會占領縣城以后,把知縣袁祖德殺掉,又把上海道臺吳健彰抓起來。小刀會起義首領劉麗川和吳健彰是廣東香山老鄉(xiāng)。道臺是廣東人,到上海來做官,旁邊必須有一批聽得懂地方話的人幫他,小刀會把吳健彰道臺身邊的人都發(fā)展成小刀會的會員。吳健彰身邊一個最重要的謀士,是小刀會潛伏、埋伏在他身邊的“地下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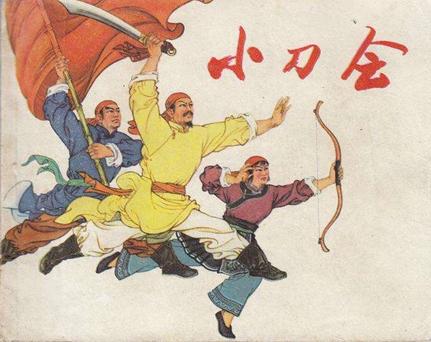
《小刀會》連環(huán)畫
當時道臺銀庫里有幾十萬兩銀子,道臺要把銀子弄走,他身邊的人知道后就把信息捅給小刀會,小刀會就要把這銀子搶出來。因此小刀會起義最初是為了這幾十萬兩銀子,但起義以后事情發(fā)生了很復雜的變化。話說回來,小刀會起義后吳健彰被劉麗川抓住,老鄉(xiāng)關系就發(fā)生作用了,劉麗川弄個繩子從城墻上垂下去,偷偷把吳健彰放走。吳健彰逃出以后,怕被清朝政府殺頭,就拼命想辦法弄錢送給清朝政府鎮(zhèn)壓太平軍。吳健彰在一條船上辦公,連個辦公室都沒有,根本管不了上海地方的事情,上海的地方政府基本處于癱瘓狀態(tài)。
各種各樣的因素湊在一起以后,1854年以后上海租界的性質就變了,從華洋分處變成了華洋混處。租界的政府就是工部局,管理社會治安有巡捕,犯法有法庭處理,這不就變成“國中之國”了嗎?
“一市三治”
上海在近代以后出現(xiàn)了一個我們今天很難想象的奇怪格局,叫“一市三治”。一市就是一個大城市,大上海。三治,就是三個政府管理。近代上海有三個政府:一是公共租界,管蘇州河南北,延安路以北那一大塊地方;二是法租界;然后是華界,包括南市、閘北兩塊。三個政府,三套法律。電壓都不一樣,有110伏,也有220伏。電車軌道不一樣,從閘北通過公共租界、法租界到南市要換三次車。黃包車執(zhí)照也不一樣,每個區(qū)域有自己的牌照,一個黃包車夫至少要捐兩張牌照才能夠跨區(qū)域,否則只能在自己區(qū)域里營生。法律的差異更是很難想象。在華界里認為是最該殺頭的事情,到租界里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權利。比如,在租界里罵清朝政府沒關系,因為沒有殺人放火,但如果是在華界里罵,就要抓起來殺頭的。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國家,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實行,其實沒什么關系,比如香港地區(qū)的法律跟廣東法律是不一樣的,但因為兩個區(qū)域有明確界限,因而總體可行。但那時候上海不同區(qū)域間是直通的,情況就非常復雜。
復雜到什么程度?我舉幾個例子。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地方,即今天的延安東路,原來是洋涇浜,洋涇浜是1914年以后才填平的。洋涇浜是走私販毒的絕佳場所。雖然,租界在名義上是反對販毒、運毒的,但是如果販毒在橋上交易,巡捕從法租界那邊來,法租界那邊吹下哨子,毒販就能從橋上跑到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不能夠越過橋來執(zhí)法,所以跑到橋這邊就安全了。反之,如果巡捕從公共租界來,也吹哨子,毒販便跑到另一邊去。橋上于是變成三不管的地方,變成大家都管不到的地方,各種違法亂紀的行為就在橋上滋生,這給上海城市管理帶來了極其復雜的問題。在老上海,這種地方很多,公共租界和華界有交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交界,法租界跟華界又有交界,這些都是管理薄弱的地方。管理薄弱就變成縫隙,“一市三治”就是這樣的特殊格局。

1914年以前的洋涇浜
“縫隙效應”
三個區(qū)域是物理空間上的縫隙,在制度上的縫隙就更大了。我們說辛亥革命期間死亡的人數(shù)遠遠比明清換代死的人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宣傳。有了報紙以后,對于人心整合有很大的影響。報紙能夠產(chǎn)生廣泛影響的最關鍵之處,就是有租界在。報紙辦在租界里,清政府沒辦法把它們封掉。那時反對清朝政府的報紙的散播,國外主要在日本,國內主要就在上海。在日本散播的,清政府可以通過海關把相關報紙和書籍禁掉。但是在上海就沒辦法了,上海在清朝的統(tǒng)治下,可清朝政府卻沒辦法進租界管理。
最典型的案件就是蘇報案。1903年,鄒容、章太炎在《蘇報》上發(fā)表反清的文字。清朝政府跟租界交涉,租界就將章太炎抓進牢里,判了三年,鄒容判了兩年。這個案件放在其他地方,十個頭都給砍掉。蘇報案之前,吳稚暉、蔡元培他們因在莊園里發(fā)表演說被租界多次傳訊,一共是六次。每次都問他們有沒有殺人放火,有沒有私藏軍火,殺人放火、私藏軍火都是犯法的,這些都沒有,便不算犯法,因此他們一共被傳訊了六次,都沒有問題。而蘇報案發(fā)生后,章太炎和鄒容完全是可以逃避抓捕的,只是因為先前寬松的租界環(huán)境而“輕敵”了,這才被捕入獄。他們兩個人能跑而沒跑,是上海特殊的時候發(fā)生的特殊事情,他們的英雄行為跟那時候的環(huán)境有關系。

1896年創(chuàng)刊于上海的《蘇報》
中共一大為什么在租界召開?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的時候,也是利用了這個縫隙。中共一大為什么是在上海法租界舉行會議,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舉行?位于新天地的中共一大會址在1921年是上海的邊緣,是城鄉(xiāng)接合部,不是今天的樣子。上海法租界剛擴張以后,一大會址的前面就是菜地,不遠就是農(nóng)田,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們才在那兒開會。二大會址位于現(xiàn)在靜安區(qū)靠近延安路高架一帶,那是兩個租界交界的地方,就是靠近縫隙,跟陜甘寧邊區(qū)一個意思。共產(chǎn)黨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時候曾經(jīng)有個規(guī)定,在上海活動一定要充分利用上海統(tǒng)治薄弱的地方。據(jù)鄧穎超先生回憶,她跟周恩來在上海搞地下活動,不到一個月肯定換個地方,每到一個地方只要報一個名字,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你交錢就能住下去,沒人管你。近代上海戶口不像后來上海戶口那么值錢,戶口沒人管,來了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

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中共一大會址
租界對上海物質文明的影響
中國有26個租界,天津有9個租界,漢口有5個租界,但沒有哪一個租界比上海的租界大,上海租界的面積加起來是全國其他23個租界面積的1.5倍。這就是上海為什么影響那么大、西方的影響基本集中在上海的原因。1949年以前在上海的外國人最多的時候超過15萬,今天上海的外國人已經(jīng)超過15萬。但今天的外國人和那時候的外國人有本質上的不同。今天的外國人是投資經(jīng)商或者買房的,很少加入中國籍、成為市民。但那個時候的外國人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家園,住在這里、生活在這里,有的人就出生在這里,把自己所有的興趣愛好都放在這里。他們在全世界范圍發(fā)現(xiàn)有什么好東西都引進來,首先為自己所用。比如,西方有電燈,上海馬上有電燈;西方有電話,上海馬上有電話;西方有電報,上海馬上有電報;西方有自來水,上海馬上有自來水。為什么那么快?因為外國人在西方怎么生活,到上海還得這么生活,于是上海的物質文明迅速發(fā)展。這對上海的影響就叫示范效應,和灌輸是不一樣的。他是為了自己用而引進,不是為了灌輸。而中國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到最后就跟著模仿。

20世紀30年代,英商在上海公共租界建設自來水公司辦公大樓及水塔
上海人一開始也抵制過自來水,說這個這玩意兒從鐵管子里下來白花花的,鐵管子從地上出來會陰陽失調,對人身體不好,而且自來水里有漂白粉的味道,有毒。原來城市里都有挑水夫,挑水夫從井里、河里給每家每戶的水缸里送水,水牌子一分錢兩桶水。自來水的使用和推廣會讓挑水夫失業(yè),因此反對自來水的人中挑水夫的呼聲最強烈。后來上海自來水公司采取辦法,聘用挑水夫為員工,解決他們的就業(yè)問題,挑水夫的問題就解決了。自來水公司又向每家每戶免費送水,讓人們逐步接受。那時候常常發(fā)生傳染病,統(tǒng)計下來租界里的死亡率比華界低,原因是華界垃圾糞便管理不好導致飲水有問題。于是上海人開始覺得自來水好。上海人對外國東西的崇尚、愛好是從心里面涌出來的,這種推崇是從以往的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不是靠教科書教出來的,而是有自己的實踐體驗。
原標題:《一條蘇州河隔開兩個世界|《八佰》中的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復雜?》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