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技術如何解決“藝術危機”?——斯蒂格勒的“技-藝”反思
文 / 劉永謀(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不少談論技術問題的哲學家也喜歡談論文藝,比如,海德格爾喜歡討論詩歌和荷爾德林。此種風尚在當代法國思想家中尤為常見,福柯、鮑德里亞、德勒茲、德里達和斯蒂格勒均如此。福柯更是提出生存美學的理論,要求哲學家做出表率,把生活當作有自己“風格”(style)的藝術品。他曾道:“藝術成了一種專業化的東西,成了那些搞藝術的專家所做的事情。為什么人的生活不能成為藝術品?為什么燈或房子可以成為藝術品,而我們的生活反而不能呢?”顯然,福柯要求哲學家同時也應是藝術家。
斯蒂格勒同樣抱怨藝術的專業化,希望藝術家成為福柯意義上的哲學家,或按照生存美學來“哲學地”生活。他認為,“何為藝術家?藝術家是個體化形象的典范——這可以理解成是心理的和集體的個體化過程”。這里的“個體化”與福柯提及的“風格”可謂異曲同工。顯然,兩人對哲學家和藝術家的要求太高,賦予他們的責任太大。在中國,“哲學”是理性、呆板和枯燥的代名詞,“藝術”則意味著感性、不羈和浮華。然而,在當代法國,哲學、藝術和技術卻常常在技術哲學中交織在一起。
今天的時代無疑是技術時代。哲學家常自詡其對時代精神的把握,先鋒法國哲學家當然勤于反思高新技術問題。而思考技術問題時,他們將“技”與“藝”放在一起審度。
“技藝不分”根源于法國文化的歷史傳統。按照沙茨伯格(E. Schatzberg)的觀點,歷史上technik(技藝)一詞長期在法國被使用,指工業藝術及其生產材料和方法,明顯是混同技術與藝術的術語。百科全書運動時期,technologie(工藝學)一詞曾流行一時,但到19世紀末,這個詞就很少出現了,被諸如applied science(應用科學)和technik等新的概念所取代。直至一戰和二戰之間,和英語中表示技術與藝術分離的詞technique(技術)的含義類似的法語詞才開始被大規模使用。法國技術與哲學學會共同發起人塞瑞祖里(Daniel Cerezuelle)指出,盡管德國哲學家和工程師常使用technik一詞,但art(藝術)這個術語在法國仍然很流行。斯蒂格勒曾指出,“我們今天所說的‘藝術’,在古代就是‘技術’(tekhnè)”。總之,在法國,“技藝不分”有詞源學上的原因。在法國人看來,藝術并不局限于在博物館和藝術館里珍藏的純粹審美物,更多的是應用于建筑、機器、家具、裝潢、服裝和園藝等領域的實用工業美學品。埃菲爾鐵塔和盧浮宮的玻璃金字塔堪稱藝術與技術完美融合的典范,巴黎人民不但不覺得“違和”,反倒引以為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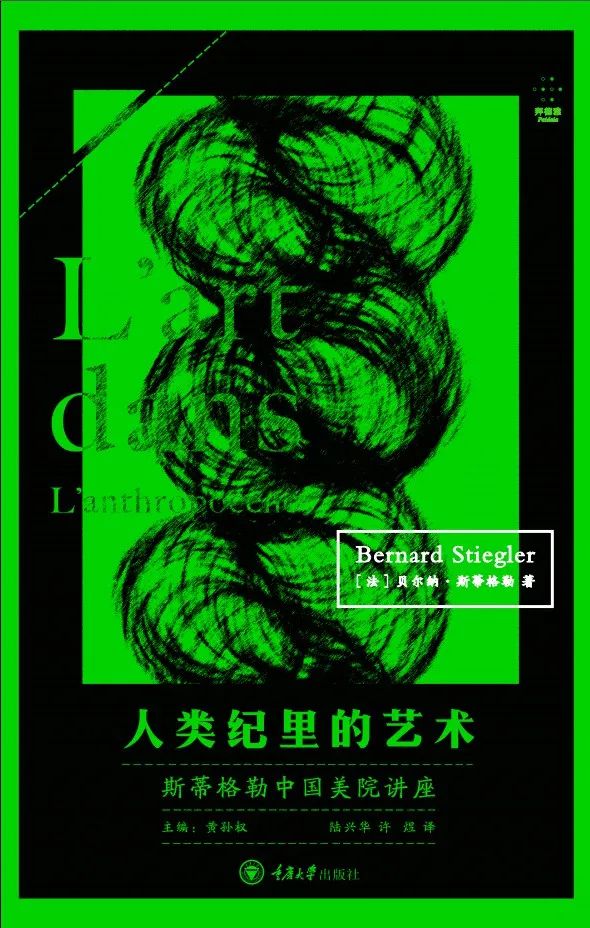
人類紀里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
[法] 貝爾納·斯蒂格勒 / 著
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6-12
有意思的是,在過去幾十年間,一些法國技術哲學家——如西蒙棟(Gilbert Simondon)和埃呂爾(Jacques Ellul)——被同行冷落,卻在藝術家、設計師和建筑師中大受歡迎。提出“巨機器”(Megamachine)理論的美國技術哲學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技術哲學發達的美國也有同樣的遭遇。實際上,技術哲學作為哲學分支的專業地位在法國一直存在爭議,很多人認為這與其“技藝不分”的文化傳統有關。
今天,法國技術哲學標志性人物(如拉圖爾和斯蒂格勒)與藝術家的聯系都非常緊密,也是有名的策展人。2006年起,斯蒂格勒擔任蓬皮杜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文化發展部主任,創立創新研究所(IRI)并任主任,新媒體、電影等是他重要的研究主題,他聲稱要用技術來解決藝術遭遇的“危機”。斯蒂格勒進入中國時最早先和中國美術學院接觸,同時,他與中央美術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也有不少聯系,在北京798藝術區參加過活動。總之,斯蒂格勒在文藝圈的名聲明顯比在哲學界大。

本文以斯蒂格勒為例,談談法國技術哲學家對“藝術危機”的看法。斯蒂格勒所謂的“藝術危機”指的是什么?他有否想過該如何解決這一危機?這得先從他如何看待技術與藝術的關系說起。
斯蒂格勒主張“泛”技術,他認為“人的行動即是技術”,舞蹈、語言、文學、詩歌、音樂乃至政治,無一不屬于技術領域。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用“技術”一詞指稱人類行為中只有優秀者掌握的專門技能,如聲樂技術——雖然人人都會唱歌,但只有歌唱家才掌握聲樂技術。而藝術則是技術的最高級形式,特定技術最終升華為藝術。
斯蒂格勒對技術的理解如此之“泛”,根源在于他對人之本質的理解。他曾用故事“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來隱喻其人性論:愛比米修斯負責給動物安排技能,結果忘記了人類,所以人一開始就是被遺忘的、有缺陷的。后來,普羅米修斯盜取技術和火給人,才讓人類能生存下去,因此,人從源頭上便是依賴技術的有缺陷的存在,人離不開技術。技術之于人并非簡單的工具,而是類似于義肢或假牙的代具(prothesis)——沒有技術就沒有人,沒有人就沒有技術,人性就是技術性或代具性,技術代具與人的缺陷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簡言之,人本質上是工具制造者(homo faber)——這是在法國技術哲學家中非常流行的觀點。雙手靈巧的人創造出同源的技術物和藝術物,都是代具制造與運用的產物。
古人類學家古爾漢(André Leroi-Gourhan)認為,人類身體內部的進化在石器時代已停止,只能突破內部而向外進化。斯蒂格勒認為,技術進化便是人類外在化的(exosomatic)進化形式。因此,沒有技術,人類不僅不能生存,也不能進化。人類的文化傳承以技術為條件,技術是文化傳承的物質載體。斯蒂格勒把技術進化視為人類器官進化的新階段,將技術學稱為“器官學”。
在斯蒂格勒看來,技術性就是時間性。動物世界沒有時間,只存活于當下,而人可以借助技術記憶通向過去和未來。他提出人有三種記憶:遺傳記憶、后生成記憶和后種系生成記憶。遺傳記憶由遺傳基因傳承,后生成記憶經人的后天經歷獲得,后種系生成記憶則由技術保存下來。第三種記憶(即技術)使人超越個體生死,躋身于整個人類文明的長河之中。換言之,技術是人類時間或記憶的“固化”。藝術屬于技術中特殊的記憶術。斯蒂格勒所謂的“記憶術”,是指專門保存人類記憶的技術,與一般所謂的“傳播技術”有很多重合。比如,遠古時期的洞穴壁畫,古代的護身符、雕刻、文身和結繩,后來的文字、符號,以及現代的錄音、攝影、電影、收音機、電視機及計算機、互聯網等,均屬于記憶術。

圖片來源unsplash @Julius Drost
從記憶的時間性上來看,斯蒂格勒區分了三個持留(retention):第一持留是即時記憶,第二持留是回憶,第三持留是技術物對人類記憶的保存。“我們所說的第三持留指的是‘客觀性’記憶的所有形式:電影膠片、攝影膠片、文字、油畫、半身雕像,以及一切能夠向我證實某個我未必親身體驗過的過去時刻的古跡或一般實物”[1],所有的藝術品均屬于第三持留。
在工業時代,藝術產業化使得所有藝術品均可被復制。斯蒂格勒將杜尚的《泉》視作復制時代藝術品的開端。他認為,進入數字化-信息化時代,所有的藝術品都具備超復制性,這使得大規模的藝術超工業化成為可能。這就是數字藝術、AI(人工智能)藝術興起的大背景。所謂超復制性主要有以下四個特征:一是數據化藝術品的復制不會損失任何數據;二是數字復制品可以隨意被處理和計算;三是不同復制藝術相互利用,融為一體;四是數字化復制與生物復制(生物科技與基因工程對DNA的復制)相結合,可復制性達到極高的自動化層次。

藝術產業化意味著藝術被商業邏輯俘虜,藝術為消費主義和消費社會服務。藝術品是技術物保存的人類意識,使得藝術可以被用來交換而商品化。在斯蒂格勒看來,藝術產業化意味著藝術的衰敗。斯蒂格勒常舉泰勒主義者[2]的例子來說明藝術如何為商業所俘虜:他們使用攝影記錄方法(chronocyclegraph)來研究工人勞動,即在被測者的關節和身體某些部位裝上小電燈泡,用攝像機拍攝工人勞動的過程并進行研究,目標是提高勞動效率,實現科學管理。
而“藝術危機”的真正到來,是從記憶術成為當代技術體系的主導技術開始的。按照斯蒂格勒的觀點,記憶術自古就有,但在數字化-信息化時代才占據了技術體系的主導地位,即整個技術-工業系統是以記憶術為基礎運轉的。
由于技術與社會之間一直存在沖突,而當代技術的加速發展極大地加劇了這種沖突,因此,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必須想方設法讓社會接受新技術,才能讓消費主義經濟順利運轉。包括電影、電視、電臺和數碼藝術等藝術形式在內的記憶術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因為它們可以在不同的觀眾和聽眾中形成共同意識,甚至塑造某種全球性共識。“在文化工業的演變過程中,被銷售的是意識本身。”[3]
斯蒂格勒特別界定了一類時間性藝術,以說明藝術在塑造當代意識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音樂、電影、電視和廣播都是時間性的,這些藝術形式屬于時間客體——“當某一客體的時間流與以該客體為對象的意識流相互重合(如音樂旋律),那么該客體即為‘時間客體’。”[4]在斯蒂格勒看來,人的意識也是時間性的意識流,與時間性藝術(尤其是電影)同構。他甚至認為,人的意識就是電影,因為人的意識處理信息的方式和電影類似,并不止于簡單地接受,而同樣要進行剪輯、蒙太奇、刪減等“后期處理”。所以說,時間客體對觀眾或聽眾的意識流影響非常大。斯蒂格勒尤其關注電影的力量,經常把當今稱為“電影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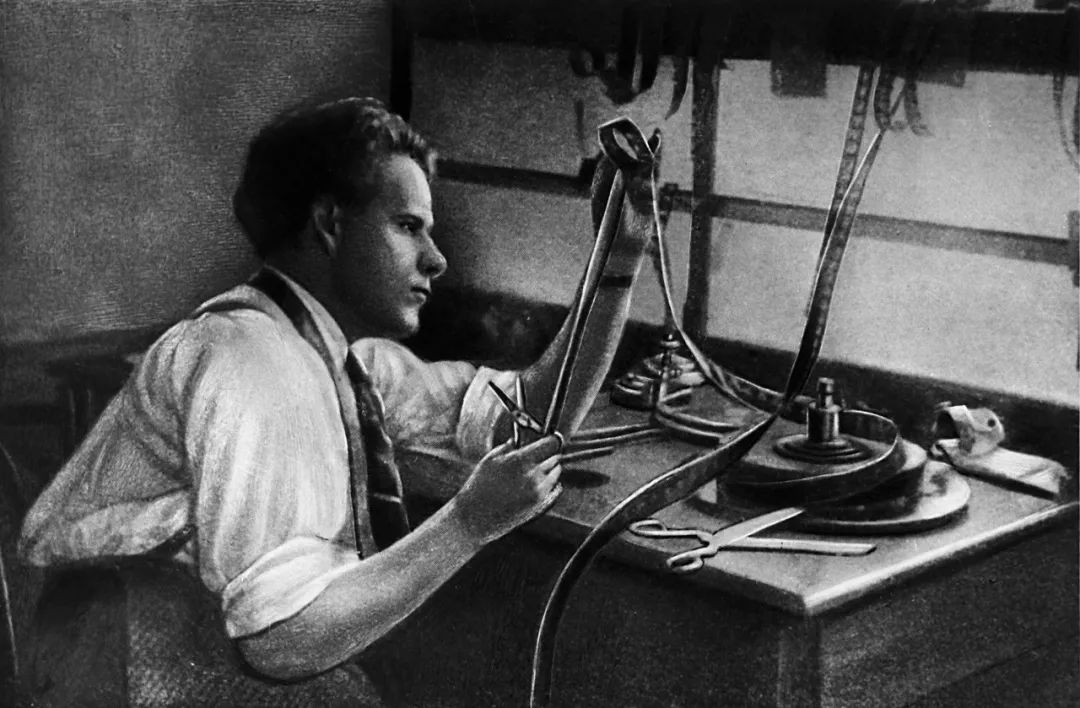
蒙太奇理論奠基人之一 Sergei Eisenstein
記憶術產業越發達,技術被接受程度越高,技術體系發展越快。此時,包括藝術在內的記憶術成為資本主義技術-工業體系的核心,資本主義社會進入了斯蒂格勒所謂的“超工業化時代”(hyperindustrial era)。其中,美國被斯蒂格勒認定為世界技術接受競爭中的優勝者。在美國,藝術和文化工業成為推銷新技術產品和“美國生活方式”的最佳工具,是技術接受和商業戰的重要手段。換言之,藝術已被完全異化,成為控制當代社會的權力形式,卷入全球資本主義商業戰、信息戰和思想戰的漩渦之中。這就是斯蒂格勒所謂的“藝術危機”。
同時,斯蒂格勒將“藝術危機”稱為“象征的苦難”(symbolic misery)。文化是象征的事業,“象征的苦難”等同于當代文化的苦難,而藝術作為文化的精華,必然是苦難的主角。由此,斯蒂格勒指出,象征的苦難是當代藝術遭受的某種“美學苦難”:
? 美學調節壓倒美學經驗。后者是人的本真體驗,前者則以藝術為社會控制術,前者壓倒后者意味著工業-技術邏輯左右象征-符號邏輯;
? 美學調節成為社會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消費主義徹底俘獲藝術,工業-技術完全征服藝術;
? 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競爭被激化為經濟戰爭,經濟戰爭變成美學戰爭,美學戰爭導致“象征的苦難”;
? 當代社會運用象征維持社會秩序,文化產業顛倒、敗壞和簡化象征,象征被生產過程所吸納,象征的生產被簡化為計算;
? “象征的苦難”導致西方社會個體化喪失或非個體化,當代個體化被程式化(grammatization)的新樣式(即數碼化)完全左右;
? 非個體化的結果是每個人失去個性和自我,整個社會成為德勒茲所謂的“控制社會”,或斯蒂格勒所謂的“蟻丘”(anthill),即個體成為社會大機器中的一個零件。就純粹審美藝術而言,當代社會已經成為藝術的沙漠,或斯蒂格勒所謂的“貧民窟”(ghetto)。
進一步而言,“藝術危機”是整個西方社會迷失方向的集中體現。在斯蒂格勒看來,技術是不確定的。新技術發展速度太快,社會抵制增加,歷史主義盛行,此即斯蒂格勒所謂的“迷失方向”,有時又被稱為“中斷”。在迷失方向的社會中,審美體驗被調節而齊一化,消費主義剝奪了審美能力,因為審美被簡化為計算,行動被還原為消費,欲望倒退為驅動力——其最終的結果是人們行動困難。

二戰后,新科技革命推動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西方發達國家紛紛進入加爾布雷斯所謂的“富裕社會”。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們陷入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質滿足的消費主義中,成為喪失批判精神和創造性的“單向度的人”(馬爾庫塞語)。從藝術異化的角度來看,斯蒂格勒承自法國技術哲學家前輩的諸多相關思想,如鮑德里亞的擬像理論、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理論和德勒茲的欲望機器理論等,都在控訴消費主義社會對人的奴役,他將這些理論融會貫通,自成一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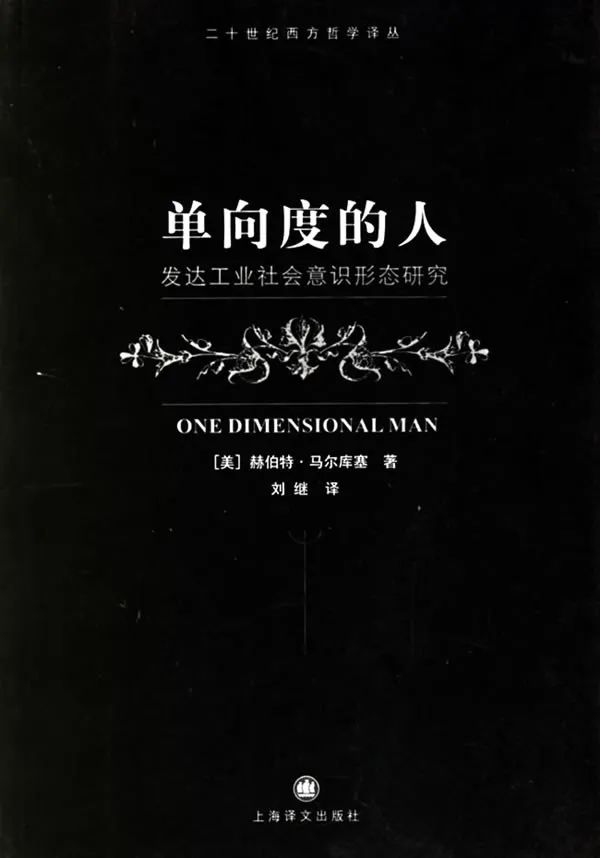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
[美] 赫伯特·馬爾庫塞 /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4
簡言之,擬像理論批評大眾傳媒的崛起使消費社會加速墮落為后現代擬像社會(擬像指的是無原本之物的摹本,即當代社會幻覺與現實混淆的仿真社會)。景觀社會理論則認為“世界已經被拍攝”,這使得當代社會進入以影像物品生產與消費為主要內容的景觀社會;而欲望機器理論則認為,欲望的生產和編碼是發達資本主義生產的關鍵,社會圍繞欲望的壓抑和解脫不斷進行權力斗爭。
面對奴役怎么辦?可以說:批判有力,出路徘徊。當代法國哲學家不約而同都走向“美學革命”的窠臼,即放棄社會改造,把解放之希望寄托于個體精神的美學提升。作為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的精神領袖,馬爾庫塞力主“心理學革命”和“本能革命”,他認為革命的關鍵是培養“新型的人”,即“性本能徹底解放的人”。后來他又轉向藝術,希望藝術能激勵人們的革命精神。而福柯在對規訓技術與知識-權力進行了一番激烈批評之后,提出了解放方案,即前述的“生存美學”,從街頭斗爭轉向雕琢有藝術品位的生活方式。德勒茲強調的則是將欲望從各種社會限制中解放出來,把自己變成“精神分裂主體”——不是精神病患者,而是在瘋狂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本真欲望支配的軀體。這與被馬爾庫塞寄予希望的流浪漢、失業者和妓女等資本主義的“局外人”有共通之處。
對于該如何解決“藝術危機”,斯蒂格勒選擇的同樣是“美學革命”的老路。他主要將希望寄托于藝術家和藝術,認為藝術必須擺脫社會控制工具的命運,走上批評“超工業”資本主義的道路——他用“超工業”一詞,是想說明當代社會仍然是現代社會,而非后現代社會。
首先,藝術家責任重大。如前所述,斯蒂格勒要求藝術家扮演“個體化推動者”的角色。所謂個體化過程,就是“我”在“我們”中成其所是的過程,即個性化與集體潛力共同實現的過程。也就是說,藝術家不僅是生產藝術作品的人,更是有能力且有責任創造新的個體化樣式的人。
“藝術危機”導致大眾喪失個性、遺忘本真的審美經驗,非個性化意味著精神的貧困化,藝術家應該為大眾創造新的生活樣式做出表率,主動與大眾合作,激發人們的審美狀態。
其次,人人都要搞創作,都應成為藝術家。斯蒂格勒曾道:“何為作品?但凡能觸發人之內心感應,具有轉化為動能之潛勢的,皆為作品。護士和面包師也是藝術家,潛在的藝術家。他們并非時刻在舞臺上,藝術家也不可能分分秒秒在搞藝術創作。”[5]因此,人人都是藝術家,尤其人人都可以做電影導演,因為如前所述,人的意識流和電影的時間流是同構的。斯蒂格勒認為,藝術創作是意外的過程,大眾在創作中可以偏離常規,打開個體化的新路線,仿佛電子躍遷到新的能量軌道。
再者,大家不能僅僅做觀眾或聽眾,而要借助數字技術成為業余愛好者。數字技術被視為“毒藥”,讓人上癮且無法集中注意力,導致所有人的美學經驗被齊一化而產生“精神危機”。但是,電子媒體亦可幫助普通人進行藝術創作或表演,打破業余愛好者與職業藝術家的界限,比如用手機拍攝短視頻、用單反相機完成攝影作品、用作曲軟件譜曲等,藝術的“門檻”在數碼時代不斷降低。按照斯蒂格勒的說法,“它(技術)既是毒藥也是解藥”。
第四,藝術應重新政治化。斯蒂格勒認為,政治問題是美學問題,反之亦然。因為政治討論需要他人的同情(sympathy),這樣大家才能共同生活,相互支持,超越獨立性和利益沖突。政治要在個體化中求得團結狀態,意味著要尋找共同的美學基礎,因為在一起也意味著一起感覺。斯蒂格勒認為,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的“愛”意指“政治共同體也是感覺共同體”。藝術聚焦人的感覺,因而美學與政治學是相通的。現在的問題是,感覺共同體完全被記憶術所控制,藝術世界不再討論政治。在“藝術危機”中,藝術完全被非政治化,與政治和批判性脫節,只剩下技術性維度。因此,藝術政治化意味著對藝術異化的反抗。此外,關注藝術的哲學家也應和藝術家一道思考,相互鼓舞,一起參與政治行動。
最后,“藝術危機”意味著文化危機。在西方文明危機的大背景中應對藝術危機,要做到以下兩點:第一,抵抗美國文化入侵。美國文化是藝術危機中的典型。斯蒂格勒主張歐洲國家應扶持自己的文化,與美式消費主義文化抗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是在反對藝術的產業化,恢復藝術的高貴與“靈韻”(本雅明語)。第二,恢復經濟與政治的聯系。斯蒂格勒認為,以記憶術為基礎的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割裂了政治與經濟的關聯,是造成“象征的苦難”的根源。因此,他呼吁重建一種政治、經濟、科學和技術等相互糾纏的新的工業模式,即“精神經濟”(spiritual economy),以阻止“超工業”文化資本主義因失去限制而自我毀滅的趨勢。
然而,“美學革命”究竟是否可行?不可否認,“美學革命”強調每個人發揮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把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救世主”的降臨。并且,它反對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張在日常生活當中不斷革命。但是,“美學革命”將個體精神力量抬得過高。個體是社會中的個體,反抗不能不包含對社會制度的改造,把解放的任務完全壓在個人身上,是不現實的。并且,斯蒂格勒把藝術家和哲學家看得太高,賦予他們的任務太重。他們能領導社會應對資本主義的“藝術危機”和“文化危機”嗎?更重要的是,“美學革命”帶有明顯的精英主義味道,普通大眾很難擺脫體制化的美學調節,更難完成創造性的個體化任務。此時,所謂美學“本能”的恢復容易淪為有關感官、色情和縱欲的虛無主義游戲。最后,“美學革命”將應對危機的挑戰引向個體精神層面的升華和對自我意識組織的調節,否定了社會變革和制度重構的價值,容易滑入保守主義中。
藝術是社會中的藝術。如果一個社會病了,藝術也不能幸免。反之,治療藝術的病也有利于促進社會的整體健康。但是,過于強調藝術的力量,只能讓藝術家背上過于沉重的“十字架”。當然,即便如此,藝術家也應更多地反思自己在技術時代的歷史使命,尤其要警惕被消費主義和消費社會所利用。
注 釋
[1] 貝爾納·斯蒂格勒. 技術與時間:3. 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M].方爾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34.
[2] 20世紀初,美國工程師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一套將科學原理和方法運用于工廠管理中的理論,以提高企業勞動效率,后被稱為科學管理思想,在歐美風行一時。
[3] 同[1],105.
[4] 同[1],1.
[5] 斯蒂格勒.反精神貧困的時代——后消費主義文化中的藝術與藝術教育[Z/OL].[2017-07-31].http://www.pinlue.com/article/2017/07/3120/193790231645.html.
(本文原載于《信睿周報》第36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