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會(huì)議|重訪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的文化運(yùn)動(dòng)與空間政治
二十世紀(jì)的世界,戰(zhàn)爭(zhēng)和革命貫穿始終,在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文化整合、民族認(rèn)同和區(qū)域重構(gòu)等方面,都形成了獨(dú)特的經(jīng)驗(yàn),也帶給我們諸多啟示。文化運(yùn)動(dòng)與空間政治的辯證構(gòu)成了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革命的重要特征。晚清以來(lái)的歷史進(jìn)程中,一系列以往習(xí)焉不察的空間范疇和概念得以彰顯。也是在這一時(shí)段中,文化為舊有的空間賦予了新的政治意涵,各式“邊/中”關(guān)系亦在運(yùn)動(dòng)中被打破、重組乃至于翻轉(zhuǎn)。在不同的歷史時(shí)段中,新的空間范疇又再次誕生出新的政治和文化運(yùn)動(dòng)。在更為宏闊和更具普遍性的維度中,以抵抗帝國(guó)主義、殖民主義及其造成的地區(qū)間不平等地緣結(jié)構(gòu)為視域,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革命當(dāng)可視作一場(chǎng)撬動(dòng)全球資本主義或“十九世紀(jì)”空間秩序的“空間革命”。
長(zhǎng)久以來(lái),我們著迷于資本主義“全球化”而來(lái)的歷史敘述卻不自知,忘記乃至摒棄了我們自己曾經(jīng)通過(guò)一系列文化運(yùn)動(dòng)、政治運(yùn)動(dòng)創(chuàng)造的既具“地方性”同時(shí)又內(nèi)在于“全球網(wǎng)絡(luò)”的空間政治和歷史契機(jī)。因此,對(duì)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化運(yùn)動(dòng)與空間革命”的重訪不僅意味著研究者對(duì)于歷史審判者位置的摒棄,同時(shí)也意味對(duì)于那些一度被遺忘、被無(wú)視的維度的重新激活,以叩問(wèn)我們所身處的當(dāng)下時(shí)空的意義。
基于此,2020年10月17-18日“文化運(yùn)動(dòng)與空間政治”秋季學(xué)期學(xué)術(shù)工坊在清華大學(xué)人文與社會(huì)科學(xué)高等研究所召開(kāi),延續(xù)了清華文科高研所對(duì)“重新思考二十世紀(jì)”這一主題的關(guān)注。本次會(huì)議由熊慶元(揚(yáng)州大學(xué))宋玉(重慶大學(xué))袁先欣(清華大學(xué))三位青年學(xué)者發(fā)起,邀請(qǐng)了北京、上海、廣州、重慶、沈陽(yáng)、廈門(mén)、寧波、延安、泉州、揚(yáng)州等地的30多位文學(xué)、歷史研究者共同參與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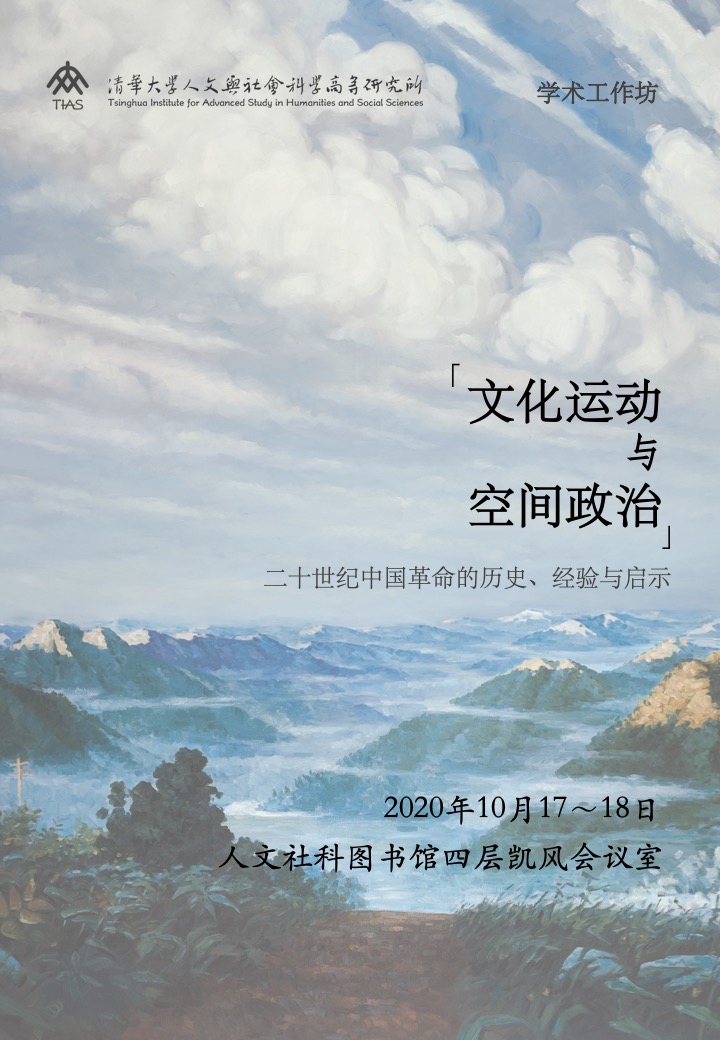
近代文明論及其不滿
會(huì)議的第一場(chǎng)討論題為“近代文明論及其不滿”。本場(chǎng)主要圍繞東亞中日兩國(guó)的近代知識(shí)分子對(duì)各種思想資源的調(diào)用和轉(zhuǎn)化,以應(yīng)對(duì)和調(diào)試不同類(lèi)型的“文明論”范式,這一過(guò)程不僅伴隨著現(xiàn)實(shí)中東亞朝貢貿(mào)易體系空間格局的崩解和轉(zhuǎn)型,也包含了重構(gòu)時(shí)空乃至其背后文明視野的嘗試。
張翔(首都師范大學(xué))在二十世紀(jì)前期東西方文化論戰(zhàn)的視野中展開(kāi)對(duì)近代知識(shí)轉(zhuǎn)型問(wèn)題的討論,他將問(wèn)題置于民族主義和民族國(guó)家興起的背景下,通過(guò)分析康有為、梁?jiǎn)⒊冉R(shí)分子對(duì)西方“文明論”框架的超克,進(jìn)而勾勒了一幅由“文明論”延伸到社會(huì)科學(xué)的歷史圖景。張翔指出,從長(zhǎng)時(shí)段的歷史角度來(lái)看,留給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革命的機(jī)遇窗口其實(shí)是非常短暫的。也正是在時(shí)勢(shì)、知識(shí)、革命的互動(dòng)中,“短二十世紀(jì)”的中國(guó)革命把握住了歷史的契機(jī),進(jìn)而爆發(fā)出強(qiáng)大的政治動(dòng)能。
圍繞琉球?yàn)橹黝}的日本漢詩(shī),孫洛丹(東北師范大學(xué))指出在東亞近代國(guó)家轉(zhuǎn)型中的背景下,詩(shī)歌不僅映射了日本詩(shī)人的琉球想象,同時(shí)還反映了個(gè)人與國(guó)家關(guān)系的重構(gòu)、政治家與漢詩(shī)人身份的重疊、地域秩序變遷與東西方“文學(xué)”觀念的碰撞等諸多問(wèn)題。她指出在“文學(xué)追隨帝國(guó)”的同時(shí),漢詩(shī)以自身的創(chuàng)作改變了帝國(guó)對(duì)于“文學(xué)”的形塑。
陜慶(寧波大學(xué))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shī)》中的“事”作為視點(diǎn),在古代“文/質(zhì)”觀念和梁?jiǎn)⒊⒑m所強(qiáng)調(diào)的“形式/內(nèi)容”的觀念的歷史脈絡(luò)中,通過(guò)具體分析黃遵憲“紀(jì)事”詩(shī)的多維知識(shí)脈絡(luò),顯示出對(duì)于西方文明史學(xué)、日本近代史學(xué)的接受和揚(yáng)棄,反映出黃遵憲獨(dú)特的文明觀。
現(xiàn)代中國(guó)不斷以其復(fù)雜性促使我們反思?xì)v史闡釋的單薄,因此,對(duì)于現(xiàn)代中國(guó)諸多思想、知識(shí)、概念的理解和分析需要放在更加多元的歷史脈絡(luò)中加以重新思考。誠(chéng)如本場(chǎng)評(píng)議人王中忱(清華大學(xué))所指出的那樣,對(duì)這一時(shí)段的知識(shí)、思想、概念的分析需要建立在廣闊的歷史視野和扎實(shí)的個(gè)案分析之上。同時(shí),需要在各種問(wèn)題的“交織”中,在對(duì)“混雜性”的把握中來(lái)理解這一時(shí)期和區(qū)域中文學(xué)和思想的“世界性”。

論壇現(xiàn)場(chǎng)。
三十年代左翼的思想文化政治
會(huì)議的第二場(chǎng)“三十年代左翼的思想文化政治”,三篇報(bào)告主要圍繞1930年代左翼思想文化政治的不同面向展開(kāi),都試圖在具體歷史情境和知識(shí)、思想的聯(lián)動(dòng)和相互關(guān)系中打開(kāi)了對(duì)左翼內(nèi)諸思想的分析。
周展安(上海大學(xué))指出20世紀(jì)中國(guó)革命是一場(chǎng)具有學(xué)理性的革命,他以“大革命”后廣義上的“中國(guó)社會(huì)性質(zhì)問(wèn)題論戰(zhàn)”作為研究對(duì)象,通過(guò)分析論戰(zhàn)內(nèi)部包含的思想和政治動(dòng)能,揭示出社會(huì)性質(zhì)論戰(zhàn)背后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脈絡(luò)及其學(xué)理性,反映出1930年代語(yǔ)境中革命、知識(shí)、思想相互激發(fā)的歷史情境。他指出“中國(guó)社會(huì)性質(zhì)問(wèn)題論戰(zhàn)”不止是“理論”的,也是“現(xiàn)實(shí)”的、“行動(dòng)”的。在論戰(zhàn)中,中共的理論家比起其他諸派更下沉,更具有將“思想”或者“理論”揚(yáng)棄到“現(xiàn)實(shí)”中的行動(dòng)性。這也就是“中國(guó)認(rèn)識(shí)”的一個(gè)極致性的發(fā)展。
伴隨著近年來(lái)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政治性”的重啟,對(duì)左翼文化運(yùn)動(dòng)的研究逐步摒棄了原有的外在的、后設(shè)性的研究思維,而開(kāi)始進(jìn)入對(duì)象內(nèi)部,連接到更為廣闊,也更為復(fù)雜的思想史、社會(huì)史、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等研究脈絡(luò)上。正是在對(duì)歷史內(nèi)在邏輯更為深刻的把握和追問(wèn)中,對(duì)“左翼文學(xué)”的理解也開(kāi)始擺脫本質(zhì)化的思維模式。
齊曉紅(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館)提出要在“關(guān)系”的視野下理解左翼文學(xué),并以文學(xué)的“大眾化”作為研究個(gè)案,在國(guó)共的理論對(duì)子中探討“大眾”背后所分立的“民族”“階級(jí)”話語(yǔ)。在此關(guān)照下,抗戰(zhàn)前夕爆發(fā)“兩個(gè)口號(hào)”的論爭(zhēng)亦可視為左翼內(nèi)部展開(kāi)的“民族”“階級(jí)”話語(yǔ)之間的爭(zhēng)論,對(duì)“大眾”理解的演變恰顯示了左翼理論在歷史動(dòng)態(tài)關(guān)系中的自我調(diào)整。阮蕓妍(重慶大學(xué))針對(duì)“文藝自由論辯”的文學(xué)史敘述提出自己不同看法,提出應(yīng)從“文化斗爭(zhēng)論爭(zhēng)”的視角看待胡秋原的論爭(zhēng)表現(xiàn),她通過(guò)分析胡秋原在論爭(zhēng)中不斷的話語(yǔ)調(diào)整,認(rèn)為胡秋原與左翼展開(kāi)的關(guān)于“文藝自由論辯”不是基于簡(jiǎn)單地對(duì)“黨派性”的拒斥,而是在不斷找尋主體介入現(xiàn)實(shí)革命的路徑中與后者產(chǎn)生的分歧,由此揭示出這場(chǎng)論辯蘊(yùn)含的復(fù)雜思想向路和歷史情境。
在“大革命”失敗的歷史延長(zhǎng)線上,1930年代的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為了探索變革現(xiàn)實(shí)的方向,以各自的努力共同回應(yīng)當(dāng)時(shí)的歷史問(wèn)題,而中國(guó)社會(huì)性質(zhì)論戰(zhàn)、“大眾”問(wèn)題的討論、胡秋原與“文藝自由論辯”等一系列個(gè)案的分析恰以現(xiàn)代文學(xué)為入口,進(jìn)入這一時(shí)期理論論辯、革命實(shí)踐、文學(xué)寫(xiě)作錯(cuò)綜的歷史關(guān)系,把握其中的動(dòng)力機(jī)制與內(nèi)部張力。
人民政治的歷史與文藝實(shí)踐
會(huì)議的第三場(chǎng)“人民政治的歷史與文藝實(shí)踐”,主要圍繞1940年代延安根據(jù)地至建國(guó)初的人民政治及其文藝實(shí)踐開(kāi)討論。三篇論文都以具體的歷史分析為始,最終落在對(duì)“人民政治”和“人民文藝”的理論化概括上,反映了延安根據(jù)地所具備強(qiáng)大的政治和歷史的勢(shì)能。
王悅(延安大學(xué))以梁?jiǎn)⒊墩闻c人民》、李大釗《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zhuān)政》三篇?dú)v史文獻(xiàn)作為線索,通過(guò)對(duì)三篇文獻(xiàn)細(xì)讀及相關(guān)歷史背景的考察來(lái)分析“人民政治”從晚清到共和國(guó)的歷史流變,揭示出由“國(guó)民”“平民”再到“人民”背后政治話語(yǔ)的變遷,凸顯出“人民政治”之于近代中國(guó)獨(dú)特的歷史定位。
吳曉佳(中山大學(xué))通過(guò)與當(dāng)代西方左翼激進(jìn)思潮對(duì)話,將西方左翼激進(jìn)理論中“找尋政治主體”的問(wèn)題推進(jìn)為“如何將政治主體化”的問(wèn)題,并將延安時(shí)期的《文藝戰(zhàn)線》雜志看作中共在塑造新政治主體進(jìn)程中的一個(gè)歷史縮影。通過(guò)對(duì)《文藝戰(zhàn)線》雜志的爬梳,她指出中共民族解放話語(yǔ)背后的超越民族主義的國(guó)際性視野,并以此呈現(xiàn)出延安根據(jù)地“人民政治”不同于西方“政黨政治”的特性。
熊慶元(揚(yáng)州大學(xué))以延安“新秧歌運(yùn)動(dòng)”作為研究對(duì)象,通過(guò)考察其演進(jìn)和變化的層次,揭示出藝術(shù)形態(tài)變化背后所內(nèi)在的社會(huì)、政治與文化的變動(dòng),揭示出戰(zhàn)爭(zhēng)條件下“新秧歌運(yùn)動(dòng)”所生成的新文化政治。
與會(huì)的青年學(xué)者就根據(jù)地文藝所呈現(xiàn)的“流動(dòng)性”與“在地性”,以及“人民”概念在不同歷史條件之中呈現(xiàn)出的變化展開(kāi)了討論。與會(huì)學(xué)者認(rèn)為要在動(dòng)態(tài)的、運(yùn)動(dòng)的過(guò)程中去理解人民政治的意涵。正是由于人民政治及其文藝實(shí)踐所蘊(yùn)含的高度現(xiàn)實(shí)性和能動(dòng)性,才賦予了作為“薄弱環(huán)節(jié)”的根據(jù)地政治以革命性,進(jìn)而翻轉(zhuǎn)了整個(gè)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的政治格局。而這一過(guò)程中產(chǎn)生的文藝的、思想的、政治的實(shí)踐也恰是需要在當(dāng)代不斷被重新思考和追問(wèn)的,誠(chéng)如本場(chǎng)評(píng)議人何吉賢(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所概括的,三篇論文都集中體現(xiàn)了20世紀(jì)戰(zhàn)爭(zhēng)和革命鍛造“人民政治”的艱難過(guò)程。
共和國(guó)文藝的譜系
會(huì)議的第四場(chǎng)“共和國(guó)文藝的譜系”,主要圍繞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建國(guó)后的文藝實(shí)踐展開(kāi),在論域上,本場(chǎng)討論延續(xù)了第三場(chǎng)人民政治和人民文藝的主題,而核心關(guān)切轉(zhuǎn)向了人民政治及其文藝實(shí)踐在革命勝利后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繼續(xù)保持其內(nèi)在的能動(dòng)性的問(wèn)題。
張晴滟(中央戲劇學(xué)院)借用“禮樂(lè)”這一概念來(lái)思考新中國(guó)政治與藝術(shù)之間的關(guān)系,她從“文革”前夕新編歷史劇壓抑革命現(xiàn)代戲的史實(shí)出發(fā),證明“禮樂(lè)革命”的動(dòng)能已經(jīng)耗盡,進(jìn)而揭示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現(xiàn)代戲內(nèi)蘊(yùn)的對(duì)原有“禮樂(lè)”形式進(jìn)行“再政治化”的思想邏輯。
石岸書(shū)(華東師范大學(xué))嘗試從“新群眾運(yùn)動(dòng)”的角度撬動(dòng)既有文學(xué)史以及“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熱潮對(duì)“新時(shí)期文學(xué)”的敘述,強(qiáng)調(diào)1950-1970年代的所遺留的文化館系統(tǒng)與“新時(shí)期文學(xué)”繁榮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從而揭示出“新時(shí)期文學(xué)”中“非支配性動(dòng)員”的特征。他指出從“新群眾運(yùn)動(dòng)”的角度去思考“新時(shí)期文學(xué)”不僅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1980年代與1950-1970年代文學(xué)之間的斷裂、延續(xù)的關(guān)系,同時(shí)還提示著我們社會(huì)主義政治內(nèi)在的復(fù)雜性。
劉巖(對(duì)外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大學(xué))以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三位東北作家小說(shuō)中的沈陽(yáng)敘事為研究對(duì)象,認(rèn)為他們的寫(xiě)作呈現(xiàn)出打破自動(dòng)化書(shū)寫(xiě)、區(qū)域景觀化書(shū)寫(xiě)的契機(jī)和可能,并展望對(duì)世紀(jì)之交的東北經(jīng)驗(yàn)的文學(xué)書(shū)寫(xiě)也將由此起步。
與會(huì)學(xué)者就“將文化館辦成小文聯(lián)”的問(wèn)題和“文化大革命”藝術(shù)實(shí)踐的內(nèi)在矛盾性展開(kāi)了討論。在“新時(shí)期”所建構(gòu)的歷史敘述中,如何評(píng)價(jià)共和國(guó)前三十年的留下的政治、文化、工業(yè)遺產(chǎn)曾是一個(gè)不斷引發(fā)爭(zhēng)論的話題。而在本場(chǎng)討論中,不論是“禮樂(lè)革命”“新群眾運(yùn)動(dòng)”抑或是對(duì)世紀(jì)之交東北經(jīng)驗(yàn)的書(shū)寫(xiě)和研究,無(wú)疑都在提示那些習(xí)焉不查的歷史陳?ài)E與我們所身處的當(dāng)下時(shí)空的關(guān)聯(lián)性,誠(chéng)如本場(chǎng)評(píng)議人毛尖(華東師范大學(xué))所評(píng)價(jià)的那樣三篇論文都富有一種發(fā)現(xiàn)歷史的洞見(jiàn)。
歷史時(shí)空中的多民族邊疆
第二天會(huì)議的第一場(chǎng)“歷史時(shí)空中的多民族邊疆”,主要圍繞不同民族區(qū)域中的文化與政治的互動(dòng)展開(kāi)。長(zhǎng)期以來(lái),我們都在民族、區(qū)域識(shí)別的既成事實(shí)中去理解民族,而對(duì)于其生成的“存在之由,變遷之故”缺乏細(xì)致的把握和分析。袁先欣、宋玉兩位學(xué)者分別從不同的個(gè)案出發(fā),在歷史和政治的變動(dòng)中,對(duì)區(qū)域、民族與文學(xué)之間的各種交互關(guān)系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分析。袁先欣(清華大學(xué))以沈從文1930年代中后期的湘西敘述作為研究對(duì)象,提出要在“民族”“區(qū)域”的動(dòng)態(tài)形成過(guò)程中理解沈從文的湘西書(shū)寫(xiě),她以《湘行散記》《邊城》與芮逸夫、凌純聲《湘西苗族調(diào)查報(bào)告》之間的互文關(guān)系,以及《湘西》《長(zhǎng)河》與苗民“革屯運(yùn)動(dòng)”前后的歷史關(guān)系為抓手,揭示出沈從文“民族”敘述的復(fù)雜性,由此提出要在中國(guó)多元與多重統(tǒng)治的歷史遺產(chǎn)和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的角度去理解族群和民族的問(wèn)題。宋玉(重慶大學(xué))以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作為個(gè)案,提出要擺脫既往研究將“東北”天然視為“邊緣”的視點(diǎn),而應(yīng)從內(nèi)在的“風(fēng)土志”視野乃至歷史地理形成的進(jìn)程中去重新詮釋關(guān)東“草原”,他通過(guò)對(duì)于小說(shuō)中人地關(guān)系的細(xì)讀,揭示出地緣關(guān)系所發(fā)生的變動(dòng)與新政治形成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
新疆自古以來(lái)就是中國(gu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諸多政治、宗教力量的介入以及中央政治所發(fā)生的變動(dòng),使得中國(guó)的西北邊疆一度產(chǎn)生危機(jī),如何正確地看待和解釋近代中國(guó)的歷史與邊疆以及邊緣地帶的革命無(wú)疑是具有挑戰(zhàn)性的。鄭亞捷(華僑大學(xué))以新疆漢族文化促進(jìn)會(huì)為個(gè)案,探討了“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在新疆的傳播和散布基礎(chǔ),通過(guò)對(duì)邊疆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歷史細(xì)節(jié)的考察,展開(kāi)了對(duì)新疆內(nèi)部多元文化脈絡(luò)和歷史變化的認(rèn)識(shí)。王詩(shī)揚(yáng)(清華大學(xué))在各種力量的交錯(cuò)中展開(kāi)對(duì)于日本“回教工作”的分析,通過(guò)對(duì)民族話語(yǔ)的核心構(gòu)造與形成的歷史過(guò)程中的分析,討論國(guó)民政府、中共黨人及回民群體幾方的回應(yīng)與爭(zhēng)論,呈現(xiàn)了20世紀(jì)兩種帝國(guó)主義的民族主義和社會(huì)革命的民族主義之間糾纏對(duì)立的歷史關(guān)系。
在評(píng)議和討論環(huán)節(jié),袁劍(中央民族大學(xué))認(rèn)為四篇論文都沖擊了原有的近代史、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敘述框架,將民族、邊疆的視野帶給近代史和文學(xué)史,幾篇論文都注意到大民族結(jié)構(gòu)的繼承性和小民族結(jié)構(gòu)的創(chuàng)造性的問(wèn)題。姜濤(北京大學(xué))提示引入了“戰(zhàn)時(shí)中國(guó)”這一變量,認(rèn)為要在不斷變動(dòng)的空間視野下,討論各個(gè)不同區(qū)域所發(fā)生的位移和變動(dòng)。賀桂梅(北京大學(xué))指出應(yīng)更加準(zhǔn)確和立體的把握“多元一體”的內(nèi)涵。學(xué)者們認(rèn)為,討論近代的邊疆與民族問(wèn)題既不能離開(kāi)對(duì)于民族、區(qū)域內(nèi)諸問(wèn)題的把握,同時(shí)亦須兼顧與之相關(guān)的世界史以及國(guó)際主義的視野。王詩(shī)揚(yáng)在討論中引用了汪暉《亞洲想象的政治》來(lái)概括近代民族解放、區(qū)域問(wèn)題和國(guó)際主義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國(guó)際主義與其說(shuō)產(chǎn)生于對(duì)于民族認(rèn)同的拒絕或遺忘,毋寧說(shuō)產(chǎn)生于一種將自身民族的解放與其他民族的解放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的政治意識(shí)或政治自覺(jué)。”
太平洋視域中的文化主義與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
第二天會(huì)議的第二場(chǎng)“太平洋視域中的文化主義與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主要是在太平洋東西兩端歷史與文化的共振與互動(dòng)中,展開(kāi)對(duì)于近現(xiàn)代歷史與文學(xué)的理解。
梁展(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提出應(yīng)該在“一戰(zhàn)”以及威爾遜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下,展開(kāi)對(duì)“五四”民族主義的思考,重新檢視“五四”爆發(fā)的歷史契機(jī)。由此,他發(fā)現(xiàn)學(xué)生與北洋政府并非簡(jiǎn)單的對(duì)立,而“五四”啟蒙亦非簡(jiǎn)單模仿西方,而是同時(shí)包含了東西方啟蒙思想的要素。因此“五四”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性的探索亦可視為重構(gòu)當(dāng)下普遍主義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
熊鷹(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以戰(zhàn)后冰心的文化實(shí)踐作為研究對(duì)象,分析冰心“五四”時(shí)期的文學(xué)立場(chǎng)如何在二戰(zhàn)后的跨文化語(yǔ)境中發(fā)展為一種涵蓋“國(guó)民性”、文化人類(lèi)學(xué)傳統(tǒng)、第三世界民族國(guó)家話語(yǔ)的“文化主義”,而這一“文化主義”為第三世界文化民主主義圖景的重繪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邱士杰(廈門(mén)大學(xué))從劉進(jìn)慶《戰(zhàn)后臺(tái)灣經(jīng)濟(jì)分析》原稿入手去剖析劉進(jìn)慶的唯物史觀,在與“臺(tái)獨(dú)”派論辯以及對(duì)于戰(zhàn)后臺(tái)灣各種思想脈絡(luò)的清晰把握中,展示了對(duì)劉進(jìn)慶的“復(fù)合社會(huì)論”“半封建社會(huì)論”當(dāng)中如何包含著一種新的臺(tái)灣地區(qū)現(xiàn)代史的論述方式。
魏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通過(guò)對(duì)“亞細(xì)亞生產(chǎn)方式”在新德里、武漢、墨西哥城理論共振的細(xì)密分析,揭示出“亞細(xì)亞生產(chǎn)方式”在各種歷史語(yǔ)境所呈現(xiàn)出的不同理論特質(zhì),而這一理論在不同區(qū)域與不同時(shí)段呈現(xiàn)出的理論意涵恰提示我們要重審全球資本主義與本土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特殊結(jié)合方式。
本場(chǎng)評(píng)議人賀桂梅(北京大學(xué))認(rèn)為四篇論文都體現(xiàn)了以太平洋為中心所形成的國(guó)際關(guān)系的互動(dòng),并且都是在互動(dòng)關(guān)系中、在唯物的基礎(chǔ)上去理解文化的。在討論環(huán)節(jié)中,與會(huì)者就“一戰(zhàn)”與“十月革命”、俄德革命的雙重視野中的“五四”以及“連帶發(fā)展理論”進(jìn)行了討論。正是在更為宏闊的歷史視野下,對(duì)中國(guó)問(wèn)題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問(wèn)題本身。而是在“全球性”的連動(dòng)關(guān)系下看待被卷入“全球化”進(jìn)程中的近代中國(guó),同時(shí),也是將“全球”納入我們自身的問(wèn)題脈絡(luò)去重新思考和表述我們自身。
本次工作坊的兩場(chǎng)圓桌討論圍繞“民族邊疆與薄弱環(huán)節(jié)”“人民政治與全球視野”展開(kāi),與會(huì)者們就之前論文所呈現(xiàn)出的問(wèn)題意識(shí)、研究視角進(jìn)行了更加深入了討論,使本次工作坊的論域和思考得以進(jìn)一步延展。
民族邊疆與薄弱環(huán)節(jié)
在圓桌討論的第一場(chǎng),宋玉作為引言人對(duì)于本次會(huì)議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空間政治與文化運(yùn)動(dòng)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進(jìn)行了概括和總結(jié),認(rèn)為參會(huì)論文不僅很好地體現(xiàn)了會(huì)議的主旨,同時(shí)也打開(kāi)了更多思考和理解問(wèn)題的空間。王中忱提出要充分把握邊疆地帶的豐富性和前沿性,并以《烏蘭夫回憶錄》為例,說(shuō)明“民族”和“階級(jí)”協(xié)調(diào)為一的“人民政治主體”并不是一個(gè)自明的或凝固不變的存在,而是一個(gè)有待探索和構(gòu)想的問(wèn)題。袁劍呼吁要在“舊大陸的新形勢(shì)”的視角下進(jìn)一步關(guān)照民族和邊疆問(wèn)題,并且要有意識(shí)將對(duì)此問(wèn)題的關(guān)照與主流議題相關(guān)聯(lián),同時(shí)要確立對(duì)邊疆間關(guān)系的結(jié)構(gòu)性理解。張翔從語(yǔ)言傳播的角度,討論了西南和東南地區(qū)語(yǔ)言接觸現(xiàn)象。王悅、袁先欣就內(nèi)地乃至中心地區(qū)呈現(xiàn)出的某種“邊疆性”展開(kāi)了交流。
人民政治與全球視野
在圓桌討論的第二場(chǎng),熊慶元認(rèn)為“人民政治”乃是20世紀(jì)產(chǎn)生的,對(duì)19世紀(jì)“政黨政治”的具有超越性的概念,提出要進(jìn)一步理解“政黨”這種政治的形式和中國(guó)社會(huì)的改造、中國(guó)革命的關(guān)系,同時(shí)也要對(duì)實(shí)踐過(guò)程中產(chǎn)生的中央與地方、人民和國(guó)家的關(guān)系進(jìn)行進(jìn)一步討論。賀桂梅認(rèn)為“人民政治”是一個(gè)在全球視野中展開(kāi)的,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政治,提出要?jiǎng)討B(tài)地理解“人民政治”的內(nèi)涵,并與資本主義的“大眾政治”加以區(qū)分。邱士杰提出要去思考“人民政治”在當(dāng)代東亞場(chǎng)域中進(jìn)行連帶的可能性。季劍青認(rèn)為要在文化運(yùn)動(dòng)層面上思考“民族”“國(guó)際”之間的關(guān)系,并以美國(guó)黑人詩(shī)人修斯與魯迅的會(huì)面為例,討論世界左翼運(yùn)動(dòng)之間的互動(dòng)和共振關(guān)系,正是在國(guó)際主義的網(wǎng)絡(luò)內(nèi),跨國(guó)的文化運(yùn)動(dòng)才得以生成。周展安認(rèn)為不僅要在實(shí)體空間,也要在抽象的空間范疇,在“薄弱環(huán)節(jié)”與政黨、戰(zhàn)爭(zhēng)的關(guān)聯(lián)中理解中國(guó)革命。在討論中學(xué)者們認(rèn)為:20世紀(jì)既是創(chuàng)造新空間的過(guò)程,也是建立新邊界的過(guò)程。不同的空間視野對(duì)應(yīng)了不同的政治議程。因此,需要在更為具體的、更加動(dòng)態(tài)的過(guò)程中去思考、理解包括“人民政治”“空間政治”在內(nèi)的一系列范疇和議題。
工作坊的最后,清華大學(xué)人文與社會(huì)科學(xué)高等研究所所長(zhǎng)汪暉教授肯定了與會(huì)學(xué)者所作出的努力和對(duì)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的關(guān)切,他提示大家:當(dāng)20世紀(jì)中的一些形態(tài)、范疇、概念在今天已經(jīng)成為歷史的情況下,要去思考和表述這些歷史經(jīng)驗(yàn)及其與當(dāng)代世界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汪暉教授希望類(lèi)似的討論和工作坊能夠持續(xù)地舉辦,清華大學(xué)人文與社會(huì)科學(xué)高等研究所也將為此提供相應(yīng)的支持。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