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對話】楊福泉:一位納西族人類學者的學術心史(下)
?楊福泉,納西族、云南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民族史博士,云南大學民族學博士生導師、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西南民族學會副會長、云南納西學研究會會長。入選“中國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獲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出版有《東巴教通論》《納西族與藏族歷史關系研究》《灶神研究》等33 部個人專著;主持過5項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曾應邀到德國、美國、英國、法國、瑞典、瑞士、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埃及等國講學訪問。
采訪者:徐杰舜,廣西民族大學教授。
《納西族與藏族的歷史關系研究》
徐杰舜: 我現在要討論您的第二本代表作《納西族與藏族的歷史關系研究》,此書是40多萬字的大作。尤中、李紹明、王堯先生等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請您對此書做簡要介紹。
楊福泉: 過去研究漢族與少數民族關系的論著相對比較多,而且多偏向于研究蒙藏、漢藏、漢蒙等大的民族。對西南少數民族之間關系的研究少,我因此選擇了納西族和藏族的關系進行研究。這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個原因則基于歷史上納西族藏族歷史關系的豐富多彩。明朝的時候,由于明廷將麗江視為“西北藩籬”防范吐蕃,木氏土司又積極擴展統治領域,因此戰事比較頻繁。兩個民族在數百年中相互打了很多的仗。但是納藏兩個民族卻沒有因此成為世仇,而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長期保持了密切的聯系,麗江成為納藏貿易和藏傳佛教噶舉派的重地。近期中央電視臺一頻道和八頻道都熱播的《木府風云》,其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反映了民族之間如何化解歷史上的仇恨和矛盾。歷史上,木氏土司很尊重藏族的風俗,花大量的錢幫助藏族建蓋寺廟。著名的四川理塘大寺就是麗江木土司出錢建造的,還請了三世達賴來開光。明代好幾個重要的藏傳佛教噶舉派活佛包括噶瑪巴(大寶法王) 都與麗江和木氏土司關系密切。噶瑪巴十世卻英多杰因為清初格魯派和噶舉派教派之爭而避難麗江,在麗江生活了33年。今年在紐約召開了一個研究噶瑪巴十世的專題國際會議。原來還擬舉辦一個噶瑪巴十世留在麗江的一批唐卡畫展覽。麗江在明清時期是噶舉派的重地,木氏土司是噶舉派的忠實信徒。噶瑪巴十世在麗江弘揚噶瑪噶舉教派。滇西北十三大寺都是噶舉派的。
木氏土司還主持在麗江印制了藏區第一套卷帙浩繁的大藏經“甘珠爾”,現藏于大昭寺,是該寺的鎮寺之寶。這套大藏經曾輾轉收藏在理塘寺,因此稱為“麗江理塘版大藏經”。納西族和藏族商人在商貿交流方面也源遠流長,非常默契。藏商一般到了麗江就不再往前走了,因為他們在語言和生活習俗等方面都不太適應與漢地商人直接經商,所以他們多把物資在麗江委托給當地的納西族商人出售,并為他們買回需要的茶葉等貨物。麗江既是茶馬古道上貨物的重要起點站,同時也是個終點站。麗江古城納西人和藏商還形成了很有特點的“房東貿易”,雙方建立了良好的誠信關系,即使有些貨物一時滯銷,納西房東也最終會將貨款如數給藏商。因為納西人認為藏人直爽坦誠,因此,麗江束河的納西族還常常請藏族人為他們管理村子的山林。我在這本書中旁征博引,引用了大量漢藏文獻和外文資料,研究了納藏兩族歷史上的政治、宗教、文化和商貿等諸多方面的交往,還把我多年田野調查所得的第一手資料與文獻有機融合,其中有不少我在納西族地區和藏族地區調研的個案。就滇川藏毗鄰地區而言,我們還可以深入研究很多民族和族群之間的歷史關系。這里不乏很多對當前建構和諧民族關系可以借鑒的歷史智慧。目前藏學界對這本書的評價也比較高。
徐杰舜: 民族之間打仗卻沒有結為世仇的原因是什么?
楊福泉: 因為雙方在打仗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停止過文化、宗教和商貿的交流。木氏土司移民到如今的迪慶和四川的巴塘理塘等藏族聚居地,但并沒有把原住藏民都趕走。大家住在一起,慢慢地互相適應、互相學習。木氏土司把水利技術和各種種植技術輸入藏區,建造寺廟,互相通婚。一個民族在戰后通過尊重對方的文化和信仰,通過加強有利民生的經濟交往,逐漸化解了戰爭的創傷。納西族東巴圣典中的《創世紀》中說: 納西族、藏族和白族是一對祖先育出的三兄弟,就是這種友好關系的最好的說明。我們需要尋找歷史的經驗和積累的智慧來研究當前的民族問題。這也是我這本書中的大量篇幅所透露出的歷史信息。

在西藏芒康縣鹽井鄉訪問當地老人。(2002年)
徐杰舜: 戰爭的交往是不是使得雙方的交往更深入?
楊福泉: 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因為戰爭導致的移民等使兩個民族的交往加深了,民族在遷徙過程中有摩擦又有交流,交流的形式有和平的形式,也有沖突的形式。在磨合和相互溝通的過程中,戰爭與摩擦會越來越少,大家都生活在一塊土地上,各方面都有密切的相互交流,于是也逐漸形成了在宗教信仰、文化交流和商貿交流方面互動互補、相互包容的局面。比如這本書中提到一個典型的例子: 作為大東巴的父親和作為寧瑪派活佛的兒子各自信奉自己的宗教,但在宗教祭祀上有殺生觀念方面的沖突,東巴認為祭神驅鬼,要用祭牲才會靈驗,但是兒子認為不應殺生。后來父親在儀式中的殺生慢慢減少了。滇西北的納西族與藏族都有相互請對方的宗教專家舉行特定儀式的習俗,東巴和藏傳佛教僧人各司其職做儀式,這是相互尊重對方的信仰與文化的結果。
徐杰舜: 宗教對精神方面的影響可以定民心,是吧?
楊福泉: 明朝時納西族與藏族之間的戰爭比較多,清代以后,兩族之間在宗教、文化和商貿交流方面加深。各地藏民每年朝拜佛教圣地雞足山,首先要去麗江的文筆山上“借鑰匙”(相傳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摩訶迦葉尊者把鑰匙留在這里了,因此要借鑰匙) 才能打開雞足山之門。藏民要一路化緣來到麗江,麗江納西人都會給藏民朝山者好的食品。
納藏兩族民眾之間的通婚比較普遍,兩族聚居一地的也比較多。兩族相互之間非常信賴。我聽有的馬鍋頭講過,過去納西跑茶馬古道的趕馬人沿途去藏族寺廟中借錢糧等物,僧人二話不說就會借給你,我的書中也記錄了不少類似佳話。
徐杰舜: 藏族和納西族在經濟上應該是有緊密聯系?
楊福泉: 各種納西地區和藏區的土特產之間的交流互補,各種工藝和農業技術的交流、飲食的交流等,宗教人士也借助茶馬古道做交流,僧人進藏學經朝圣和茶馬古道上的商人一起走比較安全,因此常常結伴而行。
徐杰舜: 您的研究的現代價值可能在思考當代我們和日本、美國之間的關系時會凸顯出來。
楊福泉: 我現在在思考為什么云南的藏區能保持穩定發展? 云南的藏區在長期的歷史交往中,和多民族有交流交往的穩定基礎,現在政府各級部門采取了各種有效措施固然也很重要,但這種和諧局面也得益于過去歷史上各民族長期交往形成的格局。這個對政府的施政應該有啟示性。
國際合作交流概述
徐杰舜: 您的研究之所以水平高,是因為您是一個真正的人類的學者,而不單純是某一個民族的學者。當然這個也與您的求學經歷有關。
楊福泉:1983—1988年我先后兩次在德國訪學了4年,其間不僅把英語練成能用來一起做研究,還一起完成了“德國亞洲研究文叢”第七種《納西研究》系列著作4種。
雅納特教授原來是梵文專家,他在1962年開始對東巴經典感興趣。意大利羅馬東方學研究所的所長圖齊(G.Tucci) 是國際上的藏學權威,他意識到洛克所做的東巴文獻的研究的價值,他對洛克的納西文化研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在為他的論著所寫的序言中多次稱洛克為“偉大的學者”。他認為納西文化在宗教學、民族學的研究中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20世紀60年代初,聯邦德國國家圖書館動議購集已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的東巴經。在阿登納總理的支持下,以昂貴的價格把洛克原先贈送給意大利羅馬東方學研究所的500多冊東巴經悉數買回。當時,該研究所急欲出版洛克的《納西—英語百科詞典》兩大卷,但苦于資金短缺,只好忍痛割愛,賣出經書籌資。聯邦德國國家圖書館隨后又從洛克那里得到他個人收藏的1700多冊東巴經原本及照相復制本。1962年1月,洛克應邀赴聯邦德國講學和編撰東巴經目錄及經書內容提要。雅納特博士協助洛克從事編撰工作。至1962年10月,編訂和描述了527本西德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東巴經,編撰成《德國東方手稿目錄》第七套第一部《納西手寫本目錄》一、二卷。編撰工作尚未完成,洛克不幸于1962 年12 月在夏威夷度假期間去世。雅納特繼續進行西德所藏東巴經的編目工作,完成了《納西手寫本目錄》三、四、五卷。
德國人在他們的經濟處于非常困難時期的20世紀60年代初就由總理親自支持以巨資購買東巴經收藏在國家圖書館,反映出德國人一種文化上的世界眼光,珍視世界上的歷史文化遺產。德國學者常常和我談起,像東巴經這樣珍貴的文獻,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創造的,都是人類的瑰寶。
我在德國是做合作研究,因忙于工作,沒能讀學位。后來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進行過3個月的博士后研究。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參加的國際合作交流項目比較多,先后和美國、加拿大等國學者進行過關于麗江玉龍雪山農村發展和生態保護的合作研究,關于抗日戰爭期間聞名遐邇的中國“工合”(工業合作社) 的歷史和在新形勢下重建農村合作社的研究; 關于藏族和納西族問候語的研究等等。從1999年以來的幾年間,我參加云南省政府和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TNC) 合作的“滇西北保護與發展行動計劃(含國家大河流域公園)”,作為麗江地區的課題組組長,和同事們先后調研了近20個納西族和彝族的村落。其間我還擔任了兩年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云南項目的文化顧問,與國外學者展開廣泛的交流。記錄了這期間我所做工作的研究成果《策劃麗江》《云南玉龍山區域農村發展和生態保護調研》《云南藏族納西族的問候語研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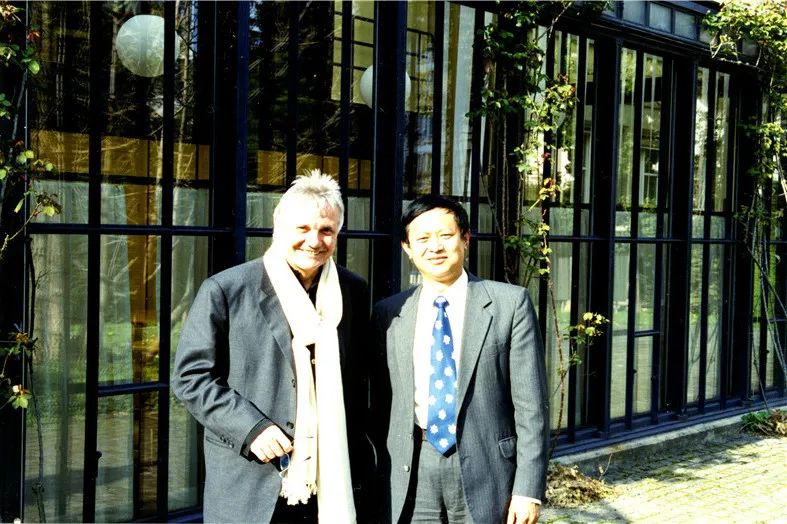
應邀赴瑞士蘇黎世大學民族志博物館講學時與館長、德國人類學家歐皮茨(Oppitz M)合影。(1998年)
我在20多年來的國際學術交流中也開闊了自己的學術視野,汲取了不少國外同行的治學方法和經驗。1995年至1996年,我獲得聯合國大學博士后研究基金,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U.C.Davis) 分校研究訪問; 多年來,我先后應邀到瑞士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方語言學系、瑞典國立遠東文物博物館、瑞典“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亞洲部、德國斯圖加特巴德·伯爾科學院、瑞典倫德大學、亞洲理工學院、加拿大西門大學、美國多個大學進行學術交流。還曾經到加拿大卑斯省的印第安人社區進行學術考察。2003年在美國惠特曼學院的首次“亞洲文化教育年”期間,為美國學生開設了半年的“中國西南的民族性與現代化”(Ethnicity and Modernity of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中國納西族的文化藝術》(The Culture and Art of Naxi People of China)等課程,受到美國學生的好評。其間還與該校人類學系主任孟徹理(Chas Mckhann) 教授合作出版了一本《圖像及其變化——東巴藝術中的再想象》[Icon and Transformation:(Re)Imaginings in Dongha Art ]。
我覺得我們治學,了解國外學術界的研究狀況和成果很重要,所以,我還花了很大功夫,翻譯了一些國外納西學論著,主持審校和重譯(部分)了美籍奧地利學者洛克博士研究納西族的重要代表作《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由于此書很多正文和注釋需要核對大量漢、藏、納西文獻以及外文資料,還對不少植物學詞匯進行重譯,因此,審校這本書所花費的功夫是相當大的。近年來,我還組織翻譯了當代國外納西學名著《納西、麼些(摩梭)民族志》(Naxi and Moso Ethnography )。
從我的研究而言,對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變遷和文化沖突的深入研究成果是研究納西族殉情習俗的三本著作,最早的一本是《神奇的殉情》,此書1994年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后來也在臺灣出版了。2000年在深圳出版了一本《殉情》,列入“人類學田野”叢書; 一本就是2008年出版的《玉龍情殤—納西族的殉情研究》,列入尹紹亭先生等主編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系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這本書入選了“2014書香中國”“300位名人名家推薦300本好書”)。
我在此書中增加了很多田野調查資料,增強了理論分析。我關于殉情研究的書的有關章節也在國外出版了英文版。這本著作分析了主要由政治制度和文化變遷引發的納西族的殉情悲劇,這是一本研究特定時代和社會背景下的殉情這一社會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歷史人類學的著作。這本書基于大量案例主要提出的觀點是: 當主體民族(清代時) 以一種大文化沙文主義的眼光來看待邊地文化、少數民族文化時,邊地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就被認為是野蠻鄙陋的文化,要加以“文明的改造”,結果就導致了社會矛盾的大沖突。麗江在1723年改土歸流之前,納西人的戀愛是相對比較自由的,不少地方即使未婚懷孕、有私生子也不會被社會蔑視。但是到了清代,極端異化的儒家三綱五常被強制地實施。按清代的法規,當時藏族如實施天葬就要被凌遲處死,非常嚴厲。納西人的火葬習俗也被認為是陋俗而強行制止,按納西人的生死觀,不火葬,靈魂可是回不了祖先之地,這是很可怕的事。因此納西族抗爭了100多年,才在一些接受了漢學教育的納西文人帶頭下慢慢接受了土葬。現在政府又號召要火葬,接受土葬習俗幾百年的不少納西老人又想不開了。在昆明的一些老人特別害怕待在昆明,說擔心自己被火葬,老了以后還想著趕緊逃回麗江葬在祖墳上。從這個實例中可以看出,一個民族的習俗可以因為一種強力的文化沙文主義的壓迫和政治改造而被徹底異化。
1723年“改土歸流”后,各種壓制婦女身心的制度也實施到了麗江納西族中。這些外來觀念和本土習俗雜糅成以一種“婚前戀愛自由,結婚則不自由”的習俗。青年男女在婚前的戀愛是自由的,這是沿襲的傳統習俗,而婚姻則要完全聽父母之命。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加上對婦女的各種限制,比如清代還有各種限制婦女參加元宵、燈會等的限制。很多婦女就覺得這世道太難了,這些社會因素加上納西人的宗教信仰因素,比如基于“祖先之地”信仰的“山中靈界信仰”,產生了一個俗稱“玉龍第三國”(舞路游翠郭) 的山中靈界,那是殉情者的世外樂園。殉情者相信他們殉情后可以去到那里,在那里可以騎著老虎到處跑,有白鹿來為他們耕田,雉雞為他們啼鳴; 他們可以用彩霞來織衣服; 這里的人不會老,青春常在等。社會因素和信仰因素一綜合,于是就有了殉情的誘導因素,納西人中就產生了大量的殉情悲劇。麗江曾被稱為殉情之都。殉情者自殺前要濃妝盛服、歌舞唱酬,要選一個能見到玉龍雪山的風景優美之處殉情。在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殉情》一書用了田野實錄和文學化的寫法,有較強的可讀性。
此外,我還出版了《納西族文化史論》(此書獲“第十一屆云南圖書獎”二等獎)、《納西文明》[此書教育部推薦為《歷史》(高一年級第一學期)教學參考書]等10多部納西學研究專著。

在云南瀘沽湖邊采訪正在舉行東巴教儀式的老東巴。(2000年)
應用性研究及其他
徐杰舜: 您是哪一年博士畢業? 哪一年結婚的?
楊福泉: 我是1999年博士畢業并獲得博士學位的,當時我已經是研究員,并入選了“中國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層次。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多學些知識,特別是我功底比較薄弱的歷史學應該惡補一下,就在職讀了博士。我是1983年出國以前結婚的,回來時我的女兒已經有兩歲了。我愛人也和我出去了一段時間。我回國時預料女兒會認生,所以在德國買了一個臺灣制造的粉紅色的電動玩具小豬,動起來會叫,還會惟妙惟肖地用鼻子拱人。呵呵,果然女兒乍見到我,有些怯怯的,不肯喊爸爸,給了她粉紅色的小豬,一動一叫,小孩可高興了,也開始喊我爸爸。我愛人家是漢族,是從麗江鄰縣永勝在20世紀移民到麗江古城的。他們家在家里是父母講永勝漢話,而兄弟姐妹之間則說納西話。我妻子精通納西語,她講話的納西口音比我還重呢。她可以說是最后一代在麗江古城被納西人同化的漢族吧。現在的麗江特別是像古城這樣的區域,則又面臨著納西人要被逐漸漢化的趨勢。我們夫婦在昆明常常和女兒說納西話,并要求我的女兒和她祖母通電話只講納西話,因為我母親聽到納西話會很高興的。所以,我女兒是當下在昆明長大的納西年輕人中還能講納西話的少數人了。她會講納西話,而她的普通話比我標準,英語也不錯。這證明年輕人學習多種語言并不相互沖突,反倒對思維和學習語言有好處。我寫的《古王國的望族后裔》這本書中,就講了不少我這個納漢合璧的家庭的不少故事。也算是一個民族融合的家庭的案例吧。我個人認為民族是個文化的概念,不適合用基因等來論證。
徐杰舜: 民族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在中國通過民族識別出來的56個民族,又被賦予了政治性。
楊福泉: 從人類學的角度看,民族的融合與分化在隨著社會的變遷而產生變化。我在藏區看到,因為藏區有對藏族的優惠政策,一些納西族逐漸傾向于報自己是藏族。而在麗江,也有因為麗江和納西族當代的文化名聲和經濟上的發展,填報自己為納西族的年青人也在增加,特別是那些父母一方是納西族的。一方面,很多納西人在致力于推動傳統文化包括母語傳承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已經日漸生疏了母語等自己的文化。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學者,我現在思考得較多的是少數民族如何在繼承優良傳統的繼承上,也廣泛學習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基于母語文化的繼承和弘揚上再創當代的文化。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是流動的,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應該增加原創的內容。但關鍵是要保留自己文化的個性特點,保持自己的魅力,不應隨波逐流地在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被徹底同化了。
徐杰舜: 除了上述很多學術研究,看來您還在應用性研究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楊福泉: 是的,除了學術研究,我看重自己作為一個民族學者與社區民眾之間的那種血肉相連的情感維系和學者對社區民眾的道義、良知和責任感;看重作為一個民族學者對社區民眾的“回報”情結。因此,除了致力于民族文化基礎理論的研究,我也積極參與關于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現實問題的研究,盡己所能為當地社區民眾辦實事。多年來致力于推動各種國際合作的社區發展研究,長期在邊遠貧困地區做田野調查,與當地老百姓同吃同住,與國內外同事一起促成了麗江納西族農村的一些合作經濟實體。爭取國際資金進行少數民族文化傳人培養和鄉土知識技能培訓、在鄉村小學里進行參與式的鄉土知識教育等方面的項目; 完成了“麗江納西族民間文化傳人培養的實踐和研究”“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白沙鄉白沙完小鄉土知識教育的實踐”“少數民族婦女傳統手工藝的培訓”、扶助少數民族貧困學生在麗江民族中學讀書等項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社會影響。

與何耀華老師一行在迪慶州調研途中。(1997年)
徐杰舜: 納西學是您的學術重心,除此之外,您在哪些方面的研究還下功夫較多?
楊福泉: 除了納西學,我還從事其他方面的專題研究。我的民俗學專著《灶與灶神》,是對中國的灶神信仰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全面研究的一本專著,在學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好評,很快重印,1996年在臺灣漢揚出版社出版,2000年在臺灣云龍出版社出版。2020年將會在學苑出版社出版修訂版。
我主筆的《火塘文化錄》是《灶神研究》的姐妹篇,此書從民俗、社會結構、宗教信仰等方面首次對過去無人論及的中國少數民族豐富多彩的火塘文化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論析,應該算是一本以小見大的拓荒創新之作。《中國社會科學》曾發表了對該書的書評。由于此書受到學術界的廣泛好評,曾兩次重印,并于2000年再版。該書還在1999年被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譯成英文。此專題系列論文之一《論火神》被《新華文摘》轉載,并入選由中國科學院編的《中國八五科學技術優秀成果選》(1990—1995) 一書中;該文亦獲云南省人民政府頒發的1993—1995年度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此外,我還出版了一些田野紀實類的圖文長卷散文,比如《尋找祖先的靈魂》, 先在臺灣出版,后來在民族出版社又出了大陸版;還有《西行茶馬古道》,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靈境麗江》,有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版、上海故事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版,《楊福泉作品選集》,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老照片學術畫冊《遠去的背影——云南民族記憶1949—2009》入選“首屆向全國推薦百種優秀民族圖書”,這本書雖然很貴,但早就賣完了。不少國外學者向我打聽,問這個書會不會出英文版。現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委托我來組織把它翻譯成英文,我正在籌劃中。這本書設計很有水平,書里的很多照片拍攝于20世紀50—70年代,這期間反映中國少數民族狀況的照片在國外很少。照片很清晰,并且按照民族分成一組一組的。從這個書可以看出來,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和政府派出的民族工作隊的工作做得很細,里面有很多難忘的歷史場景,此書有圖有真相,很有歷史資料價值。
我在編輯的時候,要求撰稿者盡量把圖說做得細一些,這樣信息量也就比較大,能了解到照片后面的很多背景內容。
徐杰舜: 謝謝您接受采訪,非常感謝!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