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關于養孩子,丁克群體怎么想?
原創 AI財經社作者 AI財經社
撰文 / 董雨晴
“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似乎是深刻的印入了一些人的骨髓。
楊麗萍在微博發個生活視頻,就有網友在底下評論:一個女人最大的失敗就是沒有一個兒女。新聞聯播昔日主持人張宏民獨自一人在街邊吃雪糕,網友必然要去群嘲無兒無女的落魄。

看楊麗萍微博下的留言,人們對于丁克的態度是異常割裂和沖撞的:一方認為丁克是自私的,他們沒有考慮家族繼承問題;另一方的觀點是學區房、升學教育問題讓人頭疼,“沒有孩子的我除了40歲也擁有少女的身材,更重要的是我想去哪就去哪,丁克無錯。”
無論哪種觀點,不可否認的是,70、80一代作為中國最早一批丁克群體,如今也已到了不惑與天命之年,丁克族如何養老的人生命題被不斷推到他們眼前。
我們為此和3位丁克一族聊了聊,他們中有人因為父母離婚產生陰影而選擇丁克,有人為了事業而選擇不要小孩。但細究他們對于做丁克這件事的態度,給出的答案卻是相似的,“從不后悔,且不擔心養老問題。”
劉雅,北京土著,80后,婚齡10年
因父母離婚陰影“丁克” 準備“拼團”養老
劉雅雖然年近40,但干練的短發,簡單的白T,再加一個運動款背包,讓人猜不出她的真實年齡。
舉手投足間,你甚至會有她還是一個孩子的錯覺。
劉雅做丁克的想法,幾乎貫穿了她的青少年時光。在結婚之后,碰到了一位尊重她意愿的先生,這個想法終于徹底落實。“當時我先生還覺得女生到一定歲數會喜歡孩子的”。劉雅偶爾會覺得對不起先生,“他其實是喜歡小孩的,也想過我會不會有觀念的轉變”,但現實情況是,劉雅一直到今天,都在堅定的表達,她不想要小孩。
對劉雅而言,做決定不是最難的。難的是在漫長的歲月里,總是有人在不斷提醒她,作為女人,她應該要個孩子。這種提醒潛移默化,從爺爺奶奶到父母姑姑。
“我覺得選擇要不要孩子這事取決于你的耳根子夠不夠軟,因為家長會擔心你老了之后能不能養老,他們會不斷的去提醒你,要孩子才是安全的。”
實際上,劉雅最后告訴我們,父母的做法只會起到反面效果。她不想要小孩的最核心原因,就是不希望孩子出生后要去平衡家庭關系,“我不想讓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背著這個重任,成為平衡家庭關系的籌碼。”
劉雅是北京土著,從學習到工作,多年來只扎根在北京,土生土長的北京孩子活動面積十分有限。劉雅有時候挺羨慕同事,離家在外,各個小家庭間也非常獨立,能碰到面的機會就是春節。
但劉雅的親戚圈,甚至沒能超過只有50平方千米的北京市西城區。“關系太緊密了,我跟我姑、叔叔什么的住的都很近”,而在與親戚走動的過程中,劉雅能感覺到,長輩們一直在向自己灌輸一種觀念:你是晚輩,你得服從我,服從家里人的意見。
過重的家庭觀念,對孩子而言就像一道枷鎖。
有一段時間,劉雅工作壓力非常大,回到家她只想緘口休息。“我已經沒有任何情緒回到家庭去演一個孝順開心的孩子了。”
在劉雅的印象中,八零后一代習慣于跟爸媽報喜不報憂,單位、公司事情再多,也絕不跟父母傾訴。“但我們卻處在一個特別典型的習慣于制造復雜關系的社會。許多家庭的利益關系會互相牽扯,孩子也不可避免要站隊。”
“我的爸爸結婚兩次,從小生長在一個特別復雜的家庭關系里,我不喜歡他們,也不在乎他組建什么樣的新家庭,就干脆無視”,說起這句話時,劉雅特別坦然。
讓劉雅壓力最大的人是她的姑姑。幾年前姑姑失獨,對劉雅的關心呈指數級上升。相比之下,這種關心甚至超過了劉雅的父母。
劉雅的爸爸也有無數次機會希望改善家庭關系,她經常向劉雅表露想法,“我覺得咱倆不親,不夠近”。但這種洽談沒辦法改變劉雅的觀念。現在,她把盡孝當作是例行公事,不帶任何感情。
長年累月的負面情感積攢,讓劉雅越來越害怕養一個孩子,“不確定這種不可逆的結果會走向成什么樣,所以我堅決的不要。”如今,平均每三個月,劉雅會和丈夫進行一次深入溝通,話題圍繞要不要孩子展開。但現在,劉雅在對于要不要孩子的問題上,越來越不想留后路。
“狡兔有三窟,工作上、職場上大家都會想一想,留個后路”,但劉雅說,丁克是個原則性認知,不想給自己留任何后路,包括凍卵技術,她壓根不想嘗試。

對于養老問題,劉雅和身邊人交流的特別多,“有沒有孩子都是抱團取暖,我們現在決定一塊去養老院是最好的”;與此同時劉雅也在北京周邊已經在河北購買聯排別墅,想著一旦退休就和丁克朋友一起拼團就住到那邊。
把錢all in 進服務業,也能活的很好,這是劉雅的觀念。
李民,科技行業從業者, 70后,婚齡15年
“曾設想要孩子,學區房、升學壓力打醒了我”
和劉雅不同的是,關于要不要孩子這事,李民一直挺搖擺。剛結婚的時候沒想清楚,李民就決定“等等看”。近幾年,隨著身邊同齡人的孩子都開始面臨小學、中學競爭壓力時,李民突然有點想明白了。
去年,李民看了一部黎巴嫩的電影《何以為家》,片中主角贊恩的處境讓他動容。這部電影也在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如果處于赤貧生存狀態的父母,無法給孩子提供成長過程中必要的物質要素和教育環境,那么父母是否應該生下孩子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李民口中是“不應該”。當然,李民的家庭狀況很好。老家在河北,畢業后李民就來北京打拼。四十幾歲的年紀在北京已經有車有房。幾年前,他把父母從老家接到了北京安置。現在,正是李民收入最穩定的時期。
但作為一個天生的悲觀主義者,李民時常感到焦慮。特別是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現在社會上講的太多的就是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恨不得從幼兒園開始就要拼爹拼媽”。
李民朋友的一段真實經歷讓他挺觸動。最初,李民推崇讓孩子自由成長的理念,他常勸朋友不要給孩子報太多補習班、課外興趣班等等。一開始朋友的孩子過得還好,但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從三四年級開始,孩子的學習成績就一落千丈。班級排名不斷落后,這對孩子而言是一種打擊,“孩子會開始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好”。
真實的情況是,小學課程中奧數并不是必修門類,通常奧數是在小升初之后正式涉及。但是大量的家長會在課外時間給孩子報奧數補習班,以至于最后老師們會習以為常的將奧數算在考核門類里,有些不愿意讓孩子在課外時間補習的家長會逐漸發現問題。“為了讓孩子跟得上整個班級的平均水平,他們只能被迫讓孩子上補習班,最后整個班的孩子恨不得都得被逼著學。”
朋友的經歷,讓李民對要小孩這件事越來越持否定態度。“我沒辦法改變大家的想法,最后我干脆決定還是不生了。”
每到放假休息的時候,李民想約朋友出去轉轉,有孩子的朋友基本上全被“拴”在了家里。特別是在今年國慶期間,李民在朋友圈里曬著祖國山河,而朋友們不得不遵循孩子學校的要求老實留在北京。“我能感覺他們在教育上越來越吃力,有時候孩子問的問題讓他們啞口無言”,在李民看來,今天95、00一代,已經是徹頭徹尾的網生一代,過早的接觸網絡,讓他們擁有和7080一代全然不同的世界觀。
“為什么現在人都要管孩子叫神獸呢”,這個問題李民想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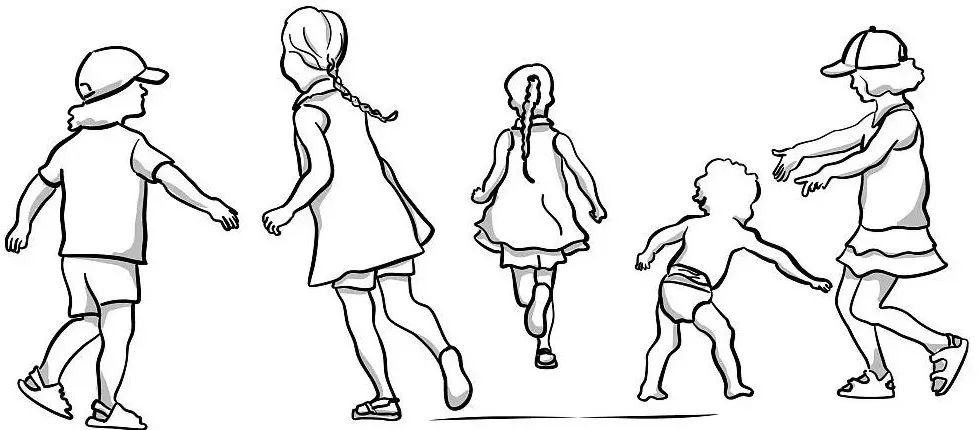
關于養老的問題,李民認為能不能過好晚年的關鍵不在于是否有個孩子,在一線城市越來越少的人希冀孩子養老,而是期望自己要儲備夠足夠的資金以及社會的健全的養老制度。這種制度是公平的,我相信不僅僅是丁克需要,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敢說不需要?
因此關于不要孩子這件事,李民更加想通了。
斯榮,影視行業從業者,70后,婚齡22年
“希望社會對丁克寬容一點?丁克又沒有錯,為什么要寬容”
斯榮的第一個孩子在婚后第一年就來了,有點突然。那時她剛25歲,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在當時中國的第一家互聯網公司。“一家做通訊業務的公司,我跑業務。”
她和丈夫原本是同事,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兩個人因為工作產生了聯系,他們戲稱自己是中國網戀第一人。公司總部就在北京,1998年,斯榮的丈夫也調到了北京總部,正式開啟戀愛,再然后就是結婚,一切順理成章。
結婚半年時間不到,斯榮發現自己懷孕了。“真的,我想都沒想,肯定是不能要這個孩子。”
對斯榮而言,事業剛剛有眉目,居無定所,夫妻二人都在打拼的階段。她甚至沒跟雙方父母打招呼,就和丈夫二人做了決定,把孩子打掉了。“你自己都在一個動蕩的狀態里,有什么資格要小孩呢?”
從小到大,斯榮習慣于一個人做決定。本科學的是金融專業,斯榮一畢業就進了家鄉當地的銀行工作,在父母親戚看來,這是鐵飯碗,體面又穩定。但工作的第二年,她就給媽媽列了一張表,表格的左邊一列是留在家鄉的理由,表格的右邊一列是離開家鄉去北京打拼的理由。她把表格給了媽媽,什么也沒說。那張表格的右側列出的理由明顯是左側的好幾倍。
最終,斯榮如愿離開了家鄉。“我這樣做,我媽當時就明白了,我想清楚了,她也同意了我辭職到北京來。”
關于要不要孩子,斯榮心里也有一張表。一側是要孩子的理由,另一側是不要。“我如果要了孩子,一定會全心全意給他最好的”,在斯榮看來,丁克與否只是個選擇問題。但無論你選擇了什么,你都得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就像她當初決定到北京打拼時,她也清楚的思考過每一種后果,她是不是可以承擔。“你會不會后悔,能不能承擔,在要孩子上,我已經思考的特別清楚了,你說我自私也好,說什么都無所謂,我想好了。”
30歲的時候,斯榮還在猶豫。35歲的時候,斯榮似乎想明白了一點。現在,已經將近50歲,斯榮卻忽然特別堅定。
在斯榮看來,不同年紀的人,組建家庭的需求都不同。“每個人在家庭里的定位是一直在變的,包括孩子也一樣。”
或許是因為心態不同,斯榮身上沒有一些中年女性的疲憊感。她的皮膚很光亮,身材管理很好,巴掌大的小臉,看上去更像是一個80后。因為不需要陪伴孩子,斯榮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作為一家創業公司CEO,現在正是斯榮事業的巔峰期。晚下班是常態,偶爾可以休息的時候她就去做個SPA、打打球。
她還是會想起1998年的那個夏天,她剛來北京漂泊,無房無車,事業很不穩定。“如果再加上一個孩子,我的人生可想而知會是多么艱難”,所幸,她沒有讓這樣的情況發生。
就在當我們問道,現在這個社會會不會對丁克寬容度更高了。斯榮理直氣壯的回復道,我們又沒有犯錯?怎么是“寬容”呢?
斯榮是這樣想的,丁克文化是這個時代下孵化的,選擇做丁克與否沒有大是大非。
“就是個選擇,真的,就是個選擇。”她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本文系【AI財經社】原創內容,未經授權,禁止任何轉載
原標題:《丁克20年,我更加堅定了》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