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讀書會︱張經緯、維舟:歷史記憶與華夏的塑造
“華夏”對中國的民族身份認同有很重要的作用。華夏認同是如何發展演變的呢?著名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教授在他的成名作《華夏邊緣》中討論了中華民族族群認同與歷史發展問題,為回答“什么是中國人”提供了全新路徑。這本書出版二十年來因為其富有解釋性的框架和極具啟發性視角,成為討論中國族群認同與歷史發展繞不開的重磅研究,也成為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等多個領域必讀書目。2020年9月25日,知名書評人維舟和上海博物館副研究員張經緯受邀在陸家嘴讀書會分享他們對“華夏認同與歷史的記憶”的理解和體會。本文系文字整理稿,有刪節,經授權,澎湃新聞發布。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維舟:《華夏邊緣》這本書首部簡體版是2006年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當時看這本書的時候,印象非常深刻,因為接觸到了一個全新的觀點。以往我們談到“華夏”,通常來講,傳統敘事其實就是書里講到的“根基論”——我們是炎黃子孫,因為我們血脈相承,在血緣上有傳承關系。王明珂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即歷史記憶,也就是族群研究上比較流行的流派,叫“工具論”。工具論是說把身份認同作為爭奪資源的工具。舉個例子,有一本書叫《蘇北人在上海》,它里面一個主要的觀點就是說你的身份是可以改變的。一個蘇北人來到上海,他如果跟其他蘇北人交流的時候,他會宣稱我是蘇北人,但是如果他意識到蘇北人在外面會被歧視,他就會在外面掩蓋自己的身份。這個身份在這里就變成一個工具。
王明珂認為,工具論和根基論都有一定解釋力但也都有缺陷。因為身份涉及歷史問題,他提出一個觀點,即從歷史記憶的角度思考:我們為什么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結合在四川羌族村寨做的田野調查,王明珂發現我們現在所說的羌族不是古代的羌族,現在這個羌族實際上是1952年民族識別的時候,識別出來的一個全新的族群——當時本地人并沒有把自己稱之為“羌”,而是稱為“爾瑪”,其實就是“本地人”。所以只是民族學家他們經過比對認定以后,說你們應該是歷史上羌族的后代,你們就叫羌族。王明珂在這個過程中看出來歷史怎么演變,為什么會有不同歷史記憶嫁接到這個上面,從邊緣出發反省審視“華夏民族”這個符號、這種歷史敘述是怎么形成的。
我之前跟張經緯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我發現王明珂的理論很有解釋力,而且還有很強的人類學反思色彩,他其實突破了以往歷史的陳舊框架。但是我也注意到其他人還有一些相關的討論。譬如另一個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的學生羅泰,他是美國人,他在《宗子維城》里面提出另外一個觀點,從公元前800年左右開始,隨著中原地區文明越來越發展,它跟周邊文化發展拉開了距離。在拉開距離的過程當中,它就逐漸產生了分化。他認為這個過程中產生了華夏這個符號。我們可以看到這里面有一個差異是說,在王明珂的理論中,華夏類似于一個工具,在跟長城以外的游牧民族爭奪資源的時候,我們用華夏這個符號自我凝聚,團結起來跟長城以外的游牧民族爭奪資源。但是在羅泰的觀點當中,他認為中心和邊緣的關系不是南北沿著長城線對峙,他認為中原文明發展史,是它逐漸瞧不起周邊部落,慢慢顯示出自我的優越感。想問一下張經緯怎么看待這兩個觀點?
張經緯:感謝維舟兄幫我們先回憶了一下《華夏邊緣》這本書里一些主要內容,又引入了羅泰的觀點。羅泰的觀點就是他認為有一個實實在在的華夏,這個東西是真實存在的。我把維舟兄的觀點拓展一下。這樣的華夏在夏商周時期,是中國地理上的核心即中原一帶開始出現,不光是一個地理上的區域,同時也是一個人群的集團。這雙重的華夏標簽賦予這個區域的人,成為華夏核心,然后經過兩千多年中國歷史上王朝的積累,像滾雪球一樣慢慢變成今天理解的,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包括海外也有很多赤子之心的中國人這么一個華夏觀念。
我覺得兩種觀點從不同角度來看都是能站得住腳的。我想聊聊自己對《華夏邊緣》這本書的理解,這樣大家就明白為什么我覺得這兩種觀點都有可取之處。看《華夏邊緣》這本書之前,我本科也是學歷史的,歷史上說秦始皇的時候在嶺南設象郡,那時候中國好像就已經是從北邊的流沙一直到南邊的大海,都在中國的版圖里面。但是《華夏邊緣》這本書顧名思義,我們從題目里也可以感覺到,他想提出華夏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怎樣一個漸進法,舉一個大家一聽就明白的例子。在漢朝的時候,我們今天說的“四岳”——北岳恒山、南岳衡山、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四岳當中的南岳,還不是我們今天說的位于湖南衡陽的衡山,而是安徽安慶有一個叫潛山的地方。潛山這個地方有一座天柱山,至今那個山峰上還刻著字——“古南岳”。如果我們以四岳,東岳、南岳、北岳、西岳劃定華夏自我認同的位置,安徽安慶這個地方,就是漢朝時候人們覺得挺靠南的地方了。而南岳從安徽安慶天柱山跑到湖南衡陽衡山,經過了多少年呢?經過了九百年。我們知道在漢朝安慶這個地方受封為南岳,時間是公元前一百多年,等到唐朝的時候,大概公元前七百年以后,從安徽遷到湖南,這個才有了我們今天心目當中東西南北四岳的位置。
“華夏邊緣”給我的一個啟發是,它打破了我們心中的刻板印象,好像古代中國的版圖和今天已經沒有什么區別了。但是這個動態的華夏邊緣觀念就告訴我們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再往前追溯四岳,我們會發現四岳更小,最小四岳可能就是陜西山西交界這個區域里面。他們當時所謂的四岳就是我們今天看來很平凡的小山。夏商周到漢朝說明華夏已經擴大,擴充到今天理解的北岳、西岳、東岳,南岳還不是我們今天的。又過幾百年到唐朝,華夏像滾雪球一樣變大了,像同心圓一樣。核心是中原那一帶,周邊越滾越大。
周圍那些人群也很有意思,比如說匈奴,在西漢的時候匈奴和漢朝打得很激烈,大家互有勝負。在東漢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匈奴分裂成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里面有一派南單于和漢和帝說,每年漢朝給我們很多糧食,我們生活在漠南很好,覺得每年光吃你們的糧食光拿你們錢不干活也不好意思,我決定幫助你們主動攻擊北匈奴。他也有自己的算盤,其實是借漢朝名義把北匈奴領地搶下來,但是上表奏章不能這么說,上表說得很冠冕堂皇,不能白拿你們錢和糧食,我替你們出征作戰,因為我有一顆華夏的紅心。等到東漢滅亡,三國的時候劉備跑到四川,建立了蜀漢政權,號稱是延續了漢朝正統。等到蜀漢滅亡,西晉也快滅亡的時候,又有一群匈奴貴族出來說,他覺得漢朝被魏晉滅亡,他要延續漢朝正統,就是十六國時期漢趙的開國皇帝,叫劉淵,實際上他是匈奴人。因為漢朝的宗室經常和匈奴通婚,在母親這一系已經完全具有漢朝宗室系統,他覺得他有義務來繼承漢朝的,繼承華夏的。這里羅泰和王明珂的觀點就可以統一在一個框架里面。
維舟:華夏邊緣有三重意義,一個是地理上,比如剛才說到四岳遷移。還有一個是人群上,這個人群原來不屬于華夏正統,慢慢融合進來,認同自己是華夏正統。第三重意義是文化上,在古代的時候,中原地區自居是文化正統,的確周邊民族可能有一些自卑感。我們可以看到王明珂和羅泰的觀點里面,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認為在最早的時候,華夏邊緣實際上是統一的,或者說并沒有分化。比如說古代所謂的圣君舜帝,他也算是東夷人,理論上也算是夷。《左傳》里,尤其是晉國,他們跟周圍羌族或者是蠻族通婚往來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說,最早的時候雙方沒有分化,我們彼此差不多,只是后來這個差距越來越大。一部分可能是文化上的差距,另一部分是占有資源越來越多,另外是族群身份上面。可以看到這個身份在歷史上是動態的過程,這個身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互相轉換。有的時候漢人也會變成蠻夷,蠻夷也會變成漢人,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只是慢慢可以看到邊界越來越擴散了。
王明珂在《華夏邊緣》里面講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就是歷史記憶,比如他講到吳國怎么攀附祖先的。傳說吳太伯是吳人創業祖先,他們聲稱吳太伯其實就是周人的祖先,當時是為了把君王位置讓給自己的弟弟,生怕父親把王位讓給他這個長子繼承,所以跑到吳國來。但是王明珂書里駁斥了這一點,公元前1000年左右不可能從陜西跑到江南這么遠。他認為當時所指的吳實際上是在河南洛陽附近的虞國,這個確實考古各方面比較合理。王明珂和早先史學家不一樣,比如顧頡剛,他在《古史辨》中認為很多上古傳說是“層累地造成的”,他的重心在于我們要破除對于三代傳說的迷信,要破除他們的神話地位。但是王明珂的重點是要強調和發問:如果傳說或敘說是假的,那么當時的人為什么編造這些,編造這些動機是什么,編造這些故事對他有什么好處?王明珂的觀點基本是,他認為歷史文獻可能靠不住,而是人們出于某種動機記下來,或者是經過篩選或者是經過篡改。我覺得這里面有一個問題:我們怎么知道我們猜的是對的。
張經緯:我們以前看文獻會有一個印象,《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等一般講周邊華夏邊緣講得很籠統。什么時候開始比較具體?南北朝有一個《南史》《北史》,《北史》里頭特別出現一個新類別,除《南蠻傳》外專門出了《僚傳》。“僚”是什么?這一群人生活在貴州以東,湖南南部以南,江西、福建這一帶,也包括兩廣這一代。在北朝人眼中,他覺得這個區域里面的人是僚人,因此有了新的傳叫《僚傳》。以前民族史專家有一個觀點,既然這一群僚人是《北史》里出現的,《僚傳》是魏晉南北朝時出現的傳記類別,就認為這是他們首次出現在中國歷史上。但是從王明珂的《華夏邊緣》里面,我們看到另外一種觀點。當《僚傳》出現在《北史》中,恰巧說明是懂得漢語寫作的人來到了僚人生活區域里面。僚人不是剛剛出現,而是北方來的漢人首次來到他們所在的最南邊,進入僚人的世界,而僚人本來就在南邊,可能夏商周就已經在了。
通過這樣的視角轉換,我們看到了一種動態的過程。原來是到了南北朝,北方人才大規模進入到湖廣一帶。我發現在之后的二十四史傳記里面,比如兩唐書,又出現了新的類別。可能在《僚傳》下面又劃分出《俚僚》,俚人分布在廣州以南一直到海南島的區域,他們的出現直到唐代才在正史中有記載。我們發現,越到后面的唐、宋、元、明、清,在周邊敘事里面都會增加一些類別。就像中學里面有等高線圖,一圈圈往外擴散。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少數民族列傳中新的類別發現唐朝時候華夏邊緣在什么區域里面。這些東西被記錄在正史當中,實際上是有一個背后的時間軸,這個時間是固定的,不管記錄下來的事情是真是假,被記錄下來這個事情本身都是有意義的,證明記錄這個事情的人是有華夏標簽的人。他來到這個區域,見到這些人,可能缺乏鑒別能力,真真假假地記了很多。他是一個盡職的記錄者,他把看見的都記錄下來,無論真假,這樣的記錄本身就非常重要。
我們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把華夏邊緣從虛無的角度慢慢落實。我們所討論的不在于事件本身真假,而在于記錄這個事情的人類實踐。通過這種方式我其實還延伸出來很多類似的研究路徑。比如說可以去研究一個地方的虎患,很多中國古代的記錄里面會記下來這個地方有老虎吃人或者是類似情況。這和我剛才說的邊緣敘事很接近。當一個地方頻繁出現虎患,說明這個地區不是老虎下山吃人而是人跑到老虎的活動空間,人和老虎遭遇頻繁。如果文獻記載10年、20年出現了多起虎患,我們就知道這個區域里人類開發開始頻繁。
不光是老虎,我們知道韓愈被發配到潮州,他說這個地方有很多野象出來踐踏農田,他覺得大象趕不走,只好寫一篇文章譴責一下他們。那個地方有很多鱷魚,他就寫了《祭鱷魚文》。潮州這個地方雖然是挺野生,但是現在肯定沒有大象、鱷魚這些野生動物存在,在唐朝的時候這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區域,隨著人類的開發導致現在沒有鱷魚也沒有大象。通過這樣一個視角,變成華夏如何開發邊緣,把它周邊的那些曾經邊緣做實變成自己的核心區域,然后有新的邊緣繼續出現,一層一層這樣子遞推出去。

活動現場圖
維舟:王明珂很多講述實際上是沿著長城邊境,跟游牧民族的沖突。主要是三個地方,西北青海一帶、正北方蒙古高原,還有東北方鮮卑、契丹民族。三北地帶沿著長城一帶對峙,爭奪資源。當然討論已經延伸到跟南方有關,關于南方的研究可以補充一些觀點,有幾位歷史學家,像魯西奇、羅新,最近幾年都有相關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北方和南方狀況不一樣,南方就像剛才講到一直到漢朝,漢人中原文化在南方是孤島,周圍是汪洋大島,都是少數民族。令人驚奇的是,最后孤島和海洋關系逆轉了,變成漢人越來越多,少數民族越來越少。為什么會這樣?可以說一方面是因為普遍認為漢文化比較高等所以他們最終就都去投奔,但是從另外一方面,其實是隨著中央王朝對南方地區的深入開發,對于人口和土地控制能力越來越強。
這個過程不是線性的,而是不停反復互動,是個極其復雜的過程。舉例子來講,最后我們會發現,一直到清朝,甚至南方腹地仍然有大片少數民族沒有被漢化。最復雜的一點是,有些學者討論過,我們現在所說的兩廣地區的瑤族,他們其實本來是被王朝用來征收徭役的。在徭役之外,他們不愿意服從體制,不愿意交稅,想要生活在戶口制度之外逍遙法外,就像水滸英雄一樣。這地方有一些漢人也不愿意過被約束的生活,也逃到山里面去,這些漢人后來就變成了瑤族。后來大家發現,區分漢人和瑤人關鍵并不在于祖先是誰,也不是他們的文化,是否講漢語,區分關鍵在于是不是服從政府的控制。所以這個過程是相當復雜的,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這其實不完全跟你的根基狀況一致,有的時候是與政治控制體系復雜互動的過程。
王明珂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書中里也講到一個非常典型現象,在云南少數民族當中特別常見。傳說中云南幾個主要少數民族,傣族、佤族、漢族、白族,最早是同一個祖先。他們的祖先是從一個葫蘆里面走出來的,第一個是漢人,第二個是傣族,類似的傳說不止佤族有,很多民族都有。這樣一個傳說代表什么?王明珂從歷史記憶角度來解讀,他認為這個其實是當地對于周邊民族現狀的解釋,我們這些民族屬于兄弟民族,最早的時候是祖先同源,只不過我們現在比較倒霉沒有你們漢族這么發達,但是追根溯源我們其實都是兄弟。這個是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一點,他給了現狀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他跟我們現在所謂的中華民族多元體是暗中吻合的。王明珂這本書雖然從《華夏邊緣》切入,但最終歸根到底,現在我們說華夏其實不僅僅指漢族,而是指整個中華民族。中華民族這個整體又是怎么形成的,他認為這些歷史記憶心性與中華民族這個概念被接受有一定相通之處。如果沒有原來這些解釋的框架,那你就很難接受中華民族這個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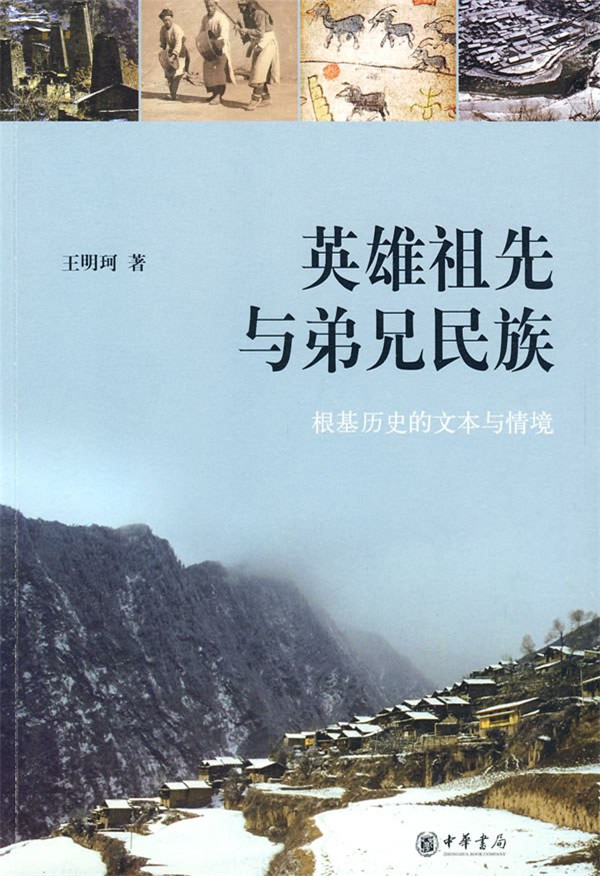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
我又要提一個問題,我覺得一本好書最關鍵的是能不能給你啟發出一些新問題,而這本書非常具有啟發性。我的問題是,他的框架實際上以中國現狀為依據,那么我們怎么解釋那些沒有被整合進框架的民族或者國家。舉例來講,像越南,它在歷史上長達一千年的時間里都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朝鮮也類似。為什么這些國家也曾接受中華文化深刻的影響,但是他們卻沒有被整合進中華民族框架里面來?
張經緯: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一是從文化親密度考慮。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長期生活在你的身邊的,大家關系很緊密,那種文化交融就更強。比方在清朝的時候,朝鮮和明朝的疆域之間隔了一個清朝曾經生息發展過的東北滿洲區域。今天看來,好像朝鮮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和中原王朝版圖接在一起,但這是我們逐漸建構起來的觀念。其實在歷史上,在東北這個區域里面有一些古國,唐朝時有高句麗,唐朝以后有渤海國,再往后還有一些,雖然我們的歷史書上說,漢朝的時候曾在朝鮮建立過幾個州郡,但其實時間很短。朝鮮半島和我們中原王朝長期以來都隔著今天東北那一塊。東北那一塊在歷史上都不是特別的中原化,就更不用說比他們更遠的朝鮮了。這些說法可能很多時候也有我們自己的一些主觀感情在里面,這是一方面。同理,越南和中原王朝還隔著兩廣。剛才討論過,兩廣地區其實在完全中原化之前也有很長一段時間。至少在明清以前,他自己的本土文化氛圍還是很強的,兩廣文化還是起到一個中原和越南之間的過渡角色。
還有一個我們今天常會說到,可能是人家自己自我感覺良好,譬如日本,它覺得明亡以后,明代正統消失,明儒遺老遺少渡海跑到日本去,日本才把中華文化保存得最好。他它自稱自己是“小中華”,這其實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日本沒有一開始就覺得自己是“小中華”,在日本還沒有完全走向現代化的時候,經濟不發達,國力不強盛的時候,小中華的感覺沒有這么強;等到明治維新以后,它的國力上去了,在國際舞臺上有自己的話語權以后,他的認同就提升了。
這很像中國的兩個區域。一個是兩廣一帶。這一帶雖然我們感覺他們保留了自己本地的一些特點,但是我們看兩廣的地方文獻和地方文人的自我表述,他們都認為從衣冠南渡(東晉五胡亂華)以后,他們已經繼承了中國正統。很多地方有稱號叫“海濱鄒魯”。“海濱鄒魯”,就是中國歷史上認為山東魯國、鄒國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核心的區域,北方這些華夏正統慢慢受到侵蝕就跑到福建、廣東一帶了。咱們生活的吳越一帶也很有意思。在明清或者兩宋時期也出現過像廣東一帶的現象,覺得自己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但是隨著這一帶的經濟發展,等到明清以后,這里的經濟發展到很高的程度,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核心以后,它反而會覺得吳越文化并不是不能拿到臺面上說的事情,會覺得我們在華夏這個大的框子里面我們還有一部分吳越自己的。
維舟:本土文化自覺。
張經緯:對,我認為是否有華夏認同還有一個原因。一個方面是越南、朝鮮離中心近不近,另一方面是看自己本土經濟發展的情況。如果你經濟發展足夠好,有足夠的文化自信,不管是華夏身份好或者是本土身份好,都會比較自然地接受。
維舟:這談到另外一個話題,即王明珂書里提到的另一個觀點——邊緣的漂移。原來在上古的時候,華夏邊緣可能在陜西關中以外,甘肅等地方。后來甘肅天水、隴西一帶,已經被公認為是華夏人,青海才算是華夏邊緣。后來連青海都被漢化了,這個邊緣就會再往外推。羌族原來生活在很核心的地區,洛陽一帶都有。所謂姜戎,姜戎就是羌戎。姜太公說起來也算是羌戎。姜在當時本身是大姓,最初是與羌人有關,因為都是羊字頭。但是后來,留在核心區的這些人已經全部被漢化了。這部分人完全被漢化以后,蠻夷的稱號就留給了漢化程度比較低的人。原本羌在核心洛陽一帶,后來慢慢往外移,一直到延伸到四川深山老林里面的一些人,才被稱為羌人。他提出“邊緣的漂移” “邊緣的漂移”這樣一個觀點,實際上是指邊緣是動態的,在不停調整的。這個觀點非常有意思。
剛才我聽張經緯說這個觀點,還有另外一面是中心的漂移,華夏正統也可以漂移。我們現在可能認為中國核心在北京或者是沿海發達地區,但是如果你去看河南博物院會發現,有一展中原流金歲月、天下樞紐的感覺。我看過整個河南博物院的布展,感覺中國古代文明火炬在西安、洛陽、開封不停傳遞,一直到1127年被女真人攻占以后被熄滅。那種中原自豪感是非常強烈。我們可以看到中心其實也在漂移,中國歷史上首都一直在遷移,從西安往洛陽、開封再到北京,往西北方向遷移。朝鮮、日本都自稱過“小中華”,甚至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像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日本天皇宣戰詔書里面還有提到“神州”。我們一般認為神州是中國專語,日本怎么也稱神州呢?但是這種文化正統觀念或者是自我認同感,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想。在歷史的動態過程當中,一些人自稱接受中華正統,這也是相當強大的動力。講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清朝時越南有一個使者進京,途徑兩廣,驛站里的人出來歡迎他,大概不小心說漏了嘴稱其為“遠道而來的夷人”。這個人聽了大怒,說壯族、黎族可以稱為夷,我堂堂越南人受過中原衣冠禮儀,怎么能把我稱之為夷。他對正統觀念是非常認真的。
這本書我看完以后很大的啟發是,《華夏邊緣》在講怎么看待中國歷史中深層次結構動力,人群怎么逐漸演化的問題。它不僅解釋了這段歷史形成的過程,也給我們提供了方法論。它告訴我們讀歷史不要只讀字面上的歷史記載,還要透過表面來看核心。當初為什么留下這些文獻,留下這些文獻動機是什么,是誰在寫,什么人試圖用這些歷史機遇為自己爭取資源。當然我自己比如說寫書評或者是歷史的時候也有受過蠻多啟發,經緯可以談談他對你的治學啟發有哪些?
張經緯:受王明珂先生啟發,我寫了一本書叫《四夷居中國》。其中一個核心方法是,我如何把正史當中記載的,或者我們曾經認為的周邊民族首次出現在中國版圖上的數據,轉化成一個漢人首次來到這個區域的時間。這能幫助我們從以往的歷史敘事當中走出來,形成一個自己看待歷史的方法。
另外一個從王明珂先生書里面得到的啟發是,我們以前看歷史書甚至小時候聽評書,經常會出現某某大王想要打到金鑾殿、當地的將領想要當皇帝的故事,造反的理由千篇一律。我從這樣一個新視角里發現,老虎和人發生沖突傷人,并不是老虎每天肚子餓了從山上下來填飽肚子,而是人跑到老虎正常活動的區域里和老虎發生了遭遇。如果用“遭遇”這種觀點來理解中國歷史上的這些叛亂會發現不一樣的視角。漢文文獻里記載在明代四川發生過奢崇明叛亂,文獻里說是因為這個人想當皇帝所以要來和明朝中央政府抗衡,我試著抹掉這種狂妄自大的觀點,再從華夏邊緣角度來看就發現,這個部落領袖叛亂之前,明朝正和女真人進行交戰,兵員不足,明朝中央就到四川征兵征糧。奢崇明族人一開始也很配合,但到最后實在心有余力不足,在政府的壓力下,就和征兵地方官吏發生沖突,然后一不做二不休舉起反旗。
我們通過華夏邊緣這種觀念,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研究歷史的時候多一種視角,另外對被歷史打入另冊的人群也可以抱有同理心,理解他們在歷史上的具體活動,也讓我們看歷史的時候放下激動的心情,保持比較平靜、更加寬容的同理心情看中國古代歷史,這也是塑造我們自己的個人修養、個人史觀比較好的方式。這是《華夏邊緣》給我的兩點啟發。
維舟:這個也很有意思。我們以往中國歷史的講述通常來說是一元論,常常規定歷史的某一種說法是正確的,其他說法是錯誤的。但是王明珂強調歷史記憶,歷史記憶是什么意思,其實就是多元。
我覺得這里面還有一個關鍵點,王明珂強調歷史記憶的主觀性。對于主觀性的強調使他比較偏重歷史心性,就是社會心態怎么形成的,對于我們每一個人心里會產生巨大影響。但是我覺得看完書以后,我第一個感覺是說,他這里面所說的“華夏”,反思下來看不是血緣共同體,也不是文化共同體,而是政治共同體。這本書給我們的反思在于,不止是對歷史,甚至可以看周邊的人,就像《羅生門》,聽一個人的講述要理解他為什么這樣講述。這對我們理解社會、理解歷史有很好的啟發。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