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瀛寰新譚|八國聯(lián)軍進逼,清廷和地方卻在為“還洋債”斗心機
【編者按】
近日,復(fù)旦大學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編的《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第一輯(十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叢書第一輯聚焦晚清時期的中外交涉與交流。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外交學人”特邀這批史料的幾位整理者,基于史料對晚清外交和中外交流做更深入的解讀和分析,在以更豐富的細節(jié)盡可能還原歷史事件的同時,也希望能激發(fā)對當下中國外交與中外交流的一些思考。
120年前,當清朝中央政府對外宣戰(zhàn)時,東南各省督撫卻與外國達成和議。這荒誕一幕背后是弱國的悲哀。本文所述即是這幅扭曲的歷史圖景中的一個片段。
120年前,仇洋排外的義和團運動最終招致八國聯(lián)軍入侵。然而,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南北卻出現(xiàn)了畫風迥然不同的兩幅圖景——北京的清廷不遺余力進行戰(zhàn)爭動員,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在東南一隅苦心維持中外互保,兩頭擰的顯然不是一股勁,但卻微妙地保持了平衡。其中較大的一次風波,即“停解洋款”事件。
所謂“洋款”,即清廷歷次向列強所借外債,以關(guān)稅、厘金、鹽稅等為抵押,其中以關(guān)稅為最大宗,據(jù)借款合同由各海關(guān)分期直接扣還或代為扣還本息。清廷以為中外既已開戰(zhàn),洋款自應(yīng)停付,一律改撥軍餉,用以彌補緊張的中央財政。這一如意算盤,實際給地方督撫出了一個莫大難題。劉坤一、張之洞和兩廣總督李鴻章等人頻繁函電往來商議如何打消朝廷這一旨意,甚至密函京中的軍機大臣以求助力。
本文即以《庚辛史料》結(jié)合其他文獻,勾勒庚子事變中地方督撫與朝廷這場“斗法”的曲折過程。
“索然無味”的電報有何價值?
《庚辛史料》,許同莘輯,連載于《河北月刊》1935—1936年第3卷第1—8、10—12期,第4卷第2、4、6、11期。許同莘,江蘇無錫人,曾留學日本,歸國后入張之洞幕府為幕僚。1909年張之洞去世后,許同莘曾為其編纂《張文襄公全集》(編注:關(guān)于《庚辛史料》及輯錄者許同莘其人,作者曾于澎湃新聞撰文做過詳細的介紹,可參看)。
據(jù)輯錄者“題記”,此種“史料”主要匯輯庚子事變時期官方電報,可以說是許同莘編纂《張文襄公全集》的一個副產(chǎn)品。據(jù)編輯體例,“已見李文忠、張文襄(編注:指李鴻章、張之洞)全書者不重出”,則這部分資料是《張文襄公全集》及今人所編《張之洞全集》所未收者,可與兩書互補。目前可見《河北月刊》連載者,起自庚子五月初九日,迄至九月初三日(即1900年6月5日至10月25日。本文以漢字表示農(nóng)歷日期,以阿拉伯數(shù)字表示公歷日期),共528件,總計約7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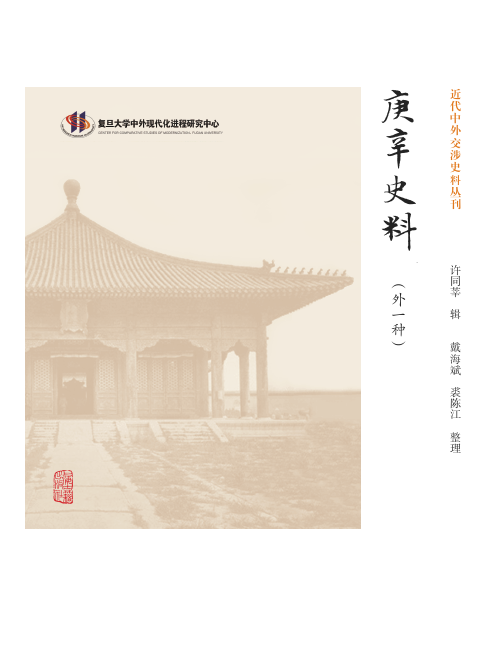
《庚辛史料》,許同莘輯,戴海斌、裘陳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據(jù)筆者整理統(tǒng)計,《庚辛史料》所錄主要是庚子事變期間張之洞所收各方來電,不錄發(fā)電,而來電責任人總計近百人,上自各省督撫、將軍大員,下至湖北派往各地的“偵探委員”,涵蓋范圍相當廣泛。各方來電,大多篇幅短小,且內(nèi)容零散,頭緒紛雜,初讀者一時難免困惑。不過,如許同莘所指示,“一事之起,必有由來;一端之發(fā),必有究竟。電文既略,若不與來電參觀,則如隱謎、歇后,索然無味矣”。
電報這一類史料,實有其特殊的性質(zhì)與利用方式。而《庚辛史料》所涉時段恰值庚子事變的高潮時期,各電雖多屬只言片語,卻反映了不少重要時事及時人觀念,如將此材料置放于合適的語境,不僅與先后電文相補充,而且與同時期其他文獻相印證,往往可以顯現(xiàn)較高的史料價值。如庚子七月初五日(1900年7月30日)“江督(劉坤一)致鄂督(張之洞)電” 便是一個好例:
“江電洋款事,先致榮、王(編注:榮祿與王文韶)兩相公函,自是穩(wěn)著,已擬稿電請慰帥馳遞,僅會公及袁銜,以期迅速。榮、王處似可無庸多銜。公謂如何?坤。”
下文即詳敘“停解洋款”一事之經(jīng)緯,通過與其他史料相互印證,可知《庚辛史料》收錄的這條電文所透露出的信息,對我們理解這場地方督撫與朝廷的博弈提供了更多的維度與視角。
朝廷下旨“停解洋款”,東南督撫陽奉陰違
1900年六月初十日(6月30日),即清廷宣戰(zhàn)詔書下達后第十日,軍機處寄戶部及各省將軍、督撫上諭稱:“現(xiàn)在統(tǒng)籌戰(zhàn)備,迭經(jīng)諭令各省籌餉練兵,共保疆土。惟庫款支絀,餉項艱難,既與外洋決裂,所有各省認還洋款,著即暫行停解,聽候部撥,移充軍餉。”(《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207頁)

劉坤一(1830—1902)
然而,當時的中國南北卻是“冰火兩重天”。東南各省督撫不理會朝廷宣戰(zhàn)的旨意,反而與外國達成和平協(xié)議,避免整個清帝國一起陷入戰(zhàn)爭局面。這一行動史稱“東南互保”。但對于朝廷的旨意,各省督撫也不便公然違抗。因此,兩江總督劉坤一作為“專轄各口商務(wù)”的南洋大臣,在奉到“停解洋款”的上諭后痛感棘手而“憂急欲死”:如照辦,各國必將分據(jù)海關(guān),危及沿江各省;如秘密不宣,各省皆不解款,又無法向朝廷交代。逼處兩難之間,他只好向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商詢應(yīng)對之策,又電告當時在上海的盛宣懷有“萬緊事件”,令迅速趕赴南京面議。
李鴻章主張由南洋領(lǐng)銜,聯(lián)合沿海各督撫請旨“收回成命”。劉坤一依議寄電各省,歷數(shù)停還洋款之害,表明“是不還款,即失大信,又受巨虧”的立場,一面酌擬奏文,只待各省復(fù)電后發(fā)出。(《寄東南各省督撫》,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劉坤一遺集》第6冊,第2572頁)但各地反響并非一致。山東巡撫袁世凱認為,既已奉明旨,“奏必不準,且被嚴譴,于事無補。”湖廣總督張之洞也不以遽奏為然,尤其“收回成命”語太過直露,隱含抗旨的風險,當另擬一辦法,令與駐滬領(lǐng)事婉商,請展緩還款一兩月,待日后補足,并“微露內(nèi)意”以探口風。較之徑直具奏,商緩解款在政治上相對安全,李鴻章以為“可行”,并提示除商請各領(lǐng)事外,還應(yīng)與匯豐、華俄兩大外國銀行妥議。
劉坤一電召次日(7月5日),盛宣懷即乘船前往南京,在那里停留不多時,又匆匆趕回上海。關(guān)于面談情形,劉事后向李鴻章通報:“初八奉廷寄,既約杏蓀(編注:盛宣懷)來寧商酌暫緩之策,允回滬與余道(編注:上海道余聯(lián)沅)商辦,實無把握,焦灼萬分。”(《南洋劉大臣來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辰刻到,《李鴻章全集·電報七》,第114頁)
此處“商辦”者,即指張之洞提議對外商議暫緩解款而言。張之洞當時由朝廷諭旨尋找出據(jù)以引申的話頭,認為諭中本有“暫”字,證明緩解事屬可行,并暗示可加重語氣,適當給外國人一些壓力——“若苛責外省強以顯違諭旨,必致沿江督撫均行更換,東南大局頓變,彼此無益。外國若強據(jù)海關(guān),東南大亂,商稅更少矣。”(《致廣州李中堂江寧劉制臺上海盛京堂》,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巳刻發(fā),《張之洞全集》第10冊,第8099頁)

盛宣懷(1844—1916)
盛宣懷返回上海后,劉坤一又追發(fā)一電:“臺旆往返,煩勞感歉。此事關(guān)系太重,苦思無良策,能否照香帥(編注:張之洞)電商辦,務(wù)祈詳細體察,妥籌辦理。”(《劉峴帥來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愚齋存稿》卷三七,第868頁)電內(nèi)雖然指示按照張電“妥籌辦理”,但毫無把握,故叮囑必須“慎重出之”,可見劉本人猶疑不決的心態(tài)。
盛宣懷明知與虎謀皮萬做不到,洋債事“力止必不可行,亦不可播”,遂提出一折中方案:六、七兩月,英、德還款為數(shù)有限,且均在兩江、湖廣兩督轄區(qū)內(nèi),“東南力能為之”;其余洋款則在九月以后,可延宕執(zhí)行,“屆時夢已醒矣”(編注:此處指清廷屆時應(yīng)已知無法以一國之力戰(zhàn)勝八國聯(lián)軍),待朝局改觀后再行復(fù)奏。(《寄江鄂劉張二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愚齋存稿》卷三七,第869頁)這里考慮了外債償還的具體情況,同時也對時局發(fā)展抱以相對樂觀的預(yù)期。
廣西巡撫節(jié)外生枝,劉、張二督求援中樞
各省督撫幾經(jīng)磋商,最后達成共識,于六月二十日(7月16日)發(fā)出會銜電奏,除湖南、廣西兩省外,其余各省督撫均列銜名,內(nèi)稱:
“……是停還洋款,于各省籌餉有損,尤于京餉有妨。蓋停戰(zhàn)無期,則需餉尤巨,既有必戰(zhàn)之志,必寬留籌餉之源。臣等再四思維,擬懇天恩,俯念此事保疆以練兵為急務(wù),籌餉以商賈厘稅為大宗,洋款若停,牽動內(nèi)地厘金,亦礙華民生計,轉(zhuǎn)于餉需有損,京餉及北上諸軍餉需無從接濟,關(guān)系尤大。可否飭下戶部,通盤籌計,俯準暫行仍照舊案解還,以保餉源而維全局。俟數(shù)月后體察大局情形,再行請旨辦理。”(《會銜電奏》,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辰刻發(fā),《張之洞全集》第3冊,第2155頁)
奏中所提理由,均由朝廷立意反方向發(fā)揮,通篇強調(diào)“停解洋款”不僅不能如原預(yù)想的那樣增加餉源,反而影響內(nèi)地厘金等款項,嚴重有礙戰(zhàn)時餉需供應(yīng)。由于當時清朝借洋債均以關(guān)稅、厘金作為抵押,在東南督撫看來,若停還洋款,必導致各國出兵“力據(jù)海關(guān),分擾沿江沿海各省”,其結(jié)果是“洋貨不能入,土貨不能出,各省商販裹足不前”,不僅關(guān)稅“涓滴無收”,作為內(nèi)地商稅的厘金也將“因而大絀”。據(jù)當時估計,若東南各省也與外國開戰(zhàn),“洋稅全失,內(nèi)地稅、厘收數(shù)亦必十去五六,通盤核計,較之向解洋款轉(zhuǎn)受虧在千萬兩以外”。這種財源損失,當然是清朝所不堪接受的。
劉坤一等人發(fā)出會銜奏折后,自揣“準否難必”,心情一直非常緊張。至會奏到京時,天津已告失陷,清廷對外政策相應(yīng)發(fā)生調(diào)整。六月二十三日(7月19日)上諭竟“著所照請,仍照案按期解還歸款,用昭大信”。由“洋債不還”引發(fā)的一場意外風波,暫告平息。劉坤一等人懸著心才放了下來。
不過,中間仍發(fā)生一段插曲。廣西巡撫黃槐森個性保守,原不以“東南互保”為然,此次會奏也未列銜,事后又奏請維持原議“停解洋款”,對劉、張等人多作譏彈。該電奏經(jīng)由山東濟南轉(zhuǎn)奏,山東巡撫袁世凱為經(jīng)手人,他深知此電“與東南大局甚有關(guān)系”,于是按下來電。而作為中國電報總局督辦的盛宣懷,當時利用控制電報系統(tǒng)的便利,一路追查,命沿途各電局將該電撤銷。(《盛宣懷致劉坤一張之洞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義和團運動——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第141頁)
劉坤一也意識到此奏致命,“幾欲擾亂全局”,但他的考慮更為慎重,認為如不轉(zhuǎn)遞電文,將來黃槐森以隱匿奏劾,引起朝廷詰責,反而無以自解,于是一面示意不必追撤,仍請照轉(zhuǎn)(《寄袁中丞》,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五日,《劉坤一遺集》第6冊,第2581頁),一面與張之洞緊急商議,密函在京中軍機大臣榮祿、王文韶,囑托“力為主持”,“奏明將原折留中不發(fā)”。
前引《庚申史料》中庚子七月初五日電文中所謂“先致榮、王兩相公函,自是穩(wěn)著”,便是劉、張溝通中樞的明證,劉坤一“擬稿電請慰帥馳遞”,此處“慰帥”即指袁世凱,在消弭“停解洋款”后患方面,東南各督撫互通聲氣,全力合作,構(gòu)成“東南互保”的重要一環(huán)。最后為此事解圍的是由廣東北上抵滬的李鴻章。李鴻章在兩廣總督任上時,黃槐森受其節(jié)制,他聽說此事后,立即電告袁世凱不必轉(zhuǎn)遞黃奏,并知會署理兩廣總督德壽,對黃槐森予以申飭。停解洋款之議,終于不了了之。
事過境遷,至1900年八月初旬,劉坤一致各省督撫、各海關(guān)道電稱:
“據(jù)江海關(guān)道電稱,八月洋款,還期在即,各省關(guān)派款未解者甚多,滬關(guān)稅收減色,萬難籌墊。際此時局艱危,更不宜失信,再滋口實,乞迅電各省起解湊撥,共維大局,等語。務(wù)祈迅賜解滬,免致藉口,另生枝節(jié)。切禱!盼電復(fù)。坤。”(《江督致各省督撫關(guān)道電》,庚子八月初八日申刻發(fā),《庚辛史料》,第82頁)
此時八國聯(lián)軍正占據(jù)京師,兩宮倉皇西狩,中外戰(zhàn)爭形勢已然逆轉(zhuǎn),清朝一時似成“無主之國”。而經(jīng)歷風波之后的南洋大臣劉坤一仍以“不宜失信”為理據(jù),竭力維持著南省海關(guān)解還“洋款”的慣有秩序。這一幕稍顯扭曲的歷史圖景,也正體現(xiàn)了庚子事變復(fù)雜性質(zhì)的一個側(cè)面。
(作者系復(fù)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