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丁修真評《人在棘闈》︱誰的科舉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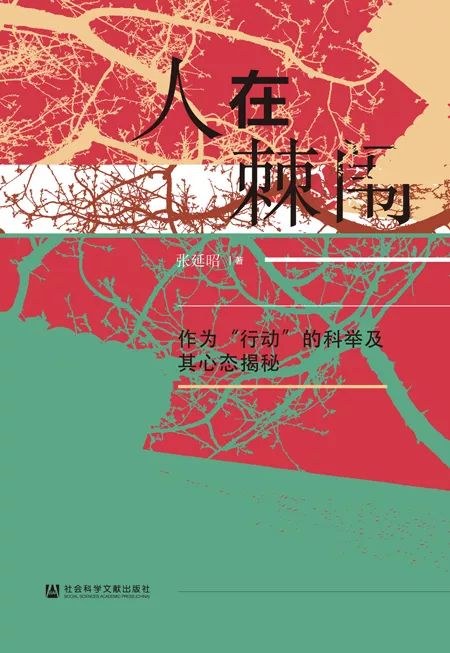
《人在棘闈:作為“行動”的科舉及其心態揭秘》,張延昭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2月版,391頁,148.00元
科舉史上,有一則耳熟能詳的故事:唐太宗微服出訪,走到宮廷南面端門時,恰逢新科進士連綴而行,魚貫而入,熙熙攘攘,熱鬧之極。見此景象,皇帝喜上眉梢,說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的故事很短,但卻由此開啟了此后長達一千多年“英雄”們的故事。
北宋嘉祐二年,歐陽修時主文省試,出題“豐年有高廩”,謂出自《大雅》,其實為曾鞏詩,結果“舉子大嘩”,歐陽修也是遭到御史彈劾,最終被罰銅五斤。
明代,某科鄉試之前,兩為平日交好的秀才,相約同赴考場。考前一日夜,其中一人將同伴擬用謄真之筆尖嚼去,以致該考生在場中無法應詩,恍惚之中,幸虧得神人相助,以禿筆應完卷,后竟得高中。
清同治年間,翁同龢出任會試考官,鎖闈后發現日常供煤不夠,過了幾日,日常供水也出現問題,一度逼得考官們“伐樹為薪”,自立更生。
直至科舉廢除,“故事”中斷近半個世紀后,清末探花商衍鎏在自述中,記憶猶新的,是“炊煮茶飯靠對號墻,至為逼仄;況復蚊蚋嗜膚,薰蒸烈日。巷尾有廁所,近廁號者臭氣尤不可耐”。
以上幾則小故事,匯集成輯,大概可冠以科場典故之類的標題。今日視之,又以其碎片瑣憶,似更難博通人一笑。然而誠如學者所言,非碎無以立通。能夠在雜蕪叢脞之中,拈得一千古通透的命題,不正是歷史工作者的職責所在?張延昭教授新著《人在棘闈:作為“行動”的科舉及其心態揭秘》(以下簡稱《棘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進行的正是這樣一種嘗試。
《棘闈》共分導論、序篇、正篇、末篇(結語)四個部分。序篇“表征與規訓”,旨在介紹全書的理論依據,正篇“人在棘闈”分為四章,分別就考官與考生兩個群體,描述其入闈、在闈的活動與心態。張延昭教授教育學背景出身,在書中,充分借鑒了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理論學說,尤其參考了法國學者福柯《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的相關概念,對科舉史中常用的貢院、科場、棘闈等表述的內涵加以重新審視,其論述,既與筆者熟悉的歷史學路徑不同,也與當下教育史的通行觀念有別。
何為貢院?
在一般人眼里,貢院,就是科舉時代的考試場所。事實上,除中央外,地方貢院的興建,可能要遲至南宋時期,此前士子應試大都借于官舍、寺廟等地。即使朝廷出臺了規定,各地具體實施的情況也很難統一。明清時期,仍可見不少地方借寺廟、官舍考試的事例。清順治初年,山東一地鄉試,仍以蘆葦草棚搭蓋,可見雖有其制,地方限于財力,往往難副其實。因此在一般的科舉史敘述里,不太會將貢院單列,往往一筆帶過。倒是隨著近年來,各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熱潮的興起,貢院遺址遂成為科舉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式,受到各級政府頗為重視的資源。一些學者就地方貢院的發展、貢院修繕的經費來源做了討論。
《棘闈》的作者則認為,貢院并不單單是一個考試的“場所”,更是一個具有政治意味的“表征”。其建筑空間的布局,時刻傳達著諸如“大一統”“至公”的政治理念。例如,“貢士于天子”這樣的表述,本身代表著地方對中央的服從,“明遠樓”“至公堂”“衡鑒堂”的命名與設計,分別傳達著國家“求賢”“取士”“至公”的理念,而掛在貢院門口那些看似裝飾用的門楹對聯,則時刻起著對士人、考官的訓誡作用(29頁)。作者認同英國學者薩迪奇對于建筑“是統治者用以引誘、感召以及恐嚇的工具”(第3頁)的定義,將貢院不再視為功能性的建筑,而是一個需要被“解構”的空間。
不過,如果只是將貢院的“至公”表征加以剖析,多少有“炒冷飯”之嫌。畢竟科舉制度所體現的公平公正理念早已為人熟諳。即使在那些激烈批判科舉桎梏人心智力者眼中,科舉對于促進社會流動,實現社會公平的功用,仍持肯定態度。即使如一度被唾棄的八股文,也因有利于考官公正評閱,而獲得了政治正確意義上的“解放”。
顯然,作者的意圖并不僅限于此,在主體沒有更換的前提下,“貢院”的敘事開始轉向“棘闈”。
何為棘闈?
在作者看來,區別于貢院、科場等概念,棘闈不僅能夠體現此空間使用者微妙復雜的心緒,更能夠體現科舉考試的兩大特點,封閉性和防范性。如果說“貢院”體現的是科舉追求“至公”的政治表述,那么“棘闈”更關乎支撐這樣一種理念的技術與行動。作者認為,在“棘闈”中,充滿著“現代性的時空建構”,闈中的時間得以細致劃分和利用,闈中的空間被人為的改造、化解、分割。以“封閉”“隔離”“監督”為特征的“規訓空間”被制造了出來(54頁)。歷史上逐漸形成的“鎖院”“內外簾官”“考生分號”等制度性規定,正是規訓意義不斷強化的體現。隨處可見的高墻,層層圍合與分割出一座嚴密防范意味的封閉式建筑群,空間圍場一旦建立,有待訓練與監視之“個體”將確定分派(37頁)。
這樣的分析表述中,可以明顯地看到福柯的影響。福柯認為規訓的達成,需要四種個體的形成,即單元性(由空間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機性(通過對活動的編碼)、創生性(通過時間的積累),組合性(通過力量的組合)(福柯《規訓與懲罰》,三聯書店2003年,188頁)。在“棘闈”之中,號舍無疑是最能體現“規訓”的制度化設計。號舍為士子應試作文的“空間”,屋頂蓋瓦,每間隔以磚墻,無門,高六尺,舉手可及檐,舍內砌成上下磚縫兩層承板,板可抽動,日間寫字,夜間抽上層入下層,伸足而臥,飲食皆在于此(69頁)。眾多應朝廷“求賢”而來的士子,在完成點名、搜檢等程序后,入場方能知曉自己的號舍,一條號巷被分割成幾十、上百間,每間號舍就是一個格子,每個考生都被鑲嵌在一個固定的位置,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相應的試題。無門的敞開式建筑,使得考生一切行動均暴露在他人監視之下。一排排低矮的號舍,與高聳的明遠樓形成鮮明的對比,顯示著“規訓”與“被規訓”的權力結構(49、52頁)。
讀者可能會有疑惑,福柯借助規訓,意圖在于來揭示現代文明對個體的剝奪和壓迫,科場之中,“規訓”的依據又何在呢?對此,作者的答復有二:其一,“棘闈”其實是中國傳統思想觀念中“幽暗意識”的集中體現。貢院本身就是各種不信任,是通過制度化的空間建構來進行防弊而建構起來的空間(66頁)。在其背后,充斥的是以富貴誘人、消弭社會不服從因素的統治者的考量。正因為如此,求賢反而無禮,求公反而無信。其二,作者似乎對時下科舉研究中的主流話語并不“感冒”,對那些“平民開放”“抑制權豪勢要”的論斷頗有些隔膜,而更愿意從“微觀行為主體”的角度,來評價科舉(67頁)。
人在棘闈
至此,作者的寫作意圖已經很明顯。其要關注的,不是大寫的“公”字,也不是科場中那些“規訓”的表征,而是那些在“規訓”的空間中,實實在在的個體。這些個體,可以分為考官與士子兩大類,他們的感受,他們的“逸事”,便不再只是筆記小說中的斷篇殘簡,而成具有“目的、手段、條件和規范”構成的規訓實踐。所以在全書主要內容正篇“人在棘闈”中,作者分列四個章節來處理那些看似相當瑣碎的科場細節。
先來看考官。考官是“棘闈”之中握有話語權力的群體,國家為體現掄才大典的莊嚴,于考官入闈也是極為重視。根據《大清會典》的記載,各省鄉試官,可以根據道里遠近,出發前由戶部支給相應的路費盤纏,入闈有明確的儀仗規定。每逢鄉試之期,考官所過之處,往往也會引發“人山人海”,“立觀者欣羨不已”的盛況。作者則注意到,在極盡顯赫的排場背后,考官更是一個功能齊備、分工嚴格、等級分明的群體,往往呈現出榮耀、激動、恐懼多種復雜的心態(133頁)。擬題有風險,考官會因出題不當而遭到皇帝奚落、士子嘲諷,乃至丟官革職。清代皇帝往往以帝師自居,《棘闈》援引雍正皇帝將考官行徑與考題內容結合審查之例,揭示考官亦是待考之人的窘境。衡文有壓力,書中所引周敘于正統九年主持順天鄉闈的事例,頗可見閱卷工作的繁重:一千二百余名士子,六名考官,三場下來,一人在十五天內,大概要審閱六百余份試卷,一天計之,也要在四十至五十份之間(明制,科舉考試,頭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等一道,三場時務策五道),以致最后“生殺機關都不管,手如雨點白珠跳”。至于考官在闈所面對惡劣的居住環境,隨時而來的病痛等,書中都有詳細的描述,在此不贅。作者通過考官們入闈前后的反差,意在說明其衡文過程,也是在棘闈這個狹窄的空間里,在嚴格制度規訓下的行動,甚至還要面對社會輿論的壓力,面對罰俸、丟官甚至喪命的結局,故其所受規訓與蜷縮在號舍中的士子并無二致。
至于士子,入闈之前,必須經歷的“點名識認”與“搜檢懷挾”便是難以言語的苦況。作者的有心之處,不僅在于羅列具體的描寫,更注意到古代士人對“名”與“身”的自我標識與遭受吏卒“點名”與“搜身”規訓間的緊張。例如直呼其名氏,在士子看來往往視為對本人縱慢侮辱的之舉。唐進士李飛,就禮部試賦,因吏大呼其名,熟視符驗,感覺受辱而徑返江東。至于搜檢,作者認為宋明理學在傳統禮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身體的人倫觀,自蒙學起,便有對身體行動的嚴格要求,“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們之間,比如同窗、朋友,也只是拱手、鞠躬表示一種誠意而已,盡可能避免身體之間發生接觸,從而保持身體上的獨立”(117頁),在這樣一種教育觀念下成長的士子,面對“摘帽去履,解衣露體,被其由上至下、由外至內進行細致拿捏,甚至搜及褻衣”的規訓,或俯首帖耳,或憤然離場,乃至反抗。
進入號舍的士子,似乎只需面對智力上的考較,但在作者看來,這恰是科舉士子群體性“失語”的開始。“失語”表現為大多數記載往往只呈現士子服從考場紀律的狀況,而非其具體的行動,即使考生事后回憶,內容也大多簡略。為此作者翻閱大量清人日記,盡可能地拼湊出士子所在的規訓空間。首先,號舍是一個被給予的“位置”。這樣一個隨機的安排,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考生十幾日的命運。寬敞嚴實的老號猶如“肥缺”,有助于文興,若碰上臨近廁所、廚房,或是漏屋篷號,則如畏途險境,甚至棄考。其次是號舍中的標配,號板。號板是考生坐臥寫作乃至飲食的主要工具,在棘闈中,號板數量不夠,質量低劣的事件時有發生,為士子所苦。然后就是天氣。鄉試雖稱“秋闈”,但在南方地區,低矮且不通風的號舍中,士子往往要與潮悶酷熱斗爭,若遇陰晴不定的時節,更是要經歷暴熱至暴涼的煎熬,同治六年順天鄉試,病暑者十之五,死號中四十余人。此外,尚有如飲水、污卷等對于號舍士子應試的影響,作者也多有描述,在此不一而足。總之,作者希冀通過對士子號舍中身體與心理的探究,來揭示縝密制度運作下舉子的真實感受。在作者看來,棘闈本為朝廷表征求賢取士的禮樂空間,但在現實中,士子在不斷地規訓中,產生了嚴重的被剝奪感與失敗感,進而對科舉本身產生了懷疑,“若不是廣寒梯跌了腳,蓬瀛路迷了道,郁輪袍走了調,因甚價年年矮屋中,喚不醒才子英雄覺”。這樣一種揭示,正是作者試圖為科場中的“失語者”發聲。
誰的科舉史?
如果要指出該書存在的一些缺憾,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把握上稍顯不夠。例如考試群體方面,考官的評卷、閱卷過程,如張連銀《明代鄉試、會試評卷研究》(西北師范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中便曾有過很好的分析,考官入闈前后的情境,陳時龍《崇禎元年會試考釋——讀明人蔣德璟〈禮闈小記〉》(《中華文史論叢》2016年第4期)有相當細致的分析。另外從作者熟悉的時段來看,主要集中于唐宋和晚清,以致遺漏了一些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元代的情況,申萬里《秋闈校藝——元代鄉試的過程》(《元后期政治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文均未曾寓目。而宮崎市定先生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為日本民眾所寫的《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盡管為通俗讀物,但該書的寫作思路,實與《棘闈》有相合之處,作者似也未有參考。不然,自可使全書增色不少。當然,由于作者并非史學專業出身,這樣的要求或許有點吹毛求疵。
也正因為如此,筆者讀后觸動較深的,倒不是作者能夠在各類專業語境與科舉場景之間嫻熟的切換,而是在書中拋出了一個關乎史學的命題。作者在書中對于福柯的參考,并非是要建立起一套有關科舉的規訓理論,而是要借此來關照那些在棘闈之中的“微觀權力個體”,將科場“求賢”“至公”背后的“幽暗意識”還原成一個個被規訓的個體行動,以此來關注那些“失語者”在棘闈中的真實境況。故從此意義上論,《棘闈》一書,更多的是為科舉史上的“失敗者”立畫像。在科舉史中,成功者畢竟只是少數,僅以明代為例,據學者統計,大概產生了十余萬的舉人,但成為進士者只有兩萬多人,終身不獲一第者在八萬人之多,遑論數量更為龐大的生員群體了。而也正是這些科場上的失敗者們,構成了“棘闈”運作的主體。“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如果借用馬克思的這句話來提醒我們注意科舉史的主體問題,《棘闈》一書無疑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此外,如果結合近年來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一個趨勢,是“從‘事件’到‘事件路徑’,從‘人物’到‘群體傳記’,從‘典章’到‘制度運行’,使研究者的關注對象從事件原委、個人行為、制度規定本身延伸開來,進而關注其背后的社會關系和制度互動,關注其文化意義”(鄧小南:《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頁)。從制度到人事,《棘闈》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科舉制度研究深化的一個方向。如果暫時拋卻制度背后的那些“幽暗意識”,《棘闈》可以視為一幅生動有趣的考試繪畫長卷,兼具學術性與普及性。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