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津街3號與北京飯店之爭:60年前中國科學家對科研體制的諫言

文|王揚宗,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北京文津街3號從1950年到1966年是中國科學院的院部所在,而北京飯店則是中科院學部成立大會(1955)和第二次學部委員大會(1957)的會場,因而在會議期間被一些學部委員視為代表學部或學部大會。1957年5月下旬第2次學部委員大會,正值整風鳴放熱火朝天之際。院領導遵照黨中央的部署,發動與會專家多提意見。會議的氣氛特別熱烈,不少專家就學部的定位、中科院體制、中科院與高校等其他科研系統的關系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見。這些意見大都發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重要報刊上,現在已成為我們了解當時科技界狀況的一手資料。這里僅就討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即如何處理中科院的黨政領導與學術領導的關系(可稱之為文津街3號與北京飯店之爭),以及科研管理等問題的討論,作一些簡單的介紹。其中的一些討論,至今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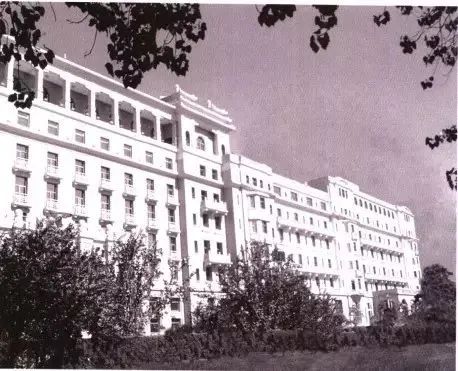
一、關于領導體制
著名植物生理學家湯佩松(1903-2001)在生物學部的會議上放炮最響,他針對科學院的體制問題發表意見說:“科學院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人在專門搞‘科學’,而另一部分人則在‘辦院’。辦院的人辛辛苦苦,關著門搞,搞得機構重疊,形成了墻。這些人在領導誰呢?不僅不能領導全國,恐怕院內各所也未領導好。另一種領導需要拿出工作,來讓人家看齊,而不是發號司令。這種領導不在文津街3號,而在這兒——全體學部委員。我希望有人在大會發言時提醒一下文津街3號的先生們,領導全國的科學院不在文津街,而在北京飯店——學部大會。……領導科學不要做行政領導,而是要每年召開一次學部委員會,由院長做一個報告,向全國人民指出全世界的科學水平,我國的科學水平和急需要發展的學科,這就是中國科學院的任務。做過這個報告的院長,應當是由大家推舉出的,真正做研究工作的人,而不是空喊口號的人。”
湯先生還指出:“科學院最大的缺點是……把科學機構辦成了衙門。科學院應當成為一個科學家的民間組織,民營合助,院長由科學家們所選舉的能代表大家的人來做。行政人員是由科學家們請來幫助工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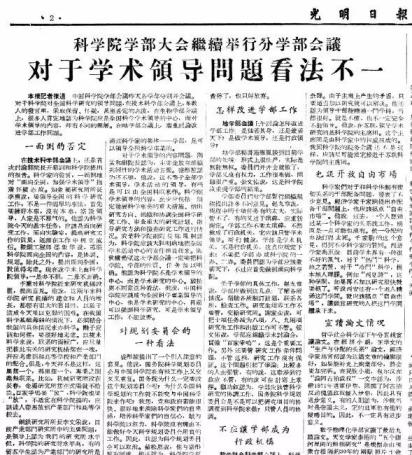
著名的實驗生物學家朱洗(1900-1962)也對領導體制和管理問題提了些意見,他說:“領導不是內行,不能順利地進行工作。科學院要不是在過去中研、北研的基礎上繼承下來,現在也不知道會鬧成什么樣子。”
植物生理所所長羅宗洛(1898-1978)也對領導體制有意見,他說:“院務常務會議是傀儡,學部是裝飾品,去年報載成立北京植物生理研究室,問竺可楨、童第周、貝時璋等,都不知道。”
醫學家吳英愷(1910-2003)建議加強學部委員等專家的權力,他指出:“以解放初期民主黨派參加國家大事的姿態來參加科學領導活動,是不夠的。學部委員的權力要加大,要起監督與推動作用。”
地質學家張文佑(1909-1985)說:“院務會議局長參加,所長不參加,院與所的情況怎么能聯系起來?”
1955年回國的化冶所副研楊紀珂(1921-2015)說:“做官的人以為科學的發展必須在會議中產生。我們認為必須在實驗室中做。現在官風壓到了學風。……秘書長很多是黨員,各所還有副所長,把科學家像牛一樣牽了鼻子走,用意是幫助科學家,到底幫助沒有?我不知道。”

沈陽金屬所所長李薰(1913-1983)說:“科學院是外行領導內行,任務與能力矛盾。科學院黨有宗派主義,為了加強領導,就加人,但量不能勝質。秘書長有很多個,做太上局長。官僚主義,忙于開會,不做實際工作。科學院黨政不分,黨內商量好,黨外來執行,干涉所長權力。”
哲學所副所長金岳霖(1895-1984)建議:“1)學部大會應在院部之上,好像人代大會,院部是經常辦事機構。2)院部要加強各學部,其他各局廳合并成一個總辦公室即可。3)學部常委應選舉輪流擔任,兩年一次,當選者脫產,以免掛名不做事。”
金屬所師昌緒(1920-2014)研究員說:“我們批評美國的民主,是兩個壞蛋中選一個。蘇聯是從一個選一個。我們學蘇聯,民主是形式,是假的,是委派。”
金屬所郭可信(1923-2006)研究員認為:黨與行政不應有兩套。黨能管,不必有行政。行政能管,黨就可以不要,精簡機構,兩套減一套。民主黨派也可以取消。
著名化學家黃鳴龍(1898-1979)主張由研究員輪流出任院長和所長。他批評科學院階層森嚴,以“長”為貴,不以研究人員才力為尊。他說:”現在科學院中不但最高科學行政領導,就是各所內若干所長副所長也是因為多年不做研究工作,甚而至于多年不能閱讀各國的科學報告。我深恐他們鑒于院內甚多以資格或社會活動求得名位,并非以才力及研究成績而受尊崇,同時院中也不要求做研究工作,于是便安于‘長’的位置,可希逐漸增高資格,一方面也樂于社會活動,借以求名。這種現象和風氣如果長期存在的話,我們如何能有希望提高科學水平,如何能向科學進軍!”他提出:“萬勿以‘長’為尊,必須以研究成績為重,勿以老資格而應以才力為貴。最好恢復從前的條例,即以研究員為主體,研究員才可兼所長或院長。最好照從前德國各大學的辦法(現在各地如何不得而知),即大學中以教授為尊,至若校長是各教授輪流兼任的,任期三年。”
二、關于科研管理
朱洗指出:“院內有一套龐大的行政機構,忙亂得很,但做的工作不多,形成文牘主義與官僚主義,而下面也窮于應付。只要一個人在誠心誠意地為科學服務,則領導不檢查也無關系。現在的情況是領導上相信科學家不夠。院應該相信所,所相信工作組,工作組相信每一個工作同志。……行政人員可大大減少,人多了反而更亂。”
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1904-1998)認為科學院需要“精兵簡政”,他說:“這幾年來,科學工作者中間有一個普遍的感覺:時間不夠用。時間哪里去了?……很忙,但是忙不出一個名堂。老是在圍繞研究工作打轉,可沒有足夠的時間用在研究工作本身上。為什么呢?工作開始之前有一套:計劃,布置,推動。工作了不久之后又有一套:檢查,總結,匯報。接著又要重計劃,重布置,如是周而復始。總結有年度總結,半年總結,過去還有季度總結。匯報,在不久之前,學術秘書處要每月匯報,學部要半月匯報,有時候還要到院務常委會議去做大匯報。檢查,除了為總結作準備的檢查外,每來一個重要的學習或是運動,也都要結合著檢查工作。……就因為形式主義地進行這些工作,就形成了開會多,填表多,寫文件多,繁文縟節占去了不少應該用在研究工作上的時間,并且打亂了研究工作所必需的穩定的進程。……總之,科學院機構龐大,人員多,花樣多,可是效率不高。……這次學部會議上要討論科學院的體制問題,是不是可以從“精兵簡政”這方面著想,做到(1)機構靈活,(2)人地相宜,(3)明確責任,(4)減少繁文縟節。要是能根據這幾條原則辦事,我相信科學院工作效率是能大大提高的。”
黃鳴龍也認為,黨和政府對科學院十分信任,但“院里仍不免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致使科學家費去無數的寶貴時間參加不可實行的會議,做了無數的不能照做不能準確的計劃(因為時間、人員、工具、經費都不能掌握)”。他舉例說:“去年院中竟限令我們幾天內完成十二年科學計劃草案(到后來才由國務院延長幾個月),我當時即大聲疾呼不可如此馬虎行事,但院中置若罔聞。”他指出:“種種偏差出之于不懂科學的干部尚可原諒,但是出之于有職有權的極易向黨政建議及糾正偏差的曾走上過科學路線的自然科學行政領導人員,實在令人難解,是不是明知故眜一意迎合我不敢斷言,不過我想我總可以拿此來相勸勉。假如覺得我的建議和批評有不合理和太主觀的地方,請勿視為惡意或認為牢騷。”
此次會議上,體制問題一時難以解決,但對大家都深有同感的保障科研時間問題,在此次大會的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千家駒(1909-2002)等27位學部委員提出的一項提請院部采取具體措施以保證學部委員及其他高級研究人員有充分時間進行科學研究的提案,并同意將該提案送請國務院研究辦理。該提案建議院部與有關部門協商,采取適當措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保證每一學部委員及其他高級研究人員均有充分時間從事研究工作。其中提出的辦法包括:
一、與統戰部及其他有關方面協商,切實減少科學家的社會政治活動。具體辦法是:
(1)人民代表或政協委員,不論全國的或地方的,每人總共至多擔任一職;
(2)外賓招待工作,每人以一個方面的對象為限,應堅決改變過去將此項工作集中于少數人的情況,赴車站、飛機場迎送外賓,應盡量減少派科學家前去;
(3)對于科學家,應盡量減少他們不必要的集會,有些大報告(如布置某項運動的動員大會,人代、政協會議的傳達報告會等)可用書面文件代替者,即分發文件,而不必舉行大會;
(4)經常性社會活動的集會,應嚴格規定在每周的一定日期舉行;
(5)臨時性的集會,在通知上應寫明會議內容,科學家認為沒有十分必要參加的,或已參加過類似性質會議的,可以不參加;
(6)開會及做大報告時間應予嚴格限制,開會一般最多以三小時為限,做大報告以二小時為限;那種內容貧乏、空話連篇或背誦文件的報告,聽眾有隨時退席的自由;
(7)對于60歲以上的老科學家,最好解除其一切行政職務,讓他們利用自己僅有的十年二十年寫出他們所知道的東西。

二、切實保證每年固定的研究時間,并減輕或解除行政職務(包括學術性的行政職務在內)的負擔,其辦法如下:
(1)每一學部委員或其他擔任行政職務的高級研究人員,每年至少應有六個月連續研究的時間或上下半年各有三個月連續研究的時間,在此期間,他們應被允許不參加其他任何社會政治活動(可向有關方面請假);
(2)科學研究機關、高等學校或國家機關的行政職務,在正副主管人員間,應采取輪流負責制,以保證在每年的固定研究時間內專心從事研究工作;
(3)應該建立工作五年休假進修一年的制度;
(4)對在高等學校擔任教學的學部委員,應避免使他們負擔過多過重的教學任務和指導研究生的任務,以保證他們有必要的研究時間
專家們的意見很多,有的非常尖銳,這里就不多摘抄了。從他們的意見看,中科院建立不久,在領導體制和科研管理方面的問題就已相當突出。本來建立學部是要發揮專家的學術領導作用,但由于那時從上到下執行知識分子政策都比較左,對科學家并不放心,學部的性質和定位因此難以明確,沒有從體制上解決好黨的領導、行政領導與學術領導的關系。實際上這些問題也引起了院黨組的高度關注,曾期望通過制訂院章加以明確和解決。但一個多月后就轉入了反右運動,學部大會上的許多意見被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遭到嚴厲的批判。盡管由于院黨組有意保護科學家過關,絕大多數專家沒有因為這些意見被打成右派,但他們反映的問題也不再受到重視。在后來的半個多世紀里,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再也沒有觸及過,致使有的問題甚至延續至今。
當然,關于我國學術治理體制的問題,在當時和如今都不是科學院一家的爭議,事實上,這一問題在某些系統更為突出,但身處其中的科學家們卻鮮有表達意見的機會。第二次學部委員大會過去60年了,但在協調黨政系統與學術系統的關系、克服學術行政化和改革科研管理方面,我國科技界和學術界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在當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勢下,重溫這些前輩專家學者發自肺腑的諫言,仍有振聾發聵之感,值得人們深思。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文津街3號與北京飯店之爭”為題發表于2015年8月21日《中國科學報》。此次刊發,作者作了增補和修訂。此處轉自 科學春秋 公眾號)
原標題:《文津街3號與北京飯店之爭:60年前中國科學家對科研體制的諫言》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