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對話】施傳剛: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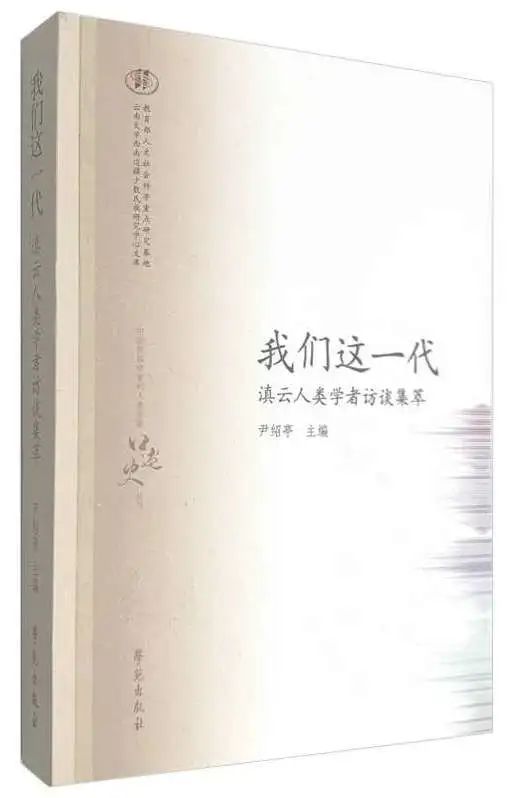
本文摘編自《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施傳剛,男,1951年生,云南大學歷史學學士、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碩士、博士。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以及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等院校和機構從事研究或教學工作。現在佛羅里達大學人類學系任教。
采訪者:趙翰超,美國佛羅里達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研究生。
從歷史學轉向人類學
趙翰超:這篇訪談錄的題目是您定的。是否可以請您先談談為什么用這個題目?
施傳剛:你一定知道,這是《中庸》里摘出來的一段語錄。我是云南大學歷史系七八級的本科生。1982年畢業前夕班里決定做一個同學錄。我當時并沒有現成的座右銘,就從自己更年輕時做的讀書筆記中選了《中庸》里的這段話作為印在同學錄上的座右銘。我從來沒有刻意遵循過某種指導思想,平時也沒有經常溫習四書五經。但現在面對自我總結的任務時,我驚奇地發現,幾十年來在我追求知識的道路上,下意識中引導我的竟然一直是這段話表達的理念。今天看來,談到治學,我最服膺的還就是這15個字。所以我覺得就用這句話來做這篇訪談錄的題目是非常合適的。
趙翰超:您剛才說您的本科是歷史專業。您是怎么會從歷史轉到人類學呢?當時中國就有人類學嗎?
施傳剛:中國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是世界上研究文化人類學的四個重鎮之一(其他三個是美國、歐洲和日本),但是在50年代初就中斷了,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才陸續恢復。80年代初,只有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有人類學專業。我是到美國以后才讀人類學專業的。
趙翰超:您又是如何到美國的呢?
施傳剛:在我大學三年級時,我從短波廣播中得知美國國際交流總署在中國的7個省圖書館中放置了美國各級大專院校的介紹,鼓勵有志于到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前去查閱。云南省圖書館剛好是提到的7個圖書館之一。1981年的中國還非常封閉。見到大量美國學校的介紹堆在自己面前,就像無意中推開了一扇原先緊閉的大門,突然闖進一個新奇而又令人神往的園地。我們班最后實際報考美國學校的同學只有我和后來在康奈爾大學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的譚樂山。我申請了4所學校,兩所申請的是歷史,其他兩所申請的是人類學。結果很幸運,4所學校全都錄取了我,而且都給了獎學金。我就是這樣來美國的。
趙翰超:您申請攻讀人類學的是哪兩所學校?為什么選擇那兩所學校?
施傳剛:斯坦福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就人類學而言,美國的人類學系一般都注重自己陣營的多樣性和區域文化覆蓋面的廣度,而避免教授們研究區域和研究方向的重疊。當時全美國只有斯坦福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系各有兩位研究中國的教授。斯坦福大學有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和武雅士(Arthur P.Wolf);哥倫比亞大學有莫頓·H. 弗里德(Morton H. Fried)和孔邁隆(Myron L. Cohen)。他們都是非常杰出的資深人類學家。這就使這兩個系成為當時美國研究中國最強的兩個人類學系。
趙翰超:那您為什么選擇去了斯坦福而不是哥倫比亞呢?
施傳剛:我在云南大學讀本科時,省政府決定在云南省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組建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成立之初,云南省社會科學院亟須充實科研隊伍。從為本院吸引和培養人才的角度著眼,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所長鄒啟宇先生到云南大學歷史系講授東南亞史。鄒先生的學術視野極其廣闊。他在課堂上把東南亞研究領域中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各國學者都逐個向我們做了盤點。其中對施堅雅先生關于泰國華人的兩本著作做了重點介紹。可以說,從我剛開始接觸學術研究時,施堅雅的名字就在我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這是選擇斯坦福最主要的原因。我到現在都認為,我這一生最好的運氣就是有機會在斯坦福完成我的本科后教育。

2012-2013年訪學期間攝于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趙翰超:您還沒說您是怎么從歷史轉到人類學的。
施傳剛:在老舍的話劇《北京人》中第一次聽說過“人類學家”這個詞。那個劇中提到的人類學家是研究古人類化石的。少年時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上也讀到過費孝通先生的回憶文章,記敘他跟隨馬林諾夫斯基學習人類學的往事。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費先生的自我認同是社會學家。他當時努力推動的也是社會學在中國的復興。我當時和大多數人一樣,對什么是人類學毫無概念。真正把這個學科介紹給我的還得說是譚樂山。我們同學時,他十分偏好民族學和民族史。記得有一年暑假他完全泡在圖書館里,結果寫出一篇論文發表在中國民族學的最高刊物《民族研究》上。本科生就在學科最高刊物上發表論文,這在中國學術史上是非常罕見的現象。而他也告訴我人類學是一個比歷史學更廣闊、更有趣的學科。我記得他對我說,搞歷史就是翻故紙堆,而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包括人類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當然也包括歷史。按照他的看法,像我這樣興趣愛好廣泛、語言基礎扎實的人,人類學比歷史學更能滿足我求知的好奇心,也能更充分地利用我在古代漢語、英語、法語、德語等方面已經下過的功夫。他還借了一本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cliffe Brown)寫的關于社會人類學方法的書給我。我的這位同班同學就這樣成了我走向人類學的指路人。
通過和譚先生的交談以及閱讀,人類學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已經逐漸清晰起來。聯系到自己的故鄉是云南這個做人類學研究的寶地,到需要做決定時我就不再猶豫了。
摩梭文化研究緣起
趙翰超:您對摩梭文化或與摩梭文化有關的各種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您是怎么選中摩梭文化作為自己研究的題目呢?
施傳剛:這就說來話長了。前面說過,我來美國攻讀學位之前對人類學的認識非常膚淺,申請學校時必須提交一篇英文的寫作樣品,我就寫了一篇有關云南少數民族的多樣性和民族關系的文章交上去。我雖然生長在昆明,但基本沒有接觸過少數民族,感性認識并不多。文章根據的都是已經出版的二手資料。到臨動身到美國前,我想到應該帶一點有用的書過去。當時剛好有兩本關于摩梭的民族學專著新近問世了。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詹承緒、王承權、李近春、劉龍初著的《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另一本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嚴汝嫻、宋兆麟著的《永寧納西族的母系制》。兩本書我都帶到了美國。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系不招收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畢業生都可以申請攻讀博士學位。所以我一進去就算是博士生,但還不算博士候選人。進入博士班后要在第一學年結束時提交一篇被稱為“春季論文”的文章,由四位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后,才能獲得博士候選人的資格。如果通不過,獎學金和學生資格都將被取消。對我這個基礎極差的學生來說,壓力可想而知。
進入學習過程后,系里沒有給我絲毫緩沖適應的機會。教授們把所有學生一律當作最優秀的人才來要求。在那種巨大的壓力之下,在應付每學期功課的同時,我實在沒有余力為春季論文做廣泛的研究之后再定題目。在上一門有關文化性別的課時,我聯想到了從中國帶來的那兩本關于摩梭的書。根據兩本書一致的敘述,傳統社會中的摩梭女性享有比男性還高的地位。這和西方主流的女權主義對所有文明社會中都是男性占主導地位的論述不符。于是我就抓住這一點,又做了很多圖書館調研后寫成了一篇題為“A Challenge to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Male Authority over Female”《質疑男性普遍對女性擁有權威的概念》的春季論文。60多頁的論文總算是如期交了上去。話說到這里,還得折回頭去交代另一個頭緒。
除了春季論文之外,第一年我還得考慮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博士論文寫什么題目。有一次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圖書館翻閱資料,看到中國人民大學的一篇研究報告中提到,云南西部中緬邊境上的一個佤族社區和一個拉祜族社區在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一段25年的時間里人口增長呈現出巨大的反差。拉祜族的人口翻了4倍,而佤族人口卻呈現出負增長。我在為申請入學的寫作樣品做研究時就知道拉祜族和佤族的繼嗣制度和家庭組織不一樣。看到這個報告后就想當然地以為兩個民族人口增長的反差是繼嗣制度和家庭組織造成的。我的兩位導師武雅士和施堅雅都很重視人口問題,都是人口學領域中有影響的人類學家。他們對我的研究興趣有很大的影響。我找到這個切入點后非常興奮,認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有價值的博士論文題目。于是我寫了課題申請提交給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獲得批準后,我就利用第一年結束后的暑假回云南去進行前期調查。滇西實地調查的結果卻令我大失所望。原來人民大學報告中提到的佤族的人口負增長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原因造成的。真實的原因是,那個佤族社區就在邊境線上,居民在邊境兩邊都有親戚。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政治運動不斷。中國一側的佤族邊民往往利用地緣的便利,運動一來就逃過邊境。我被告知,有時村里各家各戶正在吃飯,聽說工作組來了,丟下飯碗就跑。工作組進屋后,矮桌上的飯菜還是熱的,人已經不見了。因為人口調查時這些跑出去的人無法計入統計數字,所以這一地區佤族的人口報表上才出現了顯著的負增長。而拉祜族居住的地方卻不具有這樣的地緣便利。所以不存在政治原因造成人口統計嚴重失真的情況。既然真實情況如此,比較拉祜族和佤族的人口與家庭制度也就失去了人類學的意義。我為尋找博士論文題目所做的探索又被打回到原點。
我懷著沮喪的心情回到學校并向導師報告了前期研究的壞消息。武雅士教授只是輕輕皺了一下眉,略微沉吟了一下對我說:“你何不就以摩梭作為你博士論文的題目呢?”說著他把我回中國前交上去的春季論文遞還給我,并告訴我論文已經通過了。我松了一口氣,急忙查看附在后面的評語。當時的系主任Harumi Befu(別府春海)教授在他的評語中寫道:“He already has a dissertation in the making.” (他的博士論文已經在寫作過程中了)。既然老師們的意見都是如此,我何樂而不為呢?這樣一來,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摩梭也就此成了我長期研究的對象。

2013年與合作二十三年的研究伙伴合影
摩梭文化的學術價值
趙翰超:從您開始研究摩梭文化到現在快30 年了吧?摩梭文化為什么值得您花費畢生大部分的精力?它的學術價值究竟是什么?
施傳剛:我是1987年10月第一次到永寧開展田野工作的。我研究摩梭已經超過30年了。我曾經在自己的一些中英文著作中從不同的角度討論過摩梭文化的人類學價值。如果你想比較詳細地了解,可以查閱那些出版物。這里我只是做一個簡要的概括。
20世紀60年代,摩梭文化剛進入中國民族學家的視野就立刻引起了轟動。這個案例的價值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學術研究。它被認為是為馬克思主義人類發展史宏觀學說的證據鏈補上了原先缺失的一環。簡單說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及其所依據的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理論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是恩格斯和摩爾根關于“血緣家庭”和“群婚”的判斷是根據推論而不是民族志的例證做出的。這就為后人質疑整個社會進化論的架構留下了很大質疑的空間。中國民族學家發現“永寧摩梭”的實例后,認為這個新發現的案例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進化論的證據就像猿人化石作為人類體質進化過程的證據一樣。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其重大意義自然不言而喻。我在這里重提這一點并不是為了回顧摩梭研究的學術史,而是因為你問到摩梭研究的價值,所以我想告訴你:摩梭研究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同凡響。還有一點想要告訴你的是,以不同的眼光可以看出不同的價值來。從更為廣闊的視角來看,80年代初出版的兩本關于摩梭的民族學專著確實在理論和方法的各個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局限性。但我們必須承認它們都是摩梭研究的奠基之作。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在內,后來的摩梭研究都繞不過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中國民族學家們對摩梭研究做出的貢獻(包括那兩本書和一系列內部流通的調查報告)。下面我再簡要歸納一下摩梭研究在我眼中的價值。

與云南母校學友和學生合影
全人類的任何一個文化都存在于變動不居的狀態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變化的速率會有快慢。變化的幅度有可能在很長的時期內都很微小,但文化傳統不會是恒定不變的。我們在估量一個文化的研究價值時,必須把文化變遷的因素納入考量。從20世紀50年代摩梭地區被完全納入中國大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以來,摩梭文化經歷了比此前可知的歷史性文化變遷的總和還要更大的變化。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摩梭地區也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卷入全球化的洪流。摩梭人的整個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過程也是摩梭文化和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趨同的過程。換一個角度講,也就是摩梭傳統文化的特征逐漸消失的過程。所幸我開始對摩梭文化展開全方位探索的時間是在80年代后期。雖然研究的條件已經比不上60年代進入摩梭地區的前輩民族學家,但我還有機會多年和大量對摩梭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并在摩梭傳統社會中有切身體驗的老人進行深入而廣泛的交談。長期的田野工作使我對摩梭的文化傳統積累了較為深厚的感性知識。對比摩梭文化的傳統和現狀,摩梭文化傳統的人類學價值當然要遠遠高于其現狀的價值。所以我所說的摩梭文化的人類學價值指的是摩梭傳統文化的價值。
概言之,摩梭傳統文化的特征主要體現在走訪制、沒有父系稱謂的親屬制(kinship terminology)、母系繼嗣、沒有婚姻單元(conjugal unit)的大家庭、女性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等方面以及與這些文化實踐相應的一整套意識形態。由于這些核心特征的相互作用,摩梭社會還有諸如人口發展率相對較低等其他一些附屬特征。在已知的人類文化中,摩梭文化是集中了上述所有特征的唯一的鮮活案例。正是這些獨特性使摩梭文化閃耀出珍稀的光芒。和其他所有文化一樣,摩梭文化是摩梭先民在不斷適應生存環境的過程中形成的。摩梭文化的存在說明其中體現的文化價值和宇宙觀對摩梭民族的合理性。在傳統時代,摩梭社會和外部世界很少接觸。由于崇山峻嶺的阻隔,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才有成批的外來商賈進入永寧。除了佛教僧侶出外求學和馬幫到外地經商以外,很少有摩梭人離開自己的家鄉。這些因素形成了摩梭文化長時期的穩定性。
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摩梭社會的分水嶺。自那時以來,摩梭社會和外部世界融合的步伐日益加快。全新的政治制度和生產方式被引入摩梭地區。摩梭人也通過參軍、上學、提干、勞務等各種途徑走出自己的家園。20世紀60年代初,民族學家開始在摩梭地區展開系統的調查。20世紀80年代末,電視開始進入摩梭家庭。2000年,摩梭人開始使用手機。現在,我工作了20多年的4個摩梭村落絕大多數青年或有過打工經驗,或正在外打工。分布的地區從內蒙古到海南、從深圳到麗江。有的摩梭人甚至到過緬甸、印度和北美。與外界的交流不可避免地會使摩梭人反思自己的文化。千百年來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外部世界的映襯下突然成了問題:“我們為什么和別人不一樣?”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人民共和國的不同歷史時期,摩梭人對這個問題的思索和理解經歷了曲折的過程。這一過程還在繼續。我們可以看到,摩梭文化本質中的獨特性在這一過程中已經悄然發生了巨大變化。舉最突出的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現象:我曾將傳統的摩梭走訪制的性質歸納為三點:非契約性、非義務性和非排他性。今天,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性聯盟,只有第一點,即非契約性,仍然適用于摩梭走訪制。其他兩點都已經成為過去。因為生活方式和家庭關系的改變,摩梭傳統文化中獨特的親屬制在現實生活中也發生了變化。父系的親屬關系和親屬稱謂都出現在日常生活中。從純學術的角度看,因為和其他文化制度日益趨同,摩梭走訪制獨特的研究價值也逐漸喪失了現實的借鑒意義而停留在歷史的和理論的層面上。(未完待續)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