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旅行作家劉子超:旅行是我的工作狀態(tài),很少有度假的心情
本文為鏡相欄目獨家首發(fā)訪談,如需轉(zhuǎn)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聯(lián)系。
采訪并文 | 劉成碩
不是詩歌,也不是小說或者別的什么形式,作家劉子超的選擇是旅行寫作。
這和在枯坐中就能實現(xiàn)的天馬行空完全不一樣。他需要對準溝壑縱橫的土地上,把自己毫不保留地空投下去。異鄉(xiāng)在發(fā)生什么,發(fā)生過什么,那里的人們在抱怨什么,期待什么。所有的命題沒有顯露的答案,全憑他徒手刨掘。
遼闊的中亞是中國的近鄰,也是不被注視的他者。很少有中國旅人前往。蘇聯(lián)解體后,那兒像失去引力的衛(wèi)星,涌現(xiàn)出失落之心和所托非人的希望。劉子超既是觀察者,又是被觀察者。當(dāng)他在中亞街頭,在車上,酒吧和餐廳里,向他們搭訕:你叫什么名字?你結(jié)婚了嗎?因為驚異于他孤身前來,很多人樂于奉上自己的故事。
他當(dāng)了多年記者,職業(yè)素養(yǎng)和敏感度都用上了。他知道上哪兒找人,如何吞下觀察到的一切,避開危險,把枯燥和索然無味轉(zhuǎn)化為持久的興奮感。
他推崇的是西方那些優(yōu)秀的旅行作家,保羅·索魯、奈保爾,擁有長達一生的探索精力和寫作熱情,到年老了依然走得動,寫得好。
劉子超出生在北京,成長過程平順,但咂摸起來始終有些寡淡。他記得高中時候全班坐火車去陜北玩,幾十號人擠在窯洞里過夜。那是2000年,那時候家長還不像現(xiàn)在的父母一樣,焦急地為孩子謀劃一個又一個開闊視野的機會。那次是他為數(shù)不多的少年旅行經(jīng)驗,再次憶起依然津津有味。他的外表看上去有一種沉穩(wěn)感,但自認為內(nèi)心不像外表看著那樣穩(wěn)。
2016年,“創(chuàng)業(yè)”像誘餌一樣在空氣里招搖。哪怕是文藝青年,也無法保持巋然不動的心。他只在那會兒搖擺過一陣子。“后來想通了”,他說,認清自己不適合干別的,“寫作掙不了大錢,也餓不死”。
他至少懷揣一樣自信。在同樣的領(lǐng)域中,恐怕沒有人能像自己一樣,愿意花費巨額的時間、精力,去制作一部充沛的作品。這是一項需要高投入度的工種,付出孤勇,才能交換得到迷人的故事。《失落的衛(wèi)星:深入中亞大陸的旅程》就是這樣得來的。
他記得在中亞的某些日子,午夜時分,自己被運送到一個新的地方,走出空曠的車站,外頭是一無所知的土地和夜空,只有一種廣袤的陌生感像攝魂怪一樣聚攏在他的腳邊,這個時候,一個天生的旅行寫作者會分泌出巨大的興奮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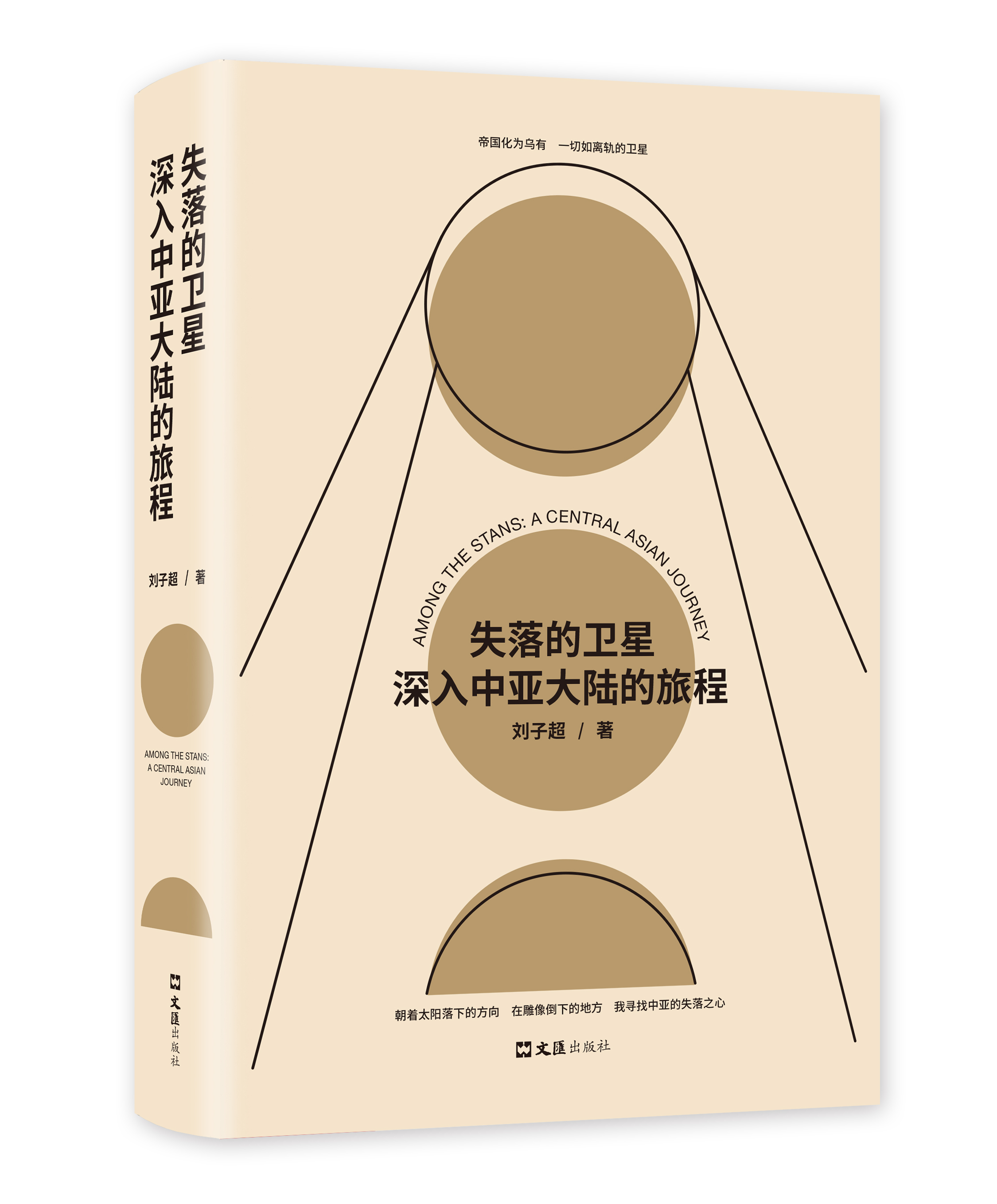
《失落的衛(wèi)星:深入中亞大陸的旅程》
劉子超 著
新經(jīng)典 出品
2020年7月
以下是鏡相欄目與劉子超的訪談:
鏡相:這本書是在9年探訪中亞的基礎(chǔ)上完成的,前后去了幾次,總共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第一次是2011年,去烏茲別克斯坦待了半個月。那次沒有任何計劃性,是偶然認識了一個烏茲別克斯坦駐北京大使館的一個人,他邀請我過去玩了一趟(后來這個人也與我失聯(lián)了,中亞就是這樣)。那次回來之后,我發(fā)現(xiàn)自己寫不了什么。
2017年,我自己又去了一趟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這當(dāng)中幾年,想去中亞很難,簽證辦下來難,也貴。如果不是有人邀請我,幫我辦好邀請函,過去是非常困難的,其他幾個國家比烏茲別克斯坦還難。到了2017年,簽證政策有松動,同時如果你乘坐哈薩克斯坦的阿斯塔納航空,經(jīng)阿拉木圖或阿斯塔納轉(zhuǎn)機,可以免簽72小時。我當(dāng)時正好從圣彼得堡回國,然后就坐阿斯塔納航空的航班到阿拉木圖,待了三天。
當(dāng)年10月我又去了一趟烏茲別克斯坦, 2018年再次去了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2019年,我用單向街“水手計劃”的資助基金又去了一次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是一直沒進去的,到了邊境也沒讓我入境。后來我在國內(nèi)又申請過兩次。一開始以為也許簽證官看我一個人去土庫曼旅行很奇怪,所以找了兩個朋友陪申,結(jié)果他倆都過了,我依然被拒。不知道為什么,沒理由。接下來如果這本書有幸再版,我想把土庫曼斯坦的部分補上。

鏡相:第一次去了以后,為什么會有寫不出來的感覺?
那時候我不了解中亞,完全不知道應(yīng)該把那里放在怎樣的維度上打量。當(dāng)你去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如果你想有把握去寫這個地方,首先得把它放到一個觀察的維度里頭,這實際上是長期積累了解的結(jié)果。直到后來慢慢了解多了,然后去的次數(shù)多了,我才能把它重點放到一個維度里,就是這個書名的提煉——失落的衛(wèi)星。中亞在歷史上經(jīng)歷過那么多復(fù)雜的變化,但自始至終都是在大的文明的邊緣,無論是唐朝、阿拉伯帝國還是蘇聯(lián),受著周圍更大的文明和勢力的影響,得出這個結(jié)論,我就有了觀察和寫作的角度,很多瑣碎的細節(jié)也可以包進去,并且有信心就算舍棄某些部分,也不會對我的寫作有任何影響。
鏡相:當(dāng)你帶著這種眼光去觀察,會不會像是在找素材去在印證你的觀點,這樣是否會過濾掉一些事實?
我認為我是了解之后的提煉,不是先入為主,我去并沒有預(yù)設(shè)任何立場,是把所有得到的東西歸納之后,寫作的時候提煉出來的思路。
鏡相:《失落的衛(wèi)星》里大部分內(nèi)容是你與當(dāng)?shù)厝私佑|、交談的結(jié)果。你在當(dāng)?shù)厥侨绾慰焖偃谌肴巳海c他們建立關(guān)系的,你怎么會有這樣的本領(lǐng)?
我其實沒這本領(lǐng),我只是比較善于觀察,在意細節(jié)。我以前是做記者的,跟采訪對象聊天經(jīng)常冷場,經(jīng)常不知道怎么發(fā)問,怎么接話,比較笨拙,但是我捕捉能力強。比如昨天下午和一個新朋友見面,我們倆聊天一個多小時的期間,我發(fā)現(xiàn)——他用的是蘋果電腦,戴著蘋果手表,穿一件優(yōu)衣庫的綠色 T恤,一條牛仔褲配Converse帆布鞋,他是92年生人,原本大學(xué)畢業(yè)想去中青報,沒去成,所以進了上海的一家媒體。他是那里年齡最小的人,他喜歡吃附近一家叫“弄堂小餛飩”的店……他或許隨口一說,但我會捕捉到并且記住。細節(jié)性的、生活化的東西看似不重要,而寫出來卻有意思,也更能跟讀者有一種親近感。
其實重要的不是我去談,是讓他們談。會傾聽是更重要的,不需要我像常規(guī)意義上的采訪或者電視節(jié)目上的對談,展示自己的聰明和機敏。那種感覺像是把自己往下沉,讓對方更主動。我問的問題可以非常簡單,隨便聊。我不是那種看上去有攻擊性的人,隨意的交談,對方不會有戒備心。有些故事也不是我主動問的,只是被我記住,捕捉到了而已。然后,我會跟有的人說我們再約時間,問對方明天有沒有一小時的時間跟我再聊會兒。奈保爾提到過,他可能采訪一小時,拿到六千多字的素材,就能寫出來1萬多字的稿子。其實就是在那段時間里,盡量捕捉更多的東西,然后把它的細節(jié)、紋路描繪出來。

浩罕小巷的賣馕少年(本文圖片除標注外均由劉子超拍攝)
鏡相:你會對哪些人做進一步的交談?
主要看能不能跟這個人做有效溝通,這很重要。因為大部分人接觸以后發(fā)現(xiàn)做不了有效溝通,我可能就放棄了,有的時候受限于語言,談不了很深的東西,也可能這個人不那么善于表達。也許十個人中有七八個人在接觸后我沒有再往下追,只有一兩個人是有意思的,他們會表達,有交流的渴望,他們的故事能反映出這個國家的側(cè)面。
旅行寫作與別的類型寫作不一樣。你怎么去掌控節(jié)奏,做到什么程度收手,感覺到“我對這個地方了解的差不多了”?
對一個地方的了解可能永遠都沒有到“夠”的程度,只能說夠自己寫。一般像中亞那種普遍規(guī)模的城市,如果能和至少四五個人做過有效交流,他們有不同的背景,反映不同的側(cè)面,我覺得能達到的我寫作素材量。中亞的城市大部分還是比較簡單,一般四五個人,你差不多能通過他們的故事把這個地方給解剖出來。但如果是孟買,上海或者紐約這種地方,那就遠遠不夠了。
鏡相:他們對你的好奇在哪?
他們之中很多人都沒怎么見過中國人。可能見過一些去中亞做生意的中國人,或者做基建的工程人員,像我這樣中國旅行者幾乎沒見過。烏茲別克斯坦有一些跟團游客,其他國家?guī)缀鯖]有。他們對我的好奇一般是,為什么來這里。因為他們沒覺得這有什么好玩的,你來干嘛呢?
其實大部分人很難做具體的發(fā)問。這有點不公平,當(dāng)我們站在發(fā)展時間線更快的坐標,去往時間線慢的地方,我是知道怎么發(fā)問的。如果我去了時間線靠前的那些地方,我覺得就不太好問,可能問出來非常荒誕,或者沒辦法提出切實的問題。比如他們問,中國人是不是都吃狗肉,或者以前看到過一個什么視頻,向我求證是不是真的。

鏡相:你抵達一個城市以后,行程是怎么規(guī)劃的?
一般從外部進入,肯定是先到首都,最大的城市,再一點點往下沉,中小城市,鄉(xiāng)村,最后再返回大城市。
鏡相:充斥在旅行之中的不適感怎么克服?有負面情緒的時刻多嗎?
沒別的,忍著扛著,不然還能怎么辦。吃得差的、洗不上澡的時候都有。條件上的艱苦肯定是旅行的一部分,是早就做好心理建設(shè)的。有人可能會有這種不適感,有一個哈薩克向?qū)Ц嬖V我,一個英國攝影師去哈薩克拍荒野,他必須要有西式馬桶才能上廁所,所以非常痛苦,到了荒野可沒地方給他找能坐下來的廁所。
有負面情緒的時候很多,比如坐十五六個小時的車,夜里一兩點到了一個陌生的小地方,之前訂好的旅館聯(lián)系不上,也完全不知道這個地方是什么情況。這時候站在街頭就會有點沮喪,也有點興奮。這種戲劇性的東西對旅行來說是悲慘的,對寫作來說又是好事。
有時候,一天下來沒遇到合適的人,沒找到值得寫的東西,連著好幾天都沒什么收獲,感覺自己進不去核心、一直在表面打轉(zhuǎn)。這時候也會有很大的焦慮感。
鏡相:你每時每刻都是在一種工作的心態(tài)中?
肯定的。個別一兩天有度假的感覺,比如在伊塞克湖,一片蔚藍色的湖泊,有沙灘,還能游泳,不遠處是天山,跳到湖里的一瞬間是幸福的;在烏茲別克看到撒馬爾罕的建筑也會有這種感覺;看到玄奘看到過的佛塔遺跡,也覺得值得。但是這種時刻很少。
鏡相:書里似乎沒有特別書寫那些驚險的情形,這種情況是沒有碰上還是都化解掉了?
我想有過一次,有那種恐懼的感覺。在天山徒步的時候,在山谷里去找一片湖,途中完全沒有人,那里沒有信號,也沒有任何現(xiàn)代化的設(shè)備幫助,身上沒有帶補給,天上又開始下暴風(fēng)雨,腳下的泥濘幾乎把我的鞋給淹沒了。那時候離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地方還有好遠的距離。后來幸虧遇到了當(dāng)?shù)啬撩瘢纤鸟R才被帶了回去。

天山深處的阿爾金-阿拉善山谷
這個地方按當(dāng)?shù)厝说恼f法,天氣好的時候是容易走的,上了年紀的人有時候也會去踏青。所以我就沒覺得會有什么太大問題,但一是下雨,二是沒有當(dāng)?shù)厝四敲词煜ど焦鹊沫h(huán)境。本來聽說是三個小時能走到,但沒有地圖,也沒有導(dǎo)航,就不知道走到哪了。
還有一次是,我在塔吉克斯坦,經(jīng)過一條從杜尚別去往帕米爾的路。那條路在我離開之后的幾天,聽別的旅行者說有恐怖組織ISIS出沒,殺了兩個騎行的旅行者。
除了少數(shù)時刻,我覺得中亞整體是比較安全的,我很少在那里遇到來自別的惡意。
鏡相:中亞五國在外人看來是一片比較相似的地帶。你看到了其中的差異性嗎?
差別挺大,每個國家之間都有糾葛,互相看不上,彼此也沒有任何興趣。除了塔吉克人是波斯人,其他四國基本是突厥人,這兩個民族之間有糾葛。除此之外,國與國之間也有邊界沖突,暴亂,族群之間的仇殺等等,關(guān)系一直很緊張。記得有一個我有個朋友曾經(jīng)問過一個烏茲別克人,問中亞這幾個國家會推出一個統(tǒng)一的簽證,這樣不是更便于大家去玩。對方表示他們很少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因為彼此之間的沖突矛盾太多了,不可能達成一致。
鏡相:他們身上有與中國人的相似之處嗎?
吉爾吉斯斯坦人、哈薩克斯坦人有的跟中國人長得非常像,在吉爾吉斯斯坦街頭看到的一個大媽,與上海北京街頭看到的差不多。更多的相似是大家對生活的期待,怎么活下去。所以書寫他們的故事,我們也能理解,因為生活的本質(zhì),各國都是共通的。

鏡相:為了中亞的旅行,你掌握了哪些語言?
我在國內(nèi)報班學(xué)過俄語,其他語言比如語烏茲別克語就是買了書,在當(dāng)?shù)匾贿呑咭贿呌茫苷f一些簡單的是字詞和短語,可以問出類似于你叫什么名字,結(jié)沒結(jié)婚,有沒有孩子這樣的問題。其實主要是為了impress一下他們,拉近距離,表示我很尊重他們的文化,也在努力想跟他們交流。實際好處當(dāng)然是買東西吃飯解決了不少,或者打上車,司機不收我錢。
受過教育的人英語說得都不錯。蘇聯(lián)解體之后,英語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美國在中亞辦過很多學(xué)校,比如有中亞-美國大學(xué)。他們對英語的重視比我們可能更甚。
鏡相:我想聊聊你早期的成長環(huán)境和經(jīng)歷。
我是北京人,但好像不太喜歡北京,只不過這里剛好是出生長大的地方,沒有特別的感情。我們家在西城區(qū),周圍都是機關(guān)大院。我爸媽對我沒太管過,成長比較比較順,一路上的是比較不錯的學(xué)校,不像很多作家有過的殘酷青春。這也是我想從旅行寫作入手的一個原因。
高三畢業(yè)以后,我獨自去了一趟麗江和瀘沽湖,那時候去那里的游客還不多,回來以后我寫了一篇小說。當(dāng)時的寫作還是比較基于自己的旅游體驗,真正有旅行寫作的概念要到成為記者以后,去國外旅行開始。
鏡相:北大中文系是你自己選的嗎?
對。上大學(xué)之前讀了很多小說,先鋒派那一批作家,余華、馬原、孫甘露都是高中讀的,還有國外的海明威、喬伊斯、卡夫卡。選了中文系,現(xiàn)在來看有點后悔,還不如學(xué)語言,法律或者是歷史。中文系好像沒給我什么幫助。
鏡相:那中文系給了你什么?
給了我一個文憑。肯定也有人學(xué)到很多東西。但如果想當(dāng)作家,其實跟中文系沒什么關(guān)系。把文學(xué)當(dāng)作一門學(xué)問來研究,對我來說沒什么意義。
鏡相:你當(dāng)了很多年的記者,這對你在之后的旅行寫作有哪方面幫助?
一些技巧性的東西,比如去哪找人。我做過幾年調(diào)查記者,很多時候去一個不熟悉的地方,你要找到愿意對你開口的人,這需要技術(shù),需要突破能力。另外一點是對人的關(guān)注。做了人物記者之后,覺得應(yīng)該通過人的故事來反映時代和國家,而不是直接寫歷史。
鏡相:你有過迷茫期嗎?
2016年。從牛津大學(xué)做訪問學(xué)者,回國之后就沒工作了。當(dāng)時大家都在創(chuàng)業(yè),紙媒停刊的很多,媒體人轉(zhuǎn)行的也多。當(dāng)時那種狀態(tài)下,我不知道自己應(yīng)不應(yīng)該該追隨這個潮流。當(dāng)時我覺得要么選寫作,要么做一個壓根跟寫作沒關(guān)系的事,徹底改變自己的人生。后來,我接受了自己是文藝青年的現(xiàn)實。創(chuàng)業(yè)或者找份每天坐班的工作都不適合我這種人,還是想專注在寫作上。其實有的工作跟寫作也不沖突,但我沒辦法,必須得用盡所有能力,才可能讓自己滿意。
鏡相:那時候你就很確定旅行寫作有它自己的價值?
當(dāng)我開始決定寫中亞這本書的時候,我就知道如果寫出來會是好看的,信心一直都有。因為沒有別人寫。對時間的投入,對語言的要求,對旅行技巧的要求,對寫作能力的要求,所有的要求加到一起,別人可能寫不了。
鏡相:你擔(dān)心人們愛看嗎?
我的第一本書《午夜降臨前抵達》反響還不錯。另外,后來我想通了,反正靠這事發(fā)財是不可能的,當(dāng)然也餓不死。想通之后簡單了,一往無前地去做就好了。我希望像喜歡的作家那樣,到了七八十歲還在從事旅行寫作。比如保羅·索魯,已經(jīng)快80歲了,去年還在出了關(guān)于墨西哥的游記作品。我也在鍛煉,堅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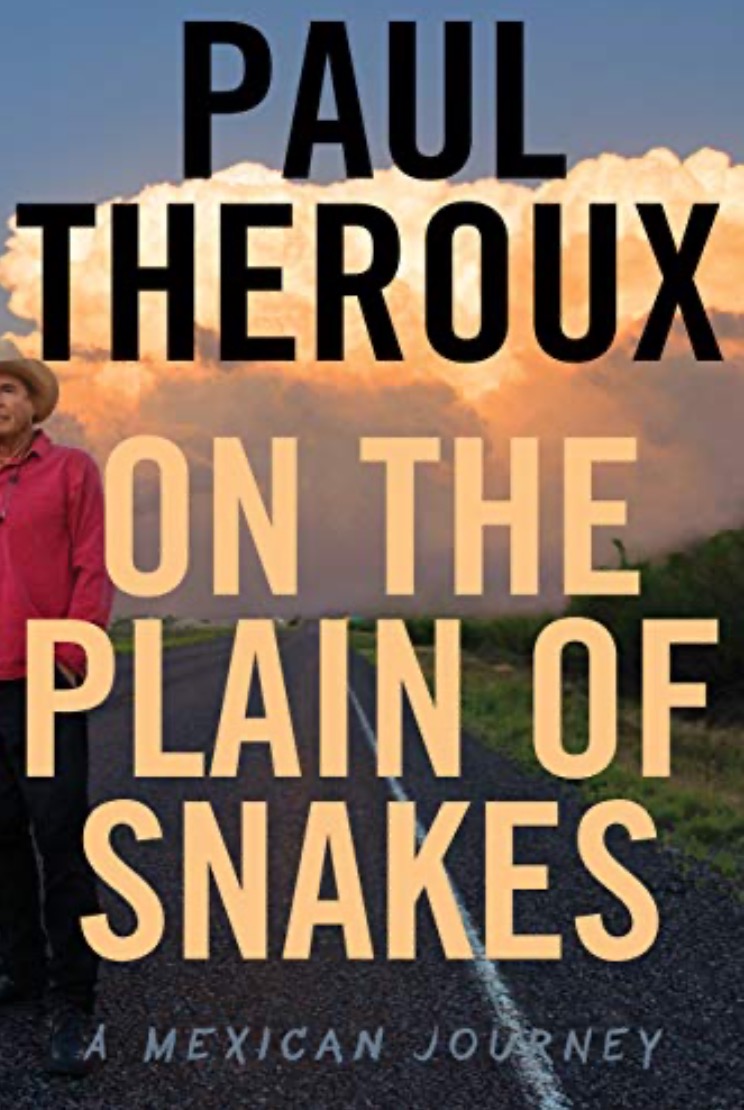
鏡相:你覺得身為一名中國的旅行作家,和那些西方作家相比,有什么獨特的地方嗎?
我們永遠是用自己的文化打量別的文化,我對世界的看法肯定深受到我從小長大的環(huán)境影響,比如我怎么呈現(xiàn)伊拉克的后薩達姆時代,肯定與西方作家的視角是不同的,我的視角肯定是與中國的文化歷史有強烈的關(guān)系。傳統(tǒng)中國會認為穩(wěn)定更重要,美國作家肯定會覺得推翻獨裁更重要。
鏡相:如果沒有贊助方的支持,你也會去完成自費的旅行嗎?
只要能承擔(dān),錢不是阻止我去旅行的障礙。歐美國家有很多這類基金會的支持,我們國內(nèi)幾乎沒有,鼓勵旅行寫作的獎項也很少,這是遺憾的一點。比如《紐約客》有個記者是90年的,叫本·陶布,他獲得2020年普利策獎的作品《關(guān)塔那摩最黑暗的秘密》也是得到基金會的支持,先拿到錢,再去做調(diào)查采訪。這種機制國內(nèi)比較少,官方也沒有鼓勵深度國際報道的獎項,即使有,也很難給我這種自由職業(yè)的人。
很多時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沒有意識到這個事重要。其實有能力的中國企業(yè)不在少數(shù),很多企業(yè)的業(yè)務(wù)已經(jīng)擴展到世界各地,但是他們沒想過做生意的基礎(chǔ)之一也建立在本國的知識分子或作家有沒有對這些地方的觀察之上。大家也許覺得寫作和生意沒關(guān)系,但如果一個地方有幾部中國作家或者記者寫成的關(guān)于當(dāng)?shù)氐臅菄俗錾庖埠茫蛘呤歉?dāng)?shù)厝擞衅渌耐鶃硪埠茫耆遣灰粯拥母杏X。
鏡相:接下來寫什么呢,如何避免陷入自我重復(fù)?
環(huán)黑海和環(huán)地中海。我要找有沖突感的地方。沖突感就像一個舞臺的背景,在這個背景下上演的各種故事。在好的布景下寫出好的故事,是最好的。
環(huán)黑海有斯拉夫文明帶和土耳其文明帶,其中有克里米亞、烏克蘭、俄羅斯,格魯吉亞,土耳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每個地方之間都不一樣,這一圈走下來,把其中人的故事給挖掘出來,大概想想都覺得挺豐富的。環(huán)地中海更豐富,北非,巴爾干,希臘,中東的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有歷史、有現(xiàn)實、有沖突、有未來,各個維度都有。只要疫情結(jié)束,能讓我出國,隨時可以開始實施。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gòu)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