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日本發(fā)現(xiàn)“洛陽”:理想都城與想象空間
京都里的洛陽
到京都旅行,大街小巷里會頻頻出現(xiàn)“洛陽幼稚園”“洛陽莊”“洛陽織物”等招牌,手中地圖用“洛”加上東、南、西、北、中等方位詞來表示,連街頭大幅的宣傳畫也是《洛中洛外圖》屏風(fēng),一瞬間讓人生出“今夕何夕、此處何處”的恍然之感。
尋其緣由,“洛陽”乃京都的雅稱。洛陽與京都的聯(lián)系,可追溯到9世紀(jì)末。日本的宮室、都城的源流都出自中國,模仿唐代的長安城和洛陽城的意識非常強(qiáng),其中平安宮和平安京最為著名。《帝王編年紀(jì)》中有記載,恒武天皇時(shí)“東京左京,唐名洛陽”“西京右京,唐名長安”,10世紀(jì)后期“左京=洛陽、右京=長安”的說法開始固定下來。右京長安部分所處地帶為濕地,后因環(huán)境原因,荒廢不用而有名無實(shí),唯有左京洛陽部分繁榮發(fā)展,因此“洛陽”作為京都的別名一直保留下來。
王仲殊對此做過專題考察,認(rèn)為左京比右京繁華主要源于都城、宮城內(nèi)部的形制和布局,還指出平安京在形制、布局上主要模仿長安,命名卻多來自洛陽。左、右京中大約有13個(gè)中國式坊名,其中銅駝、教業(yè)、宣風(fēng)、淳風(fēng)、安眾、陶化、豐財(cái)、毓財(cái)?shù)?個(gè)坊名仿自洛陽,除了應(yīng)天門以外,宮城的上東門、上西門之名也仿自漢魏時(shí)期的洛陽城。
元初忽必烈進(jìn)攻日本因遭遇臺風(fēng)而失敗后,1298年元成宗放棄軍事進(jìn)攻,派名僧一寧(1247-1317)為使,賜金襕袈裟及“妙慈弘濟(jì)大師”稱號,命他赴日以“通二國之好”。一寧的日本之行,被當(dāng)時(shí)的名僧虎關(guān)師煉(1278-1346)詳細(xì)記錄:伏念堂上和尚(一寧)往己亥歲,自大元國來我和域,象駕僑寓于京師,京之士庶奔波瞻禮,騰沓系途,惟恐其后。公卿大臣未必悉傾于禪學(xué),逮聞師之西來,皆曰大元名衲過于都下,我輩盍一偷眼其德貌乎!花軒玉驄,嘶騖馳,盡出于城郊,見者如堵,京洛一時(shí)之壯觀也。可見此時(shí)將京都稱為“京洛”,已成為日本人的習(xí)慣,這個(gè)稱呼沿用至今,并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詞語。如“上洛”這個(gè)詞,在日語中本意表示各地藩主大名來京都覲見,相當(dāng)于“進(jìn)京”,至今仍在使用,只不過隨著首都遷移,現(xiàn)在可用于東京。雖然14世紀(jì)時(shí)京都城市的中軸線大大向東偏移,人們還是習(xí)慣于用“洛”加上方向詞來表述京都的方位。特別是有把京都城市內(nèi)外用“洛中”和“洛外”表示的傳統(tǒng),江戶初期畫家狩野永德的屏風(fēng)畫《洛中洛外圖》就是描繪京都繁榮市街及郊外名勝古跡的杰作。建筑學(xué)家唐克揚(yáng)指出:“為特定空間制作的洛中洛外屏風(fēng)不只是現(xiàn)代人眼中的一幅裝飾‘畫’,也是在室內(nèi)營造出的一種‘以小觀大’的幻境,足以透視出時(shí)人對于理想城市風(fēng)景的一般印象。”

《洛中洛外圖》金閣寺部分。資料來源:日本郵政2016年發(fā)行的郵票《上杉本洛中洛外圖屏風(fēng)》。
日本佛像中的洛陽
經(jīng)過遣隋使、遣唐使的往來,日本全方位接受中國文化,從政治、經(jīng)濟(jì)制度到文學(xué)藝術(shù)思想等,幾乎所有領(lǐng)域都打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大唐的文明風(fēng)貌,如同旋風(fēng)般席卷了整個(gè)日本,由上層貴族社會滲透到下層民間。從天平時(shí)代、平安時(shí)代到以后的鐮倉時(shí)代、室町時(shí)代,日本的制度、思想﹑城建、文學(xué)﹑藝術(shù)﹑風(fēng)俗習(xí)慣等各個(gè)方面都充滿了中國風(fēng)格。
一般認(rèn)為佛教最早正式進(jìn)入日本是在552年(也有538年之說),朝鮮半島的百濟(jì)國派使者給當(dāng)時(shí)的欽明天皇送來一尊釋迦牟尼的金銅像和佛教經(jīng)典、佛具,崇佛派蘇我氏的蘇我稻目在自宅中供奉佛像,此舉成為日本佛寺造營的濫觴。崇峻天皇元年(587),蘇我馬子依靠百濟(jì)所獻(xiàn)寺工、爐盤博士、瓦博士、畫工等工匠的技術(shù)力量,興建了規(guī)模宏大的飛鳥寺。根據(jù)近年的考古發(fā)掘,飛鳥寺的結(jié)構(gòu)已大致判明,以塔為中心,東西金堂分列兩側(cè),北面正中配置中金堂。從建筑角度看,這種寺院樣式是經(jīng)百濟(jì)工匠之手從朝鮮半島傳入的,帶有明顯的北魏洛陽伽藍(lán)的特征。
飛鳥寺中金堂供奉的本尊為丈六釋迦坐像,俗稱飛鳥大佛,是尊銅制丈六佛像坐像,高2752厘米。這座佛像是推古天皇十四年(606)建造的,雖然在近1500年間多次損毀,除頭部和雙手之外都經(jīng)過修復(fù),但從雕塑角度看,依然可以辨識出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本尊的原貌,研究者據(jù)此推斷北魏文化是日本飛鳥文化的源頭之一。
制造飛鳥大佛的鞍部止利是飛鳥時(shí)代日本著名的佛師,其祖父是從百濟(jì)移居日本的司馬達(dá)一族。司馬氏是中國兩晉王朝的皇姓,有人認(rèn)為渡來人司馬達(dá)有可能是東晉皇族的后裔。“鞍作部”是渡來人的姓,受封于大和朝廷,表示整個(gè)族群世代為朝廷所做的工作內(nèi)容。這個(gè)家族在日本以“鞍部”(也稱鞍作部)為姓,很可能是僑居百濟(jì)的南朝工匠,也有可能是直接從南朝梁遷徙過去的。僅從字面上也不難看出,“鞍作部”原意是從事馬鞍和馬具的制作,后來這一家族演變?yōu)閷iT從事佛像制作。
飛鳥大佛竣工后的第二年,圣德太子發(fā)愿的法隆寺落成。止利派創(chuàng)作活動以法隆寺為中心,于7世紀(jì)前期達(dá)到鼎盛,其中金堂釋迦佛堪稱止利佛師的代表杰作。根據(jù)《法隆寺金堂釋迦佛造像記》可以得知,這是為悼念一年前去世的圣德太子而鑄造的。中間的釋尊手施無畏與愿印,結(jié)跏趺坐,據(jù)說是模仿圣德太子的等身像,兩側(cè)有侍像,這種一主二仆式的造像方式也是模仿了北魏龍門石窟的樣式。

法隆寺金堂本尊釋迦三尊像。資料來源: 法隆寺御朱印,https://法隆寺-御朱印.jinja-tera-gosyuin-meguri.com/category/奈良·法隆寺の仏像-一覧【國寶·重文%EF%BC%88畫像寫真/法隆寺·%EF%BC%88金堂%EF%BC%89釈迦三尊像「釈迦如來と文殊菩。
法隆寺雖在遭遇火災(zāi)后重建,但豐富的飛鳥文化元素基本都被保存下來,有一些原屬法隆寺現(xiàn)收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造像佛,幾乎都是止利派的造像風(fēng)格。這種風(fēng)格較之肥體薄衣的云岡樣式,更接近長臉、瘦身、厚衣的龍門樣式,特點(diǎn)是眼睛呈杏仁形狀,唇邊隱約露出古樸的微笑,長長的耳垂上沒有開孔,等等,與洛陽龍門石窟佛像的親緣關(guān)系清晰可辨。
止利風(fēng)格佛像的佛衣采用的是中國式的“通肩”設(shè)計(jì),是用圓潤彎曲的線條來刻畫衣紋,上衣襟張開,襟邊沿上斜穿,掩蓋住左肩和右腋的內(nèi)衣,且可以看見衣裙帶子的結(jié)頭,這是中國獨(dú)創(chuàng)而印度佛像沒有的。結(jié)跏趺坐的佛像下面拖出長長的衣裙,這也是止利派造像的一大特色。這種衣裾垂于座前的坐佛像被稱為“懸裳座”,最早出現(xiàn)于云岡石窟,在龍門石窟時(shí)發(fā)展成熟。厚重的衣裙上強(qiáng)化了裝飾性刻畫,屬于中國北魏“褒衣博帶”類型,形成類似云紋的浮雕,這種佛像造型顯然是學(xué)自中國北魏后半期的“龍門樣式”。另外,手足指間有縵網(wǎng)相連是北魏造像的典型風(fēng)格,這也體現(xiàn)在止利派造像中,佛像的手足猶如水禽的腳蹼。以村田靖子為代表的日本學(xué)者認(rèn)為,長臉、瘦身、厚衣等相貌表現(xiàn)以及懸裳座的完成,標(biāo)志著止利佛像成為日本古典佛像的典范。
武則天大力推動佛教的消息經(jīng)由留學(xué)僧等傳至日本,圣武天皇(701~756)也希望借助佛教的力量賑災(zāi)驅(qū)邪、祈禱國家安泰。明顯是受到武則天在洛陽紫微城造大佛銅像、通天浮屠,在龍門奉先寺雕刻盧舍那大佛石像的啟發(fā),圣武天皇參拜河內(nèi)國大縣郡知識寺大佛后發(fā)愿“朕亦奉造”,743年下詔筑造大佛。在光明皇后的大力協(xié)助下,于奈良以東(現(xiàn)東大寺的位置)建起以洛陽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坐像為原型的高達(dá)14.9米的盧舍那大佛坐像,該佛像也稱奈良大佛。
洛陽與日本的佛緣不止于此,因請鑒真東渡而著名的日本僧人榮睿、普照733年隨第九次遣唐使來到中國,在洛陽大福先寺受戒學(xué)習(xí),并于三年后請福先寺僧人道璇赴日本弘法傳戒。當(dāng)時(shí)住在大福先寺內(nèi)的印度僧人普提仙那也一同前往日本,住奈良大安寺宣講戒律。道璇作為先于名僧鑒真赴日的傳戒師,是首位獲日本天皇敕請的唐僧,為華嚴(yán)宗、禪宗、律宗等各佛教宗派東傳日本做出巨大貢獻(xiàn)。東大寺大佛的開眼儀式由普提仙那主持,道璇擔(dān)任咒愿師。后來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在大佛殿前臨時(shí)建造的戒壇上向圣武太上皇等僧俗授戒。道璇和菩提仙那歷經(jīng)萬難從洛陽福先寺來到奈良,鑒真年輕時(shí)也曾在東京洛陽游學(xué),聚在異國的幾位高僧,從奈良大佛身上看到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的影子時(shí)該是怎樣的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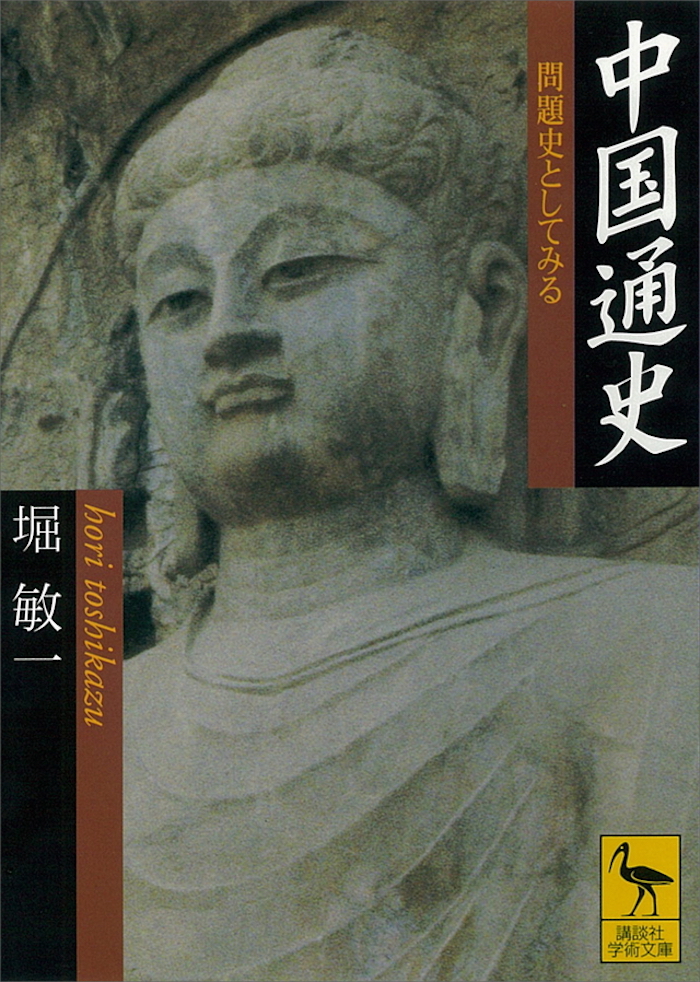
在日本被用作歷史書封面的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資料來源:講談社學(xué)術(shù)文庫,https://bookclub.kodansha.co.jp/product?item=0000151032
從北魏到隋唐,洛陽佛教的盛況對日本佛教影響深遠(yuǎn)。特別是龍門石窟造像,不僅是日本古代佛像的源流,也是飛鳥時(shí)代日本吸收中華文明的有力實(shí)證。有學(xué)者認(rèn)為南北朝時(shí)期北魏文化是通過高句麗傳入日本的,兩者之間具體是如何傳承的、止利派風(fēng)格的佛像制作方法來自龍門石窟的直接證據(jù)等,尚需繼續(xù)考證。
日本漢詩中的“洛陽”
地名是人們賦予某一特定空間位置上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實(shí)體的專有名稱,將平安京(京都)稱為“洛陽”即是通過命名表達(dá)一種對理想都城的向往。這種向往基于洛陽曾是多個(gè)王朝都城的歷史地位,同時(shí)也是因?yàn)榇罅亢吐尻栂嚓P(guān)的詩文名作,長期憧憬中華文明的日本人通過文字構(gòu)建起關(guān)于洛陽的想象空間。
日本漢詩來源于中國詩歌,同時(shí)又體現(xiàn)日本社會文化傳統(tǒng),在東亞漢文化圈中獨(dú)樹一幟。完全不懂漢語的日本人能作出無論是結(jié)構(gòu)還是音韻都符合規(guī)定的漢詩,令人難以置信,卻是不爭的事實(shí)。日本人從大約1300年前就開始創(chuàng)作漢詩了,這得益于他們?yōu)榱俗x懂漢文著作而發(fā)明的漢語訓(xùn)讀法,即在漢文字上加注稱為訓(xùn)點(diǎn)的標(biāo)記。用這種方法對中國的古籍文章稍加標(biāo)示,就能讓日本人像閱讀日語一樣看懂漢文。
訓(xùn)讀法大約從八世紀(jì)以后開始在日本普及,時(shí)至今日也是當(dāng)代日本中學(xué)生必須接受的訓(xùn)練。這使日本人能夠直接閱讀漢籍古文,從理論上來說即便不會漢語也能夠自由地作漢詩、研究和閱讀漢文,大大加快了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和吸收。前文中所述白樂天的詩歌在日本被奉為瑰寶,就是古代日本人感受到漢詩之美而癡迷熱愛漢詩的源頭。日本的貴族文士競相模仿白氏風(fēng)格作漢詩,在相當(dāng)長的時(shí)間里習(xí)慣于通過漢詩文記錄情感和生活。
細(xì)讀古往今來的日本漢詩,能夠?qū)覍业靡藻忮寺尻枴@纾?/p>
火舶鐵車租稅通,魯西以外一家同。
東京自此洛陽似,道里均平天地中。
——大沼枕山《東京詞》
大沼枕山(1818-1891)是明治維新時(shí)期著名的漢詩詩人,他出生于江戶時(shí)期,親身經(jīng)歷風(fēng)起云涌的明治維新,出版詩集《東京詩三十首》,被收錄于1934年出版的《明治詩話》中。以上是七言絕句中的一首,借吟詠江戶成為東京的滄桑巨變,諷諫了幕府末年遷都等時(shí)政。日本人對洛陽十分熟悉,《史記》等中國古文獻(xiàn)中周朝營造洛邑時(shí)“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的典故信手拈來。在洛陽早已退出中國政治中心舞臺數(shù)百年后的19世紀(jì)后期,日本遷都之際,仍然能夠有意識地首先將東京比作洛陽,說明洛陽的古都印象在日本已經(jīng)根深蒂固,作為天下之中的象征即使在日本也深入人心。
九朝帝闕風(fēng)霜古,幾處河山光景新。
請看當(dāng)年金谷路,笙歌今日是何人。
——石川忠久《禹域游吟之十四洛陽》
如今雖說是日本漢詩衰微的時(shí)代,但仍有不少修養(yǎng)較高的日本人作詩不輟,一直保留著寫漢詩的傳統(tǒng)。現(xiàn)代詩人石川忠久(1932~)在日本當(dāng)代漢詩界德高望重,他不僅出版著作介紹和賞鑒中國古詩,還多次游歷中國,在洛陽周邊的二里頭、龍門、杜甫墓等處游覽時(shí)留下不少詩篇。
瞭望熏風(fēng)楊柳新,懸崖萬洞各佛宸。
龍門大佛無言坐,腳下慢和寧靜人。
——平田稔《拜望龍門石窟》
不僅是有名的詩人,即使是普通人也以作漢詩為樂。以上一篇就是筆者在網(wǎng)上無意中發(fā)現(xiàn)的,作者是一位喜愛漢詩的老人,他常常在博客中解讀中國漢詩,也發(fā)表自己的作品。這首就是他親赴洛陽體會杜甫的《游龍門奉先寺》之后自己創(chuàng)作的,不懂日語的中國人讀起來也完全沒有障礙。
洛陽知己皆為鬼,南嶼俘囚獨(dú)竊生。
生死何疑天付與,愿留塊魄護(hù)皇城。
——西鄉(xiāng)南洲《獄中有感》
日本漢詩中出現(xiàn)的“洛陽”,很多時(shí)候是指代京都的。這一首非常著名,是波瀾激蕩的幕府末年的漢詩,作者是“維新三杰”之一的西鄉(xiāng)隆盛。西鄉(xiāng)自號南洲,發(fā)起尊王攘夷運(yùn)動,失敗后被流放于孤島作成這首詩。詩中豪情不減,抒發(fā)了他愿意為推翻幕府、王政復(fù)古而鞠躬盡瘁之情。該詩被勝海舟刻于石碑上作成“留魂詩”碑,如今立于東京上野公園。

西鄉(xiāng)隆盛留魂詩碑。資料來源:西鄉(xiāng)隆盛留魂詩碑,https://i0.wp.com/koedo-sanpo.site/wp-content/uploads/2018/08/fullsizeoutput_a80.jpeg
另外,近來一度成為社會性話題的一首漢詩也和“洛陽”有關(guān)。
夢上洛陽謀故人,終衛(wèi)巨奸氣逾振。
覺來浸汗恨無限,只聽鄰雞報(bào)早晨。
——武市半平太《絕命詩》
這是2011年7月在日本高知市民間發(fā)現(xiàn)的手稿,作者是領(lǐng)導(dǎo)尊攘運(yùn)動的志士,曾與坂本龍馬相交。他的活動被鎮(zhèn)壓,入獄后受命切腹自盡。因此,這是一首獄中所作的絕命詩,寫夢見自己到京都與友人會合、共同謀劃,終于成功扳倒巨奸,意氣風(fēng)發(fā),可是醒來后卻發(fā)現(xiàn)只是美夢一場,自己身處囹圄,遺恨無限。
日本漢詩中的“洛陽”,除了以上兩類可以明確判斷指向的以外,還有不少從意義上來說是模棱兩可、任憑讀者意會的情況。浸淫于漢文詩風(fēng)中成長起來的日本文人,盡管很多人終生未到過中國,卻借助文字在心中構(gòu)造起一個(gè)典雅精致的想象世界,常常創(chuàng)作以中國風(fēng)物為主題的漢詩。由于京都也可雅稱洛陽,字面上和洛陽相關(guān)的日本漢詩很可能是日本詩人看似不經(jīng)意,實(shí)際上卻是有意識地把中國漢詩典故中原有的洛陽悄然與他們所處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中的“洛陽”(京都)嫁接起來的結(jié)果。例如:
洛陽一別指天涯,東望浮云不見家。
合浦飛來千里葉,閬風(fēng)歸去五更花。
關(guān)山月滿途難越,驛使春來信尚賒。
應(yīng)恨和羹調(diào)鼎手,空捋標(biāo)實(shí)惜年華。
——新井白石《千里飛梅》
新井白石生于江戶時(shí)代的破落武士家庭,卻積極向?qū)W,專習(xí)朱子學(xué)數(shù)年,成為江戶時(shí)代的學(xué)者型政治家。《千里飛梅》的詞句明顯與“浮云一別后,流水十年間”(韋應(yīng)物《淮上喜會梁川故人》)、“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李覯《鄉(xiāng)思》)等唐宋詩句的語意相似,可見作者的古典文學(xué)素養(yǎng)深厚,對中國詩文可以信手拈來。新井因著有《古史通論》和《外國之事調(diào)書》等研究邪馬臺國與曹魏王國交往歷史的著作而聞名,對于古代洛陽的人文地理非常熟悉,所以詩中使用了“合浦杉”的典故。在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合浦葉或者杉葉常常作為思?xì)w洛陽的形象出現(xiàn),表達(dá)鄉(xiāng)愁。明朝的楊慎在《升庵文集》中專門設(shè)立了“合浦杉”一條,列出“傳聞合浦葉,遠(yuǎn)向洛陽飛”“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州”等詩句。新井白石作這首詩的具體情況已不可考,這首詩通常被看作含著青春少年的豪放與自許,又包含壯志未酬、空白了少年頭的悲慨。其中“合浦飛來千里葉”與“洛陽一別指天涯”既有邏輯上的照應(yīng),也有意象的連接,無論是實(shí)指還是虛指都很和諧。
這類詩歌數(shù)量不少,其中“洛陽城里飛如雪,不送行人空送春”(室直清《楊花》)、“春雁似吾吾似雁,洛陽城里花背歸”(直江兼續(xù)《春雁》)等已成為日本膾炙人口的名句。這些詩句明顯因襲了“洛陽城里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fā)”(宋之問《寒食還陸渾別業(yè)》)、“洛陽城東西,長作經(jīng)時(shí)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范云《別詩二首》)、“洛陽愁絕,楊柳花飄雪”(溫庭筠《清平樂·洛陽愁絕》)、“鄉(xiāng)書何處達(dá),歸雁洛陽邊”(王灣《次北固山下》)等,讓“洛陽”一詞在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的風(fēng)花雪月的浪漫形象在日本文學(xué)中也得到繼承。
日本漢詩中的洛陽書寫,無論是實(shí)際語義、借用典故還是使用氛圍,都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形象中的洛陽一脈相承。這既可以理解成日本詩人的隔空致敬,也可以理解為以“洛陽”指代京都。日本詩人有意識地繼承和使用獨(dú)具洛陽特色的相關(guān)典故意象,又將京都的實(shí)際意義和“和習(xí)”描繪入詩,詩中兩種所指都符合邏輯,創(chuàng)造出一種嶄新的詩歌意境,達(dá)到“一弦二歌”的效果。這種寫作手法顯得異常精妙,也使得“洛陽”一詞體現(xiàn)出中日在文學(xué)、文化、審美方面的共識得以繼承,成為理解中日兩種文化的一種特殊路徑。

“春雁似吾吾似雁,洛陽城里花背歸”屏風(fēng)。資料來源:筆者攝于日本京都。
(本文節(jié)選自黃婕著,《華夏之心:中日文化視域中的洛陽》,社科文獻(xiàn)出版社2020年出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刊發(fā)。)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