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東莞20年:一座世界工廠的青春期與成人禮
原創 李屾淼 新周刊

1988年才升格為地級市的東莞,是中國城市化浪潮中的一個樣本。它有抱負,有夢想,有起伏,也有悲傷。

沒等來國家分配,四川南充人鄭小瓊就在當地一家資質不明的私立醫院做了三個月護士。
醫院靠小廣告誆來的病人大多來自農村,文化程度有限,被夸大病情恐嚇一番后,花了不少錢做無用治療。衛校畢業的鄭小瓊覺得此事太缺德,離職去了一家小餐館端盤子,聽同鄉說廣東好打工,決定一塊兒去看看。
準備一輩子在國企“旱澇保收”的余嶠,已經有半年沒收到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資;丈夫徐野所在的國營機械廠,效益同樣不堪。
余嶠的表哥在廣東打工,建議他們實在不行就去廣東找工作。夫妻倆一咬牙,把不到5歲的獨生女交給爺爺奶奶,帶上5000元的全副身家,去了珠三角一個連名字都沒聽過的城市。
目的地叫東莞,他們聽說那里有光明的前途。

331年建縣的東莞,1988年才升格為地級市。1978年在東莞虎門誕生的“三來一補”模式,開啟了近30年密集型加工產業的蓬勃發展。
大膽的政策嘗試以及靠近港澳的地緣優勢,讓這個原本不起眼的農業縣迅速成長為以加工和制造業聞名,“東莞塞車,全球缺貨”的世界工廠。1996年至2002年,東莞出口總值連續7年在全國城市中排第三位,僅次于深圳和上海。
世界工廠對于勞動力的大量需求,掀起了1990—2000年間的南下民工潮。大量涌入的外來務工人員,很快讓按照地級市標準設置的行政管理機構和基礎設施不堪重負。生產總值以兩位數增速狂飆突進,工廠里人頭攢動,東莞變得生機勃勃;但它同樣因為治安差而被外界詬病,并被稱為“血汗工廠”。
日后成為詩人的鄭小瓊在《東莞》一詩中寫道:“外鄉人將悲傷與希望嵌入它的軀體/它混亂而嘈雜,糙肉般充滿活力/漫長而溫熱的黑夜,繁華而冷漠的白晝/它的大街遍布各種形狀的夢想。”
剛到東莞時,鄭小瓊一直忙著找工作,鞋廠、家具廠、毛織廠、玩具廠……工廠很多,用工需求很大,面試往往粗暴高效:先由保安看畢業證、身份證,刷掉學歷太低、來歷不明的,這就去掉了一半;再讓他們跑步、做俯臥撐,身體太差的不要,又沒了一半;最后人事小姐出來,挑順眼的面試,定下其中幾個。用工合同之類的一概欠奉,招進來當天即培訓開工。
余嶠在春節后的一個傍晚到達樟木頭。車上的人說粵語,她一句也聽不懂,還以為這些人喝多了。她輾轉應聘到臺資廠做文員,宿舍統一7點起床,被子要疊出豆腐塊,不合規格要扣錢。午餐時間,臺方管理人員去專用餐廳,大陸工人進員工飯堂。飯堂沒有桌椅,上萬人端著碗站著吃飯,余嶠看著碗中的白飯、白菜以及一塊連著皮毛的豬肉,嘩嘩掉眼淚。
待了兩天,余嶠覺得不是辦法,打算去丈夫所在的工廠碰碰運氣。她跟工頭說“要到附近租房住”,匆忙帶著行李離開——因為走辭工程序的話,還要等到晚上所有室友回宿舍簽字確認沒丟東西之后,工廠才放人。
外資工廠在東莞的興盛,帶動了上世紀90年代末當地民營企業的崛起。
從事調味品代理的王慶和在代理產品被廠商屢次提價后,終于決定自己開廠。
永益食品有限公司創建于1995年,主打產品鳳球嘜番茄醬于兩年后投入生產。同年,以小霸王學習機締造中國游戲機銷售奇跡的段永平因股權分配問題與老東家鬧崩,他帶著后來vivo、OPPO、小天才手表的創始人離開小霸王,來到東莞,創辦步步高電子工業有限公司。三年后,步步高無繩電話市場份額全國第一,VCD市場份額沖進全國前三。

就在余嶠在飯堂被豬毛氣哭之際,東莞大學生陳燕玲在賣網絡長途電話卡的過程中接觸了許多工廠,她發現大多數工廠飯堂做得實在不堪,覺得在工人吃飯這個剛需上大有可為。于是,她跟幾個合伙人成立鴻駿膳食管理公司,專門做食堂承包。
開廠創業,在東莞變得稀松平常。
2001年,東莞民營企業登記注冊數達12.96萬家。陳燕玲等人花了近一年時間才拿下第一個工廠訂單,但市場一打開,他們很快發現,下訂單的工廠工人規模動輒上萬,只好設限,3000人以下的工廠的訂單不接。
斷斷續續打工的鄭小瓊迷茫且苦悶,城市的繁榮似乎與她無關。2001年,她住在城中村的出租房,沒電視、沒手機,也沒網絡,工作之余,只能在地攤搜羅各種書籍和雜志看。
她發現雜志上刊登了一些打工者寫的詩歌,覺得不難,自己試著寫了起來,四處投稿。當年年底,她的一首詩作出現在《東莞日報》上。
在一家日資電子廠,徐野、余嶠夫婦終于做到了管理崗,月薪加起來有六七千元。但他們覺得在廠里做下去不是長久之計,于是一起離職,自己開廠做包裝材料。為了接女兒來上學,他們在南城區買了房子。
首付一交,積蓄也差不多見底,生活開支和每月3000多元的房貸懸在頭頂,2003年又碰上“非典”疫情,二人不敢懈怠。為了拉訂單,他們時常開車去東莞、深圳兩地的城中村小廠逛,一聽說有需求,馬上跑過去接洽。
熬過艱難的開頭,生意漸有起色。接下來幾年,他們發現以前看著驕傲又洋氣的港臺客戶和國外客戶變得客氣了,消費和生活上的差異也越來越小。跟港商通電話談訂單時,他們還沒來得及學會粵語,對方的普通話倒是越來越好了。

2007年5月底,首家“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袋廠倒閉,廠房拆除。鼎盛時占地8000平方米的太平手袋廠,成為一個時代開啟的標志,也是一個時代落幕的序曲。
原材料價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上漲,人民幣大幅升值、政策環境日益嚴格,東莞“三來一補”以及勞動密集型模式企業的黃金時代完結。東莞部分企業逐漸往中國中西部地區或東南亞遷移,留下的企業則在掙扎中謀求轉型。
身處團餐產業的陳燕玲,更早察覺到局面的變化。來自玩具廠、鞋廠、制衣廠的飯堂承包規模越來越小,最終這些廠子徹底轉移,離開東莞。
電子產業則因為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和采購體系,萎縮得相對緩慢,但勢頭同樣明顯。“像三星的廠,最多時有1.7萬人,然后降到7000人,再到3000人……”陳燕玲說。
陳燕玲所在的鴻駿膳食,2006年起將業務向東莞以外的珠三角城市乃至全國擴張。東莞本地的廠雖然在減少,但留下的工廠企業,對飯堂質量的要求明顯提升。“到了2010年,你會發現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以前不規范的同行逐步被淘汰。”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東莞作為外貿大市、制造業重鎮,一時間遭受重大打擊。2009年一季度,東莞經濟增速為-2.3%。據《南方都市報》報道,2009—2014年這6年間,東莞的GDP增速已有4年未能完成當年的目標任務。
老客戶紛紛離開東莞,徐野、余嶠的包裝材料廠漸漸做不下去了。他們早就考慮要轉型,下重本在江蘇投資建廠做節能燈,原本一切就緒,碰上全球金融危機,客戶拼命壓價,成本根本扛不住。他們投了近百萬元,最后不得不止損退出。
最輝煌時有七八十名員工的老廠賺到的錢越來越少,看在員工分上不得不勉力維持,為了不多的訂單還要費勁跟客戶聯絡感情,夫婦二人疲憊不堪。恰逢女兒要高考,他們索性讓出工廠的所有股份,在家陪孩子復習,自己也稍作休息。
2008年,江蘇姑娘孫彌奇因父親工作關系來東莞打暑期工。她只敢在南城市區活動,不敢下鎮街,“那個時候只要下鎮街,經常會被摩托車飛車搶包”。
同時,服務業的興盛,讓東莞在全國以一種隱秘而又曖昧的方式聞名,這讓在東莞工作的許多年輕女性十分苦惱。在東莞工作后,去別的地方出差,被問從哪來,孫彌奇一概說“廣州”。她好幾次試圖通過換工作離開東莞,但每次新東家看到她在東莞的經歷后,都讓她回去繼續處理與東莞相關的業務。

在互聯網搜索引擎企業工作的經歷,讓孫彌奇看到了一個極具危機感、對新生事物敏感且從善如流的東莞。“政府大力推行企業上網,政府給我們費用,讓我們教育企業怎么上網,怎么通過電子商務實現產業轉型、開發客戶。”
辦一場培訓,政府至少補貼3萬元,相關主管領導幾乎隨叫隨到,幫忙站臺宣傳。企業搜索競價排名業務,最好的時候在東莞一天凈收500萬元,“錢來得跟水一樣”。
資深媒體人、報業發行人譚軍波2008年開始擔任新創辦的《東莞時報》的總編輯。到任沒多久,他就見識了一次光天化日下的搶劫:一名記者在報社門口被扯上一輛路過的車,錢被搶走,人被扔到鎮街。
走南闖北的譚軍波,在東莞學會了“打炮”這種酒場新玩法——一個高杯架在另一個高杯上,酒不溢出,謂之一炮。據說是虎門人受古炮臺啟發,創造了這種喝法。
然而酒風頗盛的東莞卻沒一條像樣的酒吧街。“酒吧街老是起不來,說明這個城市是缺乏中間白領階層的,講小資情調的人少。這跟這個城市的杠鈴型人口結構有關,不是土豪就是工人,是一座比較粗獷的城市。”譚軍波說。
經濟上的波動,似乎并未給百姓生活帶來太大影響。人情氛圍濃重的東莞,餐飲等服務業消費反而越發興旺。“基本上,春節前一個月和中秋前一個月,每天晚上就是各單位或者朋友互請,沒空自己吃飯。不間斷地你請我一餐,我請你一頓。”譚軍波說。

故鄉已經回不去了。女兒上大學后,徐野、余嶠夫婦打算在老家開茶廠,卻發現困難重重。
首先是跨界有門檻。從做工業到做農業,因循的關于標準、流水線和成本控制的思維方式沒有用武之地,而在環境相對落后的產地建茶廠,要創立品牌,請設計師包裝品牌形象,還要請業務員……一套下來,他們發現收益根本劃不來,而且運氣也不大好——茶葉品牌剛問世,正好迎來送禮消費的低潮。
更關鍵的是,老家的社會規則和人情世故讓他們大感不適。在東莞,他們早已習慣了當地直來直去的做法,辦事規則明確,要花的錢明碼標價,從來不含糊。在東莞的一個村開廠,不認識村支書也沒關系,而到了老家,就是另一套法則,從辦營業執照開始,處處都要托人。
“申請個變壓器也一直拖,我們也不知道為什么要拖這么久,需要給錢還是怎樣他就不說,他就說還要‘研究一下’。”徐野說。
生活上也有諸多矛盾。這對川籍夫妻已經不大習慣吃辣,一吃就上火。逢年過節給紅包,在東莞向來只包十幾二十元,親戚結婚包600元也會被嫌多;但在老家,動輒要上千元。
他們投了五六十萬元,虧錢、虧時間、虧人情,只得抽身止損,準備回東莞試試做餐飲。
新疆作家丁燕在2011年初次來到東莞,在樟木頭,她看到這樣一幅景象:一條不是很寬的街道,中間行車,兩旁是附近工廠下了班逛街的工人,商鋪和攤販沿街排開,叫賣不絕,大排檔的煙火氣飄在半空中。
當時年近四十的丁燕立即決定在此安家。她找了一家對年紀要求不嚴的小工廠打工,以便就近觀察、記錄一同打工的年輕女孩的生活。經過兩年的采訪和寫作,她發表非虛構作品《工廠女孩》。

在《工廠女孩》的采訪階段,丁燕發現了外來工人群體的新變化。女工變得緊俏,因為老板們更喜歡用女工,好管理,干活精細。隨著其他地方加工制造業的興起,選擇越來越多,來東莞的女工開始減少,許多工廠不得不招募更多男工。但躁動的男青年,往往會打架、爭風吃醋、頻繁跳槽……
2010年后進入東莞的人,多為85后。他們是第二代農民工,精神面貌、價值觀和第一代相比,差異明顯。“更個性化,更追求自由,更強調自我,脫貧養家已經不是他們最重要的問題了。”丁燕說。
年輕男工會根據女員工數量和質量選擇就業的工廠,男男女女說上兩句話,覺得感覺不錯便開始同居,換工作往往意味著舊關系結束、新關系開始;一個月3000元的收入,他們就敢買5000元的手機,分期買,經常換;男孩子尤其喜歡折騰自己的頭發,發型和手機款式經常變化。
但凡條件允許,大多數務工青年不會住集體宿舍,他們會盡量租房,擁有一個獨立空間……如果還有余錢,他們會用來裝點QQ空間,或者給手機游戲氪金。他們的手機號碼毫無意義,想跟他們保持聯系,必須用QQ,微信都不好使。
在餐飲業跟新一代務工者打交道的徐野、余嶠夫婦,對這些跟女兒一般大的員工頭疼不已。這些幾乎沒有養家負擔的孩子,“一言不合就走了,錢也不要。不來上班也不請假,管理規定對他們就是一紙廢話……以前我很嚴厲的,對員工要求很高,現在發現這種管理一點用都沒有,只好天天找員工談心、講道理,勸他們好好上班”。
就大背景而言,全國人口紅利開始弱化,東莞產業結構調整后,對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升級。2000—2010年,東莞常住人口年均增速為2.5%;2010—2017年,人口年均增速降到0.2%。2014年,東莞實施“機器換人”三年行動計劃,幫助企業節約用工近20萬人。
丁燕為寫作《工廠女孩》進行采訪的一年間,她所在的電子廠,規模從1萬人減到3000人,3年后,全廠搬遷至湖南;永益食品車間最初有100多個人負責一條生產線,逐漸減到10人不到,產能卻是過去的10倍。

2011年前后,余嶠開車路過松山湖時,見此處山清水秀,心想能住在這里也不錯。回去跟家人一合計,她在這里買了房子。不久后,坊間傳出華為供應鏈部門遷到松山湖的消息。
2013年8月,華為總裁任正非宣布,華為終端公司將遷移至松山湖,園區占地約1900畝,總投資100億元。自此,深圳一批高新產業加速向東莞外溢。依靠成本、土地、地緣、產業配套和政府服務等優勢,東莞成為近年來深圳產業轉移的首選地。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2014年至2016年,東莞全市共引進深圳企業項目604宗。
陳燕玲的團餐業務,客戶群從以往的工廠變成企業寫字樓、學校,客戶的要求也越來越復雜:要講究營養搭配,飯堂裝修設計要有氛圍,用餐時間要有音樂,熱量統計和用餐大數據也開始納入日常應用。
2018年7月2日,華為正式啟動搬遷,40輛車前后分60車次,拉來了2700名華為員工。松山湖基地建成后,配備近3萬名研發人員。在同年發布的《東莞市重點新興產業發展規劃(2018—2025年)》中,東莞將定位調整為“全球影響力的先進制造中心和創新型城市”。

東莞的治安,也不知從何時起發生了變化。
如今走夜路下鎮街,再也不是什么值得擔心的事。孫彌奇出差時大大方方地說自己從東莞來,也不會再從對方臉上讀到詭異的表情。
最多時有四五家門店的徐野、余嶠夫婦,最終沒能在餐飲業做出滿意的成績。折騰好幾年后,留下最后一家店,他們退出日常管理。二人時常出游,在家時喜歡在正對著松山湖的陽臺上喝茶;吃飯要煲湯,每逢變天,余嶠便給全家做祛濕的糖水。跟親戚朋友聚會或出游,大家默認AA制結賬。
鄭小瓊最近通過微信、抖音等找到了一百多個以前的工友。當年他們打工的錄像帶廠在2003年因一場大火倒閉,錄像帶行業也不復存在。
工友們天各一方,回老家的不到一成。在東莞安家的二十幾人,身份大多發生了變化,有人自己創業做工廠或餐飲,有人做到了企業高管,也有人還在工廠做普通工人。大家一起回憶往昔時,鄭小瓊聽到一句話,感慨不已:“東莞的工人好像越來越少,但是人越來越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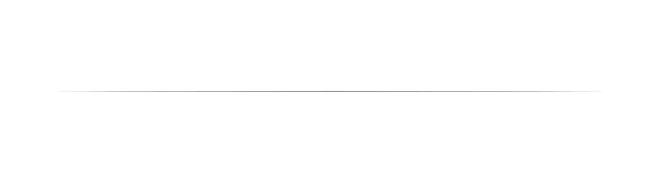
(應受訪者要求,余嶠、徐野為化名)
歡迎分享到朋友圈
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原標題:《東莞20年:一座世界工廠的青春期與成人禮》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