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幸與正義:現(xiàn)代社會(huì)的責(zé)任觀
就像我們無(wú)法直接感受到時(shí)間,而必須要參照依次發(fā)生的事情或頭腦中閃過(guò)的想法來(lái)證明時(shí)間的存在一樣,我們同樣也無(wú)法認(rèn)識(shí)到一個(gè)人的思維,而只能依靠對(duì)這思想的每一個(gè)觀點(diǎn)的回溯,才能側(cè)面的認(rèn)識(shí)到一種思想。更困難的是,就連觀點(diǎn)也不是隨意就能被認(rèn)知的,必須要在現(xiàn)實(shí)事件這面鏡子前,才能照出一種觀點(diǎn),而這觀點(diǎn)并不是指向事件的,而是反射回觀點(diǎn)者自身的思想的。

就像那個(gè)通俗的舉例,對(duì)于半杯水,有人看到了至少還有的一半,有人則看到了已經(jīng)丟失的那另一半。亦如在對(duì)于某一個(gè)國(guó)家疫情的觀點(diǎn)中,有人說(shuō)這是遭受自然不可抗力的不幸,也有人說(shuō)這其中體現(xiàn)了一種“不正義”,在不可抗力之中,貧困的人由于社會(huì)的不公而承受了更多的苦難。
不幸與不正義,在略有相似的含義背后,實(shí)則表達(dá)著截然不同的觀點(diǎn)。一個(gè)是天災(zāi),一個(gè)是人禍。但如果從這兩個(gè)觀點(diǎn)回到表達(dá)者的思想的話,可能會(huì)看到更多的不同,甚至可以翻出人類社會(huì)文明加速的主要進(jìn)程,這一切,要從一次震動(dòng)西方的大地震開始。

里斯本大地震 對(duì)不幸與不義的初次深刻思考
1755年11月1日,當(dāng)時(shí)歐洲最富有的海港,葡萄牙的里斯本沉浸在對(duì)萬(wàn)圣節(jié)慶祝的準(zhǔn)備中。而距離里斯本大約100公里的大西洋海底,醞釀著一股力量,在上午9時(shí)40分徹底釋放,先是地動(dòng)山搖,隨后將近30米高的海嘯直奔港口而來(lái)。距離里斯本200公里之內(nèi)的人們都能感受到這股力量的狂怒,英、德、法三國(guó)海岸帶均受其害。以當(dāng)今的視角來(lái)看,里斯本大地震震級(jí)高達(dá)8.9級(jí),是人類史上破壞性最大和死傷人數(shù)最多的地震之一,里斯本失去了1/4的人口,一半的城市被夷為平地,除此之外地震在西班牙西南部和摩洛哥也奪去了上萬(wàn)人的生命。
時(shí)隔兩百多年之后,當(dāng)時(shí)人們的悲痛早已消散在歷史之中,這場(chǎng)大地震,除了幾乎毀掉一座城市以及帶來(lái)了一個(gè)全新的里斯本之外,還意外地留下了一些副產(chǎn)品,這些副產(chǎn)品甚至在整個(gè)人類文明的角度來(lái)說(shuō)更加有價(jià)值,以至于有一些學(xué)者,將1755年作為現(xiàn)代世界的開端。
經(jīng)歷了大航海時(shí)代的里斯本,是當(dāng)時(shí)的世界城市,一如當(dāng)今的紐約、上海一般。這場(chǎng)大地震,也成為了當(dāng)時(shí)西方世界的全民事件。就像今天發(fā)生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之后,各大媒體、各個(gè)意見領(lǐng)袖會(huì)紛紛發(fā)表言論一樣。里斯本大地震之后,當(dāng)時(shí)歐洲文明世界中的那些大咖們,從伏爾泰、盧梭到康德,紛紛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而他們都在反思一件事情——
在這個(gè)宗教的節(jié)日里,在人們爭(zhēng)相表達(dá)自己的虔誠(chéng)的時(shí)候,正義且仁慈的上帝,為什么會(huì)不加以區(qū)分的摧毀了他的信徒們?
那個(gè)一直都很反感“無(wú)論何者,皆為正確”(用現(xiàn)在流行的話來(lái)說(shuō),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伏爾泰率先發(fā)聲,寫下《里斯本的災(zāi)難》,“如果你看到這些事實(shí),這恐怖的景象,你會(huì)認(rèn)為他們的死是罪有應(yīng)得嗎?那被抱在母親的胸前、流著血的嬰兒,你能說(shuō)他們有什么罪過(guò)嗎?難道在這坍塌的里斯本,你能找到比花天酒地的巴黎更多的罪孽?比起崇尚奢靡的倫敦,里斯本的放蕩豈敢媲美?但大地吞噬了里斯本,法蘭西的輕狂兒女們,還延續(xù)著無(wú)度的宴飲,跳著瘋狂的舞蹈。”
盧梭對(duì)伏爾泰這種對(duì)上帝的抱怨表示出了反感,一方面他認(rèn)為伏爾泰的說(shuō)法剝奪了窮苦之人最后的希望,亦即對(duì)善良的神明與死后之生活的信仰;另一方面,盧梭也指出,這場(chǎng)地震之所以是一場(chǎng)災(zāi)難,更多是人為所犯下的錯(cuò)誤。在后來(lái)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盧梭宣稱,肯定是某種諸如此類的大災(zāi)難促使我們從自然之安適中走出來(lái),進(jìn)入了人為的且永遠(yuǎn)帶有傷害性的社會(huì)性存在。
相比當(dāng)時(shí)早已大名鼎鼎的伏爾泰和盧梭,康德那時(shí)候還是不過(guò)是一個(gè)年輕講師,他在地震之后發(fā)表了一些科普的內(nèi)容,讓人們了解地震的本質(zhì)。而差不多60年后,歌德也回憶起當(dāng)他還是個(gè)小男孩時(shí),這場(chǎng)地震給他思想帶來(lái)的困擾。
從伏爾泰到盧梭、康德,雖然力度不同,但實(shí)際上他們的觀點(diǎn)都指向了同一個(gè)時(shí)刻,也就是韋伯所說(shuō)的“祛魅”,把神圣的觀念從世俗的生活中驅(qū)逐出去,自從亞當(dāng)和夏娃被趕出伊甸園之后,人們?cè)谶@一刻才真正的失去了上帝的庇護(hù),失去了“樂(lè)園”。
對(duì)上帝正義之心的質(zhì)疑,讓這個(gè)無(wú)所不能的存在,在這個(gè)星球的世俗事物中退場(chǎng)了,上帝對(duì)個(gè)人的苦難、對(duì)世界性的災(zāi)難沒有一絲一毫的興趣。“上帝”也變成了逃避責(zé)任的犬儒主義借口,至此,人類走出了神圣的庇護(hù),真正的對(duì)自己負(fù)責(zé),真正用理性、用行為對(duì)所遭受的一切提供解釋,而不再把一切歸咎為壞運(yùn)氣、命運(yùn)和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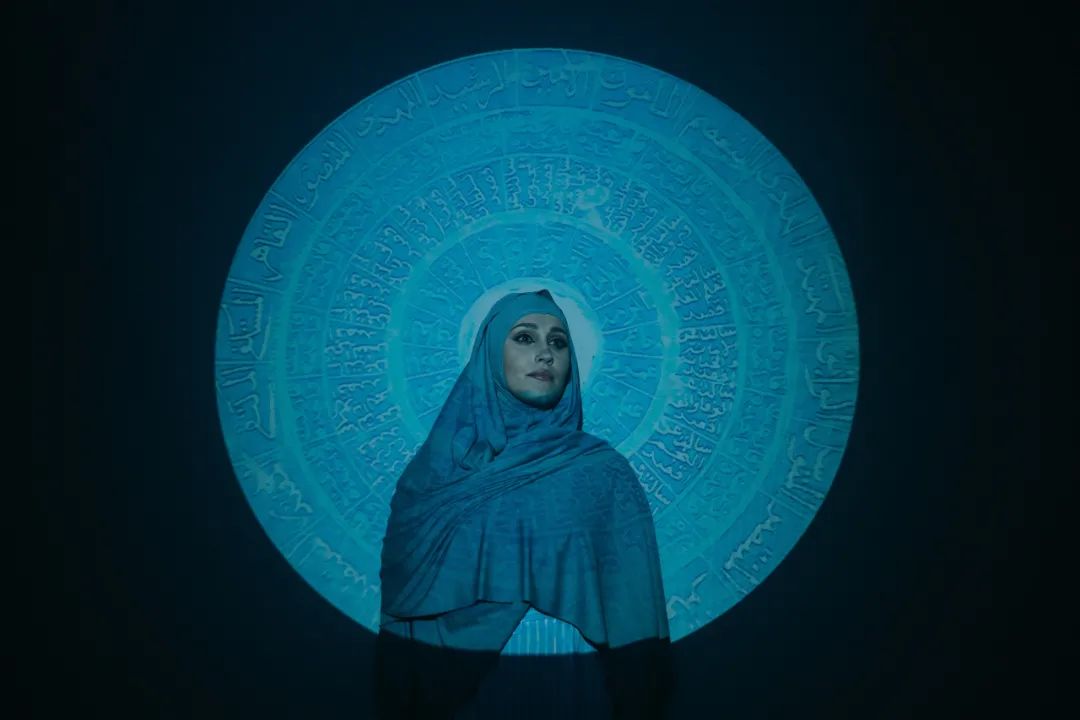
德伯家的苔絲 身為女人是不幸的嗎?
在托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中,苔絲被描寫成了一個(gè)“純粹的女人”,這可并不是什么稱贊的話語(yǔ)。有個(gè)男人誘奸了她,他們的孩子死了。第二個(gè)男人娶了她,但得知她的過(guò)去之后拋棄了她。當(dāng)誘奸者再次毀掉她的幸福的時(shí)候,她殺死了那個(gè)男人。最后她因?yàn)檫@一罪行被處以絞刑。
從這樣的故事情節(jié)中,我們可以理解“純粹的女人”,意味著苔絲僅僅就是個(gè)女人,他的命運(yùn)完全被性別決定了,這甚至是一個(gè)自然的詛咒。正統(tǒng)猶太教徒,會(huì)在每天清晨,感謝上帝沒把他們?cè)斐膳恕?shí)際上,這些都說(shuō)出了壓在女性頭上的文化“詛咒”,身為女人,就是被生育功能所限制,成為自然之中的弱者么?
雖然里斯本大地震開啟了人們對(duì)神圣庇護(hù)的放棄和對(duì)自身能力的思考,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個(gè)世界就一切都風(fēng)平浪靜。就像這個(gè)延續(xù)了百年的偏見——從自然的角度,女人就是女人,但從社會(huì)的角度,作為女人變成了一種不幸,本質(zhì)上這不幸是一種不正義。
“不幸”往往是人在面臨災(zāi)難時(shí)候的一種思考,特別是這災(zāi)難是不可抗的,人們就會(huì)放棄對(duì)責(zé)任的追究,因?yàn)闊o(wú)論怎么追究,最后都?xì)w結(jié)到命運(yùn)、上帝身上,好吧,“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承受的痛苦,也只能用一個(gè)不幸來(lái)帶過(guò)。
而“不正義”,則是除了天災(zāi)之外的人禍,當(dāng)災(zāi)難有加害者,有施暴方的時(shí)候,人們就可以在這個(gè)事件中找到真正的責(zé)任人,并用“不正義”為他們的行為命名。特別的,這種不正義往往會(huì)激起更多人的感同身受,在發(fā)現(xiàn)他人遭受不正義的時(shí)候,人們會(huì)產(chǎn)生一種共情心理,仿佛自己也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回過(guò)頭來(lái)看,營(yíng)造出身為女性就不幸的這種觀點(diǎn),本身就是不正義的。而很多人還經(jīng)常以“這世界本來(lái)就不公平”為借口,試圖將不幸背后的不正義掩蓋,使其光明正大的成為一種定論。
不正義大多是對(duì)公平的破壞,是在歧視、偏見下的一些行為,這些行為造成了相對(duì)的剝奪感,即用一些欺騙性的手段,剝奪了某些人的權(quán)力。
如果同樣是去吃飯,有的人享受了折扣,有的人沒享受,那這就帶有歧視性,那些沒有獲得折扣的人就有一種相對(duì)的剝奪感,相對(duì)那些有折扣的人,他們的權(quán)力被相對(duì)的剝奪了。那么如果商家有很好的理由,比如享受的人是老客戶,沒有享受的是新客戶,就可以解釋的過(guò)去,否則那種隨機(jī)的“歧視”,就會(huì)被認(rèn)為是一種不正義的行為。
所以在那些長(zhǎng)久以來(lái)一直存在歧視的領(lǐng)域,比如性別、種族、職業(yè)等等,最終都是不正義在作祟。但大多數(shù)時(shí)候,人們卻用“不幸”來(lái)模糊這種不正義,以至于受到歧視的人也同樣被麻痹,放棄了對(duì)責(zé)任人的追討,而最終對(duì)現(xiàn)狀默認(rèn)。

人只因承擔(dān)責(zé)任才是自由的
卡夫卡曾經(jīng)說(shuō),“人只因承擔(dān)責(zé)任才是自由的,這才是生活的真諦。”而薩特也說(shuō)過(guò),如果存在主義有核心的話,那么就應(yīng)該是“ 自由承擔(dān)責(zé)任的絕對(duì)性質(zhì)”。不幸和不義,最大的區(qū)別,就是在責(zé)任上面。
在傳統(tǒng)的哲學(xué)中,有一個(gè)被公認(rèn)的原則——萬(wàn)事有因,而在這原因不斷向上追溯的過(guò)程中,在整個(gè)因果鏈的盡頭,宗教認(rèn)為那是上帝,是一切的源初,上帝是因,那么上帝就要對(duì)一切負(fù)責(zé)。而尼采說(shuō),上帝死了,現(xiàn)代思想諸如存在主義就認(rèn)為,人是原因,人也要肩負(fù)起這個(gè)原因的責(zé)任。
當(dāng)啟蒙將上帝逐出世俗世界之后,人實(shí)際上被迫走入到一個(gè)困難的境地,也就是自己即是自己的原因,也是自己的結(jié)果。在享受自己生活的同時(shí),也要承擔(dān)這種享受背后的責(zé)任。從此,“不幸”,這個(gè)能讓人略有寬慰的借口在世界上消失了。
所有我們口中的“不幸”,最終都是一個(gè)個(gè)的不正義,教育的不幸,婚姻的不幸,工作的不幸等等,這些不幸只不過(guò)是一種不正義的代名詞或隱身法。像盧梭所說(shuō),人被迫從自然狀態(tài)中走出,從此就進(jìn)入了一個(gè)無(wú)奈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之中,也從此無(wú)法再逃離。
就像宗教能找到一個(gè)上帝一樣,一切社會(huì)層面的不正義,都能歸結(jié)到一種“原初正義”上,這個(gè)就像上帝有很多名字一樣,“原初正義”在世俗世界也有很多名稱,比如分配制度、所有制等等。分配的不正義,幾乎是大多數(shù)不正義的起源,也是大多數(shù)不正義的歸宿。
也許有的人會(huì)認(rèn)為,自己跟不正義掛不上鉤。但很多時(shí)候,人們往往會(huì)陷入“消極的不正義”而不自知。對(duì)不正義行為的漠視,對(duì)他人不正義遭遇的毫無(wú)反應(yīng),實(shí)際上是大多數(shù)人在一種麻木的社會(huì)生活中,喪失追究責(zé)任的想法和能力的體現(xiàn)。
當(dāng)然,這并不是大多數(shù)人的主觀意向,施加不正義的人往往會(huì)制造一些假象,讓不正義變成不幸,導(dǎo)致旁觀者無(wú)法分辨,最終完成了施加不正義的人與消極不正義的人的合謀。就像疫情之中,把所有的問(wèn)題都?xì)w結(jié)為“不幸”,而所有的行為都?xì)w結(jié)為“正義”,最后“正義”戰(zhàn)勝了“不幸”,只有功勞,而沒有責(zé)任。
面對(duì)“不正義”,人可以報(bào)復(fù),但面對(duì)“不幸”,人只能默默承受。以不幸作為借口,就讓一切責(zé)任化為空氣,讓一切能夠修正、改良甚至進(jìn)步的拳頭都揮空。里斯本大地震之后的幾百年里,人們擺脫了“不幸”的困擾,真正的肩負(fù)起人之為人的責(zé)任,才有了現(xiàn)代世界的車水馬龍、繁花似錦。但“不幸”依然沒有在這個(gè)世界死去,那些試圖利用它的人,總是在不斷招魂,讓不幸蒙蔽人們的雙眼,將人忘記可以承擔(dān)的責(zé)任,甚至忘記承擔(dān)責(zé)任這一種能力。
不幸與不義,就是現(xiàn)實(shí)鏡子,反射回的光,照出每個(gè)人的思想,以及作為人的一切可能。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chǎng),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qǐng)澎湃號(hào)請(qǐng)用電腦訪問(wèn)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