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橫山廣子:東亞視野中的大理社會文化(下)
受訪學者:橫山廣子(YOKOYAMA hiroko) 日本人,出生于東京都。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人類基礎理論研究部教授,兼任日本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教授。專業為文化人類學。以云南省大理白族為主,中國西南地區直至東南亞各民族為研究對象,基于廣泛的田野調查,致力于以上各民族社會的社會結構、文化變遷、 民族認同以及民族關系等主題的研究。編著《少數民族文化和社會動態——來自東亞的視野》,共同編著《流動的民族——中國南部的遷移和民族認同》《“民族”概念在中國的產 物》等40多篇日中英文的學術論文與著作,并主編 20 余篇影視民族志作品的制作。
訪談者 :張人大,出生于大理周城,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化人類學研究室碩士研究生。
大理時光
張人大:我們都知道橫山老師是在大理周城村展開的田野調查,但是大理盆地內是有許多白族村莊的。您當時為什么要選擇大理周城作為田野點?
橫山廣子:其實這也并不是我自己決定的。當時批準我可以在大理進行調查之后,我提交了詳細的調查計劃書的同時,也提交了自己想要在怎樣的村莊展開調查。不過,我接到的相關部門的決定通知是調查地點只能是周城村,而且調查期間要住在下關的洱海賓館。在去大理之前,在昆明就有一位研究者建議我說,一方面周城是一個示范村,外來訪問大理的人通常都會被帶到那里,要做田野調查的話去到外來來訪人比較稀少的村莊比較好;另外一方面周城距離下關將近40公里的路程,住在下關每天要來回似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不過,調查開始之后我卻漸漸感到,可以在大理盆地之內典型的白族村莊做調查這也是非常幸運的一方面。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周城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最大的白族自然村,在這里你可以觀察到白族的生活、民俗和風俗習慣的方方面面。但是話說回來,周城和下關之間遠距離來回這一點的確讓我吃了苦頭。當時沒有現在這么方便的面包車,去周城只能搭乘洱源方面的長途汽車。由于下關是始發站,楊國才老師和我可以順利搭乘早上7點準時出發的汽車。由于汽車在途中走走停停,到周城就已經是8點半,有時已經是9點多。周城鎮(現在的行政單位是喜洲鎮周城村民委委會)是擁有16個社的大村莊,所以我決定先選定其中一個社進行全戶采訪。當時周城鎮政府指定了靠近公路的一個社,該社的社長每天陪同我們進行采訪。在當時的大理農村,村民一大早就早早出門干農活,到了大概上午10 點半左右再返回做早飯。我們也就盡快趁著這個時間點去周城飯店吃飯。大概到了12點多一點,吃完早飯的社長就過來和我們會合開始下午的訪問。但是,當時完全不清楚回下關的汽車幾點從滇藏公路經過周城,一旦到了下午3點多鐘就必須要在路邊等候。公路旁邊經常塵土飛揚,即使3點左右開始等候,汽車還不一定馬上就來。有兩次等到下午5點車還沒來。這種情況只能搭乘大貨運汽車。站在拉木材貨車后面的空位上,貨箱風特別大,有一次吹感冒了,發高燒引起肺炎,還在大理州人民醫院住院。

采訪周城村民(攝于2006年)
張人大:以前的交通的確很不方便。剛才談到了入戶訪談的主題,而且您之前也提到了在和楊國才老師學習白族話,那么在田野調查中是使用白族話嗎?從語言方面來看您覺得對您最困難的是哪里?
橫山廣子:說實話,白族話本身對于我來說就很難。首先一點就是沒有教材。這個東西在白族話里是這么說的,那個又是這么表達的,如此而來在我筆記本上確實是記錄下了很多內容。不過即便將這些內容匯總起來,也很難掌握白族話的語法體系。這樣一來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這門語言的整體性。所以很遺憾的是現今白族話的水平還是比較低。不過話說回來,多虧學了一些白族話。在田野中你一說白族話,和村民的距離感是完全不一樣的。例如,“您家有多少人?”或者“今年多大啦?”當時這些已經會說了。不過也是經常遭遇村民懷疑的眼光,“你是做什么的,是來查戶口的嗎?”雖然我進行的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類學基礎調查,但經常不被理解。而且由于當時我的白族話語言能力很低,經常被村民說 :“完全不明白你在說什么,還是講普通話吧!”但是比如說像一部分老人,也有不會普通話的,這時就讓在場的會普通話的人進行翻譯。一些比較復雜的問題基本都用普通話進行訪談,所以白族話就一直保持在一定的水平,沒有進一步改善。這一點我至今都感到非常遺憾。我認為做人類學研究,通過第三者進行翻譯是無法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的。在我看來,自己提出問題并傾聽對方的回答,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旁聽他人的交談、對話,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解這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從主位理解的觀點來看,精通研究對象的語言也是必須的。
張人大:除了要精通語言,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我們會經常提到與研究對象同吃同住同勞動,來進行參與觀察。您在調查期間也曾經有一段時間是住在農戶家里是吧?我還記得聽爺爺奶奶說是我們老家的隔壁。
橫山廣子:是的。我按照進入田野調查的順序跟你述說。第一次過去調查的時候,就像剛才跟你說的那樣,每天都要往返下關與周城之間,來回奔波在四十公里的路程上,我曾一度病倒住院。所以在第二次下去調查之前,我了解到周城飯店不僅提供餐飲,里面還有為長途汽車司機提供住宿的房間。因此,我提出了住在周城飯店的申請,后來順利得到了批準。這次陪同我進行調查的是出生于喜洲、并且畢業于抗日戰爭期間曾遷移于喜洲的華中大學的楊希孟老師。如此一來我便可以一直待在周城,在夜間舉行的儀式也能夠得以觀察。第三次的調查時間比前兩次都要長。在此之前曾經和馬曜老師商量過想要在大理做田野調查一事,他當時建議我在大理教日語,這樣一來我后來在大理做半年調查的申請也得到了批準。由于半年的時間也算比較長,所以陪同我做調查的老師也三個月調換一次,后來分別來陪同我的是做民族藝術研究的楊均老師和出生于喜洲的董學紅老師。
在第三次調查抵達周城之后,我和來自云南民族學院和大理州政府雙方的外事辦公室的相關人員一起去周城鎮政府打了招呼,在磋商的時候我又提了另外一個要求。就是希望能在某一家村民的家里吃飯。因為當時周城飯店的飲食整體比較油膩,我的腸胃受不了。當我還身在昆明為下田野調查做準備的時候,接到了日本NHK打來的國際長途電話,NHK希望作為少數民族研究者的我配合他們在云南的采訪工作。得益于此,早于我自己正式的田野調查,我就陪同NHK一起去了麗江和大理。但是意想不到,當和NHK采訪團一起回到大理之后,全部人員當中就我一個人感染了痢疾,并第一次住進了州醫院。所以第一次調查真正開始于出院之后的5月初,而并非事先計劃好的4月。有了這樣的前科,雖然第二次住院之后檢查的結果確認并不是痢疾,但是醫生也很謹慎,并沒有輕易同意我出院。和在周城飯店一樣,以每個月支付一次伙食費的形式換一個地方解決伙食問題,這件事本身其實并不困難。問題在于,在一般的農民家庭里面比較難調整吃飯時間這個問題。那時一旁的外事辦工作人員就建議要不就索性將住宿也定在提供伙食的農戶家里。對于這個建議鎮政府也表示同意。之后數天的協商結果我的入住的農戶家庭就得以確定了。入住的農戶是一個兩戶人家居住的院子,家里人口相對比較少,給我騰出來一間面朝堂屋右手邊的房子。在那里居住的半年時間,真的是很充實地度過了每一天。作為一家之主的張騫先生是一位很親切的人,不僅僅讓我和家人一起就餐,無論是農活,還是婚喪嫁娶之事,他們家所參與的活動只要是我希望做的都允許我一起參加。白族話也是在那半年里最有長進。
張人大:1980 年代中期,住到農民家中進行調查的外國人在云南省也是很少見的吧?
橫山廣子:是的。可以說這也是在云南許多人的理解與配合之下才得以實現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曜老師的幫助。回顧整個我個人1980 年代以來在云南的調查研究,所到之處始終都有馬老師的各種關心與建議。此外在我1984 年剛到昆明之際,馬老師給我介紹的何耀華老師,自從他 1990年代擔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以來,一直都非常關心我。無論是對我個人的調查,還是中日兩國學者之間的共同研究,兩位老師都給予了很多的建議與協助。

與1985年入住的房東家人在一起(攝于2006年)
我的學術研究總結
張人大 :現在試著回顧一下的話,你如何總結自己至今的白族研究和研究的整體成果?
橫山廣子:如果根據研究主題進行分類的話,我認為大致可以分為以下 4 個方面:(1) 親屬組織和社會結構;(2) 宗教儀式;(3)民族認同;(4)文化和社會變遷。
自從可以在白族村落里做田野調查以來,我最初注意到的是 Edmund Leach 在《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1982)里所展開的討論。Leach 將 Hsu 和 Fitzgerald 的著作進行了比較。在他看來,Fitzgerald 很好地闡述了如何在云南的歷史和地理上去定位大理人的問題,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由于 Hsu 過于熱心地去表明大理的這個村莊,即 West Town(通稱 :西鎮)作為中國整體的典型這一點,導致他幾乎沒有觸及生活于此的“民家人(白族)”的地方文化特性。僅從這點來看,Leach 的評價和批判可以說是很中肯的。但是,對于斷定 Hsu 著作中的描述是他個人童年期的經歷和在大理進行田野調查時作為成年人所了解的混雜這一點,我感到懷疑。因為我認為,其一,兩本著作主要的研究著眼點并不相同 ;其二,雖然說調查地點都是大理盆地,但是調查對象的地點和社會階層的不同會產生差異。我還了解到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有過關于在漢語里被稱為“民家”的人們應該被歸為漢族還是少數民族的爭論。此外,從中央政府認定民家為少數民族并將之稱為“白族”,直至 1956 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的這一過程中,支持“民家人”是漢族的民家出身的學者和文化人并不少見。因此我強烈感覺到沒有對當地的情況進行詳細的調查是無法簡單地對兩本著作做評價的。Hsu 主張西鎮人是文化上的中國人主要依據的是祖先祭祀的形態。因此,我自身的白族研究也是將重點置于親屬組織和社會結構而開始展開調查和分析的。從家族形態等非常基本的方面出發,與親屬組織相關聯,探求其與普通的漢族或者是漢族規范之間是否存在差異。結果,我發現從妻居的婚姻形態和漢族規范或者是一般的情況有很明顯的不同。從我當時對周城16個社當中2個社全部家庭的婚姻情況調查結果來看,從妻居婚姻的比例大概分別占到10% 和 20% 有余。而且不僅僅是存在比例高,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即某家富裕家庭老二以下的兒子會到其他沒有兒子的富裕家庭上門,并在改姓之上,按照女方家的字輩重新取名,此后正式成為女方家的繼承人。在與漢族相比較之時,要了解如何定位白族的從妻居婚姻的興盛問題,是有必要對漢族進行理解的。大學研究生以來,我已經看過Kulp、Maurice Freedman 和費孝通等人的著作,而且閱讀并參考了 1970 年代后期之后的包括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在內的漢族研究文獻。其中,Arthur P. Wolf 等人編著的《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中國的婚姻和收養,1985—1945)》(1980),對現象的考察建立在廣泛的地域以及將近 100 年的時間軸之上,對宏觀考慮從妻居婚姻很有幫助。我早年對從妻居婚姻的相關研究成果收錄于“大理白族的從妻居婚姻”,伊藤、關本、船曳編《現代社會人類學第 1 卷 親屬與社會的結構》(1987)。但是,中國地域十分寬廣,在沒有對各個地區的漢族進行徹底研究的情況下,這并不是一個最終的結論。不過在我看來,當時非常興盛的白族從妻居婚姻,我們是否可以將其考慮為與漢族的連續性的一個對立呢。此外,在親屬關系和社會結構方面,我還研究了白族的“老友”習俗。這就像在拉丁美洲地域常見的宗教儀式性的共同親子關系(compadrazgo)一樣,是一種由與兒童相關的擬制親屬關系而衍生的成年人之間的社會和經濟關系。通過對這種關系的研究我指出 :“老友”可以讓在地理上或文化上有距離間隔的雙方結成紐帶聯結。
張人大:對宗教和儀式的研究興趣也是源于您開展云南田野調查之初嗎?
橫山廣子:基于田野調查的宗教和儀式的研究,我最早的論文是于1985年8月在西南民族研究學會上發表的《彝族密枝節小考》,收錄于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西南民族研究彝族專集》(1987)。此外,自從在大理開展調查以來,我一直關注白族特有的本主信仰和火把節,長期以來持續收集著相關田野資料。然而,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自己究竟能開辟怎樣的新地平線,調查當初的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最初開展的本主研究類似于之前的親屬研究,以漢族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漢族與白族之間的異同為切入點,嘗試了以往我所開展的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研究里未曾嘗試過的研究視點。尤其是以下兩個方面在此后都一直持續進行著,可以說已成為我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第一,將田野調查與歷史文獻知識相結合進行考察的方法。我認為正是由于中國擁有諸如地方志等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此研究方法才具有其可能性,雖然這對于中國本土的研究者來說可能是極其普通的事情。
第二,在注意歷史過程的基礎上,來考察某個概念的成立以及由此概念的成立所引發的社會分節化與其伸展(即依據某個概念的成立,社會或被重新分類,或被賦予某種意味,如此社會被重新構建)。如此研究可以順利進展的契機,歸根結底仍然是田野調查。1986年訪問鶴慶縣時,我試圖以“本主”一詞來詢問鶴慶的基本宗教情況,結果和當地人完全無法溝通。在涉獵云南的地方志之后終于搞明白,“本主”一詞的出現比較晚而且具有地域局限性。在此之前,在云南廣泛有“土主”的記載。無論是本主還是土主,都是對某種范疇的神格的總稱概念。通過考察“各個概念是什么人依據什么樣的觀點而命名?”,可以進一步開拓出新的理解。我提出了如下的假設,即從處于中國文明中心的“文”來看,處于邊緣極端的是“土”;從周邊來看自己是“本”,此后新參的為“客”,進而我們可以通過這兩組對立概念來闡明“本主”這一名稱的確立過程。在1987年湖南的田野調查中,我了解到人們以將除夕提前一天的形式來說明民族間的區別。火把節研究的啟發正是來自于這點。此后,在云南省大理州以外的地區的田野調查中,我特別注意火把節的日期,并在盡可能的范圍之內詳細查詢了歷史文獻中關于云南以及周邊相鄰地區火把節的記載。在此基礎之上我斷定,有關日期區別的相關歷史文獻記載,為我們留下了有關民族集團邊界、分布狀況、人口流入以及民族集團間的勢力盛衰等方面的痕跡。

采訪村莊法師(攝于2006年)
張人大:可以說您關于白族宗教與儀式的研究,是以歷史的觀點以及白族與他民族之間的關系、邊界等方面的討論為中心吧?
橫山廣子:可以這么說。無論是親屬組織和社會結構,還是宗教與儀式,我一邊關注其與以漢族為主的他民族的差異和邊界,一邊開展白族研究。我認為這樣可以與第三民族認同領域相連接。我生于日本長于日本,從小生活的環境與像中國這樣將民族平等與團結列為基本國策的環境完全不同,可以說我還是缺乏與民族有關的日常感覺。因此,在大理盆地進行田野調查中,通過觸及當地人日常性的民族認同感覺,我逐漸開始認識和理解民族認同相關的諸問題。比如那時我為了收集生活中所使用的基本白族話詞匯制作了列表,然后逐一向寄宿家庭的張騫先生請教這些詞匯的白族話說法。像“白族”“漢族”這樣的單詞也列入了單子中。不過在聽到他在稍做考慮之后用白族話說到“sua bai no(說白族話的)”“sua ha no(說漢族話的)”的描述的時候,我暗暗地在心里鼓掌喝彩。因為 Fitzgerald 書中所寫的內容得到了確認。不過,是在此后對周城周邊的回族長老進行訪談之后才開始深思其意思。
張人大 :也就是說在大理除了白族之外,您對回族也進行了調查?
橫山廣子 :是的。不過不是為了研究回族而研究,而是為了更深入地理解白族。我認為研究白族,很有必要把握大理盆地這一整體社會。在清朝末期杜文秀的檄文中,有關云南有這樣的記載:“回漢夷三教雜處,已千百年矣。”此處將云南的住民劃分為回教、漢教與夷教,而且這里所提的“回教”一詞并不是指伊斯蘭教,而是伊斯蘭教徒的意思。對于回族人來說,宗教是區分人最重要的基準,而對于大理白族來說,語言才能體現本民族與漢族的邊界。居住于大理盆地的回族,日常所使用的語言根據所居住的環境有所區別,或者是白族話或者是漢話,但是以回族的觀點來看,在體現民族邊界之上語言并非占據重要的地位。在某一地域的歷史、文化環境之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作為自身感覺而培養起來的民族集團之間的邊界線是豐富多彩的。以這樣源于田野調查的察覺為基礎,我在1987年撰寫了名為《大理盆地的民族集團》的論文。此后,民族認同研究成為我自身研究的一個重要支柱。 其內容可以分為以下兩大類 :一是從中國社會整體來把握有關民族識別和民族概念等方面的研究,代表成果如《少數民族的政治與話語》、《巖波講座文化人類學第五卷·民族的生成與邏輯》(1997);“民族概念在中國的產物”,端信行編《民族的二十世紀》(2004),等 ;另外的一類研究不僅將目光置于現代,而且通過追溯歷史來考察以大理白族為中心的民族邊界以及民族認同的形態,代表成果如“遷移到云南白族地區的漢族 : 由來于明朝軍屯的住民”,塚田誠之、瀨川昌久、橫山廣子編《流動的民族——中國南部的遷移與民族認同》(2001);“關于民族認同變化的研究——以云南楚雄地區白族和漢族的關系為例”,《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等。為了進一步了解在20世紀上半葉為主的白族民族認同情況,我又去緬甸做了調查。但是由于緬甸的調查材料基本上是個人材料,現在我還在考慮如何將這些調查材料寫成論文公開出版。
張人大 :是否可以談一下您關于文化和社會變化的研究呢?
橫山廣子:從我開始調查的1984 年至今,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斷地蹲點、集中調查的周城,在大理的農村中屬于發展非常醒目的村落之一。一方面是大量由包工頭帶領的外出打工副業隊很昌盛,另一方面在這個大理州最大規模的自然村里,由村辦企業或者是個體戶所帶動發展起來的制造業以及商業活動也很繁榮。特別是1990年代扎染的發展所帶來的與以往沒有接觸過的外部社會所進行的經濟交流,不僅帶來了新興產業的抬頭,也讓白族自身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我當時對這一點非常感興趣, 寫了《從云南白族的村落看中國社會的變動過程》。在信息、交通都已經很發達的今天,將諸如西部大開發一樣,在經濟上相對落后地域的發展情況也加以考慮的話,在地理上相對遠離的人群之間關系的維系的意味顯得越來越重要。對于文化資源的認識,新的關系所帶來的革新是很有可能與經濟發展相聯系的。其次,與經濟發展并不掛鉤的重要傳統知識和技術正不斷地流失,針對這樣的形勢,我認為研究者和當地人民相互溝通協助來推進記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我們是否應該認真考慮基于與調查地的人們合作活動的研究的重要性。無論是經濟發展比較困難的地域,還是諸如周城一樣經濟發展相對比較順利的地域,文化與社會的變動正在發生。特別是在周城,我感覺到風俗習慣上的變化正逐漸凸顯。“具體是什么在變化?”“以何種方式在變化?”“應該如何解釋這樣的變化?”我覺得現在正是加以重視、考察的時期。
張人大:到此我們大概回顧了您迄今為止在云南的研究歷程,訪談的最后您能做一個總結與展望嗎?
橫山廣子:除了之前已經提到名字的各位老師之外,正因為有云南各方面人的善意,我的研究才得以延續。在此也對抽空接受我采訪、直接協助我調查、為我泡茶以及給我借板凳的各位表達我的感謝之情。對于我迄今為止的研究,研究成果產量低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田野調查、閱讀文獻并進行考察,如此研究進行到中途,仍有許多的主題尚未撰稿。想著再整理一下文獻調查再執筆,但是總是忙于工作單位大學院的教育工作和其他的事務工作,結果仍有許多研究都還沒有結果。雖然現在從生物學年齡來看已經是老年人類學者,但是我覺得自己還算不上是一個真正成熟的研究者。今后,在推進實地與文獻雙方調查的同時,讓以上所陳述的研究結出果實,發表研究自己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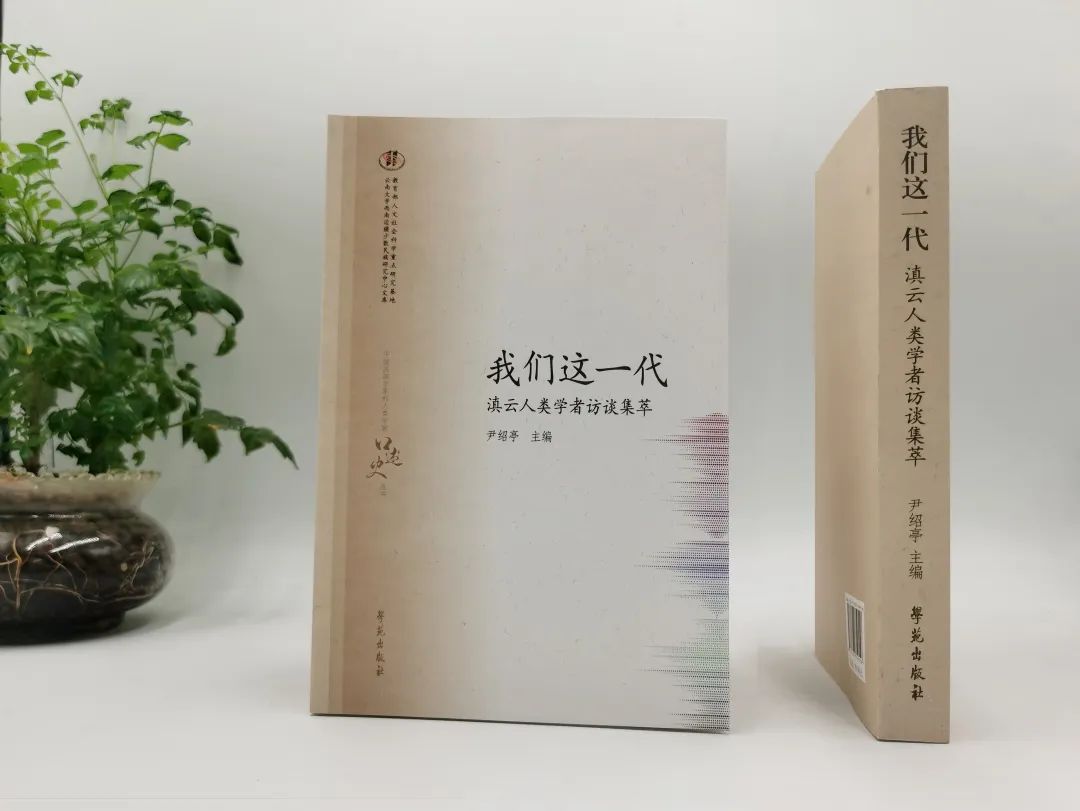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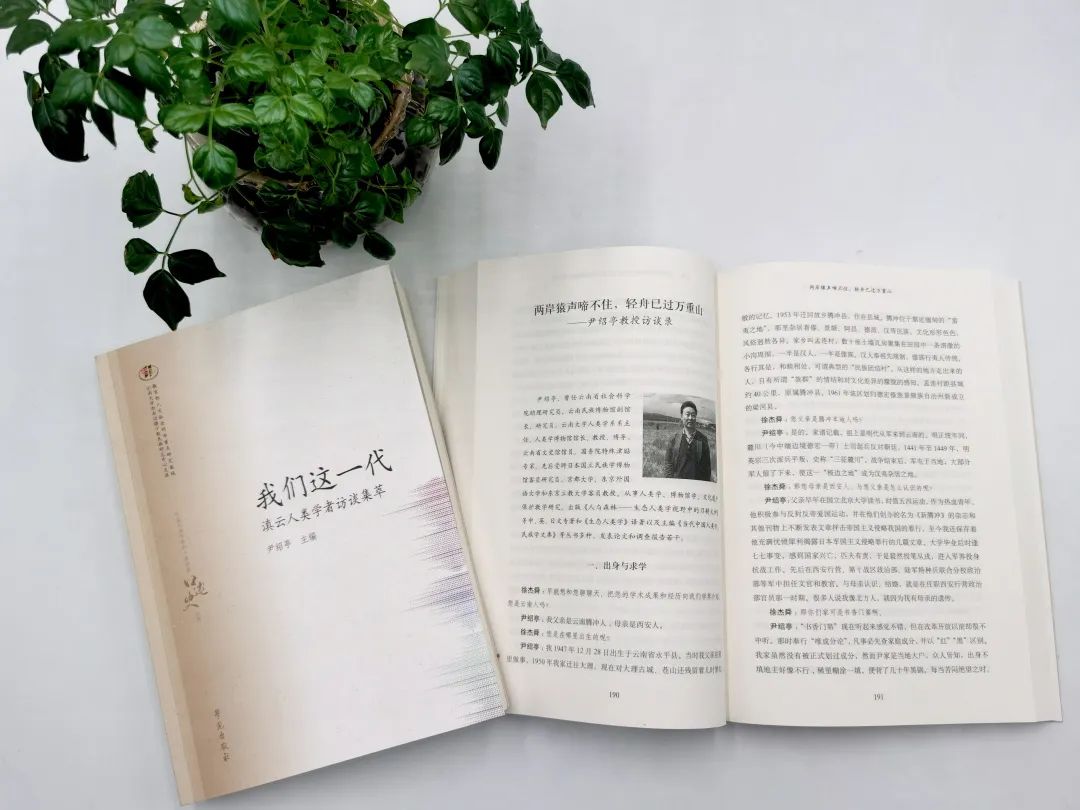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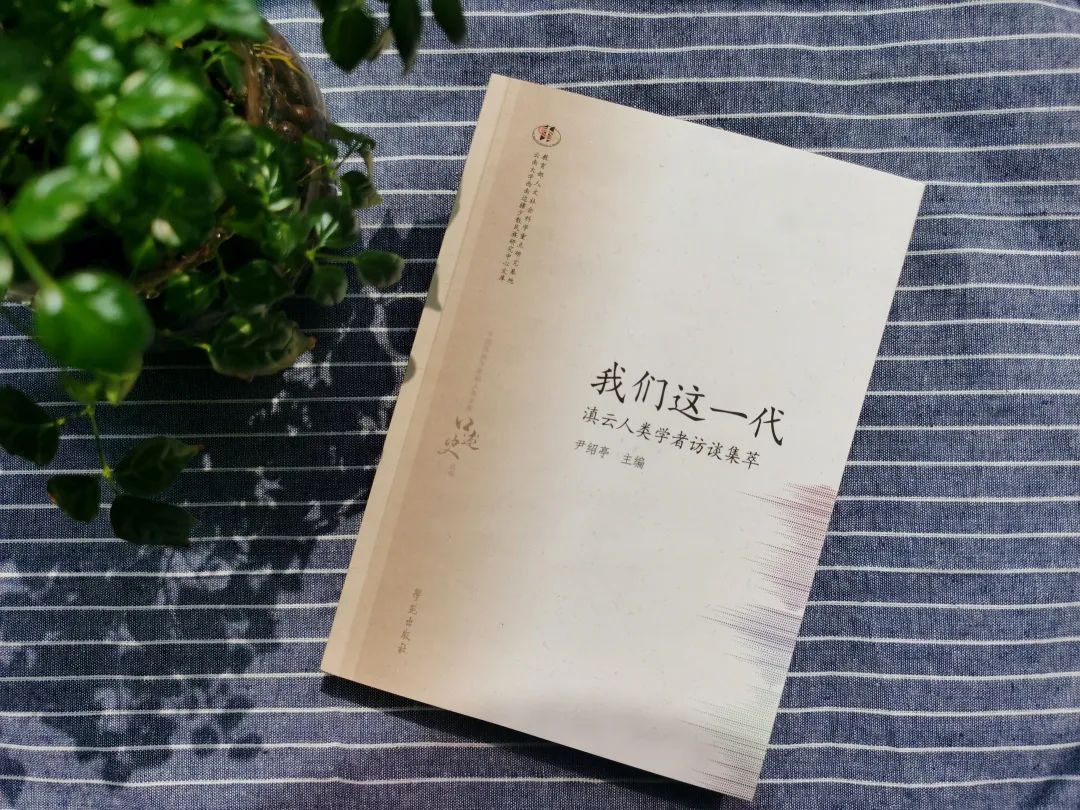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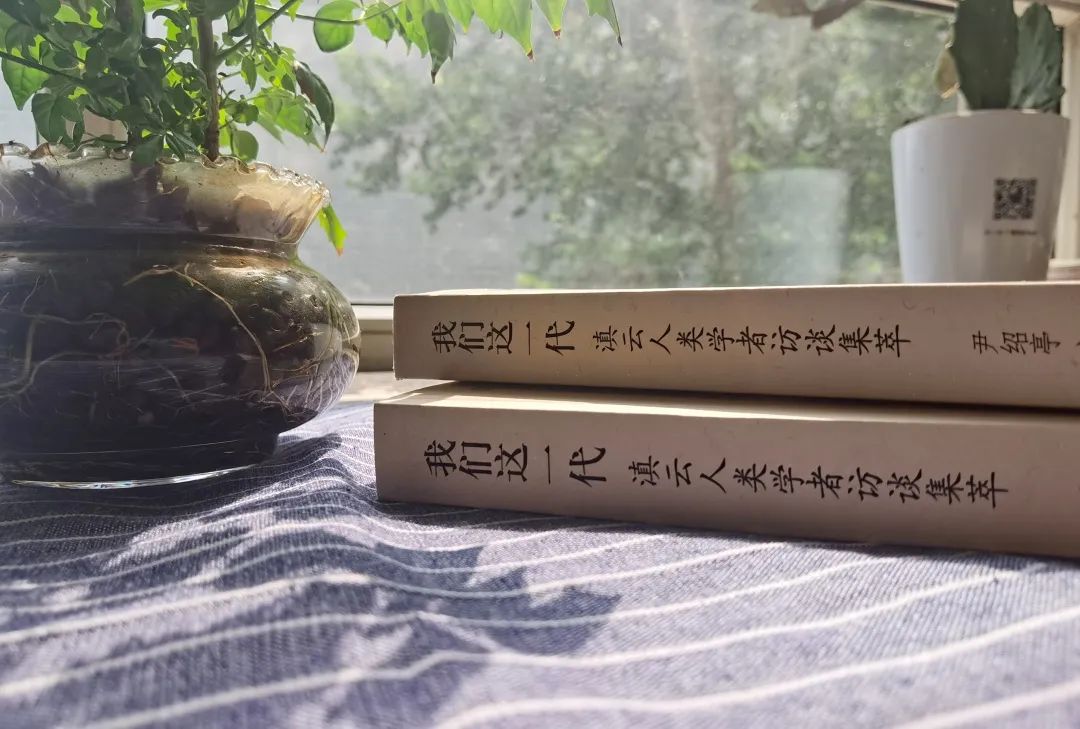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0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
序/1
邊緣學術與前沿思想
——趙捷研究員訪談錄 / 1
從景頗研究到西南界域人類學
——何翠萍教授訪談錄 /20
東亞視野中的大理社會文化
——橫山廣子教授訪談錄 /45
吃千家飯,爬萬重山
——梁旭研究館員采訪錄 /69
矢志如一, 百折不回
——楊庭碩教授訪談錄 /94
但開風氣不為師
——林超民教授訪談錄 /112
以物知史 以物證史
——江曉林館長訪談錄 /136
終是不忘讀書心
——顧士敏教授訪談 /149
亞洲、太平洋的海洋和森林生態人類學的足跡與前景
——秋道智彌教授訪談錄 /164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尹紹亭教授訪談錄 /190
積沙成塔,跬步前行
——方鐵教授訪談錄 /208
揚長不避短 :我的醫學人類學實踐
——張開寧教授訪談錄 /227
田野有哲人
——李國文教授訪談錄 /249
樂史 :云南之路
——唐立教授訪談錄 /270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施傳剛教授訪談錄 /290
云南吾師
——鄧啟耀教授訪談錄 /314
一個納西族人類學者的學術心史
——楊福泉研究員訪談錄 /345
調查之路,參與行動之路
——郭凈研究員訪談 /370
駑馬不舍騏驥功
——郭家驥研究員訪談錄 /388
梯田、絲路及影視人類學研究的開拓者
——王清華研究員訪談錄 /407
“猶欣曠燭青光好,最怕聞雞是枉然”
——段玉明教授訪談錄 /431
博聞強學,啟智創新
——何明教授訪談錄 /449
膽大包天,碩果累累
——瞿明安教授訪談錄 /474
水文明探索中的苦旅者
——鄭曉云研究員訪談錄 /494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