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胡文輝︱記梁承鄴先生:經(jīng)濟(jì)史大家梁方仲遺事述聞
就在寫此文的前一天,我才在微信群里轉(zhuǎn)發(fā)過有關(guān)《梁方仲遺稿》的東西。而到了當(dāng)天晚上,就在朋友圈里見到梁承鄴先生故去的消息。
我分明記得,最近一次見承鄴先生,是和沈展云一同跟他午飯(幾乎每次都是我們?nèi)耍驮谒腋浇牟宛^。就是那次,他送了我一套廣東人民出版社刊行的《梁方仲遺稿》,共八巨冊,我背回去時(shí)覺得沉重?zé)o比——可想而知他提著書過來有多費(fèi)力,也可想而知他那時(shí)身體還甚健旺。人世無常,如露如電,信然!


我與承鄴先生結(jié)識(shí)甚晚,想來應(yīng)是起于我在《現(xiàn)代學(xué)林點(diǎn)將錄》里寫到他父親方仲先生。后來見面所談的,也大體有關(guān)他父親的著述和軼事。承鄴先生的本行是植物遺傳學(xué),我無所了解,他似也未曾談及。故而我只限于略述與他接觸時(shí)的所聞,鴻飛無跡,這算是承鄴先生留下的一點(diǎn)泥上指爪吧。
我不算是有記性的人,自2010年起意,就留有一份斷續(xù)的筆記:與師友飯局時(shí),尤其是拜會(huì)長輩時(shí),若覺得有特別的事,返家后輒草草記下,作為個(gè)人的“如是我聞”,自名曰《師友燕談錄》。查檢筆記本,果然找到與承鄴先生見面的四次記錄。今據(jù)筆記錄出原文,除明顯的文字疏誤之外,只個(gè)別地方稍有刪略,其言有未盡者,則間下按語說明。
第一條記錄是2010年9月3日(東湖新村麥當(dāng)勞餐廳):
中午跟展云、梁公承鄴吃飯,梁公贈(zèng)我其父方仲五十年代聽陳寅恪講課的兩種筆記,席間多涉梁方仲事。
梁公還出示了梁方仲四十年代在美國時(shí)聽胡適講演的筆記(英文),大約是中古思想史方面(展云說其中多涉及禪宗人物)。我說梁方仲和胡適的交往,似無人談及。梁公說起,梁方仲對胡不無芥蒂,大約是因?yàn)榱_爾綱——羅在北大研究所整理拓片,是胡介紹去的,但待遇很低,后來吳晗和梁設(shè)法使羅另謀高就。
梁公又謂,梁方仲跟向達(dá)關(guān)系也不錯(cuò),六十年代去北京——承鄴自己在場——梁方仲曾想將吳晗、向達(dá)請到一塊,但向達(dá)當(dāng)即拒絕。他對吳晗不滿,吳在1957年反右時(shí)表現(xiàn)太狠,而向達(dá)自己是右派。
我提起前兩天看《懷念吳晗》,里面提到,羅隆基四十年代末托吳轉(zhuǎn)給當(dāng)時(shí)在香港的民盟領(lǐng)導(dǎo)人一函,要他們對中共保持獨(dú)立性,但吳扣下未轉(zhuǎn)。到了反右,吳拋出此信,遂成“章羅聯(lián)盟”的一大罪證。
梁公說:梁方仲本來跟陳序經(jīng)不太熟悉,陳后期不得意,兩人才交往漸多。六十年代陳序經(jīng)娶媳婦,還向梁方仲借過錢呢!
我跟展云建議梁公,將關(guān)于梁方仲的回憶和評述文字匯輯起來,編一本《梁方仲學(xué)記》。我說,梁是夠格進(jìn)入這個(gè)系列的(三聯(lián))。后來我又補(bǔ)充,可以將梁嘉彬收入(就像《容庚容肇祖學(xué)記》)。
梁公完成了寫梁方仲的一本書,約三十萬字。他說過一陣可考慮此事。
按:梁方仲聽陳寅恪講課、聽胡適講演的筆記,今已收入《梁方仲遺稿·聽課筆記》。承鄴先生當(dāng)時(shí)寫完的著作,即后來由中華書局刊行的《無悔是書生:父親梁方仲實(shí)錄》。至于我們當(dāng)時(shí)提議的《梁方仲學(xué)記》,大約承鄴先生無力兼及,而我過后也忘了此事。現(xiàn)在想來,這仍是個(gè)很值得做的題目。
然后就到了2017年2月15日(東湖新村表哥茶餐廳):
原來承梁公承鄴贈(zèng)所著《梁方仲實(shí)錄》,讀后校出一些錯(cuò)誤(有幾處較重要,也較有難度),連同張求會(huì)的糾錯(cuò)文章一同交給他。還是展云一起。
席間梁公談起其書出后,王則柯專門找他聊天,表示比不上梁,自己對父親(王起)的了解不多。其實(shí)王則柯本來研究經(jīng)濟(jì)學(xué),寫文章的資格非梁可比……
又說起容庚跟梁方仲來往特別多,見于梁(方仲)的日記(梁自己不名為日記,估計(jì)是故作低調(diào),以免萬一惹麻煩)。梁去世后,容跟他說:你父親不玩收藏,你也不玩,但你父親藏有一幅祝枝山的東西,拿給我看看吧。梁公就拿給他,容就不還了,說是他的學(xué)生馬國權(quán)想要。我說:可查查容捐贈(zèng)的書畫(廣州藝術(shù)博物院的古代書畫藏品據(jù)說十分之一系容原來收藏的)。梁公卻說算了,反正也要不回來了。梁公可能只是私下跟朋友提起,不會(huì)寫文章,但我卻不可不記也。
以容老所藏之豐之佳,一幅祝枝山未必算得上什么,但在老友身后,忽悠小孩子,未免失德了。
按:《實(shí)錄》一書,當(dāng)年我在廣州學(xué)而優(yōu)書店新媒體一個(gè)訪談欄目里,作過簡單推薦:“在中國經(jīng)濟(jì)史領(lǐng)域,梁方仲是有數(shù)的人物,真正有國際影響。作者身為后人,不滿足于寫出個(gè)人和家族的回憶,外緣的史料搜集甚勤,敘述踏實(shí),見解平實(shí),完全達(dá)到了學(xué)者傳記的標(biāo)準(zhǔn)。梁方仲畢竟是純學(xué)者,若非作者的努力,世間恐怕就沒有這樣的傳記了。”這個(gè)評價(jià),自覺非阿私之言。當(dāng)然,承鄴先生本從事自然科學(xué)研究,退休后始因紀(jì)念父親之故介入文史領(lǐng)域,難免較為吃力,尤其手稿釋讀方面頗有疏漏,此固不必諱言,亦完全可以理解。由這一點(diǎn),倒益可見他為表彰先人德業(yè)而不避難的精神。張求會(huì)寫的書評題為《〈無悔是書生〉瑕疵錄》,后發(fā)表于山東大學(xué)《國學(xué)季刊》第五期。至于梁方仲的日記,包括案頭日歷、工作日記,時(shí)間跨度為1957年至1969年,內(nèi)容多較簡略(最宜與《劉節(jié)日記》對照);但照我的印象,這一政治高壓時(shí)期留存的學(xué)人日記似甚罕見,雖片紙亦可珍也。
另有一事:梁方仲散篇論文的最早結(jié)集,應(yīng)是中華書局1989年版的《梁方仲經(jīng)濟(jì)史論文集》,集中了梁氏最精萃的論著。原先手頭只有復(fù)印本,后來才補(bǔ)購一冊原版——就在這一天,我特意拿了過去請承鄴先生簽名。方仲先生不及親承謦欬,請他的哲嗣留下筆跡,也是一個(gè)特別的紀(jì)念吧。如今字在人亡,區(qū)區(qū)簽名,固不可復(fù)得矣。
又同年6月16日(東湖新村表哥茶餐廳):
上次跟梁公承鄴說起,請他問中大圖書館,是否還有《梁方仲捐贈(zèng)圖書目錄》,要一本。承他弄來一本——回來翻看,整理之粗率難以理解。我猜這書之所以難弄,未必因?yàn)閳D書館已沒有,而是太差,羞于示人吧。
臨走時(shí)梁公說起一事甚重要。
《梁方仲捐贈(zèng)圖書目錄》
梁方仲對傅衣凌是很有看法的,認(rèn)為傅用馬克思主義來套史料,大約貶之甚力。(我在《學(xué)林點(diǎn)將錄》中以梁與傅對比,揚(yáng)梁貶傅,梁公泉下有知,當(dāng)引為知己!)在讀史筆記有一條,惜中華書局出版時(shí)承鄴公不愿得罪人,刪去了。
又在一本傅的著作上留有不少眉批,提了不少意見,承鄴公早年將此冊借給葉顯恩(梁方仲學(xué)生),后來找他要回,但葉推說找不到。承鄴公覺得葉后來頗承傅衣凌關(guān)照,故不愿公開這些——但承鄴公自己都不愿公開,又怎么怪得了葉顯恩!
我建議他要求葉提供眉批部分的復(fù)印件。徑要原書,葉可能干脆不還(據(jù)說找不到,拿他沒辦法)。葉已年過八十,此事再遲就更難辦了。(可能是又一例當(dāng)代學(xué)人“借書不還”公案!不過此事時(shí)間長了,梁這邊記得是“借”,但葉那邊可能當(dāng)是“送”,都是老人家,不易說得清。)
另,我剛好早上去看“容庚捐贈(zèng)書畫特展”書法部分。梁公就問起有沒有祝枝山的畫?我笑了。上次看繪畫部分我已特別留意,未見。
按:傅衣凌著作的梁氏批注本,不知還有沒有公布之日呢?此事讓我想起,汪榮祖先生在《槐聚心史》里談到,錢鍾書生前有意將自己看過的《柳如是別傳》贈(zèng)予他,但到2003年他拜會(huì)楊絳時(shí),吳學(xué)昭說“此本已不存在”,想來是錢先生對陳著必有一些負(fù)面的批注,其書遂被“人道毀滅”了!希望梁氏的批注不會(huì)落到一樣的命運(yùn)。但也需要說明,葉顯恩先生對承鄴先生也甚有幫助,《無悔是書生》的序就是他寫的。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是2019年8月1日(德政北路潮州菜館):
梁公承鄴約我和展云午飯。送我一套《梁方仲遺稿》。略看目錄,頗有可觀,梁方仲年壽不永,但遺稿之外又得此,確是專注、勤勉的學(xué)人。
席間即建議將梁氏所寫陳寅恪講課記錄及講義(元白詩)批注出單行本,今年陳氏去世五十周年,有紀(jì)念意義。蓋陳講梁記,本身亦是可貴記錄也。
說起陳美延,他們小時(shí)很熟,都就讀于嶺大(按:嶺南大學(xué))附小,陳美延比梁承鄴高兩級。前些年陳美延表揚(yáng)他為梁方仲做了不少工作,他答:都是學(xué)你的呀!
又說同濟(jì)大學(xué)某機(jī)關(guān)約他寫一文,回憶1949前后的經(jīng)歷和聞見。說起當(dāng)時(shí)人物有來有往(如姜亮夫自臺(tái)灣返回廣州),而楊慶堃,當(dāng)時(shí)系嶺大社會(huì)學(xué)系主任,1950年曾被調(diào)去參加《毛選》英譯,回來未久赴美——此事未聞,梁氏亦未寫過,甚可貴也。(略搜索楊氏,似未有回憶錄。)
又提起借書葉顯恩不還事。還是催說他設(shè)法解決——但葉已年老,梁公與其子女亦不熟悉,軟硬都不宜,確是甚難設(shè)法。
按:梁方仲手書的陳寅恪講課記錄,當(dāng)然有特出的價(jià)值,但單獨(dú)刊行,終是我的一廂情愿。講課記錄包括《兩晉南北朝史料》《元白詩證史》兩種,原來承鄴先生給過我復(fù)印件,但手跡頗不易讀,直到排印收入這部《遺稿》,我才細(xì)讀一過。其內(nèi)容雖較簡略零碎,但所涉豐富,且有趣味,多可見陳氏論著、講義所無或有異同者,吉光片羽,自可珍重。《遺稿》中還有一種影印的《元白詩證史·選詩》,系梁方仲批注,也甚有價(jià)值。只是《遺稿》的釋文仍有不少錯(cuò)訛,若出單行本的話,還需要作更細(xì)致的校讀。
以上就是我接聞?dòng)诔朽捪壬娜坑涗浟恕T谖覀€(gè)人,只是直書所聞所感,至于涉及的人事細(xì)節(jié)是否必定無所偏差,就只好“君其問諸水濱”了。
總的來說,承鄴先生晚年為父親的遺業(yè)盡了最大心力,是可與陳美延女士有關(guān)陳寅恪的工作相提并論的。承鄴先生享年八十三歲,已比其父高出許多,不為不壽;在他的努力周旋之下,其父遺稿已大體整理出版,他本人亦留下了《無悔是書生》《梁方仲學(xué)術(shù)評價(jià)實(shí)錄》這兩部相配合的著作,亦可謂無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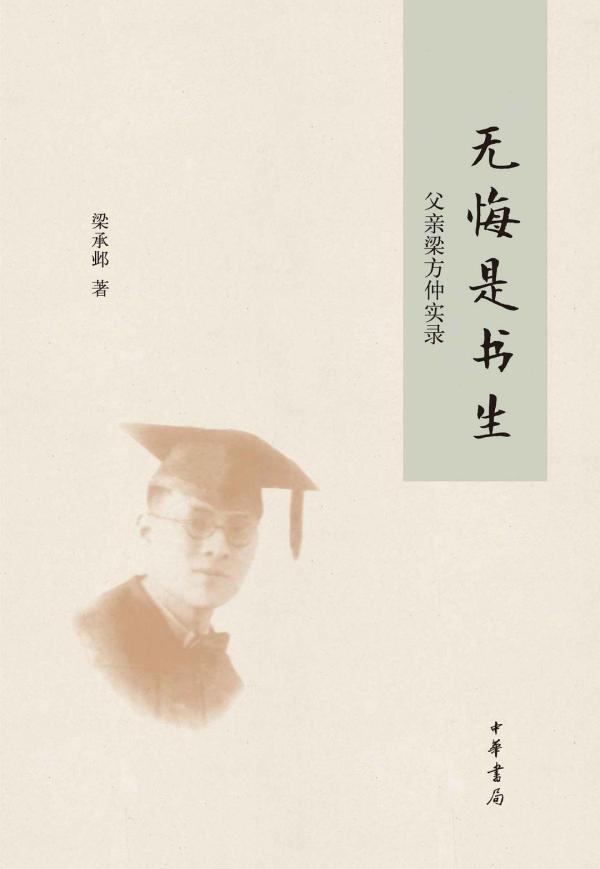
梁承鄴先生所贈(zèng)
說起來,承鄴先生也有微信,他在2018年6月加了我,只是老人家當(dāng)然不太熟練。查看微信記錄,兩年來我們主要有過這些互動(dòng):他轉(zhuǎn)贈(zèng)我一套其家族先輩的未刊著作《梁松年集》,我在《南方都市報(bào)》2019年圖書年鑒里寫了一則短評;他和葉秀粦先生合寫了一篇《記馮秉銓和梁方仲交往片段》,我轉(zhuǎn)給上海《文匯報(bào)·文匯學(xué)人》發(fā)表了;我檢讀《梁方仲遺稿》,發(fā)現(xiàn)一些釋文上的問題,用手機(jī)拍下轉(zhuǎn)給他參考。
若不是新冠病毒流行,他是不是會(huì)再約我們吃一次飯呢,我的《師友燕談錄》是不是會(huì)多記下一筆他說的舊人舊事呢?
6月初的時(shí)候,有朋友告知,“孔夫子舊書網(wǎng)”有一套朝鮮丁若鏞著的《牧民心書》,內(nèi)容有關(guān)為官治國之道,封面有題字“中華民國廿六年六月廿七雨夜,與尤炳圻兄、文仲舍弟同游東京本鄉(xiāng)區(qū),購于本富士町二番地琳瑯閣書店。 方仲記”,內(nèi)頁更鐫有“梁方仲教授贈(zèng)書”印章,看起來是真品,估計(jì)是從圖書館中流出的。當(dāng)時(shí),我不無心動(dòng),而一轉(zhuǎn)念,還是將書的鏈接轉(zhuǎn)給了承鄴先生,想先看看他有什么意見。可是他沒有回復(fù)我。當(dāng)時(shí)覺得老人家或者不常看微信,也就放下了。那是我最后一次想聯(lián)系他。
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又疊加上新冠時(shí)代,讓我們在現(xiàn)實(shí)的三維空間隔得更遠(yuǎn),在網(wǎng)絡(luò)的二維空間靠得更近。而承鄴先生的死,也是既顯得很遙遠(yuǎn),又顯得很接近。
世界上最遠(yuǎn)的距離,是生與死;世界上最近的距離,是生與死。聊草此文,以當(dāng)憶念。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