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劉道玉口述:親歷1977年恢復(fù)高考決策
《口述改革歷史》——親歷1977年恢復(fù)高考決策
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學(xué)和教育工作座談會(huì)在北京人民大會(huì)堂召開。這次會(huì)議做出了恢復(fù)高考的決定,這標(biāo)志著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斷了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fù),中國恢復(fù)了大學(xué)的教學(xué)秩序,也迎來了尊重知識(shí)、尊重人才的春天,給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發(fā)展帶來了重大而深遠(yuǎn)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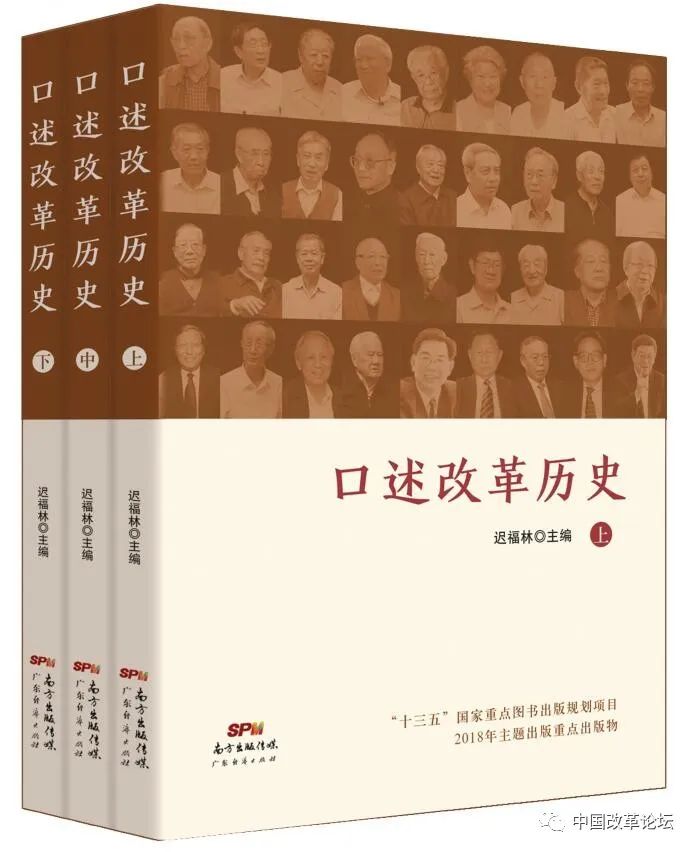
廣東經(jīng)濟(jì)出版社 出版
2020年高考已啟幕。中改院“口述改革歷史”人物訪談曾有幸訪問親歷恢復(fù)高考決策的見證人。下面,我們一同回顧這段歷史。
口述者:劉道玉(時(shí)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zhǎng))

借調(diào)教育部
沒有經(jīng)歷過“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當(dāng)時(shí)撥亂反正的任務(wù)有多么艱巨。教育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zāi)區(qū),粉碎“四人幫”以后,面臨著“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wù)。當(dāng)時(shí)我是武漢大學(xué)的教師,同時(shí)擔(dān)任武漢大學(xué)黨委副書記,深刻地感受到基層廣大教師希望盡快恢復(fù)正常的教學(xué)秩序和學(xué)術(shù)研究工作的迫切心情。就在這種情況下,我被借調(diào)到教育部,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huì)議的籌備工作。
1977年4月15日,我到教育部報(bào)到。由于當(dāng)時(shí)我覺得是臨時(shí)借調(diào),待不了多久,于是就在教育部辦公大樓二層的一間辦公室住了下來。它既是辦公室又是臥室,室內(nèi)放置了一張木板床、一副臥具、一張木制的辦公桌、兩個(gè)開水瓶和一個(gè)洗臉架。我沒料到,一個(gè)月以后,中央組織部正式任命我為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司長(zhǎng),雖然我極不情愿當(dāng)京官,但身不由己呀,于是我這一住就住了兩年,當(dāng)了兩年的“臨時(shí)工”。
當(dāng)時(shí)高教一司、高教二司、高教三司、科技司、研究生司、教材辦公司6個(gè)司局單位都由我領(lǐng)導(dǎo),我負(fù)責(zé)的范圍相當(dāng)于教育部的“半壁河山”。那時(shí)候教育部黨組11個(gè)成員中,只有我是從大學(xué)去的,也只有我熟悉高等教育的情況。
會(huì)議背景和籌備工作
當(dāng)時(shí)的形勢(shì)非常嚴(yán)峻,盡管粉碎“四人幫”已經(jīng)一年多了,但遵循的還是“兩個(gè)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jiān)決維護(hù);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當(dāng)時(shí)各省市和大學(xué)還是由革命委員會(huì)領(lǐng)導(dǎo),提出的還是堅(jiān)持無產(chǎn)階級(jí)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口號(hào),教育戰(zhàn)線上的“兩個(gè)估計(jì)”也沒有被推翻,這“兩個(gè)估計(jì)”把我們這些在學(xué)校的知識(shí)分子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們都是“臭老九”,是接受工農(nóng)兵再教育的對(duì)象,當(dāng)時(shí)就處于這種情況。
那時(shí),鄧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當(dāng)中是被打倒的對(duì)象,直到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huì)召開,全會(huì)一致通過《關(guān)于恢復(fù)鄧小平同志職務(wù)的決議》,決定恢復(fù)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wù)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zhǎng)的職務(wù)。
鄧小平復(fù)出后,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決心從科學(xué)和教育方面進(jìn)行撥亂反正,實(shí)現(xiàn)“四個(gè)現(xiàn)代化”,讓國家趕上世界先進(jìn)水平。撥亂反正從哪里入手呢?他打算召開一個(gè)會(huì)議,征求專家們的意見。后來在會(huì)上他也說了:“請(qǐng)你們參加這次座談會(huì)的目的,就是要請(qǐng)大家一起來研究和討論,科學(xué)研究怎樣才能搞得更好更快些,教育怎樣才能適應(yīng)我國四個(gè)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要求、適應(yīng)趕超世界先進(jìn)水平的要求。”
鄧小平辦公室通知教育部,這個(gè)會(huì)議要從教育部和科學(xué)部各選15個(gè)知名專家參會(huì),會(huì)議時(shí)間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我作為教育部黨組成員和高教司司長(zhǎng),受教育部的指派,負(fù)責(zé)選定名單,初步選拔了16人,最后科學(xué)院也選派了17人,總共33人,加上國務(wù)院有關(guān)部委負(fù)責(zé)人和新聞?dòng)浾撸偣?0多人參加座談會(huì)。
當(dāng)時(shí)確定名單的時(shí)候有兩點(diǎn)考慮:第一,必須要是知名的科學(xué)家和教育家,而且要敢于說真話。比如說楊石先是南開大學(xué)校長(zhǎng),著名化學(xué)家;蘇步青是復(fù)旦大學(xué)教授、校長(zhǎng),知名數(shù)學(xué)家,等等。第二,當(dāng)時(shí)我也考慮到名單上還得有一些中青年,遵從老中青三結(jié)合嘛,所以一些中青年像溫元?jiǎng)P,他當(dāng)時(shí)還是30出頭的小青年吧,還有中山醫(yī)學(xué)院的宗慶生等參加了會(huì)議。
中國科學(xué)院的吳明瑜和我,分別代表中國科學(xué)院和教育部組成了會(huì)議秘書組,負(fù)責(zé)會(huì)議記錄、簡(jiǎn)報(bào)和會(huì)議代表的生活問題。與會(huì)代表都是我們兩個(gè)人通知的,也是我親自到機(jī)場(chǎng)接送的,當(dāng)然,大部分代表都來自北京,所以我的接送任務(wù)也不是很重。
決定恢復(fù)高考
座談會(huì)是在8月4日上午9時(shí)開始的。鄧小平同志作了一段開場(chǎng)白。說實(shí)在的,當(dāng)時(shí)這個(gè)會(huì)議,剛開始大家思想上還是有顧慮的,心有余悸,剛開始還不一定就敢講。于是鄧小平同志反復(fù)啟發(fā),希望大家暢所欲言,他說:“‘四人幫’粉碎了,不會(huì)再‘抓辮子’‘戴帽子’和‘打棍子’了,大家如果有什么問題由我負(fù)責(zé)。”經(jīng)過小平同志的反復(fù)動(dòng)員,大家開始講話,并逐步活躍了起來。
我記得,首先講話的是復(fù)旦大學(xué)的蘇步青。他說:“我想不通高教戰(zhàn)線17年是資產(chǎn)階級(jí)專政,那我們過去做的工作都是為誰服務(wù)的?難道都是為資產(chǎn)階級(jí)做的工作嗎?但明明是在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他問得很有道理,明明是在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我們?cè)趺闯闪藶橘Y產(chǎn)階級(jí)服務(wù)的知識(shí)分子呢?鄧小平同志就插話說:“17年是黑線專政講不通,17年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嘛。”對(duì)于這個(gè)問題,他在8月8日的講話中也明確提出:“對(duì)全國教育戰(zhàn)線17年的工作怎樣估計(jì)?我看,主導(dǎo)方面是紅線。應(yīng)當(dāng)肯定,17年中,絕大多數(shù)知識(shí)分子,不管是科學(xué)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lǐng)導(dǎo)下,辛勤勞動(dòng)、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jī)。現(xiàn)在差不多各條戰(zhàn)線的骨干力量,大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自己培養(yǎng)的,特別是前十幾年培養(yǎng)出來的。如果對(duì)17年不做這樣的估計(jì),就無法解釋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這樣慢慢地氣氛就活躍起來了,大家思想都放開了。
北京大學(xué)的沈克琦說:“我們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zāi)區(qū),聶元梓在北大挑動(dòng)群眾搞批斗,我們受盡了苦。‘文化大革命’時(shí)期北大非正常死亡幾十個(gè)人,像翦伯贊、俞大絪等,都是知名教授。而且‘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教授都被反復(fù)抄家,他們收藏的文物、著作手稿都被抄走了,希望中央能夠落實(shí)知識(shí)分子政策,幫他們找回他們最珍貴的書稿、字畫等。”
南開大學(xué)校長(zhǎng)楊石先是國家非常重要的研究農(nóng)藥的泰斗,他說:“國家科委的大樓被軍隊(duì)占了,科委都解散了,這么大一個(gè)國家沒有科研、沒有科委、沒了科學(xué),怎么行呢?”他要求盡快把被占的國家科委大樓歸還給國家科委,并且要恢復(fù)國家科委。講到這里的時(shí)候鄧小平同志插話說,應(yīng)該收回,國家科委應(yīng)該恢復(fù)。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會(huì)上慢慢地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發(fā)言也踴躍了。
我作為高教司司長(zhǎng),心里有點(diǎn)著急,因?yàn)闆]有人提到恢復(fù)高考問題。在會(huì)前我做了調(diào)查:高等教育的撥亂反正該如何入手?那時(shí)是工農(nóng)兵上大學(xué)、管大學(xué),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xué)。那個(gè)時(shí)候工農(nóng)兵學(xué)員進(jìn)校以后都以改造者自居,以知識(shí)分子為改造對(duì)象。當(dāng)時(shí)的大學(xué)招生就是從工農(nóng)兵里招,有一個(gè)“十六字”招生方針,即“自愿報(bào)名、群眾推薦、領(lǐng)導(dǎo)批準(zhǔn)、學(xué)校復(fù)審”。說是自愿報(bào)名,你報(bào)了,領(lǐng)導(dǎo)不批準(zhǔn),有什么用?所以這“十六個(gè)字”就變成四個(gè)字:領(lǐng)導(dǎo)批準(zhǔn)。領(lǐng)導(dǎo)決定一切,導(dǎo)致當(dāng)時(shí)走后門之風(fēng)猖獗,領(lǐng)導(dǎo)要誰上誰就上,不讓誰上誰就不能上。舉個(gè)例子,有個(gè)著名作家熊召政,1976年時(shí)他是湖北英山縣的一個(gè)知識(shí)青年,群眾已推薦他上大學(xué),但是到了縣里,縣委書記不同意:“你明年去,今年我兒子要上。”當(dāng)時(shí)就是這種情況。會(huì)前我到沈陽、天津做調(diào)查,后來到了順義縣,該縣革委會(huì)姜副主任對(duì)我說:“現(xiàn)在大學(xué)雖然恢復(fù)了招生,但我們工農(nóng)子弟仍然沒有上大學(xué)的權(quán)利,因?yàn)椤帧猩结槪褪情_后門的方針,因此我們強(qiáng)烈要求恢復(fù)高考,我們工農(nóng)兵子弟不怕考,不信你查一查‘文革’以前,上大學(xué)比例多的還是我們工農(nóng)兵子弟。”
是的,我上大學(xué)那會(huì)兒,來自農(nóng)村的大學(xué)生要占70%左右。當(dāng)時(shí)大學(xué)招的工農(nóng)子弟文化程度嚴(yán)重參差不齊,大多是初中畢業(yè),甚至還有小學(xué)文化程度的,高中生極少極少,因?yàn)楦咧猩枷锣l(xiāng)了。當(dāng)時(shí)說“不讓一個(gè)階級(jí)弟兄掉隊(duì)”,所以大學(xué)教學(xué)就沒辦法教了,有些學(xué)生甚至連小學(xué)的東西都不會(huì),你要讓他不掉隊(duì),大家都得等他,大學(xué)就變成中學(xué)、小學(xué)了,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培養(yǎng)出合格人才的。所以我一直記住順義縣革委會(huì)副主任的話,一定要恢復(fù)高考。
但會(huì)議開了兩天了,沒有人講到這個(gè)問題。武漢大學(xué)代表查全性副教授晚上來找我,他說:“我坐了兩天了沒有發(fā)言,一直在聽,我想講的別人都講了,我不知道講什么好。”他是來征求我的意見,因?yàn)槲覀兌际俏錆h大學(xué)化學(xué)系的教師,我又是會(huì)議秘書長(zhǎng)。我說:“雖然大家都講得不錯(cuò),但有一個(gè)問題大家都沒講到,就是推翻‘十六字’方針,恢復(fù)高考的問題。”其實(shí)當(dāng)時(shí)提這個(gè)問題是非常冒險(xiǎn)的,弄不好就要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因?yàn)椤皟蓚€(gè)估計(jì)”還沒被推翻。但是我這個(gè)人歷來膽子很大,我敢說。我說你就講這個(gè)問題,他同意了。
當(dāng)晚,查全性副教授做了認(rèn)真的準(zhǔn)備。他發(fā)言時(sh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上大學(xué)是靠錢,“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上大學(xué)靠分,現(xiàn)在上大學(xué)靠權(quán),群眾說“學(xué)會(huì)數(shù)理化,不如一個(gè)好爸爸”。他的這番話,引起了與會(huì)人員的強(qiáng)烈共鳴,大家紛紛發(fā)言,像吳文俊、汪猷、唐敖慶等都表示附議。
當(dāng)時(shí)劉西堯是教育部部長(zhǎng)。鄧小平同志問他:今年恢復(fù)高考怎么樣?劉西堯說,要改就得推遲,現(xiàn)在是8月6日,當(dāng)年6月29日到7月15日的招生會(huì)已經(jīng)在太原開過了,還是按照“十六字”方針布置的,招生報(bào)告已經(jīng)給國務(wù)院送去了。鄧小平同志說:“既然今年還有時(shí)間,那就堅(jiān)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bào)告收回來,根據(jù)大家的意見重寫。招生涉及下鄉(xiāng)的幾百萬青年,要拿出一個(gè)辦法來,既可以把優(yōu)秀人才選拔上來,又不要引起波動(dòng)。重點(diǎn)學(xué)校要統(tǒng)一招生。今年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學(xué)生要符合要求。”教育部說那我們今年就改。
全國第二次高等學(xué)校招生工作會(huì)議召開
8月13日,當(dāng)年全國第二次高等學(xué)校招生工作會(huì)議召開,到9月25日結(jié)束,開了44天。在會(huì)議爭(zhēng)執(zhí)不下的情況下,鄧小平于9月19日再次找劉西堯等人談話,要求教育部爭(zhēng)取主動(dòng),盡快結(jié)束招生會(huì)議。這是鄧小平關(guān)于恢復(fù)高考的第二次拍板,說明當(dāng)時(shí)的阻力還是很大的。
1977年,我們是恢復(fù)“文革”以前的高考,完全按照“文革”前的做法統(tǒng)一命題、統(tǒng)一考試、統(tǒng)一劃錄取分?jǐn)?shù)線。恢復(fù)高考,重新招生,但當(dāng)時(shí)我們的教學(xué)計(jì)劃還是針對(duì)工農(nóng)兵的,教材都是為工農(nóng)兵大學(xué)生配備的,統(tǒng)一高考招進(jìn)來的學(xué)生不能再用一樣的教材了,怎么辦?我就給黨組織提出建議,說必須馬上召開一個(gè)高等學(xué)校教學(xué)工作會(huì)議,重新研究制定新的教學(xué)計(jì)劃、教學(xué)大綱,不然統(tǒng)一招進(jìn)來的學(xué)生我們沒辦法授課。當(dāng)時(shí)時(shí)間很緊,我提議馬上向國務(wù)院報(bào)告。國務(wù)院也很重視,說這個(gè)會(huì)很重要,安排我們到北戴河國務(wù)院招待所開會(huì),這個(gè)招待所在“文革”中被當(dāng)作“封資修”的安樂窩封存了,我們親自啟封,打掃衛(wèi)生。
這次會(huì)議要形成恢復(fù)高考以后的招生工作計(jì)劃和教學(xué)大綱,當(dāng)時(shí)我們怕控制不住,意見不能統(tǒng)一,就只通知了15所學(xué)校參加,再加上北京師范大學(xué)和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的兩個(gè)教育研究所,一共35個(gè)人參加。8月12日至18日正式開會(huì),恰好與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ì)同一天開始和結(jié)束。
會(huì)議爭(zhēng)論得十分激烈,但最后還是統(tǒng)一了思想。制定新的教學(xué)大綱必須肅清“左傾”思想流毒,堅(jiān)持“三基”和“四性”,最后我們制定了一個(gè)比較滿意的《會(huì)議紀(jì)要》。座談會(huì)結(jié)束當(dāng)天,我們與北戴河鎮(zhèn)的居民一起上街慶祝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ì)勝利閉幕。最后通過的那個(gè)教學(xué)大綱,基本上一直沿用至今。
意義和感觸
據(jù)統(tǒng)計(jì),1977級(jí)、1978級(jí)總共招了60多萬名學(xué)生。當(dāng)時(shí)在農(nóng)村還有860萬名知青,很少數(shù)的幸運(yùn)者才能夠被錄取上大學(xué),這些都是真正的佼佼者。20世紀(jì)80年代學(xué)校的風(fēng)氣好得很,不是“你要我學(xué)習(xí)”,是“我自己要學(xué)習(xí)”,沒有考試作弊的人,都是自覺地考試,自覺地要學(xué)習(xí),因?yàn)樯洗髮W(xué)是很艱難才得到的權(quán)利,他們很珍惜這個(gè)機(jī)會(huì)。
我覺得恢復(fù)統(tǒng)一高考功在當(dāng)代,利在千秋,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一個(gè)意義,雖然它不是改革也不是創(chuàng)新,但是在那種特殊情況下,在“兩個(gè)凡是”“兩個(gè)估計(jì)”沒有被推翻的情況下,能夠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針,那是了不起的。
第二個(gè)意義就是拯救了一大批知識(shí)青年,他們現(xiàn)在絕大部分都成了國家棟梁,成為學(xué)術(shù)界、政界、經(jīng)濟(jì)界、企業(yè)界的骨干。我們武大有位一級(jí)教授、著名數(shù)學(xué)家叫李國平,他的兒子是知青,招工到武漢市當(dāng)理發(fā)員都高興得不得了啊,因?yàn)樵谵r(nóng)村沒飯吃、吃不飽啊,回來就是當(dāng)理發(fā)員,他還高興得不得了。后來,他參加了1978年高考,被錄取到武漢大學(xué)歷史系,現(xiàn)在是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我有個(gè)學(xué)生叫謝湘,后來是《中國青年報(bào)》的記者部主任、副社長(zhǎng),也是1977級(jí)的學(xué)生。她返城后是襄樊市紡織女工,當(dāng)個(gè)女工都高興啊,她媽媽要她參加高考,她堅(jiān)決不參加:“我不參加,我做女工很好,我是工人階級(jí)。”而且她當(dāng)時(shí)準(zhǔn)備提車間主任,她都不想高考。她媽媽親自跑到襄樊棉織廠,說:“你考也得考,不考也得考,不考就不是我女兒。”強(qiáng)迫她考,最后她考取了,考到了武大中文系,畢業(yè)后分配到《中國青年報(bào)》,一直升到副社長(zhǎng)。要是沒有高考,這一批人就被埋沒啦。所以我開玩笑說:恢復(fù)高考招收了1977級(jí)、1978級(jí)、1979級(jí)的學(xué)生,他們就是從石頭縫里邊蹦出來的人才,將來一定能夠擔(dān)當(dāng)大任。
第三個(gè)意義,恢復(fù)高考使社會(huì)風(fēng)氣、學(xué)習(xí)風(fēng)氣煥然一新,這是無法衡量的重大意義,把過去的“讀書無用論”“教書倒霉論”一掃而光。那時(shí)候我們大學(xué)的很多教授,都把書當(dāng)廢紙賣掉了,認(rèn)為這一生不可能再教書了。雖然我的書沒賣也沒燒,但是我也準(zhǔn)備改行學(xué)木工手藝了。恢復(fù)高考以后,大學(xué)里進(jìn)了一批高中、初中文化的學(xué)生,教師不提高自己的教學(xué)水平是不能教他們的。所以,教風(fēng)學(xué)風(fēng)煥然一新,老師們上下班都是跑步前進(jìn)的,實(shí)驗(yàn)室的燈光晝夜通明,大家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shì),甩開膀子大干,要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shí)間全部搶回來,當(dāng)時(shí)就是這么一種心態(tài)。
所以說,沒有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教育受災(zāi)多么嚴(yán)重;沒有經(jīng)過撥亂反正,就不知道撥亂反正多么重要。我對(duì)改革的情結(jié)這么濃厚,原因就在這里。
(本文原題為《口述改革歷史|親歷1977年恢復(fù)高考決策》,作者劉道玉時(shí)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zhǎng),選自由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zhǎng)遲福林主編的《口述改革歷史》一書,微信首發(fā)于公眾號(hào)“中國改革論壇”,澎湃新聞獲授權(quán)轉(zhuǎn)載。)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