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兒童文學應該怎樣面對和處理“禁忌”書寫
最近的一系列相關事件讓我和幾位兒童文學從業者朋友(他們中有研究者也有創作者、出版者,做過孩子們的老師,大多數也為人父母)心里頗為沉重。先是由真實生活中的一個殘酷案例發端,接著人們開始討論孩子閱讀的書籍中是否有著“越線”的“自殺書寫”。有母嬰號呼吁“監管”[1],然而全文沒有明寫“監管”應由哪些人員和機構主持把握,是由學院文學研究/批評者們或是國家相關部門或是指飛天面條協會組織給出大致的衡量標準,讀者不得而知。
這篇文章想談一談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和處理兒童文學中的自殺書寫(或者說“禁忌”書寫)。開門見山地說,我不認為有兒童文學必須回避之題,關鍵全在于作者怎樣呈現。假如呈現得不好,所有讀者理應有質疑、批評的權利,但對于監管力量的呼吁應當慎重。筆者想從兒童文學創作本身和“真正的要害在文學之外”兩方面來全面整理探討這個問題。

我想,不論“監督”以何者為主導,可以肯定的是,對童年文化和兒童文學的學理研究成果都必然成為判斷的重要參照依據。
然而就筆者所知,目前國內專題探討兒童文學創作內“禁忌主題”(如自殺、性欲、暴力等)的研究十分少見。甚至即使在兒童文學與文化研究已經相對成熟的國家,“死亡”這一命題所獲得的關注也遠低于兒童情欲或暴力現象,遑論其中的兒童自戕行為。研究的滯后一定程度上照映的正是創作的匱乏。要知道,20世紀初期死亡主題才開始通過動物形象進入世界兒童文學,之后老人的死亡得以被呈現,而一項調查發現,90%關于死亡的兒童書籍都是在1970年之后出版的[2]。這樣看來,似乎我們整個人類文明在面對、闡釋特別是向下一代講述 “死亡”這一人人都要經歷的終點以及事實上大量存在的兒童自殺現象時,心照不宣地選擇了諱莫如深的姿態。
這首先當然和自殺本身涉及的倫理爭議有關。人們對自殺的恐懼和厭惡大致有兩類哲學基點,其一是自殺意味著個體的行為準則與普遍的自然法則將發生矛盾,儒家文化下我們常常聽到的關于自殺者對其重要他人的所負“責任”的質詢(比如“你自殺怎么對得起父母”)可以看作是這一條的延伸問題;其二也是筆者個人認為更有分量的理由,即死亡本身的特殊性決定了自殺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種“自由選擇”。死亡是不可逆的,一旦此刻選擇結束生命,將再無反悔和重新選擇的機會,憑今日之我將未來之我的一切可能性(特別是“生”的欲望)就此斷絕關閉,是不公平的。
但多數人也不會不承認,我們對自殺者常常是抱有許多同情和悲憫的。尤其當我們發現該行為中包含的不止是絕望和陰郁,還有不甘和拒斥時。涂爾干《自殺論》的結論部分告訴讀者,自殺行為也總是會體現一個社會所認可的某些高貴的德性。也就是說,人們承認世界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美德存在,否則這個社會大約也會止步不前。
既然我們對自殺行為本身的態度并不僵硬封閉,那么何以對這次被發掘出來的幾個兒童文學作品反應激烈呢?我想,問題并不在書寫自殺行為上,而在于“怎樣寫”。“死生亦大矣”,人們不愿意看到生死攸關的命題被作者用一種輕佻的態度隨便寫來。
我們對自殺的正向態度是建立在對沉重而崇高的價值的認同基礎上的,而在楊紅櫻的漫畫里,兩個主人公仿佛說吃飯睡覺等日常重復性瑣事那樣笑著蹦著討論各種自殺方式,在視覺畫面的輔助下尤為扎眼。退一步說,以文學對日常邏輯的尊重而言,即使是我們做孩子時與朋友說起類似話題,難道會是這種歡笑雀躍的飛翔姿態嗎?假如一個孩子真因為不堪課業重負自戕,我們面對的難道不是一個由童書提出的需要嚴肅對待的社會議題,反而要以惡搞的方式去嘲笑那個孩子上吊的丑態嗎?“滑稽”是一種有力量的文學修辭,但有良心的文學往往將其用在小人物對權力上位者的嘲諷里以撬動對方的話語權力,解構上位者聲音的合法性,而不是擱到受害者身上,成為其消解自我意志的工具(如果我們承認“自殺”在此處代表的是成長主體隱隱萌動的對“不合作”的表達)。正如《意外抽得幸運簽》《馬克的完美計劃》,在這兩部“自殺”主題的兒童文學里,前者的幽默自嘲和后者從始至終的悲戚最終通向的都是對生命價值的認可。而《淘氣包馬小跳》《裝在口袋里的爸爸》《超時空小子》等作品顯然沒有認真對待“死亡”一詞的內涵,那些我們希望孩子在生命初期就能夠有所了解的基礎內涵——“知死”是為了“知生”。

在后兩部作品里,輕佻的不是敘述語氣而是想象和情節編織的手法——撐起手絹就能平安降落、跳樓竟然完成穿越遇見伯樂,這樣的故事情節在想象力上乏善可陳、顯得隨便而無設計匠心,讀者沒有閱讀欣快感,而是“哦,勉強也行吧”的姑且觀望式的接納,而這“姑且”的別扭感部分就來自于作者對自殺行為的輕浮態度。希利斯·米勒在《文學死了嗎?》中提到,閱讀文學是讀者和作者簽訂信任契約,當文內邏輯的隨便和荒唐程度超過了讀者的接受范圍時,契約就無法繼續,作品的世界就產生了裂隙。好的文學作品確實是一只盡可能少裂隙的“精致的甕”。作家亨利·詹姆斯更是曾經毫不留情地說,作品人物真正“偉大起來”是從作家不要求讀者憑空相信他們那一刻開始的。因為“作家是騙子,騙子最不會做的事,就是直接要人憑空相信他……而是要通過操縱各種精巧微妙的言語行為,讓讀者自然而然地擱置懷疑”。而將自殺這樣的事件與承接不住其分量的下文情節隨便地連接起來,會讓讀者產生斷裂和“交代空缺”感,實質上是不夠高明或者懶惰的作者利用自身特權為故事推進保駕護航而已,這種作者對自身絕對權力的強化和濫用不一定所有讀者都能明確意識到,但那種微妙的別扭生硬感可能是很多人都能隱隱察覺到的。
可以說,歸根到底不是不能寫自殺、也不是不能以幽默筆法寫自殺(當然這對作者是更大的挑戰),而是即使撇除道德考量,這些作品也寫得并不好的問題。
而另一方面,從文學的社會功能角度來說,擔心這種對“禁忌”書寫的輕佻態度會影響孩子有沒有道理呢?空口論辯不如實證研究更有說服力。
當然,這樣的實驗并不好做,尤其是長期觀察跟蹤對照更可能涉嫌違背社會研究倫理,但我們可以試著參考一些正向研究。首先,“行為可以從榜樣中學習”這一樸素觀念確實是有社會學研究支持的[3]。其次,歐美一些國家對將死亡主題的書籍當作“閱讀療法”的工具已經有了一定的經驗,這些閱讀往往用于幫助孩子理解生命/死亡,疏導安撫喪親兒童,他們甚至有專門的“悲傷閱讀療愈小組”和專業輔導員。不少實驗研究證明閱讀和回應文學作品確實是處理創傷性事件的有效方法,輔導員使用閱讀療法可以讓孩子與故事元素建立聯系,反過來處理自己的復雜情緒[4]。同樣,也有實驗證明當父母的悲傷或父母對如何與孩子交談的不確定性阻礙了交流時,孩子的誤解和恐懼可能會加劇。因此,準備與孩子開放交流的資源是很重要的。這些資源包括故事書和圖畫書,它們旨在幫助兒童準備或應對死亡,并以適合發展的方式理解死亡。“傷痛咨詢師”和社區“悲傷小組”使用并推薦它們。這些書還可以教育兒童有關生死和文化悼念儀式的基本事實——要知道,理解“死亡”并不止理解生物性事實而已[5]。
在當下這樣的信息社會里,要完全禁止孩子接觸、搜索各類信息是幾無可能的。在兒童不斷接觸死亡相關經驗的同時,他們也被迫發展和尋找自己的經驗。很多次這樣的搜索都留下了影響他們生活的不健康的態度。已有的文獻研究證實了媒體和社會對兒童的重大影響[6]。
同樣,對照實驗告訴我們,“怎樣講”故事很重要。懷特·埃爾森和巴萊特的一項研究考察了在講述一個故事的兩個不同版本(童話改編和新聞報道)之后,聽故事的孩子對死亡的主觀感知。結果表明,兒童對死亡的理解與所呈現的不同故事沒有相關性,但講故事的方式影響“兒童對死亡原因的看法”。童話組的孩子對死亡有更多細節敘述、能指出死亡事件的因果聯系和不可逆轉性、更側重情感表述,常用幽默和玩笑來表達死亡的不可避免性,而媒體組孩子的表述則更顯得有邏輯性和淡漠[7]。
這些研究都表明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孩子通過閱讀卓越的文學書籍來了解“禁忌”是更值得被鼓勵的做法。
值得推薦給孩子的文學
關鍵是,什么樣的文學是更值得推薦給孩子的?
首先,越是卓越的文學作品,越是要求人們在閱讀的生物反應快感和自我克制之間取得平衡——好作品追求隱喻的多層性和新穎性(雖然它們的語言可能看上去很簡單,比如《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鼓勵讀者發展出更復雜的理解和回應,讀者能因此從中獲得多樣化的滿足,而不是止步于快節奏、單一可能性的結論直白地、不證自明地得出。反過來去看上文的暢銷書,那些關于自殺的觀點、語句和情節推進,這些快速敘述、隨便得出結論和結果的方式不利于兒童反思文本結論的合理性,不利于他們更深入、全面地思考生活現象。

其次,好的文學精通一種魔法,不是讓人覺得它反映了現實,而是讓虛構的世界入侵現實,是通過其文字敘述讓人不由自主地相信這個故事(哪怕它再荒唐,比如有個小職員一早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甲蟲)即使真的發生在當下此刻世界的某個角落里也仿佛是可能的。也就是,它會改變讀者認知世界的方式,特別是改變你對“現實”和“虛構”二者界線的原有認知,你可能因此不時會疑惑并反思何者為“真實/虛構世界”。舉個例子,快速回答下面這個問題:開膛手杰克和貝克街221b福爾摩斯的住處哪個是虛構的,或者都是虛構的?
最后,不論是為兒童,還是為文學,我們都必須面對一個有些“功利”的問題:如果有可能,你愿不愿意去設想一個更有希望的世界,特別是希望你的孩子、我們這個族群的未來能夠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誠如亨利·詹姆斯所說:“有一些體面事,以全體的自尊的名義,我們必須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有一種基本的思想榮譽,為了文明的利益,我們是必須至少要假裝具備的。”
這個答案意味著,我們應該盡量選擇激勵孩子建立“自我”意識而不是妥協于世故之道的書籍,哪怕你暫時覺得它可能有爭議,至少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選擇它;你可能還需要了解一些專業人士的見解,以幫助你回答質問的聲音,而不滿足于“難道孩子不夠聰明不能自己處理這些事情?”以及,在國內學者尚未制作提供類似的閱讀指導手冊之前,你還可以借助一些機構網站提供的指南手冊試著檢驗維護或控訴兩方的言論和他們提到的作家是否“真金不怕火煉”,比如美國英語教師委員會制作的《學生閱讀權》(The Student’s Right to Read)小冊子,加拿大的自由閱讀周小冊子When the Censor Comes(你可以在www.freedomtoread.ca/ cemsor.htm上找到)。
其實,中國曾有過優秀的兒童文學自殺題材的作品,我愿意分出一些文字來聊一聊它——陳丹燕的日記體小說《女中學生之死》。女主人公寧歌對學校教育系統將其視為“流水線產品”而不予人格尊重深感不滿,且其無法從母親和朋友處得到有效的支持,終于在學校蠻橫武斷地判定其“早戀”并侵犯其隱私權后,選擇從高樓上躍下結束生命。我不止一次地想,假如我將來有了孩子,在我的“國內作家作品推薦書單”上,一定會有這部作品。因為它講的是一個在東亞文明下生長起來的普通人皆能懂得的故事,一個普通學生的故事。更難得的是,它是民間童話體系之外的一個“屬于我們自己的故事”,我想要孩子們知道幾十年前的學生曾經有過怎樣的校園和家庭生活,兩代學生的困擾竟如此相似,而那些孩子們又是怎樣思考自己的生活和世界的。這部作品的第一頁上寫了女記者看到的寧歌房間里遺留下來的書籍,作者是這樣一些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徒生、德萊塞、毛姆……女主人公的摘抄本上引用了萊辛的短文。要能“寫得動”這樣一個讀過《死屋手記》的女孩,可想而知首先作者必得有基本的文學學養。此外,陳丹燕和當時上海《青年報》的記者鐘雪燕為了獲得第一手材料,到寧歌的原型、女中學生施驪家里翻了許久找到她的日記。鐘雪燕抄了滿滿40頁的日記內容[8],而陳丹燕更是連夜將日記一篇篇錄音——第二天施驪的母親就將這本遺留的日記要了回去[9]。無須詳談作品的特殊的敘述話語和結構方式,單從寫作的準備工作而言,就不是流水線暢銷書作家可望其項背的了。順帶一提,鐘雪燕后來為此撰寫的通訊《愛的呼喚》在當年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它提醒人們應直面青春期情欲的真實存在以及少年獨立人格所獲尊重的不足。這篇報道獲得了1986年度“上海好新聞獎”一等獎亦是社會認同的明證。筆者過去翻閱期刊文獻時亦發現1986~2005年期間《少年文藝》與《兒童文學》上“早戀文學”題材在小說文體中占到了多數比例,而后這一現象隨著社會對青春期情欲認知的成熟化和普及化而自然而然地走入了歷史的塵埃。這樣自信的“探討和批評”比之一刀切下架如何呢?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作品是殷健靈的《紙人》,以一個“早熟”的女孩秋子為全文隱線,虛幻的秋子之魂喚起成年女主人公對過往成長的記憶。隨著文本的鋪開讀者才知道秋子因為家庭和戀愛問題得不到有效疏導,后又未婚懷孕,重壓之下跳樓自殺——這成為主人公的心結,直到她成長為“青春熱線”的主持人、敘述者“我”完成了整個故事的寫作,并用科學的性知識幫幻影秋子化解了自慰羞恥、解開了其對幼年被性侵經歷的心結(發現了嗎,這是四個“禁忌”撞到一起的作品),秋子的幻影才終于離去。雖然在藝術成熟度上不及《女中學生之死》,但其書寫“禁區”的勇氣、作者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對孩子的殷殷關愛卻也是時下作品中十分稀缺的。
結合《兒童文學》《少年文藝》等影響較大的兒童文學雜志發表的情況看,我們的兒童文學書及自殺題材時,往往集中于兩大命題:學生個性與僵化、發展遲緩的教育體系的矛盾,以及青春期性發育和戀愛行為帶來的無處傾訴、求助的困擾,也就是說,對其他自殺原因的關注較為匱乏。同時,對自殺者性別的呈現亦有偏好,對男孩的心理困境關注不足。再者,近二十年再也沒有出現過像上述兩部那樣較有分量的“問題意識”作品。如果有人說楊紅櫻的作品雖然粗糙但反映了真實的校園生活,那么筆者認為這種“真實”也是討巧而膚淺的,這些煩惱大多是精心篩選過的輕巧的煩惱,或者是把嚴肅的議題通過敘事的小聰明輕巧地遮蔽過去的虛假的“真實”。如果這些浮皮潦草的、部分的“真實”就可以壟斷對“真實”的最終解釋權,并占據國產童書市場的巨大份額,那么關于童年的另一部分真實、特別是那些嚴肅認真而勇敢的“禁忌寫作”何以自處呢?他們不“真實”嗎?從長遠的精神滋養而言,不是這些作品更能進入孩子的生命深層,成為他們日后抵御人生路上霜雪風暴的有力支柱嗎?
文學之外的“門道”和獨立批評的缺失
不過,通常當“文學問題”發酵醞釀到引起大范圍的社會熱議時,問題的真正要害總是在文學之外,那么我們最后就來談談這個“要害”。
這些年來,家長們對兒童閱讀的關注可以說是前所未有,書評、導讀、線上直播薦書,國內的兒童文學市場持續火熱,但關于優秀的圖畫書、兒童小說如何有利于孩子成長的好聽話我們聽了太多,反思和批評相對卻太少。批評文字大多是母嬰公眾號在寫,這些文章又往往“語不驚人死不休”。從根源上說,它們提出的問題正是熱火朝天的市場從未直面的購書者關于“兒童到底是什么”“兒童文學到底邊界有多寬”這樣的困惑。困惑得不到解決,疑懼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一旦其中一些文本刺激了大眾的樸素直感,母嬰號以“疾言聲討”的方式質問兒童文學的從業者并得到許多共鳴便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但這中間的聲音泥沙俱下,譬如表述含糊地呼吁“監管”卻不寫清呼吁哪些人來組成“監管”的隊伍。如果是呼吁商家下架,那么從這兩天的后續來看,已經實現了——一份出處目前難以考查的“排雷書單”列出書目(每本書只用一兩句解釋了該書有何不妥,最荒唐的是其中對《巴夭人的孩子》一本,博主只是說自己可能是沒有欣賞水平看不懂便把作品列了進去),然而書店不假思索按照這份書目全盤下架,這樣的一刀切,且不論殃及池魚,也是不可持續的,只能是冒出一波打一波,而且沒有一個好把握且相對穩定的衡量依據,家長和老師們只能持續迷惑,最后便是哪邊聲音大哪邊是贏家。我能確定的是,“閱讀保衛戰”用這樣的打法,最后輸的一是文學、二是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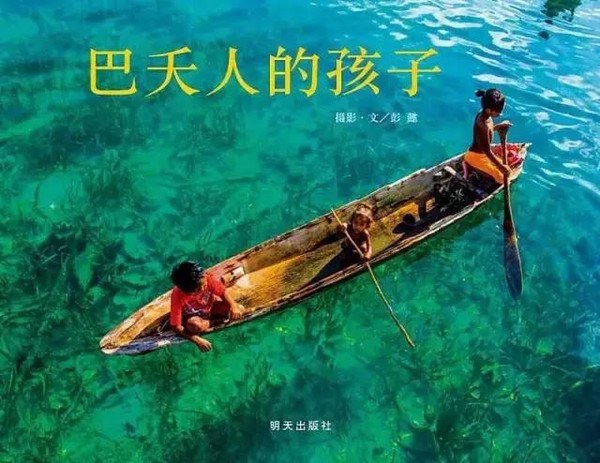
我們其實都清楚,光靠市場自發自覺地淘汰劣幣是不可能的,市場永遠以逐利為第一原則。那么靠作家自覺如何?目前在童書暢銷市場上大家耳熟能詳(也是在前幾波批評質疑中被列出來)的幾位作家,獲得的國家投資款項多、出版資源極多[10],從一些“國際出版工程”的組織多語種翻譯出版、安排國際專家對談和專門審校、獎項參評、書店及書展推廣,到各種省市以及跨省級別的圖書館活動、各學校組織的暑期書目活動(往往需要學生寫讀后感、做手抄報等等,這種重量級的入校簽售真像他們回應辯解的那樣,家長和孩子真有自由擇書的權利嗎?),再到媒體平臺資源等等。這些“壟斷作家”中有的有著語文教材主編的身份,有的是省作協副主席,只要作家獲得某些特別的大獎,發行就會加印作品;另外,很多讀者不知道的是,對于出版社而言,獲獎也可以完成實際的加分任務;在“做書”公號今年6月10日推出的文章里,作者更是直接質問“在自己主編的教材中推薦自己的作品,是否有以權謀私之嫌。作為市場的‘指揮棒’,所謂的‘閱讀工程’‘必讀書目’‘指定版本’中間又存在著多少尋租的空間?”該文章引用開卷數據報告《中國教輔圖書市場的20年》的結論,即“課外延伸閱讀欄目”的設置在孩子的閱讀選擇中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推薦書目在實體書店和網店都有不錯的表現,甚至成為圖書市場惟一的“亮點”。
那么哪些書哪些作者會成為受益者呢?指望壟斷者檢視自身是不現實的,如果輕易就能得到更好的扶持,那么即使不考慮人情因素,出版社出于逐利動機會作何選擇是一目了然的。
很顯然,最該發出批評之聲的人缺席了。我們需要獨立且專業的批評者和愿意為這些批評者提供發聲平臺的媒體。
我們的專家學者不該只是坐在書齋里發論文,或更有甚者與“劣幣們”形成利益聯盟——批評和研究者應有一些社會擔當,更何況兒童文學的社會功能屬性更大于其他文類,我們從事的實在是與“未來”息息相關的事業,我們最終要面對的,是“孩子的眼睛”。
作為權威文學機構的閱讀審定者,我的同行們擁有最系統的學科理論知識,知道今天發生在國內的閱讀風波在國外曾經引起過怎樣的討論,而他們又有哪些思考的成果和社會層面的操作實踐可資借鑒;兒童文學學者相較其他學科而言更有常年奔波在第一線接觸各種兒童、學校和家長的優勢,我的同行中更有不少自己也投身創作以實踐檢驗理論所學,本是最應也最能在類似事件中發出有影響力、有說服力的聲音,從而幫助家長和老師們從一遍遍的撞迷宮南墻中走出來的人。
為什么說是一遍遍地撞南墻走迷宮呢?因為每一次類似的震蕩都會把從前引起過軒然大波的話題重新帶出來,比如這次自殺書寫的討論,讀者們就很自然地將從前童書中“色情”“暴力”的敘事重新翻出來。這本身就說明這些問題從來沒有在母嬰公眾號的高聲譴責與之后“孩子哪有這樣脆弱”碎片式反對意見的錯時論辯中得到解決,而是滾雪球一樣越積越多,無限循環。家長們以前無所適從的現在依然無所適從或者更加茫然,而難以在這樣的閱讀爭論中真正獲得進益,學到使自己心里有底的辨識和導讀策略。如果專業學者們能為大眾撰寫明白曉暢的閱讀指南、參考手冊,以專業知識幫助困惑的家長和老師們厘清一些兒童文學的基本理念、寫作及閱讀的法則,能將國內外兒童文學界對禁忌寫作等問題已有的探討介紹給大眾,相信這樣的“原地踏步”魔咒至少破解有望。
借用一位朋友的話,讓我們一起做“為兒童的批評,為文學的批評,為人生的批評”,我再加一句,“為民眾的批評”。
說實話,這些批評尤其是該為那些中層及以下的家庭提供的,為那些自身文化程度有歉、咨詢渠道和選擇接觸較少的父母群體提供的“公共性質”的服務,他們恰恰是最需要遠處的引導建議的人。于培養孩子一事上,我們這些廣義上的教育者,應該為推進公平而努力,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各階層的分野壁壘因為知識和信息資源的緣故越來越顯著。
總之,兒童文學從業者應不斷更新自我、提高審美辨識能力,更多一份責任意識,從寫作者、批評者、出版者、教育者等多個維度共同努力,爭取通過市場的自然淘汰促進良幣替換劣幣,讓文學的問題回歸文學。(事實上今次商家的下架如此迅速難道真是因為出版社重視讀者意見嗎?)行業生態需要每一個相關從業者悉心維護。
孩子的未來尤是。
[1] “掃雷”楊紅櫻《馬小跳》——監管在哪里?良心在哪里?https://mp.weixin.qq.com/s/P06RnR-W6HwzuJxz3NTn0w
[2] Hormann, Elizabeth. "Children's Crisis Literature." Language Arts 54 (May 1977): 559-66.
[3] Bandura. A.(1969).Principles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New York: Holt, Rillehart & Winston.
Bandura, A. and R. H. Walters.(1963).Social Learning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
[4] Wiseman, A.M (2013). Summer’s End and Sad Goodbyes: Children’s Picturebooks About Death and Dying. Child Lit Educ 44, 1–14.
[5] Poling, D.A., and Hupp, J.M. (2008). Death Sentenc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Children’s Death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9(2), 165–176.
[6] Truman Guy (1993) Exploratory study of elementary-aged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death through the use of story, Death Studies, 17:1, 27-54, Eron, L. D., Lefkowtiz, M. M., Huessmann, L. R., & Walder, I , . Q. (1972). Does television violence cause aggress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27, 253-263. Greenfield, P. M. (1984). Mind and med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eline, C. W. (1976). “Does the medium matt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3), 81-89. Chaffee, S. H., & McLeod, J. M. (1972). Adolescent television use in the family context. In G. A. Comstock, E. A. Rubenstein, & J. P. Murray (Eds.), Television and social 6ehauiors. Washington, DC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obson, J. (1977). Children, death, and the media. Counseling and Klues, 21(3).
[7] White, E., Elsom, B., & Prawat, R. (1978).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death. Child Development, 49(2), 307-310.
[8] 一個女中學生之死(二)[選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07e180100ik40.html.
[9] 陳丹燕.施驪?寧歌?我: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213634/.
[10] 安徒生獎緣何花落曹文軒?http://jingji.com.cn/html/yssc/39935.html?from=groupmessage IBBY國際執委張明舟:曹文軒獲安徒生獎是遲早的事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6/2016-04-04/269164.html?from=singlemess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