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印度“第三電影”:帕特瓦丹的鏡頭中,真實而殘酷的社會現實
新冠疫情掩蓋了因《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在印度持續數月的沖突。隨著印度民間批評政府疫情防控不力的聲音四起,中印邊境沖突再次拯救了莫迪政府:沸騰的民意轉移向了中國。不管怎樣,印度國內逐漸加劇的宗教族群沖突和社會階層矛盾都是難以被長久掩蓋的。揭露這些問題的文化戰場曾經是印度劇情電影,早至20世紀20年代印度電影就嚴肅批判童婚、種姓壓迫等社會暗面。而近年來隨著莫迪政府大搞寶萊塢政治(Bollytics),利用電影人為印人黨站臺,印度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印地語-烏爾都語電影界不僅隱藏起了諷刺政府、揭露不公和批判種姓主義的利刃,甚至開始為總理拍攝傳記、配合宣傳。這種情況下,印度的獨立紀錄片反映出的真實而殘酷的社會現實更引人關注,也更為可貴。
咖喱中的蒼蠅
獨立紀錄片被一些印度學者稱為“咖喱中的蒼蠅”(a fly in the curry),這些少量的“不和諧”影像,猶如落入一鍋完美咖喱的小蒼蠅,破壞了由千百部寶萊塢電影編織出的善惡有報、愛情浪漫、結局團圓的美夢。其中最受關注也最具爭議的一位“美夢破壞者”就是印度的獨立紀錄片人阿南特·帕特瓦丹(Anand Patwardhan)。

帕特瓦丹于1950年出生于印度孟買,60年代末在美國學習社會學后回國。他執導的第一部紀錄電影是1974年的《革命浪潮》(Waves of Revolution),記錄了印度北部比哈爾邦爆發的大規模反腐敗運動。此后四十余年,他的獨立紀錄片一直聚焦于當代印度受傷的政體,宗教在分化社會階層和煽動種族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中扮演的角色,不斷回歸到民族、戰爭、宗教、貧困、社區、性別、種姓和階級的痛苦糾結,徹底挑戰了印度此前由國家資助制作宣傳式紀錄片的傳統。
印度的紀錄片歷史可以追溯到殖民時期。早在20年代英殖民者就利用電影向印度人民宣傳帝國之繁盛。1930- 40年代隨著審查制度的嚴格,與甘地和獨立斗爭有關的電影得到進一步控制,英殖民者制作的二戰宣傳電影占據印度電影的絕大多數份額。1950-60年代,隨著印度國家電影部(Film Division)的成立,紀錄電影和劇情電影一起成國家指導下塑造統一民族身份的宣傳工具。這一時期的印度紀錄片多是約翰·格里森(John Grierson)式的,旁白多使用上帝般的聲音(voice of god)錄制, 敘述模式為“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式,力圖讓受眾相信,一個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仁慈國家有辦法和主動性來解決民眾所提出的任何問題,以阻止他們的直接政治行動。這種紀錄片風格與印度獨立后尼赫魯式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也許是相符的,然而從70年代開始,包括帕特瓦丹在內的很多印度藝術家和觀眾開始對“國家”失去興趣,并厭倦了以往由政府資助拍攝格里森式紀錄片的宣傳模式。
這一時期帕特瓦丹開始受到新拉美電影的影響。1970年代中期的拉美電影無論是在內容還是美學上,或者更準確地說,以創造性的方式進行內容和藝術形式的調和上,都被認為是世界政治電影的革命先鋒。因此,深受影響的帕特瓦丹早期作品,可以被看作是席卷亞非拉的跨國電影運動“第三電影”(Third Film)的一部分,并且在印度開創了獨立紀錄片的發展空間,填補了這一領域長期稀缺的屬于底層人的現實主義。
1980年代的影視技術發展為帕特瓦丹提供了更多拍攝、制作和發行便利。隨著每年兩萬多臺錄像機涌入印度和低成本的16毫米膠片的流行,便攜的拍攝設備、更低的拍攝成本以及多樣的傳播渠道為非精英階層的拍攝者提供了諸多可能,中產階級獨立紀錄片人開始成為新的文化生產者。
令人不適的真實
帕特瓦丹引起廣泛關注的第一部紀錄片《孟買:我們的城市》(Bombay,Our City)就是用這種16毫米膠片制作而成。這部拍攝于1985年片長75分鐘的紀錄片,記錄了在英迪拉甘地執政時期頗具爭議的清除貧民窟運動,以及“消滅貧窮”如何不幸地演變成了“消滅窮人”。

底層民工——孟買的真正建設者——被迫蝸居在非法搭建的臨時住所,在美化市容的運動中他們的臨時房屋被摧毀,不斷被驅逐。在陰雨綿綿的獨立日,流浪兒們在街頭出售印度國旗,努力不讓懷里的小商品淋濕;臨時窩棚幾乎被積水淹沒的一戶人家有一個孩子死去;一名臨時住在人行道上的婦女懷抱嬰兒,對手持拍攝機器的帕特瓦丹爆發了怒火:“至少讓我們熬過這個雨季!連四個月的時間也不給?!你就想拍張照片出名。你還能幫我們什么?連政府都把我們拋棄了!”
20世紀90年代,帕特瓦丹開始拍攝一系列紀錄片,講述所謂的“世俗印度的瓦解”與印度政治中日益增長的社群主義(communalism)。原教旨主義宗教團體的興起與世俗的社會主義傳統直接沖突,而馬克思主義者帕特瓦丹的美學和政治思想正是由這些傳統塑型的。1992年帕特瓦丹拍攝了《以神之名》(Ram ke naam),記錄了80年代以來右翼印度教組織世界印度教大會(VHP)進行的要求在阿約提亞巴布爾清真寺遺址建造羅摩廟的運動,以及由此引發的社群暴力。在1992年拍攝的這部紀錄片中,摧毀清真寺和重建印度教神廟的承諾尚未獲得成功,遺憾的是印度政府禁止了片子公映,到1996年影片被解禁播出時,片中貫穿始終的對即將到來的社區暴力的警告早已變成了現實。

1995年的紀錄片《父親、兒子與圣戰》(Pitra, Putra, aur Dharmayuddha),探析了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中的暴力行為(如巴布里清真寺的拆毀)與針對婦女的性暴力之間的聯系。同時著眼于當代印度城市男子氣概(masculinity)的本質、印度教民族主義如何鼓勵“厭女癥”、以及政治領導人如何將非暴力和世俗主義與軟弱無能聯系在一起。影片中提及一位參加古吉拉特邦濕婆軍競選活動的宗教領袖竟要求印度教婦女每人生育8個孩子,以此來對抗穆斯林的威脅。
這一時期帕特瓦丹逐漸發展出個人風格獨特的紀實性美學風格。他不僅親自剪輯,還親自舉著攝像機一邊拍攝同時一邊提問,街頭采訪中他傾向于聚焦于人群中的某一張臉,把他們的說話、凝視和一舉一動都記錄在鏡頭上。通過這些近景和特寫鏡頭,觀眾可以清晰的看到年輕的狂熱分子、憤怒的暴民和上層階級的自我狂歡,同時近距離共情被邊緣和被壓迫者的無奈與悲痛。在我看來這些邊緣者平靜而微弱的發聲比宗教狂熱分子和政客的激情狂歡更具力量,刺穿所有原教旨主義共有的咄咄逼人的防御。
帕特瓦丹的紀錄片曾多次獲得印度政府獎項,諷刺的是同一個給他頒獎的政府也曾多次審查和禁映他的作品。《父親、兒子與圣戰》在拍攝11年才后才被允許上映。 制作于2000年、反思印巴核競賽的《戰爭與和平》(Jang Aur Aman)曾被要求刪減21處,并經多次斗爭于2005年才得以公映。這是一部讓觀影心情持續起伏涌動的紀錄片。它的拍攝地以謀求發展核武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為主,還涉及因核武器永遠留下傷痕的日本廣島和長崎,審視了印度日益増長的核民族主義,反省了核武器對人類的共同威脅。
紀錄片總長135分鐘,全篇利用了對比的拍攝手法,用渴望和平的底層人民的平靜話語對比民族主義政客的激昂陳詞,用閱兵式上對武器的歡呼對比核試驗輻射致殘的沉默印度男子。影片大膽揭露政客利用軍備競賽中飽私囊,同時展現了底層民眾如何被宣傳利用,以及底層聲音如何被忽視。片中一名反對核試驗的印度老者在接受采訪時說“國家就像你的母親,如果母親親手給孩子喂毒,孩子能怎么辦呢?”
帕特瓦丹在巴基斯坦采訪中學生時,記錄了兩組學生以辯論的形式闡述核能的必要性,其中拿到“巴基斯坦應該緊跟印度發展核武器”辯題的女孩在結束后說, “其實我也覺得巴基斯坦目前不該發展核武器,應該先解決溫飽,消滅貧窮。”而“這畢竟是比賽,只有我們(辯手)這樣慷慨陳詞地說出觀點,才能在辯論中取勝,才可能讓聽者信服。就像我們的政客一樣,他們只說挑起民族情緒的話,為的就是讓自己取勝而已。”
2011年,帕特瓦丹推出了紀錄片《比姆同志必勝》(Jai Bhim Comrade)。這里的比姆指的是為達利特階層(編注:種姓制度的最低階層,又稱賤民階層)爭取權利的“印度憲法之父”安貝德卡爾(Bhimrao Ambedkar)。電影開篇講述了1997年達利特人在和平示威中遭受警察暴力的事件,重點探討了孟買達利特人生活和政治的各個方面。這部電影花了14年的時間制作,最終在2011年上映并斬獲多項國內外電影獎項。復雜的蒙太奇手法,配合大量對達利特人和旁觀者的采訪,串起了諸多爭論與沖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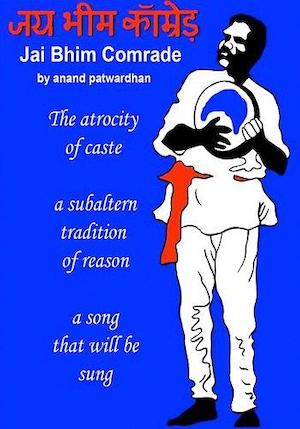
這部紀錄片的深刻之處不僅在于反映出的達利特人被壓迫的現實,還在于影片后半部分表現的格比爾藝術陣線(Kabir Kala Manch)為主的當代達利特激進主義,以及達利特活動家、濕婆軍和各種共產主義組織所代表的主流左翼運動之間的復雜關系。這部影片曾被評價為“一部馬克思主義的音樂劇,它像小溪一樣沸騰”。的確,全篇靠敘述和音樂兩者共同向前推動。達利特詩人和帕特瓦丹共同創作的反種姓主義歌曲《我們不是你的猴子》(We are not your Monkeys)引起強烈反響,歌曲批判了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對種姓制度的贊頌——“統治者控制著所有的知識/宣稱羅摩衍那是印度的歷史/并稱呼我們許多名字:惡魔、賤民、不可接觸者……”
從血腥棱鏡中看印度教特性的興起
時隔7年,帕特瓦丹于2018年推出了迄今他的時長最長(261分鐘)的作品《理性》(Vivek)。這部紀錄片于2018年9月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首映,并于2018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第31屆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上獲得最佳長篇紀錄片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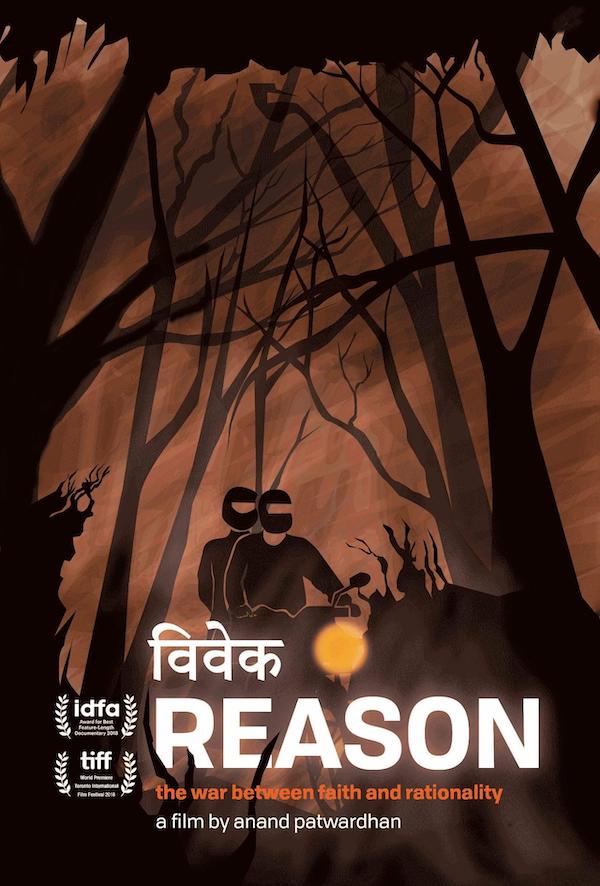
全片共分成13小節。每一節都圍繞2013-2016年以來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一起事件。(除了其中一節提到2008年孟買泰姬酒店恐怖襲擊)。通過政治謀殺的血腥棱鏡,帕特瓦丹揭示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近年來如何迅速興起,以及在印度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針對穆斯林和達利特的私行、針對社會活動家的謀殺、針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如何正在瓦解印度的世俗民主。
每一節影片用同一片頭間隔開:沒有音樂,鏡頭俯拍一男子在黑夜小道獨自騎摩托前行,車燈微弱,前路模糊,隨后砰砰砰砰四聲槍響,畫面中依次出現四位近年來被印度教狂熱分子射殺的“理性主義者”的照片: 2013年被印度教極端組織永恒會(Sanatan Sanstha)成員槍殺的著名的反宗教迷信斗士Narendra Dabholkar、2014被同一組織成員槍殺的印度共產黨(CPI)左翼政治家Govind Pansare,2015年遇害的坎納達語理性主義作家MM Kalburgi,和2017年被3名印度教狂熱分子槍殺的班加羅爾女記者Gauri Lankesh。
近四小時的視覺語言包含的信息非常豐富,除了上述四位活動家,紀錄片集中還表現了多人的故事:被印人黨政府以“叛亂”罪逮捕的尼赫魯大學學生會主席Kanhaiya Kumar,海德拉巴大學不堪歧視而自殺的達利特博士生Rohith Vemula,因被懷疑食用牛肉慘遭私刑慘死的穆斯林Mohammad Ikhlaq等。
此外,內容還涉及了甘地與安貝德卡爾關于建民選舉權的分歧;被殺的左翼政治家、馬拉地語作家Govind Pansare所著的《誰是希瓦吉》(Who is Shivaji),以及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如何通過神圣化希瓦吉而“再造”歷史;在印人黨壓力下孟買郊區一車站更名“羅摩殿站”Ram Mandir的風波;印度教狂熱青年宣稱對穆斯林女性的愛情圣戰(love jihad)等等。

采訪部分帕特瓦丹延續了以往無所畏懼的風格,每個提問都直指問題核心,向直接受害者或家人索取故事,尤其那些失去權力的人的聲音,并展現了這些聲音是如何被新聞媒體拒之門外的。
強烈的對比再次出現在片中:“羅摩必勝”的激昂高歌、受害者家人的無聲抽泣、帕特瓦丹本人深沉的旁白,讓觀眾的情緒在觀影過程中時而憤怒,時而悲傷,時而陷入沉思。片名“Vivek”意思是辨別力、理性,通過這部紀錄片,我們可以跟隨帕特瓦丹對當下印度社會最迫切、最徹底的探索,了解他的國家如何從世俗民主走向權力、種姓和宗教信仰的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暴力。我想辨別力與理性正是帕特瓦丹想要提供的出路之一。
帕特瓦丹本人不喜歡作品被稱為“藝術”(art)。他認為這個詞“老是被用壞或者用錯”。而我看來帕特瓦丹的紀錄片帶有強烈的藝術感,就像小津安二郎電影中的摒棄了一切表演手法的表演,是藝術的終極魔法。而事實本身的展現就足夠直擊心靈,觀者感受復雜如第一次看到美國的越戰紀念碑帶來的震撼、折磨、激怒和反省。觀眾的感知和同情,正是被他獨特的藝術性喚醒的。這種喚醒既來自影片中展現的殘酷真相帶來的沖擊力,也來自前文提到的特寫鏡頭和蒙太奇手法,和片中的音樂與唱誦。
帕特瓦丹作品帶有強烈的“第三電影”特點,深刻揭露了印度當前的危機不是一個人的獨角戲:莫迪是右翼趨勢的癥狀,而不是原因。經濟自由化不僅加劇了貧富差距,還使貧富差距趨于穩定,這也助長了印度日益增長的右翼共識。通過頌揚超級富豪,新自由主義的印度使貧富差距自然化,并放棄了早期對平等的民主承諾。而貧富差距和社會階層的固化產生的一個不斷增長的、未受過良好教育的失業男性階層,他們很容易就成為了宗教領袖操縱政治的獵物。
《理性》是一部沉浸式的記錄電影。影片中充斥著死亡和暴力的露骨畫面,憤怒的暴徒和穿著卡其布軍裝的軍隊,左翼知識分子走在路上被槍殺的可怕事實,讓人不得不為帕特瓦丹本人捏一把汗。但是他的勇氣和紀錄片中不放棄反抗的人們,又讓人對他記錄下的這個社會的未來看到希望。正如2019年在一次采訪中他表示能感受到“有希望”,“人們終將醒來,人們正在醒來”。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