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三十而立|離岸業務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不可忽視的一塊拼圖
在國際金融領域,一直存在著全球金融中心座次之爭。排名靠前的如紐約、倫敦,也會十分在意每一年城中所發生的金融業務總量,因為這些業務量是國際金融中心名次的重要依據。
比如一地IPO(首次公開募股,即公司上市)的年度金額及數量、全年的債券市場規模、外匯交易總量,以及其他各種金融產品的交易量、總量等,都能影響到一個城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排名。排名最靠前的紐約、倫敦、中國香港及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在國際金融市場激烈競爭,常常不分伯仲,也因此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上你追我趕,互不相讓,呈膠著狀態。
國際化大都市在意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并十分看重作為金融中心的排名,那是因為在榜單背后,是金融業務給城市乃至國家帶來的真金白銀和財源滾滾。比如,國際大型公司的IPO背后,投行財務顧問及承銷發行業務往往賺得盆滿缽滿,而其他派生的如商務差旅、會議、路演等,也將給城市帶來實實在在的服務業收入。更重要的是,金融大項目的落地,能帶來日后交易稅基的擴大,為城市作為金融中心的未來發展鋪墊下更堅實的經濟基礎。
從金融市場的規模和總量來看,2019年,上海金融市場成交總額達到1934萬億元,金融市場直接融資額達到12.7萬億元,上海證券交易所年末股票市值全球第四,上海黃金交易所場內現貨黃金交易量全球第一,上海原油期貨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貨,上海已經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了。
不過,對比上海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業務來源,就會發現大部分業務都來自“在岸”業務。相對來說,“離岸”業務就少得多,這是上海和紐約、倫敦、中國香港等排名更靠前的國際金融中心相比的一個顯著特點,可能也是未來上海向國際金融中心更高排名進發的潛力空間。
建設任何一個“中心”都需要有周邊“腹地”,如果沒有廣袤的沃野千里為基礎,就不可能產生一個以此為腹地的中心城市。歷史上城市形成的本源也是因為物流、人流、資金流的匯聚。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在世界上林林總總的城市中,逐步形成的一些金融中心,也無不是由于其存在廣闊的經濟腹地,并由本國的經濟騰飛而肇始的。但由于全球化的進程,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方面,有一塊業務逐漸的成為了國際金融中心不能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塊業務,就是所謂的“離岸”業務。
“離岸”相對應的詞匯是“在岸”。如字面意義,“在岸”是指本土本國,或從地理范圍來說指在所在國境內;而離岸,指非本地、所在國的境外,類似離開了所在國的國境線、海岸線,故稱“離岸”。離岸業務也就是指非本國(非居民)客戶帶來的業務,比如一家優秀的中國企業去美國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上市,那么對紐約來說,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離岸金融業務了。
十多年前,筆者被某國有大行外派到其盧森堡分行工作。盧森堡位于歐洲,但全國面積僅約2500平方公里,人口也就50萬,境內有名的企業僅數十家。當時不禁想:這么小的一個地方,能做什么銀行業務呢?之后在當地工作中才逐漸了解到,這個面積還不足蘇州市區面積三分之一的國家,以基金為例,管理著超過1.4萬個盧森堡注冊基金,資產總額超過4.7萬億歐元,是歐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基金中心(僅次于美國)。如按“離岸”“在岸”來分,基金業務中的絕大部分就是離岸業務。正是包括基金在內的各種離岸金融業務,使得地域不大、人口不多的盧森堡,能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
也許盧森堡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案例不夠典型,我們還可以考察一下大型國際金融中心如紐約、倫敦或中國香港,就會發現,原來大型國際金融中心城市也一樣,都離不開離岸業務的支持。
在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如倫敦、紐約,以當地證券市場上市公司中外國公司的數量為例,在美國紐約泛歐證券交易所,外國公司的數量占到了22%;在納斯達克,外國公司的數量占比為14%;倫敦證券交易所中,外國公司占比為17%。在中國香港證券交易所中,非本地公司占比有7%,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外國公司占比為0%,也就是沒有一家國外公司在國內證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8年底數據)。
而目前,A股市場總市值已達5.6萬億美元,占全球總市值的7.5%,如果加上在中國香港和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市值,實際中國公司占全球股票總市值已經超過11.8%。可以看出,境外上市的中國公司,實際上為其他國際金融中心貢獻了全球股票總市值的4%,由于上海及深圳的證券交易所沒有接納任何一家國外公司前來上市,所以這一塊對于我國的國際金融業務來說,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凈流出。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只對本國的公司提供證券發行的業務,也就是完全放棄“離岸業務”,那么紐約和倫敦今天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就不會那么顯赫。
除了股票市場之外,在全球債券市場情況也是類似。我國的債券市場總市值高達11.6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但在我國發行債券的外國或非本地企業,金額占比只有不到2%。而在美國這一比例近6%,在英國則高達54%,中國香港更高達65%。也就是說,離岸債券業務,為英國的國際金融中心貢獻了過半的債券交易,在中國香港,更是貢獻超過三分之二;而離岸債券業務對我國內地的金融中心建設的貢獻卻不足2%,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數據截至2018年底)。
金融業務離不開實體經濟,離岸業務一樣不只包括離岸的金融業務,還包括離岸國際貿易等業務。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需要離岸金融業務的支撐,更需要有離岸貿易等實體經濟業務的支撐。
在國際貿易中,有一種貿易形式為離岸轉手買賣。舉例來說,比如上海有一家大型的離岸轉手買賣貿易商,它可以從加拿大購買貨物,同時轉手賣給位于菲律賓的另一客戶。而加拿大原產的貨物,可以直接通過遠洋運輸發往菲律賓,也可以先抵達上海港進入保稅區,然后再發往菲律賓。上述這兩種貿易方式,前一種為離岸轉手買賣,后一種為轉口貿易。
轉口貿易和離岸轉手買賣中,雖然物流本身僅和上海擦肩而過(不經過或不入關),但是在這樣的交易中,資金流則是完全通過上海的,賣出貨物后收款會到上海,而購買貨物時付款也是通過上海付出。國際貿易(經常項下)相關的支付比國際投融資(資本項下)更為頻繁,所以,轉口貿易或離岸轉手買賣這樣的離岸貿易業務,也能為一個城市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乃至國際航運中心,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國際上以國際貿易促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案例有不少,特別是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其包括轉口貿易和離岸轉手買賣在內的離岸國際貿易業務,在歷史上都曾極大的促進了它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
由此可見,我國在上海等地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如能在離岸業務方面有所發展,將能進一步擴大業務范圍,提升業務體量,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新的空間和動能。但同時應該看到的是,離岸業務雖然可觀,倒也不是想叫人來人家就來的。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與一個金融中心能否在以下幾個方面提供有利條件有很大關系。
其一是稅收。不可否認,在全球范圍內,國際金融中心一定程度上也在開展稅收上的競爭。一些地方甚至不征收直接稅,所在地公司無需繳納所得稅,資本利得稅,也不征收股息、利息以及特許經營使用費等預提稅。國際資本尋求的理想離岸金融業務所在地,稅收一定不能過高,而且最好稅制簡單,稅種較少。目前,如在企業所得稅方面,倫敦為20%,紐約為21%,新加坡為14%,而上海是25%,對比來看我們還是有差距的。
其二是公司注冊便利度。公司注冊的便利度,也是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離岸金融業務的實體一半會在當地注冊成立SPV等公司,如果公司注冊成立的手續復雜,費用高昂,維護成本不菲,這也將會把許多離岸業務擋在門外。比如,對注冊資本的最低要求,公司股東人數的要求,國籍的要求,是否需要在當地每年召開董事會議,股東資料保密程度等,都將在實務中成為全球資本選擇時的一些考慮要點。
其三,法制與監管。落地離岸業務,出資方對所在地的法律環境,以及監管環境當然會十分在意,不然,資金一旦抵達,由于法律的不健全或監管得過于嚴格,造成資金或公司運營的不自由或甚至違法,這是任何一個投資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以外匯管理方面的監管為例,我國目前貿易項下的收支已經全部放開,但在資本項下,少數項目尚未放開,離岸業務選擇落地地點時,會對此類監管條件比較在意。
稅收、公司注冊、以及法制和監管等都是軟環境,國際金融中心的硬環境當然同樣重要,比如在國際經濟版圖中的地理位置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國際上在綜合性的金融中心之外,也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專業離岸金融中心。
比如,開曼是具備業務多樣性的著名離岸金融中心,世界上不少大型金融機構會在開曼設立殼公司,以至于在開曼島上,公司多如牛毛。筆者曾因業務關系到訪開曼,發現開曼首府喬治城其實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加勒比海小鎮而已。再如,毛里求斯則是一個投資印度以及投資非洲的注冊地跳板;而作為離岸金融中心的百慕大,以再保險業務聞名;塞浦路斯,則常被用來作為對俄羅斯投資的公司注冊地;馬紹爾群島,除了是一個航運傳播注冊中心之外,也具有較強的公司保密法,和美國資本市場有著較強的聯系。地處歐洲內陸的列支敦士登,在離岸金融方面,以與奧地利及瑞士相關的信托類金融出名;迪拜,有點類似中東的瑞士;英屬維京群島,是中資企業青睞的海外公司注冊地;新加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認為是以財富管理和信托見長的離岸金融中心。
這些在細分領域形成了專業特色的離岸金融中心,也是我們進一步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或未來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時,可以借鑒的一種特色化發展形式。
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一定程度上是零和游戲。比如一家優秀公司的上市,選擇了倫敦就不會選擇紐約(兩地上市除外),又比如如果完全放棄離岸業務,那么就只會有自己這邊的業務跑到他人地界去,而沒有其他國家的業務拿過來做補充,這是一種業務量的此消彼長,而只有拼上“離岸業務”這塊彩色的拼圖,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才能更有潛力,更加完備。
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包括離岸業務的發展,其實也是支持了本地、本國、乃至更大區域范圍的金融發展,支持了實體經濟的建設,因此更是一種雙贏。競爭能提高效率,合作有利于共同發展,我們樂見我國如上海等城市早日建成更有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也樂見國際上有更多更高效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建成。
(作者薛鍵為某外資法人銀行總行部門總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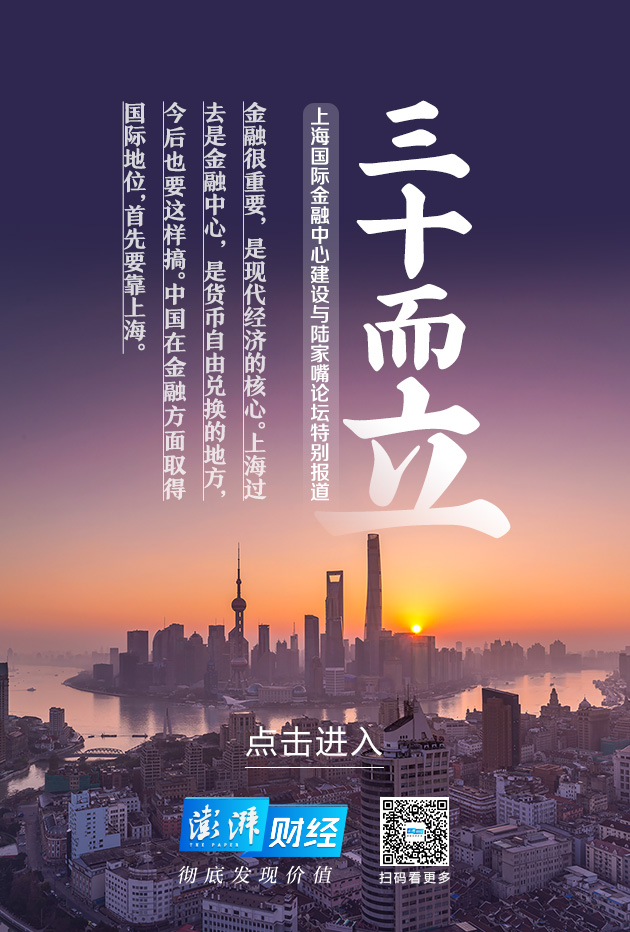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