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三合村街口

小城故事攝影作品/張燦楓
三合村街口
文/張乃述
三合村街口是片街頭廣場,是“城中村”三合村的生活中心。在這里盡顯小人物種種生存狀貌,它混雜著尚未消盡的鄉土氣息與越來越濃郁的時代風貌。
三合村街口是片街頭廣場,街面約有十幾畝地。你站在街口向北望,整個街衢呈“Y”字形,像只高腳杯,泛著煙然青暉。而游樂園高高的摩天輪映襯在大青山下,口銜街尾的屋脊飛檐,粼粼轉動,那整個街衢就似一條扶搖天際的蒼龍,一個活著的童話世界。
我打小就知道大青山下有個三合村,我好奇地問母親,為什么叫“三合村”呢?母親說,因為那個村只住著三戶人家。我說,住在天邊,不怕狼吃嗎?在我小時候的想象里,三合村仿佛就在遙遠的天邊,那里有令人神往的原野與林莽。
直到五十年后,因了“喬遷新居”,才有幸走近三合村。只是,原野與大林莽早已逝去,三合村已經變成了一處鄉鎮,參差錯落的街衢,卻還滲透著我兒時似曾享受過的市井俚俗,還殘留彌漫著一抹久違了的鄉土氣息。
三合村廣場是我平時最喜歡去的地方。它是一個熱鬧的所在,人煙聚集,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人間劇情也在這里上演。“打場子”便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傍晚,在三合村酒杯式街口廣場上,有人打了一個場子。場子很大,周圍閃爍著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兩只巨大的音箱八字擺開,中間是聲控設備,聲控設備后面的暗影里站著兩女一男:三人中間的那個女子年齡稍長,三十多歲,剪發頭,膚色很白,還算好看,拄著亮晶晶的雙拐,穿著上紅下黑的絲質衣褲,手里拿著一個麥克風,像是主持。站在她兩邊的一男一女,顯然很年輕,那個后生個子很高,他正在一展歌喉,歌聲不是很美。他身邊那個小姑娘梳著兩根小辮子,端妍清純亭亭玉立,暗夜掩飾不住她姣好的臉龐。兩個人都戴著大大的墨鏡。大黑天里為什么還要戴墨鏡呢?這讓我很是不解。后來看到場地當中的小募捐箱和聲控設備前面掛著的彩繪條幅,才恍然大悟。那條幅上寫著一行大字:三人行殘疾人藝術團。
“好!”場面上有人在喝彩,那個秀氣的年輕姑娘正在唱一首十分好聽的歌。歌聲很美也很甜,音色醇厚清潤,她唱歌的時候,面帶微笑,樣子溫柔可人。三個人中數她唱得最好,也最吸引人。這種感覺越發使你猜想著你面前這個姑娘摘了墨鏡是不是會更美?
圍觀的人中不時有“橋頭部隊(農民工)”走進場子經過那片很大的空地,把零錢放進小慈善箱里。不知為什么,大凡上前放錢的人,在眾目睽睽之下都顯得很拘謹羞澀,那種不自然的樣子倒像是他們在接受施舍。于是有人就讓自己的小孩進去放錢。也有放了錢走人的,那都是些大男人。每有人助捐,站在中間的那個拄雙拐的女子就拿起麥克風,說,謝謝。那個美麗的姑娘在美麗的夜色中唱著美麗的歌,一曲終了,又唱一曲,唱完了,拄雙拐的女子就接著來上一段承上啟下的串場詞,然后她就亮起民歌嗓子唱起歌,歌喉還可以。我注意到,一有人上前放錢,她就把麥克風換在左手,接著用右手碰碰坐在她旁邊休息的盲姑娘,盲姑娘就對著手中的麥克風微笑著說,謝謝。我發現盲姑娘好像始終在微笑,像是從心里自然流出來的,沒有痕跡。那微笑深深地流淌在我的腦海里,蕩起微瀾。
夜色漸濃,曲終人散。終于等到“殘疾人藝術團”演出散場。我見有人圍攏過去,也跟腳走到那位盲姑娘身后。盲姑娘還坐在小板凳上。我把目光越過她的頭頂和前額極想從上面看到她的眼睛,然而未能如愿。這時,一個“愣貨”對盲姑娘說,你能不能摘下眼鏡讓我們看看?盲姑娘一點沒生氣,依然微笑著說,摘了,很難看,怕把您嚇著。拄著雙拐的女子不愿意了,搶白道,天地良心,誰還糟踐自己?那個盲后生沒好氣道,愛咋想咋想。盲姑娘說,我是農村人,家里窮,小時候害眼病,沒錢看,耽誤了。拄著雙拐的女子指指盲后生說,他的眼睛讓毒氣熏了,還能看見一點。我這兩條腿每天站好幾個小時,疼得不得了,回家全憑他給按摩呢。有人問道,你是幾級?女子道,這條四級這條二級。那人道,我是三級,經過國家鑒定的。我這才看見,說話的那人也拄著一只亮晶晶的拐杖。這時有人說,你們應該找殘聯。女子說,我們靠自己,自力更生。
這時一輛破舊的中巴開過來,停在道邊。司機大漢走過來也不說話,忙著收拾家當。盲后生和盲姑娘聞聲上前,抬起一只足有一米多高的大音箱,往車前摸索著走,只見有人上去幫忙。
有人見了車說,嗨,還有車呢。拄雙拐的女子說,我們吃住都在車上。我想,顯然是大篷車了。
大篷車在夜色中拐了個彎終于走了,大篷車上同樣有彩噴:“自強自立”“三人行殘疾人藝術團”。我想起了吉普賽人。是的,他們顯然超越了“乞討”的范疇,他們甚至想活得更好,他們努力活著盡力活著,完全靠自己。
我曾經在維多利鬧市看見一個紫面皮壯士,光著膀子,滿身肌肉,叉開雙腿,兩腳踏住大理石地面,一根胳膊粗的繩索從脖子后面繞到胸前,打結成枷鎖狀,爾后又像樹根似的伸向地面。他左手卡在腰間,右手握著一根丈八木棍直杵天地。在他的腳下,鋪著一張彩噴書寫大紙。他說他是個行者,他渴望把自己的苦旅寫成大書好與世人分享。看著他的造型,我覺得他更像一種行為藝術。
這倒勾起我一段塵封已久的記憶。那是一個盛夏的中午,我和幾個等著攬活的“橋頭部隊”在三合村街口一家門臉前的陰影里納涼,只見一個身材高大束發留須的布衣道人走進陰涼,靠墻坐了下來。他把一只缽就勢放在面前,他看也不看我們,就那么旁若無人地坐在我們旁邊。“橋頭部隊”并不在意,依舊有說有笑,可我卻怦然心動。我暗自窺視眼前這個道人,雖不面善,卻似有幾分仙風道骨。我站起來像是漫不經心地走過去,掏出十元錢,十分隨意地把錢放進缽里,那道人依舊面無表情,視而不見,好像什么事情也沒發生。
我知道,乞討就丟了尊嚴。壯士與道人用一種文化粉飾包裝了乞討,乞討而不伸手,似乎就保留了尊嚴的底線。可我很快又知道,也不盡然。
這天中午,我剛出小區,就聽見三合村街口一個稚嫩的童音隨著麥克風飄了過來,夏日的中午,只有烈日和燥熱,而這個天籟般的童音一洗炙熱的煩躁,恰似一襲清風拂過心間。我循聲而去,一眼看到那個唱著天籟的小孩,卻令我心中咯噔一下,滿是凄涼。只見一家三口,兩個大人幾乎是匍匐在地,只有那個年紀大約五六歲的小男孩坐在父母前面,手里拿著一只麥克風在奶聲奶氣地唱著兒歌,盡管有時跑調兒,然而依然不失天國里的聲音。令人奇怪的是,竟無人圍觀。可孩子依然唱得純真唱得一絲不茍,唱到高音處,孩子就歪倒身子半跪著,空著的那只手杵在地上,梗著脖子往高處拔音,白皙的小臉都憋紅了,脖子上的青筋也暴綻出來。
沒有一個聽眾,孩子唱給誰呢?是唱給天國嗎?還是唱給他身邊匍匐著的一對“父母”。這時我才開始注意他們。“母親”是個瞎子,眼球癟了,眼眶深深凹陷進去,不知為什么她穿著一身土黃色的僧衣,她趴累了就直起身來坐在自己跪著的后腳跟上。“父親”卻未皈依佛門,然而他完全是巴黎圣母院丑陋的阿西莫多相貌,他的臉被燒得疙里疙瘩歪歪扭扭,一只耳朵燒得貼住了耳孔,兩只手燒成了肉疙瘩,只有右手還殘留著兩根抽搐得像雞爪子一般的拇指和食指,僵硬得勉強能捏起散落在地上的零錢。
我環顧四周,才發現,沿著街口廣場周遭的商鋪門前,都遠遠地站著商家或是過往的人們。坐北朝南的街口像一只高腳的酒杯盛滿正在中天的烈日,烈日想流瀉出去燒毀這個世界。不時有人遠遠地走過來,把零錢放進這個家庭面前的搪瓷飯盆里,然后匆匆離去。我上前趕緊放下本是買切面的錢也準備離開。
孩子唱完了最后一首歌,“父母”終于直起身來,盤坐在地上。“父親”從孩子的手里收走麥克風,孩子站起來頑皮地笑笑,張開兩臂原地轉了一圈,順手幫助“父親”整理東西,完全是漫不經心的樣子。我睜大眼睛企圖看見這個家庭的頂梁柱、這個正需要父母呵護、可父母反倒需要他來養活的、本該上幼兒園的孩子,這個時候可能表現出來的得意,我還想看見孩子向父母撒嬌、嚷嚷著“餓了”的難看的小臉,我甚至想看見孩子埋怨父母如此不利索如此難看的不屑的神情,然而我錯了,孩子依舊很乖,一副天真無邪的神情。
當一切收拾停當,我看見“父親”站起來脫去干凈的還算八成新的黑色半袖T恤,露出了像我在維多利廣場看見的那條壯漢一樣健碩的古銅色身軀,然后把黑色半袖T恤疊好放進背包中,又順手從一只小塑料桶中提出一件舊了的豆綠色長袖汗衫,穿在身上,接著把一尺多高的功放音箱背在身上。顯然,那件黑色的半袖T恤,是“父親”的演出服,是“父親”乃至整個家庭的門面,一如富豪的奔馳悍馬。
這時,只見一家人整理好行裝,準備走了。我看見孩子往后靠了一下,我以為他想依偎在母親的懷里,哪怕只一會兒,當一抹溫馨就要浮上我的心頭的時候,卻戛然而止:父親先行一步,開拔了,也就在這個時候,我看見母親的一只手搭在了兒子的肩上,腳也就挪動起來,這一系列默契的動作可能已成機械式的習慣。我目送這一家三口離開了三合村街口,不知道他們的下一站將在何處停留。
后來我知道,三合村是青城不可小視的大村之一,包括外地的許多小劇團凡來青城,必到三合村演出。
那年中秋,三合村在街口廣場搭了個大戲臺,一個鄉間劇團演出“貍貓換太子”。這是晉劇的傳統劇目。演員們重彩敷陳把你引入豪奢的皇宮生活,諸等角色唱得不錯,我尤其對那個“皇帝”感興趣,待他下場,我也像村民們那樣好奇地繞到戲臺后面,想一睹演員的風采。我用手扒開幕布間的一條縫隙,我看見“皇帝”坐在一把椅子上,身上還穿著龍袍,長靴卻脫去了,他可能累了,伸直了腿,把腳擔在一只板凳上,靠著椅背休息,讓我吃驚的是,我最先看到的竟是他的一只深藍色的襪子后跟磨破了,是因為趕路匆忙是因為懶還是因為沒有針線?那個破洞爛得很大很大,露出的后腳跟如同一顆山藥蛋。我忽然想到,身邊有個女人或是母親該多好。從此,奢華的龍袍和破舊的襪子,就時不時地在我眼前晃動。這是一個現代版的“皇帝的新衣”。那兩年,戲劇跌入低谷,大劇團都舉步維艱,何況鄉間劇團。
高腳杯式街衢之于三合村一如青城的“中山路”那般熱鬧。酒杯式或飯碗樣街口是三合村重要的“政治”中心和文化廣場。到了夏日,在黃昏的安逸和沖動里,有人就提著琴鼓絲弦隨意在廣場的某一片空地上,拉開架式搭起“臺”來開鑼唱戲自娛自樂。這里會吹拉彈唱的人很多,隨便叫幾個人就能打起場子。有唱晉劇的,大多唱二人臺。鄉間的二人臺,時有葷的,人們聽了會哄堂大笑。我細細聽來,其實那些葷的,并不下流,既恰到好處又不失幽默和智慧。
搭起臺子來,如果還缺唱的,樂手們就先一個接一個地演奏曲牌,夜幕漸漸降臨,悠揚的琴聲勾魂般彌漫開來,自然圍觀的人也漸漸多起來,這往往也是人們相互問候的時候。聽見了琴聲,就有人來唱,甚至有農民工騎著自行車摩托車,打工歸來,路過,拐個彎,下車走進場子,亮開嗓子來上一段,不過癮再來一段,贏得掌聲之后,一溜煙揚長而去。
這天,夜色已晚,可三合村街口依舊琴音裊裊,我走上前去,一眼看見趙師傅在場子當中扯起嗓子正在唱晉劇“打焦贊”中的花臉“焦贊”,唱得不錯。一則唱完,趙師傅在叫好聲中不無自得地走出場子,他好像在尋找什么人,就一眼看見了我。我說,這么晚了,還不回家吃飯?他說,過把癮就回。他轉而問我,你們咵咵也喜歡晉劇?我說,晉劇也當國粹,生末旦丑都不錯,有些敘事段尤其是苦段子,唱得宛轉悠揚如泣如訴,讓人剜腸刮肚,只是花臉黑頭的唱腔有些“刨躁”。“刨躁”是本地方言,有點暗喻“性壓抑”。趙師傅聽了哈哈大笑。我說,營生挺好?他說,近日個沒甚營生。我說,還能揭開鍋吧?他說,覺察。“覺察”是烏盟方言,含義很廣,只可意會,大意是“將就”“可以”,里面有一種感覺生活的無奈?卻又自豪?樂觀?或是信心?“覺察”在這里有種精神向上的動感,你好像能看得見。
說著,趙師傅走到一個街頭烤鴨大排檔前買烤鴨,大布棚子下面,立著三只巨大的裝奶罐般的移動式烤爐,年輕的烤鴨師傅,手里操著一把大刀一把小刀,在麻利地剁著案板上的烤鴨,說話間,那小師傅,早已一刀把鴨尖切下來并刮向一邊,趙師傅見了,伸手抓過鴨尖放進嘴里,有滋有味地說,鴨屁股也是肉啊。
是耶,是耶。我哈哈大笑。趙師傅并不尷尬,他也跟著笑。
我說,十年前,我的女兒師范大學畢業,我和女兒住在天津拖拉機廠招待所等待分配,就常常到后面也是這么一個褲襠街上的菜市場去買吃食。一日,我們在一個賣熟雞的地攤上正準備買很便宜的雞小肘,一位大哥走過來,問小老板,你是哪的?安徽的。安徽的雞幾個屁股?小老板不解地回答,一個屁股。只見天津大哥一揮手把裝著一只雞的塑料袋啪的一下摔在小推車的案板上,怒道,你媽媽的,你看介(這)是幾個屁股?說著,天津大哥回過頭對我們說,介還了得,一只雞里掖著四個屁股,介不欺負人嘛。
說完了,我和趙師傅還有烤鴨師傅就哄堂大笑起來。我學著天津話說,介是真事,我忘也忘不掉。我也忘不掉,禽流感的時候,我看見趙師傅竟買了一大兜雞蛋,我說,你不怕死么?他說,操,禽流感不就是過去的雞瘟么,有球甚可怕的,前些時雞蛋貴咱吃不起,現在便宜了,咱不吃誰吃?這時候,趙師傅提著切好的烤鴨準備回家。我說:“顯見你這生活還覺察。”趙師傅說:“我兒子早就嚷反著要吃烤鴨,我一直沒給買,今日個掙上錢了就瀟灑一回。”這時候,一個人走過來喊道:“趙哥走哇。”我回頭看去頓然驚愕道:“這不是……”趙師傅笑笑說:“是我兄弟。”我說:“好。是兄弟就好。把苦分給他一點,自己不就少受一點么?!”“是了,是了。唔哈哈哈。”我們都笑。這么笑著,趙師傅與那個人就相隨著騎上停放在不遠處的平板車,往街衢深處騎去,臨走,趙師傅回過頭對我說,“遇見活兒您老給搭照一下。”
我望著他們的背影漸遠漸逝,想道,他們是什么時候和好的呢?因為我曾親眼看見趙師傅把他的這位兄弟打倒在地。想來是窮苦人之間也沒有多大的仇恨,惱得快,好也得快。
說起來我和趙師傅的友誼頗富戲劇性。那是我第一天到潤宇裝飾城采買裝修材料,剛到潤宇西大門就遇到一場戰爭:就見三四個人追打一個人,打倒了,爬起來,逃竄,再追打,再打倒,再爬起來,再逃竄,那場面猶如獸斗,打得行云流水一氣呵成,圍觀的人也隨著潮來潮去,直到那個人被打得鼻青臉腫滿面是血,像大蝦一樣佝僂著身子躺在地上為止,只見他張開雙手護住自己的臉和頭,為首追打的那個人就勢彎腰跨在他身上,一手按住他的額頭,道:“讓你日粗!讓你動手打人!”被打倒在地的那個人嘴里一個勁地討饒,“不敢了!再不敢了!”這時有人勸解道:“這小子初來乍到,不懂規矩,算了算了。”那人這才直起身道:“球也戀不成混下滿家人,日你媽的。”說著與他的同伙走了。我打聽到,這個外來仔搶了人家的活兒。當時我認定那個為首打人者是地頭蛇是惡棍。
后來我才知道,能夠跑馬的潤宇裝飾城之所以場面不亂,是因為形成了一個潛規則:拉活兒的板兒爺們按“先來后到”的規矩,逐漸把潤宇這塊大蛋糕分割成無數塊領地,各自在自己的地盤上攬活兒,井水不犯河水。
這一日,我看好了一家裝飾材料,不巧恰是那天打群架那伙人的地盤,而那個頭兒就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形影不離,而且上趕著討好我,我愛搭不理,沒好臉也沒好話,他卻全然不去理會,其他幾個伙計流露出一點不痛快,遠遠的嘟囔著:趙哥,算了,操,離了雞蛋還不做槽子糕了。趙哥并不惱,依舊跟在我屁股后面轉。我心想,操,下三爛,那日的威風哪去了?跟球要飯的有什么區別,還稱王稱霸!
我終于沒買,我又跑了好幾家甚至西龍王廟和南昭君墳都去過了,還是喜歡潤宇那一家。好幾天過去了,眼看要停工了,只好去那一家,也必須面對趙師傅。
正是七月流火的季節,下午三點,滿世界太陽,大地企圖把人們燒烤成人肉串。趙師傅和他的一個伙計為我各拉著一車沉重的裝飾材料慢慢地“爬”行,我們小區有一大段上坡路,趙師傅爬到車下,調節了一下車鏈子,然后像纖夫般拉著繩套,頭幾乎杵在地上,兩只死勁攥在車轅上的大手青筋暴綻,脖子梗得儼然是一只拓荒的牛,他哈哈地喘著粗氣,看著自己大粒大粒的汗珠子掉在地上摔成八瓣,他耕犁著自己的汗水緩緩地向前挪移。我一下子心疼起趙師傅來,就趕緊幫他推車,他憋紅著臉苦笑了一下,困難地說:“不用不用,球,受苦人,不受苦,喝西北風?”他堅持不讓我推車,我也只好依他。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一掃前嫌,摒棄了先前對他的成見。
那天晚上,我遠遠望著趙師傅蹬著平板車在夜空下使勁扭背脊的粗獷與憨態,不禁覺察到“還覺察”。
夜色漸濃,三合村的“橋頭部隊”,披著滿天星斗,在燈光怒放的酒杯式街口,歡樂地在笑聲中洗去一天的疲憊,準備迎接明天的生活。
作者簡介:張乃述,北京人,長于呼和浩特。寫小說也寫散文隨筆,小說曾獲得內蒙古自治區文學“索龍嘎(彩虹)”獎。
本文選自《向度》2020年第一期(春夏卷)總第2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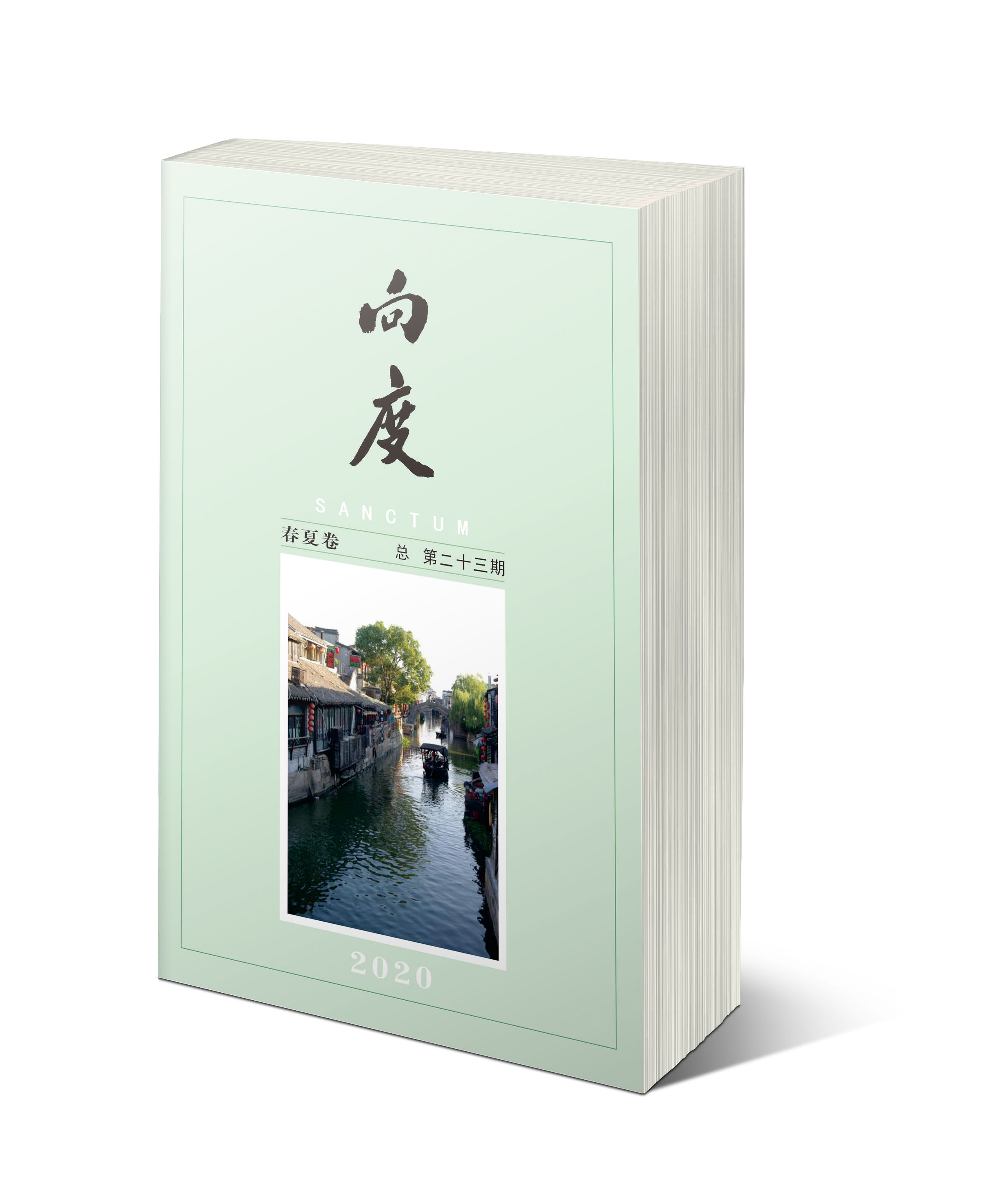
《向度》2020春夏卷(總第23期)2020年6月出版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