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約翰·塞蒙斯:“后人類”是一種哲學寓言
采訪 + 撰文 / 龍星如(中央美術學院科技藝術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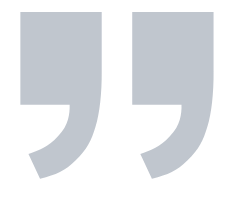
約翰·塞蒙斯(John Symons)是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系教授,也是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復雜性科學博士項目導師及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科技哲學史學會成員,他的研究和寫作方向包括心靈哲學、科學哲學、形而上學、邏輯學,尤其聚焦于計算機科學哲學領域。
2019年10月,塞蒙斯受邀在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發表系列講演,主題包括“物理世界的運算”(Computation in the Physical World)、“用身體運算”(Computing with Bodies)、“運算理論在心靈哲學中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Theory of Computation in Philosophy of Mind)、“自然信息運算”(Computing with Natural Information)和“極簡認知的涌現:模態與心靈”(The Emergence of Minimal Cognition: Modality and Mind)——這些恰是當下計算機科學哲學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也恰好與筆者作為科技藝術策展人的研究方向有所交叉。近日,筆者通過視頻連線采訪了塞蒙斯,和他就“后人類”(Posthuman)概念、計算機科學哲學等話題展開討論。

約翰·塞蒙斯,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系教授。(圖片來自University of Kansas)
今天,“后人類”的說法已經很普遍了,但對“后人類”概念的詮釋仍有不同版本。福柯、裘劍一(James Hughes)、堂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尼克·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 等來自不同學術脈絡的學者的觀點,都曾在不同語境下被援引進關于“后人類”的論述里。在您看來,組成“后人類”概念的關鍵要素有哪些?
塞蒙斯:“后人類”,如其字面所示,意為“人類之后”。我們對“后人類”的思考,實際上是關于“我們之后的存在”的想象,但在討論“后人類”之前,我們或許應該簡要地回顧一下我們對“人類”(the Human)的理解。20世紀中期,哲學領域對“人類”概念大致有兩種寬泛解釋,分別來自法國和英美。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法系哲學的代表,包括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和福柯,集中對盛行于19世紀的人本主義者所持的“人,而非神,才是價值核心”的觀點進行了批判。科耶夫、福柯和其他法國“后人類主義者”認為,人并不是上帝的替代。而在這群人里最有影響力的當屬福柯。對福柯來說,“人”已經終結。法國的后人類思潮實際上來自對神學或神學所定義的“真實”,以及對圍繞特定“中心價值”展開的理性秩序的批判——而在這些學者眼里,它們都是幻景。自啟蒙運動以降,歐陸思想界一度認為秩序和價值來自“人類”,而福柯的批判也恰恰源自于此,他認為我們 應當批判“人類”概念本身。在整個法國哲學的線索里,對“人類”的思考很復雜,也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

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
[法] 米歇爾·福柯 / 著
莫偉民 / 譯
上海三聯書店,2001-12
相比法系一派,英美語境下的“后人類”與科技發展的聯系更為緊密,尤其是科技輔助人類身體演化 的可能性及計算機讓人類成為非具身化存在、從有限的生命長度中解脫出來等潛能上。這種技術烏托邦主義的想法曾一度蔓延于20世紀的美國,那時人們認為可以通過精巧的科技發明來解決所有問題。另一條支線則是,一些哲學家癡迷于“賽博格”[1]的概念,這個概念既蘊含政治色彩,也包含了自我創生和自體解放的意義。在“賽博格”狀態下,人們可自肉身存在“升華”至一種新的生命狀態。以哈拉維為代表的學者群體認為,“后人類”的核心就是“賽博格”帶來的自我創造與解放。
你會發現,美國語境中的學者(包括哈拉維)是接觸過法國思想體系的,但并沒有對其全盤吸納。他們認同法系學派對人本主義的批判,但并沒采用福柯反進步主義的政治暗喻。與此相反,美國學派更傾向于持有革新式的、馬克思主義式的對“解放”的樂觀態度,這也包括對女性和少數族裔處境的改善。但對福柯來說,“人類解放”和正義的概念也是幻景。哈拉維對福柯觀點的(部分)采納,體現在她把對“人類”的批判延伸為對男性中心主義或族長中心主義的批判,所以她的視角像是“消化了一半”的法國后人類主義,同時糅合了某種技術烏托邦色彩和對政治的詩性想象,并不是那么自洽的,但很可能她本就不想自洽。
當然,還存在另一種有關“后人類”的思想,我們姑且稱之為“硅谷后人類主義”。它更像是在流行文化里存在的對技術發展的烏托邦想象,有時也被稱為“書呆子的狂喜”(rapture of the nerds)。這一類思考通常帶有關于“人的徹底數字化”的想象,包括人是否可以被轉換成信息、上傳到電腦,以及所謂的“奇點臨近”[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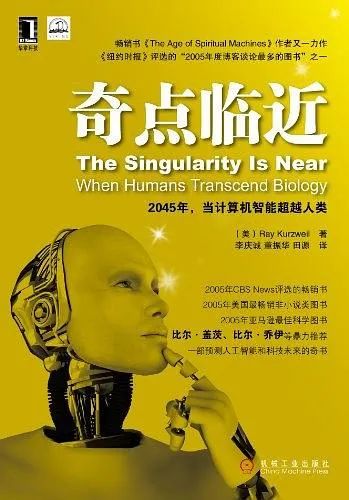
奇點臨近:當計算機智能超越人類
雷 · 庫茲韋爾 / 著
李慶誠、董振華、田源 / 譯
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10
您自己是如何理解“后人類”的?
塞蒙斯:我覺得“后人類”像一種“哲學寓言”。現代早期的政治哲學家,如霍布斯和盧梭,會討論“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即一種想象中的時空所在。對于他們來說,對“自然狀態”的想象恰恰是對所處時代的公民和主權狀態的思考,是一種頗有建設性的哲學寓言。我想,不管是霍布斯、洛克還是盧梭都不會真心相信“自然狀態”真的存在(過),他們只是透過它來理解現實。我們對“后人類”的想象也與此類似。
但在我的理解里,不論是“自然狀態”還是作為哲學寓言的“后人類”,都并非被完全外部化的思考對象,它還是會和當下具體狀態產生種種牽連和交織,換言之,我們是半置身于其中的。
塞蒙斯:你說的對,這兩者是相互交織的。這些哲學寓言會幫助我們組織起當下狀況的方方面面,而我們也會論究我們所投射或想象的未來與當下之間存在何種糾纏和協商。對于這些哲學寓言的態度也不完全是一邊倒的,我們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對。比方說,霍布斯可能認為“自然狀態”是“粗鄙而短暫的”,盧梭則將它視作我們天性里一種理想且和諧的存在。而我們在哲學寓言蘊含的各個方面之間的迂回,也會幫助我們決定今日的投入,比如,我們需要關注什么?我們想要把什么帶往未來?就像在“后人類”的語境里,有人可能更喜歡帶有硅谷色彩的“后人類天堂”,也有人認為它是末日。所有哲學寓言的內在都交織著錯綜復雜的視角和疑惑。如果你對奇點深信不疑,那它或許就是你當下最重要的工作——將奇點帶到人間,它或許就能成為我們文明的最終訴求。當然,我認為沒有人“真的”相信這些寓言。我們只是在這些哲學寓言里選擇了自己傾向的部分,并將之引入我們當下的政治和道德語境里,向前推進。

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
Rethinking Fodor and Pylyshyn's Systematicity Challenge
Eds. Paco Calvo & John Symons
The MIT Press,2014-04
今天的計算機技術(包括人工智能)似乎還是以基準(benchmark)和解決方案(solution)驅動的,同時也存在來自其他學科的研究者的追問。比如,計算機科學家凱特·克勞福德(Katett Crawford)近期的ImageNet Roulette項目就將目光投向ImageNet[3]中的“人”這個飽受爭議的分類, 并嘗試指出其中的缺漏。在您看來,我們該如何思考人工智能領域里最緊迫的課題?
塞蒙斯:當我們討論“人工智能”時,它的意義其實很復雜。在今天的語境下,多數人將“人工智能”等同于“機器學習”(我認為這是有問題的)。機器學習只是人工智能的一個方向而已。人工智能領域經歷過好幾次浪潮,它的發展和硬件的提升息息相關。而如今機器學習的發展勢頭也離不開GPU(顯卡)的運算能力。但我相信這一輪潮流也終將過去。
此外,有必要回到對有關“人工智能”定義的共識,如果我們認為“人工智能”指的是建造與人類有同等思考能力的獨立智能體,那么我對它的可能性是非常懷疑的。但如果我們認為“人工智能”指的是一系列“認知義肢”(cognitive prosthetics)工具的開發,我認為是有合理性的,這些義肢將會是我們能力的延伸。比方說,人類小孩有能力做簡單的加法,但如果要學習更復雜的運算,則需要一些技巧,也需要工具。這些工具就是“義肢”,它增強了孩童的認知能力。在機器學習領域,我們開發出了關于模式識別和假設生成的種種系統,而計算機是我們數千年來一直在開發的種種“認知義肢”的延續,就像古代的算盤能幫助商人完成復雜的計算一樣,算盤是商人數學能力的延伸。如上所述,我傾向于將人工智能視作“義肢”而不是獨立于我們之外的存在。當然,我們可以開開腦洞去想象奇點的到來,或者在我們之后存在于地球的人工智能,這本身很有趣,對這些場景的想象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下的狀況。
您在寫作中曾提到,真相的“收斂模型”[4]并不完全符合當今科學領域里密集運算的現實,但當代科學已經高度依賴運算和軟件工具。漢娜·阿倫特曾寫道,現代物理研究所設計的數據“不是現象、表象,因為我們在哪兒都不會遇見它們,無論是在我們的日常世界里,還是在實驗室里:我們知道它們的存在,僅僅因為它們以某種方式影響了我們的 測量儀器”[5]。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看待哲學層面的“真相”?

過去與未來之間
漢娜 · 阿倫特 / 著
王寅麗、張立立 / 譯
譯林出版社,2011-10
塞蒙斯:很好的問題。我想,一方面我們應該思考計算機的工具本質和它們的局限。最顯而易見的局限是:我們“創造”了它們,但我們有局限,我們會犯錯誤,比如你在前面提到的神經網絡訓練數據集的偏見問題。另一方面,“運算性”也逃不出系統的邏輯限制。計算機到底能做什么,其邏輯邊界其實是分明的。
你問到對“真相”的理解,我想現在存在著很多無法抵達的真相。我們正處于一種“實際的不透明感”(practical opacity)中,我們使用的許多工具的運作過程如今已經不完全裸露在人類的肉眼觀察之中,我們也無法如期待的那樣完全理解機器學習系統,我們只知道這些系統能給我們提供不錯的解釋。但實際上,要完全搞明白這些運算過程是超出人類能力的。
早在20世紀70年代,哲學家就曾面臨同樣的問題。當時,計算機開始被人類用來證明數學定理,比如四色猜想。計算機證明了這條定理后,哲學家卻遇到了問題——因為這個證明是“不可觀測的”(not surveyable),換句話說,對于用大量機器生成的證明,我們無法一目了然。這是早在機器學習流行起來之前發生的故事,當時的計算機執行的只是所謂“傳統的軟件解決思路”。我們或許認為,我們確實得到了某種證明,但它是不透明的,因為這個“證明”并非一目了然。但事實上,有很多學科領域早就面臨同樣的現狀,比如瑞士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我想沒有人能了解它所進行的實驗的每一個方面。對于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大科學”來說,“不透明感”就是它的現狀。
許多科學家所謂的“真相模型”更像是一種“真相的漸近”,亦即,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逐漸逼近某一特定的真相。這也被稱為真相的“收斂模型”,即我們會以漸近線的方式趨近真相。但我也認為,有理由相信這種對“真相”的描述依然有待商榷,我們的知識或許并不是逐步、漸近地向某一參考線推進的,因為我們所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可能是完全離散的。事實上,我們正走向不同的方向,而科學探究會滲透在所有的方向里。換言之,我們可能已經知道很多“真相”,它們可能是不同的真相,而在所有復雜的人類工作里,都存在一種內置的“不透明感”。

《阿麗塔:戰斗天使》劇照
至少從今天來看,關于“后人類”的討論交織著計算機科技和生物因素,也暗含著對“人”的模仿、推測甚至改變,科技在鋪設“后人類”的可能性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哲學研究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塞蒙斯:這些最終都會是哲學問題。我們不會從工程學或純粹的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解釋“人類意味著什么”,因為你無法把一個本質上屬于哲學范疇的問題分解為工程學或自然科學問題。你不能用科學本身來回答有關“科學的價值”的問題,也不能用科學論據來回答關于“科學論據的本質”的問題。對哲學家來說,我們基本是被困在哲學里的。哲學家不需要擔心自己的角色問題,但時刻需要擔心自己所思考的問題的緊迫性。
我想,“人的價值”這個問題始終無法由科技來解決。如果你是福柯,你可能會認為“人”本身也是幻景,是一種錯覺(delusion),“人類”的概念并不存在。但如果從常識來看,你可能會說“人”是一個物種,但哲學家會對此進一步追問,因為“物種”的概念也并非那么完備和清晰。我想,對哲學家來說,我們的工作恰恰在于如何建立關于對“人”的討論,對“生物身份”和“人性/人格”的討論,以及這些討論之間的認知界限。
同時,人依然是具身化的存在,我們不是某種抽象對象,因此所有生物屬性都依然和“人性”息息相關。我們已經知道自己有能力對基因進行編輯,即我們有能力“工程化”自己的生理屬性,但問題是我們應該怎么做。這一選擇恰恰和我們對“人的價值”及“人性”的思考息息相關。
雖然您說“‘后人類’只是一種哲學寓言”(我也很喜歡這個說法),但您也以“我們能教給我們的后人類后代什么?”為題發表過演講,可否綜述一下這個演講的主旨?
塞蒙斯:假設存在一種計算機智能,或者說一種“后人類”的存在,雖然它具備各種能力,但這種存在依然會是一種有限存在。它的有限性植根于計算機的底層和邏輯局限。因此,“后人類”后代也依然會面臨我們所面臨的數學和邏輯限制,比如停機問題。如果這些未來的存在足夠“智能”,它們可能會考慮這樣一個策略:既然我是一個有限存在,我該如何使用有限的資源?因此,它們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是邏輯限制,還會包括有關“標準”的問題。甚至可以設想,它們是否會思考美學問題,即如何能更“美好”地生存。它們也需要思考人格的價值,即使它們的“人格”與我們截然不同,因為它們是不同的物種。
也就是說,個體性問題會延續到您所描述的“后人類”的狀況里。
塞蒙斯:是的,它們也會需要考慮個體性問題,就像我們一樣。如果所有的計算機(在不考慮任何技術限制的情況下)有可能相互連接在一起,那么它們也有可能成為“某一智能”。機器需要決定:“我是要融合進那個‘一’,還是我要自己待著?”“作為一個個體和作為一個與所有個體連接的存在,兩者的價值有什么區別?”如果今天的我們可以接入其他人的思想和內部世界,我們或許也會面臨同樣的決定,即是否要成為“一體”。當然,我們都知道這不可能,但想象這樣的情境有助于我們反思自我的存在。如果我們能成為“一體”,你會對其他的思想施加暴力嗎?還是無條件地加入,抑或獨自走開?這樣看來,“隱秘性”似乎是人格的重要部分(如果“隱秘性”不存在,則有可能發生上述的情景,人們能進入彼此的大腦),它需要被保護。這也是為什么在今天討論隱私很重要,我們的個體性恰恰來自隱秘性。如果我們徹底裸露,則可能不再有今天意義下的“我們”了。
注 釋
[1] 賽博格(Cyborg),通常指人類與電子機械共生的系統。
[2] “奇點臨近”是由美國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提出的一種關于人工智能與人腦融合技術的樂觀理論。
[3] 當前圖像處理界最有名的數據集之一,多用來訓練計算機進行圖形識別。
[4] 收斂模型(convergence model),指我們理解真相的一種方法或趨勢,即逐漸向某一確定值靠近。
[5] 《過去與未來之間》,漢娜·阿倫特 著,王寅麗、張立立 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248頁。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26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