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政之后:警察、軍閥與文明進程中的成都④
成都的社會組織就像它的城市布局和城市建筑一樣,與晚清時期中國其他的城市有許多相類似的特點。有錢人家一心要擴大他們的住宅,好讓他們那多子多孫的家庭都能住在一個日益擴展的院子里,他們往往都能成功,住宅越建越大。他們的家仆:門房、守夜的、廚子以及轎夫都住在側院里。富裕的家庭往往會從牙婆手中購買奴婢、侍妾。這些奴婢和侍妾原本是城里或是周圍四鄉貧苦人家的女兒,被中間人要么是綁架,要么是買來的〔18〕。買不起大宅院的商人就和他們的家人住在他們經營的店鋪后面,幾個小伙計也常和他們住在一起。伙計們除了照顧店鋪外還得干家務活。生意做得不那么得法的商人以及手藝人、工匠便只能租房子住了。他們將貨物在大街上擺攤出售,或是送貨上門。許多廉價的日常生活用品,包括一些熟食,便由家中的女人和兒童來制作,再由男人沿街叫賣。家境殷實的家庭或是小康人家,他們家中的女人一般不會隨便到外面去拋頭露臉。她們外出時都會坐在遮得嚴嚴實實的轎子里。但是也有例外的場合,比如節慶的日子里。每年農歷正月十六,按照習俗,婦女也會和男人一樣,到城墻上去閑逛,走動走動,以求來年有個好身子骨〔19〕。
比家庭更大的團體以各種目的結合起來。成都市有五百多個街區〔20〕,大多數街區,至少都有一個地方性的社團組織。每年在鄉鄰中指定一個杰出的人來擔任該組織的頭領。這個鄉黨組織的頭兒負責從每戶家庭收取費用。這筆錢用來支付每年的節慶花銷,為敬拜地方上的神靈大辦宴席,請道士來做道場,請皮影戲班子來表演以及放焰火。許多街道上還設了一些小神龕、小祭壇以供奉地方上的神靈,比如“土地廟”〔21〕。
清政府時期,至少從名義上來說,成都市的絕大多數家庭,像中國所有其他的社區一樣,還被一種“保甲”制度捆綁在一起。這種“保甲”制度實際上是一種互相監督管理的機制。那時住在成都的外國傳教士把這種制度叫作“十戶制”,因為它與近代英國的十戶聯保制很相似〔22〕。就像近代英國一樣,每十戶相鄰的家庭被劃定為一個單位,叫作“牌”(a tithe 是英語中的專門名詞,相當于中文中的一個“牌”),對于“牌”這個單位中的每一個家庭來說,都負有監視這個單位中其他所有家庭及其成員行為的責任。而在中國的體制里,每十個這樣的家庭單位“牌”又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甲”,每十個“甲”組成一個“保”。從理論上來說,那些設計了并在全中國的城鎮、鄉村貫徹執行“保甲”制度的官員,在他們看來,在一個家庭眾多的單位里發生任何不軌行為以及爭執,必須上報給這個“牌”長。“牌”長是從每十戶家庭的戶主中挑選出來的,他要么平息事端,要么則向他的上級 “甲”長或 “保”長匯報。 “保”長同時也是一位戶主,他負責在他轄下的這一千個家庭和上級官員之間進行溝通,將他所負責的社區內的任何問題向政府的有關部門匯報〔23〕。
有清一朝,“保甲”制度只是一個理想中的管理模式,被政治理論家們視為至寶;但是對于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來說,它只不過是一張網,使人深陷其中〔24〕,雖然這些理論家們不這樣認為。而且,地方上的官員們是否有熱情來貫徹執行這種制度,很大程度上要依據他們的上級是否積極行動以及地方上的社會狀況而定。成都在19世紀晚期對于“保甲”制度實際執行的程度以及實際起到的作用,我們下面會做更為詳細的討論。這里我只想指出的是成都市的居民,若按照“保甲”制度所要求的標準,很難說是有理性的、有秩序的、有紀律的、服從家長約束的群體。至少富裕家庭和窮苦人家之間社會地位的差距會使得“互相監視”的任務變得復雜化。再說,就像中國其他城市那樣,在成都市內穿街過巷的人群中有許多并非是在成都市內有家有業的永久定居的居民,他們只不過是一些暫住的體力勞動者或者是乞丐。成都有成千上萬的男人從事挑夫、小販或轎夫的工作,他們都住在茅棚或小旅館里,每日所得很難糊口〔25〕。他們中有許多人要走很遠的路程去完成他們的工作,常常出城門很遠(見圖1.5)。

圖1.5 1933年轎夫們在將傳教士們從重慶送往成都的途中停下,歇
息(加拿大聯合教會資料,維多利亞大學檔案,多倫多:目錄編號:No.
98.083P/4.)
行乞是當時成都街上常見的現象(見圖1.6)。乞丐們夜里就睡在橋洞下或是城墻外面陰郁的“雞毛店”里。一個外國游客回憶說,1883年他抵達成都時,他們在東門外面遇見了成百上千的乞丐。他這樣報告:“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一座堆滿了的破布爛衣和垃圾的橋中間走了過去,這座橋橫跨在東墻外面一條往南流去的河上〔26〕。”據中國內地布道團的裴煥章(Joshua Vale)估計,成都的乞丐在1906年時已達1.5萬人之眾〔27〕,他們大多數是男子。無法在一個經濟有保障的家庭里取得一席之地的婦女,很有可能出門為娼,這些妓院、窯子大多集中在東門北邊的東墻一帶。循規蹈矩的家庭也許會是清政府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體制的支柱,但是糟糕的經濟狀況使得許多成都市的居民在水深火熱中掙扎。

圖1.6 清朝時期堵在成都一條街上的一群乞丐(加拿大聯合教會資
料,維多利亞大學檔案,多倫多:目錄編號:No. 98.083P/7.)
就像中國大多數城市常見的那樣,成都也容納了各種各樣,出于各種不同目的而成立的社團組織。比如商業和貿易的協會組織。其中最有名的是由來自中國其他省份的商人和官吏組織的同鄉會。成都有些精心建造的同鄉會會館還建了戲臺,常常請戲班子來表演,四川省有多姿多彩的中國戲劇劇種〔28〕。這里還有各種各樣工藝的同業公會,從泥瓦匠、木匠到戲劇演員,他們都在同業公會或茶館里聚會,平息爭端,為他們各自的行業立規矩、訂章程。像街坊和同鄉會一樣,同業公會也向他們的會員收取一定的會費,用來舉行各種年慶和年會,以敬奉他們各行業的庇護神。
有一些特別的節慶是專屬于這個城市的。在北門外的一處寺廟里每年都要上演一出特別受歡迎的戲劇曲目,名叫《目連救母》,能吸引大批的觀眾。每年要舉行三次迎神會,迎接的是這個城市專屬的神,迎神隊伍要走遍城內的各大街道以及城墻外面〔29〕。農歷的四月初八日這一天,是佛教的節慶日,每年一次在城墻的東門外面,望江亭下要舉行放生會。人們在這一天買來各式各樣的小動物放生,讓它們重嘗一次回歸自由的樂趣。
歷史最為悠久的公眾集會要數每年的花會了。據說它最初見于唐朝。在每年春天的一個月內,成千上萬的人每天都朝西門外的道教宮觀青羊宮擁去。那里有生氣勃勃的各種娛樂活動以及誘人的美食,這就給商人們創造了一個售賣各種風格的農產品和手工制品的大好環境和機會〔30〕。成都的冬天雖然不致嚴寒,但也還是又冷又濕的,因此你不難想象男女老少在這種花會上迎接春天時的快樂心境。作為學者和作家的郭沫若(1892—1978)將他參加花會時的體驗和這個城市平日里中規中矩的生活做過一番比較,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此時此際中國好像年輕了三千歲。”
------------------------------------------------
選自《新政之后:警察、軍閥與文明進程中的成都》
社科類重磅作品。讀過《袍哥》的人,都會來看這本書。
關于20世紀初清末新政和民國初年在中國內陸城市成都所發生的變革,特別是警察在這個變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 (美)司昆侖 (Kristin Stapleton)著 ;王瑩譯
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4-1
定價:78.00元
裝幀:精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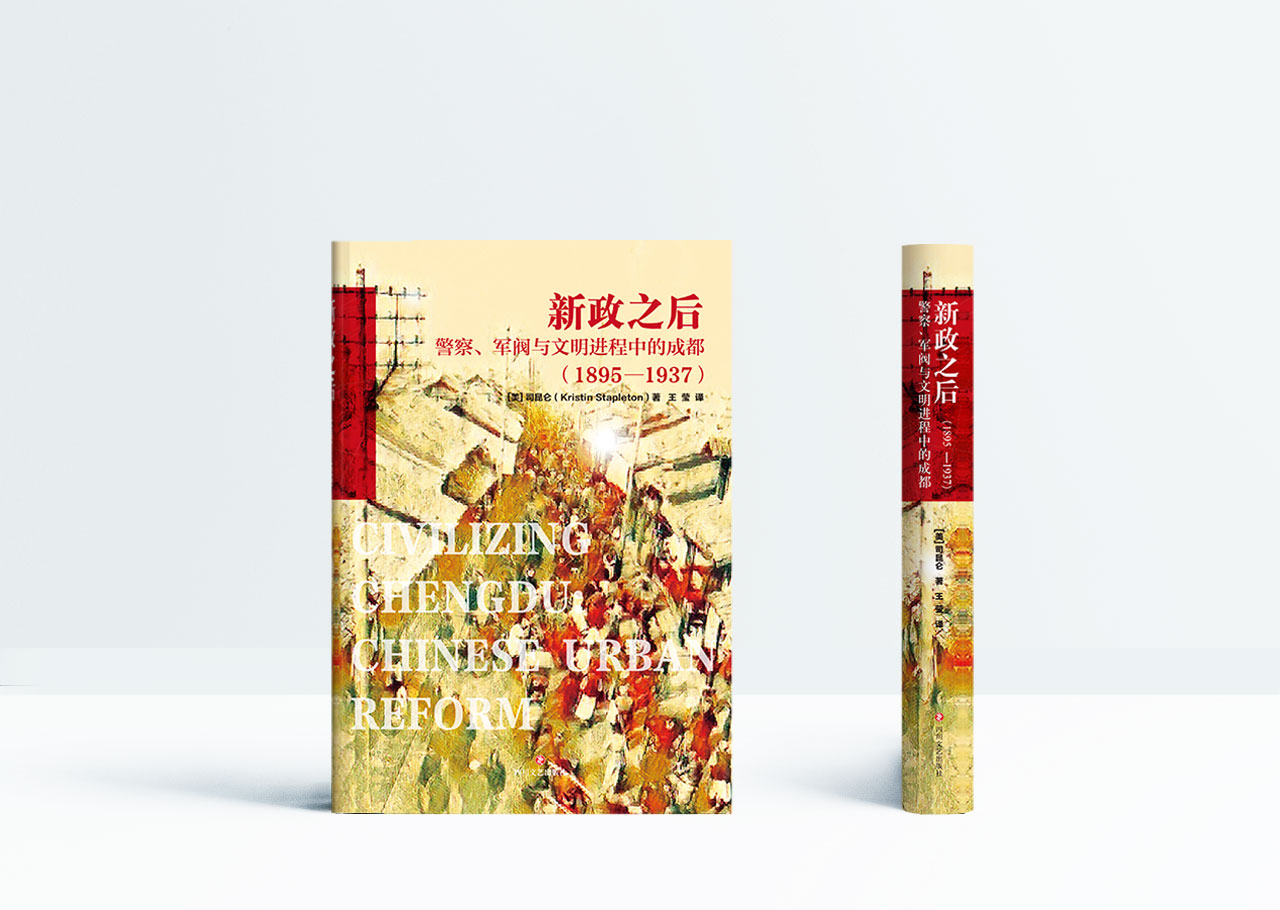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