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曹東勃︱當斯科特講無政府主義,他在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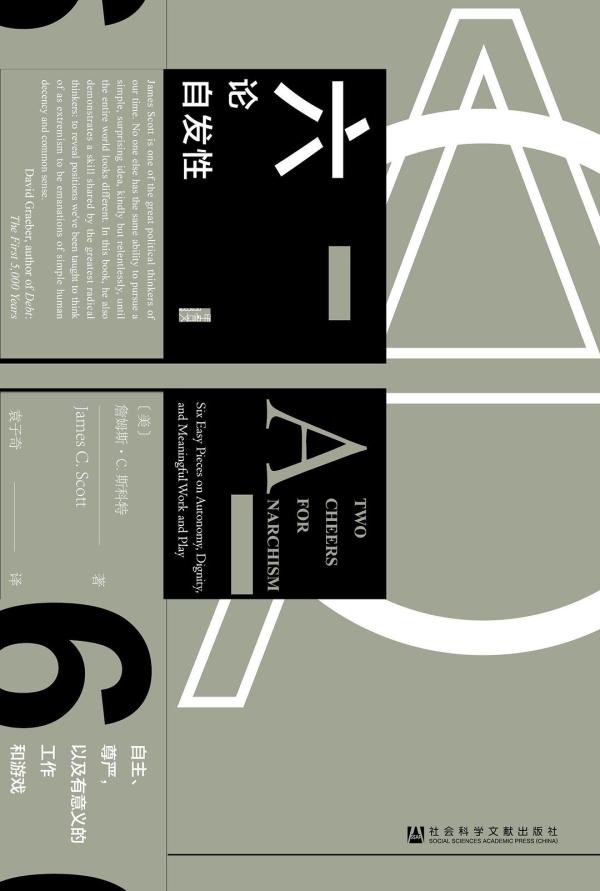
斯科特有一種魔力。他一貫擅長于小切口中見大縱深、在小概念里出大氣象。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中,他以“生存倫理”對湯普森的“道義經濟”做了新的拓展和闡釋;到了八十年代的《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他對這些底層小人物的描摹已經推進到精神世界,致力于揭示底層的日常政治或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九十年代的《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中,他再次翻轉角度,居高臨下地審視國家主體推動的現代化,其狹窄管道是如何裁剪自然狀態的豐富多元,造成“好心辦壞事”的結局;2009年,他出版了《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中譯本由三聯書店在2016年出版,2019年做了全面修訂),可謂把“腦洞”開到了極致,在政治人類學和歷史社會學的脈絡之外繼續探問,重構性地書寫了一部山地政治的可能演變史和移民史,把“惹不起,躲得起”的樸素邏輯,上升到有意為之的主動遠避現代財政和自覺逃離現代國家網格化、數目字管理的政治智慧高度,這樣的高山文明,著實是“深藏功與名”,不服都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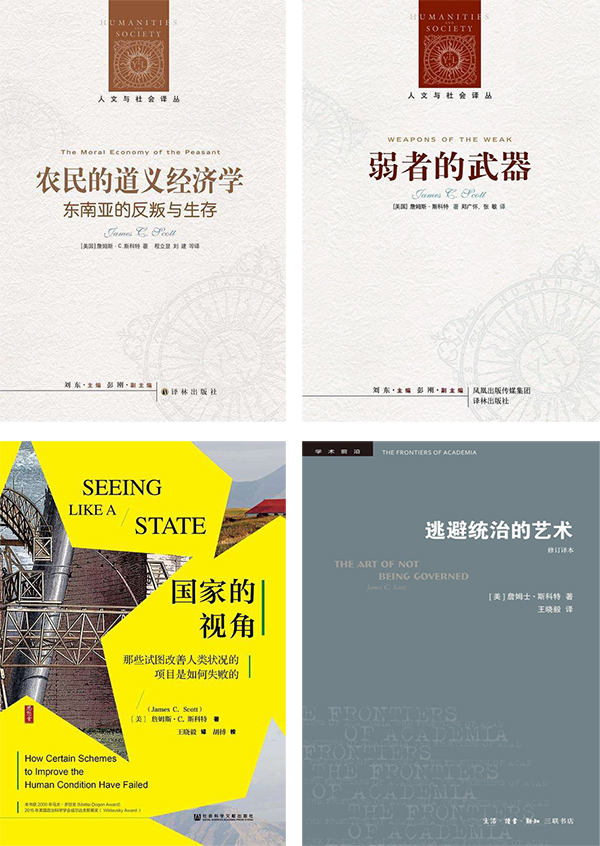
直到2019年末,讀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最新譯介的斯科特2012年的作品《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游戲》,我們終于看到了他對自己半個世紀以來一系列研究主題的終極解密與澄清,對貫穿其中的一條萬變不離其宗的思想線索——無政府主義,做了一次集中整理和明確剖白。因此,我們也不能對構成全書六個篇章的二十九個思想的“碎片”等閑視之,它們雖為斷想,卻是功力深厚、見微知著的大家手筆,也為在當下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新理解無政府主義,提供了一種全新、開放性的角度。
無政府主義的要義在否定權威。現代知識世界的權威是科學,現代經濟世界的權威是資本,現代意識形態世界的權威是自由、民主,現代政治世界的權威是國家、政府。所以不難發現,在這幾個領域中,無政府主義都以一種積極的有時甚至是一種挑釁式的姿態出場,用夸張的相對主義、多元主義方式對現有秩序提出質疑和挑戰。科學哲學史中的費耶阿本德,所取的就可理解為一種認識論上的無政府主義。他的《告別理性》和那句“怎么都行”,就成了一個標志性口號。
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幾位早期代表人物,雖大多有貴族背景,在觀念上卻與當時如火如荼的歐洲工人運動頗有淵源,更是創建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的主力。馬克思對彼時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現實的深刻批判,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歐洲知識分子的普遍聲音。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底層社會的至暗現實、底層民眾的慘淡境遇,特別是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各國政府在政治制度和經濟運行中的職能,遠不能與后來凱恩斯主義風行和福利國家興起時相比,這些都很容易促使人們將矛頭指向資本的貪婪擴張、制度的虛偽無力,尤其是在促進民眾福祉上恪守古典自由主義原教旨因而絕少作為的各類政府。此等“守夜人”,莫如去之,這是無政府主義背后的左翼立場之濫觴。
從蒲魯東開始,無政府主義者內部出現了分化。蒲魯東本人雖也時常談論革命,但更傾向于通過建立工人之間和農民之間的合作經濟組織如工會和互助社來實現和平的社會變革。互助、利他、分權的觀點為歷代無政府主義者所分享。蒲魯東之后的巴枯寧在第一國際內部與馬克思兩股力量之間的論戰,最終導致了該組織的瓦解。兩派的根本沖突在于,馬克思認為工人應該奪取國家控制權進行革命,巴枯寧則走得更遠,認為工人應當通過革命摧毀國家及其他所有形式的政治權力。蒲魯東反對以暴力革命方式實現政治制度的驟然轉變,而巴枯寧則是“不破不立”的堅定信奉者。
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早期的內部爭斗,歸根結底也多是這種爭論的延續。列寧在《怎么辦》一文中強調了工人階級政黨領導地位的必要性。他使用大量比喻來分析作為先鋒隊的黨與作為普通群眾的工人之間的聯系。黨就像教師,可以將工人階級基于樸素的經濟不滿提升為革命的政治要求;黨就像軍隊中的指揮官,調動千軍萬馬排兵布陣。在處于嚴酷斗爭條件下的列寧看來,黨是嚴肅的,具有絕對權威。群眾的反抗是天然的政治可燃物,作為先鋒隊的黨的任務就是匯聚這些爆炸物,瞄定目標,精準引爆。
列寧對自發性的反對和集中權力的傾向招致了反對。德國社民黨領袖盧森堡將罷工與政治斗爭視為一個本身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的能動過程。罷工能夠給工人以新的經驗,從而改變他們的組合與領導的特性。每一次小規模的罷工都會迫使資本內部結構發生改變,日拱一卒地逐漸“拱”出一片田地來。因而,不能以一種急不可耐的躁進觀點,視緣起于經濟性質的罷工為水平低級,進而將操縱罷工視為一種權變戰術。革命是如何發動的,與是否發動革命同等重要。故而以強制力脅迫、領導工人階級,并將工人階級政黨凌駕于工人階級之上,施以森嚴的等級統治,非但是不現實的,也是非道德的。十月革命后,無政府主義政治運動的發展受到阻遏。它作為工人階級反抗運動最初思想來源的一支和重要同盟者,隨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控制國家機器而淡出。
西方不亮東方亮,新的戰場很快開辟出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把無政府主義作為拯救中國命運的社會主義思潮引入,一時在中國政治思想界大放異彩。列寧在《兩種烏托邦》中左右開弓,批評俄國的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國家的自由愈少,公開的階級斗爭愈弱,群眾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烏托邦通常也愈容易產生,而且保持的時間也愈長。”(《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297頁)這話對著的是沙皇時代的俄國,而在清末民初的中國似乎也“不遑多讓”——在被裹挾入世界歷史進程之后,內憂外患頻仍,危機接連不斷,傳統政治權威與價值體系的穩定性喪失殆盡。此種局面下,統治者仍對全社會保持著高壓態勢,一批激進學人最終倒向徹底否定一切權威的無政府主義,也就不難理解了。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蔡和森,都受到當時聲勢浩大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普遍對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發生興趣,這本書和克氏的另一部著作《面包與自由》中提出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對一批知識分子具有很大吸引力。以典型的階級分析角度看,很有一批有閑、有志、不安于現狀的知識分子,具有一定的階級革命性和社會正義感,急于改變國家面貌,艷羨轟轟烈烈、立竿見影的政治運動。從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全黨統一了思想,無政府主義也被從它的中國母體中切割出去。
無政府主義思潮在現代世界的“復活”,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始的一系列重大轉向有莫大的關系。政治方面,冷戰的大背景下,標志性的1968年由一場“五月風暴”點燃了多個國家的反抗運動;經濟方面,二戰后長達二十余年的快速增長和繁榮期行將結束,中東戰爭、石油暴漲、滯脹的并存,讓紅極一時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政策顏面掃地,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在這一時期相繼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本身就宣示著某個轉捩點的到來;精神文化方面,思想界在整個七十年代掀起了一股后現代主義的轉向,羅蒂、德里達、利奧塔、哈貝馬斯等人均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有相關論域的重量級論著問世,總的特征是解構主體性、質疑理性、鼓吹相對主義、反對基礎主義和還原主義、去中心化。凡此種種,各個領域既存“權威”的不穩定性和范式革命的歷史大勢,都為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在思想界的“復活”,創造了極合適的氣候條件。
經濟轉型、社會轉軌的歷史巨輪快速駛過之時,留下了紛繁復雜的各類社會問題的殘跡,弱勢群體的社會被剝奪感與階層斷裂的風險增大,這是早期相對激進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重返當下的社會基礎。據此,我們似可認為,無政府主義的重出江湖,是各掃門前雪、本國優先的國際大氣候和社會問題驅動下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民族主義的國內小氣候共同作用的結果。
斯科特明確地與三類無政府主義主張劃清界限。一是技術派。這些人是天真的科學主義者,他們相信理性和知識的進步將把人類超拔出現有的困境,物的管理會取代政治,政治世界的基本命題將被簡化為一場技術治理。由此,國家不再必要。在斯科特看來,這過于幼稚,物質豐富遠不會取消政治,只會把政治斗爭的領域向縱深拓展。二是自由派。他們認為國家無處不在且永遠是自由的敵人,斯科特舉了一個例子,美國民權運動期間發生了小石城事件,艾森豪威爾總統下令國民警衛隊護送黑人孩子上學——如果沒有國家機器的直接介入,天曉得事態最終會發展成什么樣子。更何況,并非只有國家可能會限制自由,早在國家出現之前,那些前現代叢林法則之下的戰爭和奴役、那些來自思想和觀念的自我審查和禁錮對自由的破壞,遠比現代國家的有形束縛多得多,這正是“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道理所在。三是市場派。準確地說,他們更接近于古典自由主義時代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信奉市場擁有“搞定”一切的偉力,對財產和地位的極端不平等具有極大的容忍度,甚至主動尋求這一狀態的達成。幾年前曾引發軒然大波的國內某廣告公司“年紀越大,越沒有人能原諒你的窮”的文案設計當屬此類,足見這種看似與時代格格不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實從未絕跡。而在斯科特看來,如果為了拒斥政府和廢除國家制度而回到一種“自愿賣身為奴”的野蠻圖景,那無疑是自甘墮落,背棄了無政府主義倡導互助以求平等的初衷。
那么,斯科特版本的無政府主義究竟意蘊為何呢?通讀這二十九篇“碎片”,我認為可以概括成三句話:無序未必真混亂,小資何嘗不英雄,人間正道是自然。
第一,無序未必真混亂。斯科特寫作的時間,距離英國的倫敦騷亂和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相當近,他顯然是草搖葉響知鹿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從這兩起事件中精準地預估到未來的社會反抗運動的新趨勢,即抗議行動不再刻意尋求組織化,而是訴諸平民動員,以非制度化的擾亂,設定社會議程,進而成功引發上層精英的關注,促發結構性變革。分散化、小規模、無領袖、不表達明確目的的行動策略,既幫助他們躲避來自政府的報復,也以一種極其難纏的方式把慣常隱藏于歷史深處的下層政治力量激活,這種看似無組織的行動卻是一種組織力超強的政治自覺和集體共謀。
在這個意義上說,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間發生的諸多社會現象,其實是有著精心算計的、粗中有細的集體行動。在斯科特的政治社會學譜系中,他也把這種不服從稱為“日常形式的抵抗”(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因此他主張人們有必要每隔一段時間就去反抗一些細小的、沒有道理的法律,比如在紅綠燈間隔顯然過長而又與實際路況完全不符的情況下,闖過去,以理性原則修正機械的規則。正如青年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的那篇檄文《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當一個國家絕大部分地區以柴火做飯取暖,而該國絕大部分林木歸私人所有,林木管理條例規定在森林撿拾柴火或采摘野果屬于盜竊行為,要受到刑事處罰。那么真正有罪的恐怕就不是普通民眾,而是法律和制度本身了。當平素隱匿于史冊、名不見經傳的老百姓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死,死國可乎”的時候,一定是社會病了,病得無藥可救。
這里就出現了一個深刻的悖論:基于常規組織化渠道的代議制度和議會政治,長于穩定而拙于變革。歷史上的若干重大變革發生前,反而總是伴隨著激烈的社會失序和騷動。美國大蕭條時期的《農業調整法》,是在猖獗的罷工、偷盜、抗租、叛亂的形勢下,緊急出臺的。由于沒有統一的訴求,沒有可談判的對象,找不出幕后的黑手,政府只能尋求快速變革以快刀斬亂麻地化解危機。馬丁·路德·金說:“暴動就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比他早近半個世紀,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那段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句更是空谷回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顯然,要避免真正長時期的混亂,只有居上位者始終戒慎恐懼、以自我革命的姿態反躬自省,來對抗一切集團一經組織化后不可避免會遭遇的官僚化、機械化、僵硬化危機。
第二,小資何嘗不英雄。在三體人的眼中,地球人就是一群蟲子。電影《普羅米修斯》中,人造人大衛打開裝有異形的“潘多拉魔盒”時,說的是“大物始于小”(Big things have small beginnings)。可是,視同蟲豸的地球人用權謀把三體人耍得團團轉,異形最終的破腹而出更是驚悚萬分。斯科特也在他的書中不止一次提到,微小粒子看似無序的“布朗運動”會造成意外后果:“微小的拒絕服從被復制幾千次后,足以徹底打亂將軍或國家元首制訂的大計劃……正如千萬毫無頭腦的珊瑚蟲能夠創造珊瑚礁,成千上萬的不服從、開小差也能夠制造經濟或者政治上的巨大礁石。”(《六論自發性》,34頁)小資產階級,就此由邊緣走到舞臺的中央。這是一個飽受爭議和誹謗的階級,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并非“自為”因而還沒有達成足夠自覺的階級,是一個具有軟弱性、兩面性、高不成、低不就的階級。不過,如果考慮到當今世界越發呈現一種政治上的龐大官僚體系和經濟上的巨大科層化管理體制的話,我們就會驀然發現爹不疼娘不愛的小資產階級的彌足珍貴。他們不是落魄的無產者,但他們是貧窮的資產階級,是“新窮人”。他們固然從未放棄躋身大資產階級的奢望,因而只能偶爾在自身被“踩到尾巴”的時候站在“雞蛋”一邊去對抗“石頭”,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更加激進的貧困階級之間顯然有相契之處,能夠相向而行。
小資產階級是有一點資產的。或是土地,或是其他,聊勝于無。但他們的小是petty而非small,這意味著小資之小,不僅規模可憐,而且境遇可悲,甚至氣質可鄙。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業者、小業主,勤勉勞作,富于匠人精神,他們以一種“自我盤剝”的方式進行原始積累。如果你有過農村調查的經歷,一定有這樣的感受,在農戶的成本收益計算中,自身的勞動投入是無足輕重、不計得失的,他們在談成本的時候會談到種子、農藥、化肥、農忙時的雇工,唯獨不在乎自身的勞動時間,似乎那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抑或是理所當然、不謀求剩余索取權的。小資產階級自我剝削,而地方當局也竭力驅逐這些居無定所、四處流動的小生產者,更偏愛農業綜合企業、合作社、產業園、國有背景的大公司,將“預算國家”的大網遍布天下,清除無法量化管理和納入財政軌道的一切非正規經濟。
小資產階級也是有一點自由的。他們大體能夠掌握自己的工作時間,并能夠脫離早期藍領工人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的全景敞視狀態。可是這種對工作時間的支配和對自主性的渴望,一旦遭遇“體面生活”水準的全線上升,就立即變得一文不值。于是我們會看到小資產階級總會受困于內心的各種焦慮而疲于奔命地跳入一個又一個人生的“陷阱”。
小資雖然如此脆弱,但是小資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誰讓小資產者夢想受挫,誰就點燃了革命的導火索,農民就要喊出“耕者有其田”,工人就要罷工維權。小資產階級在客觀上蘊藏著強烈的權利意識和驚人的激進革命動力,著有《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的觀點發人深省,他認為,人類的自由熱望不只存在于馬克思所指出的即將奪權的階級的希望之中,更在于那些即將被進步之巨浪拍碎的階級的慟哭之中。后者在驚恐慌亂中所激發的保護主義或保守主義的捍衛力量,同樣是一股“兔子急了也咬人”的可怕力量。
第三,人間正道是自然。道在屎溺,禮失求諸野,存在先于本質。每當政府在一種強烈的沖動下希望對底層自主性基礎上的自發秩序進行指導或干預時,都應當審慎地評估一下這種控制和改造有無必要、是否可行。先生孩子后起名,是常識;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常識;多樣互補的生態環境,是常識。而日常生活中的反常識行為比比皆是。為適應國家的系統性管控需要,摒棄那些帶有地方性色彩和默會知識的符號系統,根據標準化的規劃識別方式,建構一個獨一無二精準定位的道路命名體系。以科學的林業學清晰區分良木與雜草,把視覺秩序等同于工作章法,將自然生長視作無序低效。以經營效益為唯一指標,大規模種植單一經濟作物以追求規模效益,比如我在農村調查時親見的西瓜種植對地力破壞之大,以至于地租是糧食作物的三倍還多,一旦種過西瓜,往往要修整幾年方可恢復,因此西瓜種植戶必須“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走“掠奪式經營”的道路。近年來一些城市以追求市容整潔之名,先清理小店、再統一店招,終于建成人跡罕至、人氣皆無的睡城、鬼城,這樣的人造秩序,要之何用?
斯科特用一種福柯式的視角,尖刻批判了當下社會中隨處可見的規訓機制,并提醒人們一定要抵抗那種數目字管理和標準化裁剪,反對“標準對行為的殖民”,也就是以行政代替政治、將政治問題降維成技術問題。這樣的決策過程看似不偏不倚、不群不黨,一切問題都被通約和簡化為數字的量化比較,其結果卻會直接把我們從活生生的人間拽入了無生趣的機械地獄。斯科特頗為幽默地編造了一個耶魯版的“反五唯”(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故事,請允許我全文引用這段讓人捧腹的文字:
廣受引用、引領潮流的政治學教授哈維·“寫得多”正在給一屋子學生講課,突然,遙遠的亞利桑那州有一位不知名的學者在期刊《不明覺厲的近期研究》上發表一篇文章,引用了“寫得多”老師的成果,而且“寫得多”老師正好就差一次引用就能達到最高級的教職標準。只見他的電子屏立即閃起了藍白相間的光以報告這個好消息……學生們意識到事情的原委之后,紛紛起立鼓掌,祝賀教授晉升……現在他是終身教授了。(《六論自發性》,161-162頁)
經過一番有破有立、大開大闔的后現代式表達之后,斯科特的無政府主義觀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結論:歷史的行程并非人類理性的刻意為之,而更可能是臨時起意的自發行為的結果;看似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常常是無序抗爭的產物;人類自由的拓展增進,多來自自下而上打破傳統秩序的行動。那么,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我們應當抱持的最適姿態可能就是:let it be,let it go,敬畏民心,順應自然。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