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云研討|軍事體制與王朝運行④:火器時代的護甲與戰車
軍事史是中國歷史脈絡中的重要問題。故《孫子兵法》即開篇明義:“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宋元明清時期也是中國從多政權并立走向大一統,并且疆土空前拓展的時代。4月24日,由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宋元明清制度、文化傳承與融合研討班”主辦的第四場云端論壇通過“騰訊會議”召開。從研討班“增強宋元明清史領域中的跨朝代、跨學科交流”的初心出發,此次會議主題為“宋元明清:軍事體制與王朝運行”,圍繞宋元明清時段中軍事史前沿問題的研究展開報告與討論。
本文系第四場主題報告《清入關前的“綿甲軍”與“戰車”》的文字稿。
張建的報告以《清入關前的“綿甲軍”與“戰車”》為題,探討了明清戰爭中的科學技術問題。他認為我國綿甲始于宋元。16世紀中后期,近代火器傳入東亞,剽掠東南沿海、入侵朝鮮的倭寇裝備之“鐵砲”(輕型火繩槍/鳥銃)可輕易洞穿鐵甲,迫使明軍尋求護體之物,綿甲隨之流行。明軍的綿制衣甲包括用絲綿制成的綿被、綿甲,以及用棉花制成的綿甲。
明朝綿甲(左一)
女真武士至遲在天命三年(萬歷四十六年,1618)已經身著olbo(綿甲)參戰,但有組織地大規模使用綿甲,是在薩爾滸戰役后,包含兩種不同的形制:一是類似明軍穿著的兩臂過肩,長可及膝,寬大堅厚,可穿在鐵甲之外的綿甲;二是形如短褂,綴有甲釘的短甲。穿著綿甲上陣的兵丁被稱為olboi niyalma/olboi cooha,可譯為“綿甲軍”或“綿甲兵”。英明汗時期的綿甲軍主要由巴牙喇之外的固山兵丁(cooha/coohai niyalma)擔任,并非八固山正兵,只是每逢大戰,臨時穿著綿甲作戰的甲兵之名。

關于金軍“戰車”的起源,可追溯至薩爾滸戰役中的穵洪泊原野之戰,英明汗遭遇明軍車營組成的軍陣,被迫命令親隨下馬步戰,冒著重重彈雨推開戰車,始能突破防線。身經百戰,慧眼如炬的努爾哈齊經此一役,親身體會到戰車在野戰中保護陣線的價值,意識到金軍需要能夠掩護兵卒穿過槍林彈雨,挺進到營壘之下的兵器,方能奪取遼東的堅城,sejen kalka(戰車)遂應運而生。天命六年(天啟元年,1621),英明汗以綿甲軍推行戰車,充當全軍矛頭攻打沈陽,開啟金軍以戰車上陣的先河。金軍戰車分為三種,主力是載有高8尺(約256cm)、厚8寸(約25.6cm)挨牌的四輪戰車,以及車頭樹立厚5-6寸(約16-19.2cm)挨牌,牌頂設有垛口與射擊孔的雙輪車。
努爾哈齊之所以為金軍配備戰車,是汲取穵洪泊之役的經驗,針對明朝苦心經營的遼東防線,調整進攻戰術和技術裝備之舉。遼東明軍在寧遠戰役前奉行的戰區戰略(theater strategy)是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這套戰略的核心是圍繞一系列前沿要地精心構筑防御陣地,屯駐重兵,一俟敵軍來犯,各要塞固守之余,彼此出擊應援,使之腹背受敵,不支引去,以熊廷弼精心設計的遼東防線為例,明軍以奉集堡、虎皮驛為前哨,沈陽、遼陽為核心,彼此呼應。各要塞駐軍在戰役法(operation art)和戰術(tactics)層面的基本思路是協同夾擊和背城作戰,而非嬰城自守,冀望發揚火器優勢。譬如沈陽以城墻為核心設立3道防線,最外側是10道1人高的塹壕,壕內設有尖木,再向內是一條壕溝與兩道護城河,壕溝與護城河間設有防馬木柵,護城河經改建后寬5丈(約16m),深2丈(約6.4m),最內側是高2丈5尺(約8m)的城墻,墻下環布戰車1000輛,車輛間隙筑有矮墻。后金軍進攻時,明軍出城,依托車與墻構成的工事發射火器迎敵。遼陽等處駐軍聞知沈陽有警,可以迅速集結一支野戰兵團來援。因此,英明汗揮師攻城之前,先要做好在野戰中擊破守城明軍主力和援軍的預備,落實到戰術和技術(technology)層面,關鍵在于消弭雙方投射兵器在有效殺傷距離上的落差。
金軍以弓箭為主要投射兵器,女真弓是反曲復合弓(composite recurved bow),提倡以精煉重箭頭破甲,所用的鋒鏑長逾3寸(約10cm),材質精良,銳利無比。不過,金軍弓箭的有效殺傷距離短,僅30步(約46.8m)。明軍火器在射擊距離上遠勝金軍弓箭,大將軍炮射程達400步(約624m)以上;其次為佛郎機,射程300-350步(約468-546m);鳥銃為100步(約156m)之外。如果金軍拘泥于先前野戰大獲全勝的經驗,以鐵騎突擊沈陽、遼陽這種工事完備、火器眾多的堅城,從600米外沖鋒到距城墻40米,要經歷數輪密集彈雨的洗禮,卻毫無還手之力,無疑會傷亡慘重。
可是,金軍在沈陽、遼陽戰役一反鐵騎馳射的戰法,改用步、騎結合的戰術,以綿甲軍操作戰車當先進攻。綿甲軍裝備的主力戰車在寧遠之戰前,足以抵御明軍的大部分火器。明軍唯一能夠摧毀戰車的兵器便是大炮,但限于各種原因無法扭轉戰局。遼陽之戰,明軍憑借新鑄造的“呂宋大銅炮”一度遏制金軍戰車的鋒芒,但數量不足,且難以維持高頻次射擊,難以阻止金軍抵近營壘。
由于堅固的戰車足以抵御大部分明軍火器,綿甲軍身披的綿甲亦可抵擋鳥銃和箭矢的攻擊,事實上抵消了明軍引以為豪的火器優勢。金軍精銳弓箭手藏匿車上,靠綿甲軍推行,穿越重重障礙和明軍火器的優勢區域,直抵陣地前沿,以精準的射擊壓制明軍火力,殪斃將校,掩護綿甲軍摧毀工事,令其陣腳動搖,再投入精銳騎兵夾攻,使之土崩瓦解。金軍依靠此種戰術,橫掃沈陽、遼陽和廣寧,明朝懾于女真兵威,一度打算放棄山海關外各城。
天命八年(天啟三年,1623)英明汗改革兵制,設立“黑營”(sahaliyan ing)與“漢兵”(nikan i cooha)將火器普及全軍,并繼續完善綿甲軍的攻堅戰術。金軍經重編后,已是兼具步、騎、炮、輜的強大軍隊。可是,本次軍制改革的成果因金國內部愈演愈烈的民族矛盾而未竟全功。皇太極上臺后,皇太極在天聰五年(崇禎四年,1631)重建漢兵(nikan i cooha),配備綿甲、火器和戰車。從天聰七年(崇禎六年,1634)開始,綿甲軍成為漢兵的正兵。崇德二年(崇禎十一年,1638)重整烏真超哈后,olbo逐漸取代olboi niyalma/olboi cooha,成為綿甲軍之名,漢字寫作“敖爾布”“或鄂爾博”。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設立八旗漢軍火器營,每個漢軍佐領設有2名敖爾布,負責在鳥槍隊伍前扛抬鹿角木,掩護鳥槍手施展荷蘭式的排槍齊射(volley fire)戰術。這個兵種一直存在到清末,可謂與國同休。
然而,金國的戰車時代卻因為明軍的火力升級而迅速結束。天命十一年(天啟六年,1626)英明汗率軍西征寧遠。守軍配備12門紅夷大炮,其中11門是發射12磅(約5.44kg)實心彈的“半蛇銃”(demi-culverin),攻擊戰車、挨牌如摧枯拉朽。天啟七年至崇禎九年(1627-1636),關外明軍經歷兩輪軍事改革,使明軍換裝大批16世紀中后期至17世紀初歐洲軍隊的主力火器,包括“大蛇銃”(culverin)、“半蛇銃”(demi-culverin)、攻城炮(pedreros)與重火繩槍(musket),迫使金國戰車退出戰場。
另一方面,皇太極在遼東戰場的兩次決戰,即大凌河之戰和松錦會戰中,積極謀求新的克敵制勝之法。他在大凌河圍攻明朝援軍時,因明軍步兵陣腳不亂,以大炮、火箭射擊明軍。松錦決戰時,清軍完全依賴統帥精心謀劃、各兵種彼此配合,充分發揚騎兵在運動戰的優勢而獲勝,嗣后掃蕩松山、錦州、塔山和杏山各城時,則由炮兵作為攻堅矛頭。漢兵/烏真超哈屬下施放紅夷大炮的炮手與八旗的精銳騎兵是皇太極在決戰中賴以克敵制勝的鐵拳,徹底取代了綿甲軍和戰車的戰術地位。崇德元年十二月,清軍大舉進攻朝鮮,烏真超哈攜帶戰車渡過鴨綠水。這是清軍最后一次投入戰車作戰。清(金)軍的戰車時代就此落幕。

金國的“綿甲軍”和“戰車”戰術的成敗,為研究者重新認識東亞地區的“軍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提供了優良的觀察角度。16世紀中期,近代火器傳入明朝,是否引發軍事革命,從1618-1621年的遼東潰敗看,還存在疑問。努爾哈齊使用的綿甲和兩輪小車雖然是針對火器的裝備,但在16世紀的歐洲業已過時,用這些裝備對付火器的戰術仍然是舊時代的產物,卻在遼東大獲全勝。后金軍的一系列勝利堪稱17世紀初,世界范圍內會戰級別的戰役中,冷兵器軍隊戰勝火器軍隊的獨有戰例。不僅證實明軍火器的粗劣和落伍,火器手的訓練水平不足,也說明所謂16世紀中后期明代的“軍事革命”或“步兵戰術革命”其實是當代學者建構的命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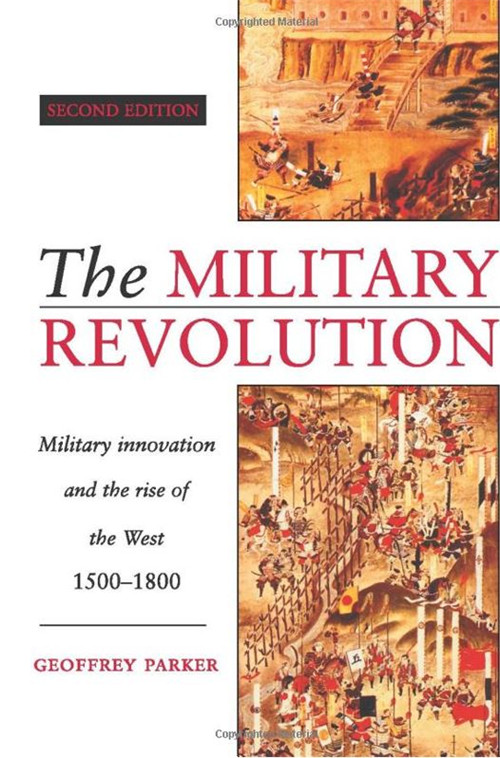
張建的報告因為脫離了傳統模式的軍事制度史研究藩籬,涉及了兵器學和科學史的問題,并介紹了大量有關的滿語詞匯,令人耳目一新,因此獲得了與會者的一致好評,普遍認為很精彩,大有收獲。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