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書城大家 | 趙園:歷史情境與現實關切
原刊于《書城》2020年5月號
袁:您這一輩學者大多有多線作戰、游動作戰的能力,您從中國現當代文學跳到明清之際,再折回當代史,這三塊研究領域看似不搭界,卻又有一以貫之的問題意識、研究路徑及材料取向。您是如何順利完成研究領域的大跨度切換的?
趙:你所說的路徑并非出于事先設計。三塊看起來互不關聯,事實卻不盡然。每一次轉場前,都為新園地的墾殖準備了條件。關于由中國現當代文學轉向明清之際,我已經在《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后記及《尋找入口》等文章中寫到,不再重復。那是一種基于個人情境與條件的選擇,不宜推廣。不斷嘗試著尋找出口與入 口,是年輕學人也不妨做的。
關于我的學術工作,史學工作者李夏恩有這樣的說法:“當她認為自己已經完成了某一個學術寫作后,她便會開啟自己頭腦中的忘卻機器,把曾經浩繁的檔案柜瞬間騰空,以便盛放新的學術研究的資料。”“趙園這種‘喜新厭舊’的善忘脾性讓人既欽羨不已,因為她可以如此輕易地出入不同的研究領域;也讓人嘆息不置,因為她竟然如此輕易將一個已然如此熟悉透徹的話題拋諸腦后,從此不再聞問。”(見氏撰《學者趙園:沒人喝彩,從不影響我的興致》,《新京報·書評周刊》2015年10月17日)其中有洞察,也有誤解。無意中讀到英國評論家杰夫·戴爾(Geoff Dyer)的話,像是與這種經驗有關,“人通過寫作擺脫了興趣;因某種興趣而寫作,寫作也將耗盡那種興趣”。至于我自己,盡管一再“清倉”,所有做過的題目,處理過的議題,相信都以某種形式在腦際甚至在生活中留下了痕跡。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趙園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我由自己的經驗,不認為對于學術研究,選題總是具有決定性的。能否做成,端在如何開發,有沒有基于特識獨見的材料。足以支撐你的判斷的有說服力的材料,可遇而不可求。有時候得之若有神助,那真的是稀有的機緣:由王夫之、錢謙益的說“戾氣”(《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到冒襄文集中的家族故事(《家人父子》)。當然,也要你能辨識、提取。王夫之、錢謙益的文集,都是被人翻爛了的,冒襄的文集也不屬于稀見書。新問題、新材料,似乎本應當問題在前,材料由問題照亮。事實有時不完全如此,即如材料誘發了思考,使問題得以形成。當然,上面所舉的例子,或許只是,你的問題還不那么明確罷了。
袁:記得您曾跟我說,好文章都是改出來的。對我來說,改文章比寫文章難得多,因為舍不得辛苦囤積的材料,舍不得靈光乍現的妙語,舍不得搖曳多姿的結構。讀您的文字,真為我這種對自己過于“仁慈”的初學者下一藥石。能否談談您的“刪”字訣,以及如何才能做到“題無剩義”?
趙:我的確對文稿一改再改。即使一篇隨筆,一節短文,也很少“一氣呵成”。這多半因了“拙”。修改也確實通常做減法:不止于刪繁就簡,而且刪落不必要的渲染、形容,可有可無的虛詞。少用虛字,是沈從文的經驗談。我也有這種癖。刪減或許不免于過。我自己也說過,芟夷枝葉,即不能得扶疏,卻仍然忍不住要刪——或許近于病態。文字的不豐腴,少余裕,多半也因此。這與我的生活狀態不無契合。在這一點上——只是在這一點上——“文如其人”對于我,還算適用。對于“度”的敏感與挑剔,與“潔癖”無關。也有相反的情況,像你那樣,對辛苦得來的材料不忍割舍,寧愿不避累贅,放在注釋中,無非敝帚自珍罷了。
選定一題,確也力求做到題無剩義。旁搜博采,由此及彼,像是一場不設終點的跋涉。窮究不已使得論題的外延不斷擴張,觸角盡其所能地伸展。即使如此,依然會限定范圍,不“橫斜逸出”,更不“橫溢”。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幾分把握,做幾分判斷。終于停下來,或許只是足力不支。前面說到的三塊,也是三個段落,每一段研究結束前都近于枯竭,要待另一段開啟,活力才被重新激活。我不厭重復地使用“題無剩義”的說法。“無剩義”只能“力求”。只不過有這種要求與沒有,結果不同。“極致”不必有“客觀標準”。目標可以不是所謂的學術水平,只是達至個人的極限。限制往往來自你自己:惰性,因循,固化,過早地定型。你的可能性或許至死也不曾被你發現。
袁:記得王汎森曾提醒說治文史之學要特別留心“從旁邊撞進來”的影響。學院內的專業訓練過于注重縱向的傳承,而忽略橫向的交互影響。直接線性的影響,來自你的學科、師門或當前從事的研究方向;而“從旁邊撞進來”的影響,可供選擇的資源是無限的。能否分享一下您專業之外的學術靈感來源。
趙:我的做中國現代文學,一向借力其他學科。閱讀書目中,大多是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論文論著,以至像是與我的題目全無關涉的文字。最少讀的,是自己所屬專業的著述。進入明清之際,材料的壓力太大,除正史、野史、文集外,更用心的,是前輩學者的典范之作,臺灣學者的相關著作。略有閑暇,仍然讀其他學科的文字,文學藝術評論,多方面尋求新鮮的刺激。關于文學藝術,更喜歡讀畫論,樂評,影評;其次是外國文學評論。當代文學評論則偏愛詩論,尤其詩人論詩。欣賞的更是文字,思理,并不因此看所評的畫作、影片,聽所評的音樂——更屬于知識興趣與文字喜好。
外語能力的缺失,是無可彌補的缺憾,失去了經由另一種語言、用另外的眼光看世界的可能,學術資源的受限倒在其次。這不便全歸因于“文革”,或許更是基因的缺陷。倘若不是“文革”中大面積的荒廢,恢復研究生考試時王瑤先生不至于不要求外語成績。考外語,我是否有機會從事學術,還真的難說。人生中的機遇,這也算得一個。不能直接讀外文原著,對國外學術的了解賴有譯介,是一弊卻也有一利,即不大容易受“潮流”影響——盡管仍然間接地受到了影響。
做學術,你的資源可以是中國傳統文化、古代文學,也可以是英語、西語文學,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舊稱“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等等。單一的資源難免構成限制,卻也可以是打開一扇門的把手。怕的是沒有所謂資源,只有普泛的知識和浮泛的閱讀經驗。
袁:在您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中,史學的品格壓過了文學氣息。在您看來,文學研究者的當行本色是什么,能從史學研究中獲得何種幫助,如何為現當代文學研究奠定更扎實的文獻基礎?
趙:進入明清之際,直接得益的,自然是史學。正史書法,受史學規范影響,至今仍然不免。我沒有條件比較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至于民國史學與當代史學,前者某些方面達到的水準,未見得被今人超越。尤其難以超越的,不如說是學人品質。
記得曾引用過謝國楨關于不取煊赫的說法。在史學著述中浸淫既久,更能適應史學方式,不大能欣賞“文藝腔”。《陳寅恪的最后20年》與《束星北檔案》,更能接受后者,覺得前者渲染稍過。會惋惜有些珍貴的資料,因文學筆法而價值受損,如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等。其中的材料倘若由楊奎松那樣的學者處理,著述的面貌會有不同。中國學術的傳統,文史不嚴于區分。也仍然有區分。史學注重材料的去取,文學更關注具體的人,人性,人的命運。二者間的平衡、互補,或許可以達成。
應對當代史研究的困局,不妨放開關于“材料”的固有認知。傳統意義上的史料又何嘗不可以質疑,即如正史、野史、筆記。有人說《明史》主要為有東林背景或持東林觀點者寫成。野史固然不免限于個人見聞、認知,筆記更往往以訛傳訛。
做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整理,自然不如修訂、校點古籍寂寞而難以見功。這個專業少的是投身其中而又樂在其中的鍥而不舍的專業精神。希望能培養年輕一代學人對于掌故的興趣,熟悉當代“故實”。有人推許朱正為當代“樸學”大家,怕的是朱后無人。中華書局徐俊編有《掌故》。“掌故”通常指有一定年頭的知識,因時間而成“故”。現代史、現代文學早已成“故”,問題是年輕學人是不是確有對所研究時段的知識興趣,耐得住寂寞,甘心下一點文獻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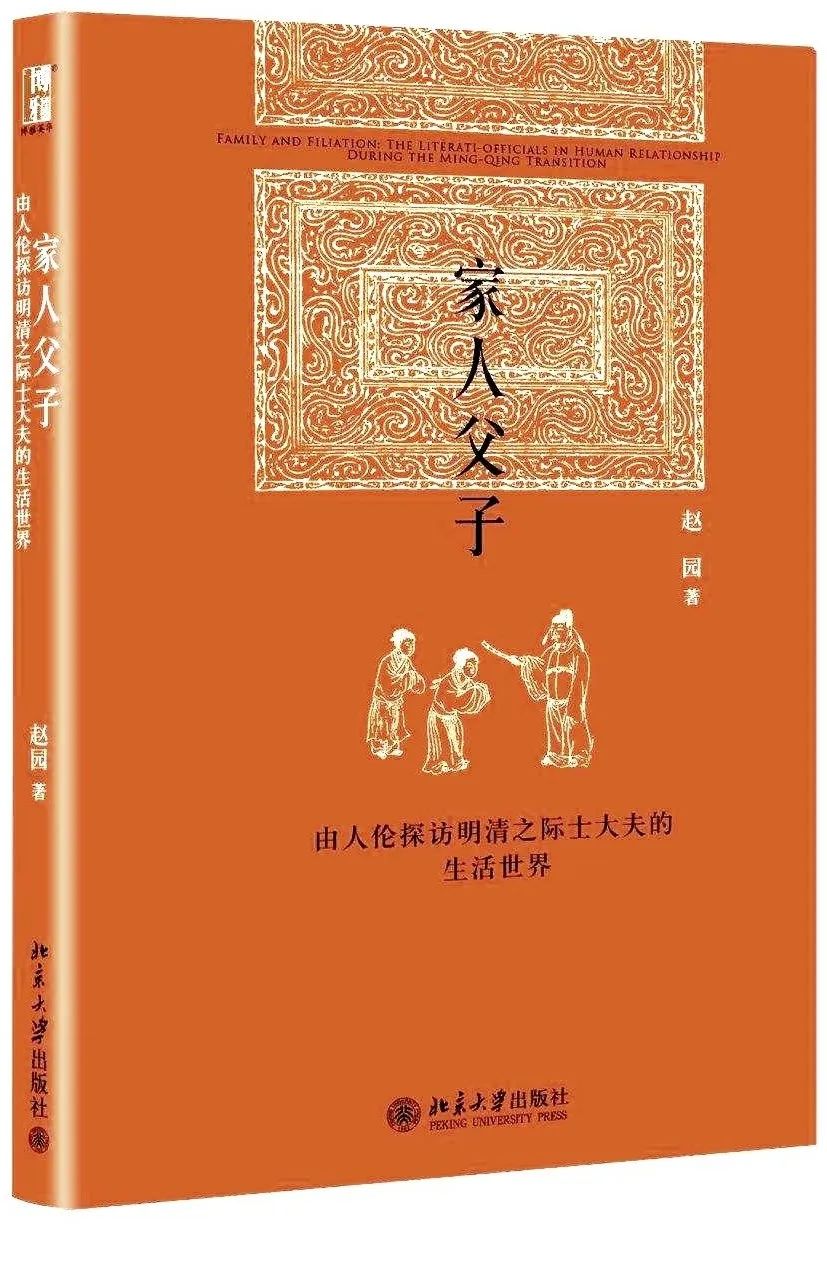
《家人父子》
趙園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袁:近些年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漸趨頻繁,大家都忙著開會,為開會而趕論文,包括我自己。過于頻繁的學術交流,打亂了正常的研究節奏,制造出許多學術泡沫。當對話壓倒獨語,必然導致人文學的同質化、圈子化。學術交流與外部認可在您的學術生涯中起到怎樣的作用?
趙:我的朋友圈子與學術關系不大,學術也從來不是交流的主要內容。進入明清之際,學術交流主要與臺灣地區學者,得到的同行的肯定、鼓勵,也主要來自臺灣學界。這多少有點微妙。但對我幾乎毫無刺激。我早已習于獨處、獨語,“無人喝彩,從不影響我的興致”。
與境外學者的交流,障礙除語言(這里是泛指,包括學術用語)外,還在身份。近幾十年來,博士學位、高級職稱的授予,因極濫而不被看重,境外仍然會以有沒有博士學位作為辨識的重要參照。當年以副研究員訪日及在香港訪學,就領教了與身份有關的或隱蔽或毫不掩飾的輕視。盡管不足以打擊我的自信,終歸是令人不快的經歷。這也更使我對臺灣地區的學術機構、同行懷有感激。他們對你中文著述的質量的認可,不賴有你的學位,也不一味強調“國際學界”通用的范式、理論模型,至少看起來對于你有沒有博士學位、有沒有歐美名校留學背景不那么在意,即使你的學術研究還不曾獲得歐美學界認可,甚至用餐時不會使用刀叉。
我的確不大相信歐美學者會認可我的研究。學術方法,概念、術語,尤其背后的歷史情境、現實關切,是一面難以穿透的墻。所幸像我已經說到的,我的學術寫作不大有“目標讀者”,也就無需費心地尋找公約數,因遷就、迎合而難以盡意。我在職期間幾次訪臺與一兩次訪港,幾無境外的學術交流。不全是沒有機會,也考慮到有沒有“交流”的可能。
受訪的機會不多,主要因為我缺乏對話的意愿。遇到的最善于提問者,是當年《上海書評》的編輯張明揚。問題簡潔直接,環環相扣,使你無可逃遁。這種有挑戰性的提問太少見。較多的提問,有表彰的意圖。也偶有奇葩的提問,似乎意在借機自我展演,且成見在前。僅由這樣的訪談也可以感知知識社群內部的相互擠壓,如何惡化著知識界的生態。
袁:我們正處在一個突飛猛進的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極大地縮短了我們占有材料的時間,擴大了我們搜討文獻的范圍,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特定館藏地對材料的壟斷。但人文研究的主體始終是“人”,是人對人的理解與關照。不知您是如何回應數字技術對人文學的挑戰,是否因此改變您的工作習慣?
趙:我對于高科技、數字化利用有限。除了用電腦“碼”字,偶爾“百度一下”,在網上收發郵件,瀏覽別人發來的與時政有關的文字,也是“老派”的作風。讀紙質書,用鉛筆在打印紙背面寫筆記,一條材料一條材料地在鍵盤上敲下去。方法很笨,卻不以為苦。手寫,再輸入電腦,或許有助于使表述不致為計算機所規范(即如現成的字庫、詞庫)。
某位影星因不知“知網”被撻伐,被懷疑為學術造假。我的探訪明清之際,使用的是單位圖書館的線裝書與校點本;偶爾去文津街的國家圖書館。至今不知如何上“知網”“萬方”等,在年輕人,是不是不可思議?前數字化時期,每周的返所日,都要在文學所塵封的卡片庫中翻尋。能將明版的線裝書提回家,今天已成奢望。你對歷史的觸感,誰說與如此地親近那些當年的紙張書頁無關?到了今天,過分依賴搜索引擎的弊病似乎已顯現出來。最難被科技手段取代的,應當是我在《論學雜談》中說到的文字感覺與對材料的感覺。這種感覺半系于稟賦,半得自閱讀、寫作的訓練。相信細讀與深描,即使到了更高科技的時代也無可替代。學術工作與其說是一種技術,不如說更是一種狀態。在變化了的社會生活節奏與文化氛圍中,某種境界盡管漸趨古老,卻不失其優雅與尊嚴的吧。
二〇一三年退休,恰當其時。當著學術界的生態、學人的工作方式被一整套學術評價體系也被科技手段改變之時,你用不著勉力調整,大可繼續做近于工匠的“老派學人”。在被新的學術風尚拋棄之前及時退場,維持了工作方式、寫作風格的連續性,誰說不是好運!對于所從事的專業“業態”的未來變化,我沒有預見能力。危機感應當是年輕一代的。我們已無須應對迫在眉睫的威脅。由這一點看,夾在劇變時代的過渡期,前輩學者的背影尚可以瞥見,與年輕世代間的代溝還沒有成形,避免了做非此即彼的選擇,也應當是幸運的吧。
袁:想聽您談談對學術工作中性別問題的看法。我覺得刻意強調女性學者如何如何,是無謂的偏見,同時這些年也慢慢意識到性別造成的隱形歧視確實存在,你無視它,它未必遠離你。所幸我接觸到的一些女學者,都以各自的方式回擊了固有的性別成見。女學者的標簽未必對您造成困擾,但對您來說,性別位置是否對應著一種特殊的觀察視角與言說姿態?
趙:我也曾經反感于與性別有關的界定,如女學者、女作家等稱謂。后來想,用不著反應過激。強調性別/身份,本來就可以由不同的方向讀解。我成長的年代,不強調性別/身份,主流意識形態對男女平等的論述,無助于培養性別意識。那個年代我們稱道一個人的文字,會說“筆力雄健”,無論男女。剛健/陰柔二分寓有褒貶(至今“陰柔”仍然有負面意義)。因了時風眾勢也出于個人取向,我偏愛剛健,如宋詞的“豪放”一派。偏好或許暗中塑造了我的文風。到有機會一再訪臺,有感觸的,就有臺灣女性學人的溫婉,由她們的名字、情態到語音(臺式“國語”,大陸有人形容為“軟萌”)、言說方式。對比之下,我自己也感到確實少了蘊藉含蓄的女性之美。
“天花板”的說法,姑且借用來指自身的極限,而非職場為特定人群設置的所謂“玻璃天花板”。即使自我期許不高,仍然會嘗試著頂一頂那天花板,冀望其略有上升。應當承認,社會對文學創作、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的性別歧視不那么明顯,高校、科研院所甚至因女性的大量涌入而出現了性別失衡,尤其文學專業。我不認為這是什么好消息,或許也由于我不大持性別立場,從來不曾自居女性主義者。我自己治學之始,學界還幾乎是男性獨霸的世界。近些年陰盛陽衰,是否會影響學術風氣,即如多了一層女性的陰柔?我據自己的經驗,較能體會女性與性別有關的弱點,如思辨能力的薄弱。當然有例外。只是我自己不屬于例外。我羨慕少數理論訓練超強的女性,卻也對學術研究中的“理論導向”持警戒態度。我發現理論能力超強者有可能滿足于理論框架中的操作,自得于嫻熟地操弄理論工具而“傲視群雄”。
年輕的時候就有理論興趣,卻不能將理論作為“體系”把握,總是將系統的理論讀成了碎片——本科的時候讀馬恩兩卷集就是如此,至今也沒有長進。自己不消說不能建立任何成“體系”的東西,即使有貢獻,也只能是零碎的、片段的。思想能力薄弱,也就少有“原創”;用已經提到過的黃侃的說法,“發見”多于“發明”。“發明”靠才氣、稟賦,“發見”(主要是對材料)可以憑借功夫。矛盾的是,一面明白自己的缺陷,一面對貌似“整全”的論述懷了狐疑。一二三四,條分縷析,怕的是設計周嚴的框架掩蓋了膚淺平庸。
袁:黃宗羲謂“師道多端,向背攸分”,您在《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中列專章討論“師道與師門”,應對這一話題深有體會。此前讀您寫的《王瑤先生雜憶》,筆調甚微妙,寫王先生對弟子的嚴苛與溺愛,寫他的世故與天真—有盔甲,但也有丟盔棄甲的時刻。您筆下的王先生,比學科史上的王瑤,復雜得多。能否談談師門對您究竟意味著什么?
趙:師門在我,是個不容易說清楚的話題。王瑤先生與故交趙儷生,均屬于涉世既深而又狂狷者。趙先生較王先生或許更有才情也更刻薄。身為門弟子,慚愧不曾多讀王先生的著述。在明清之際徜徉了一些年后,才翻出他最博好評的《中古文學史論》,竟然讀不下去。知道自己的口味已極其挑剔。有人臆測我受到了這本書的影響,想當然耳。如實地說,雖在王先生門下,那時的先生已然衰老,在他那里聽到的多半是閑談。但偶爾的點撥,背后是他一生的治學所得,足以令我終生受用。即便如此也應當說,讀研期間,得之于雜覽的遠多于師授。也因此常常對年輕人現身說法,說優秀的學術作品是最好的老師。當然,何為“最好的學術作品”,固然有公論,也賴有各自的品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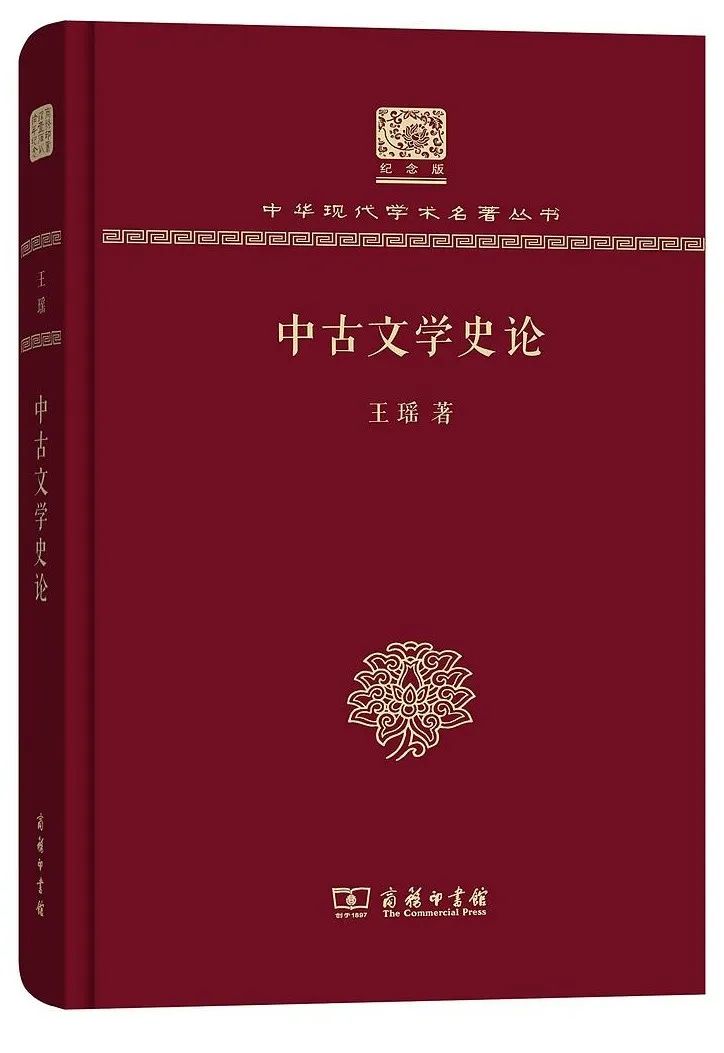
《中古文學史論》
王瑤著
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
王先生對我,曾有過“嚴苛”,也有“溺愛”,尤其我由北大畢業后。我曾經想,如若王先生讀到我后來所寫關于明清之際的文字,會感到欣慰的吧。在我看來,盡管王先生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與李何林先生均為開山老祖,“內心深處”系念的,仍然是古代文學。
盡管有師從,有這種意義上的師門,卻沒有門派。同門間異大于同。我厭惡類似教主與信徒、宗主與宗派、學派領袖與追隨者那樣的關系。相信學術是個人事業。師門對于我,意味著值得追憶和回味的三年讀研經歷,意味著交往至今的摯友。這也是當初決心考研的最大收獲。
袁:前段時間在網上看到陳寅恪寫給上海編輯所負責人的一封信,對約稿合同中的“霸王條款”逐一駁回。一位編輯感嘆,如此硬氣、碾壓型的乙方實屬罕見。我隱隱感覺編輯的自我定位與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能否簡單談談與您合作過的幾位編輯,他們的工作方式、職業素養及與作者的關系如何?
趙:我一向將編輯視為合作者,感謝的意思一再寫到,尤其曾發現硬傷的編輯(及評論者)。由學術工作起步,就備受呵護。我曾寫到《艱難的選擇》出版期間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高國平、張遼民二位,寫到過北大出版社經手我的著作的責編張鳳珠、艾英女士。近期則有從未謀面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林道群先生。
無論高國平還是張遼民,都嚴守編輯的職業倫理,處理書稿一絲不茍,卻不發展與作者的個人關系。我與他們沒有私交。這或許也可歸為海上文化:嚴于人我分際。我對此持欣賞態度。至今記得已故高國平先生的那些短函。那個時候沒有網絡,高、張二位與我書信往來,不厭其煩,回頭看去,已近于古風。
處理我的書稿最多的,仍然是張鳳珠、艾英兩位。兩位都不是治舊學出身。我雖然不過“客串”,對書稿的校對卻不無挑剔,一再近乎無理地向她們索要已經處理的校樣,對改動之處一一斟酌,有的徑自改回,并注明理由。她們從來不以為冒犯。這正是“合作者”的態度:共同完成一項事業。我珍視與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合作。盡管其間有不止一家出版機構表示過出版意向,不為所動。
還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王培元,作為編輯堪稱優秀,本人也是出色的現代文學研究者。《文學評論》的王信則是另一種風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學評論》,打上了王信的個人印記。那也是改革開放后學術文化發展的盛期。《文學評論》等一批刊物,以發現“新生力量”、推進學科建設為己任。當年的學術編輯,作風嚴謹而頭腦不冬烘,王信堪稱代表。為來稿逐條核對引文,現在的年輕編輯肯下這種功夫的恐怕不多,為人作嫁,已非所愿。處理來稿,有關系有背景者優先,早已成風氣。即使如此,我還是要說,王信的退休恰當其時。這樣說考慮到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之交學術轉型,理論范式發生了重大變動,而王信(以及他的摯友樊駿)的衡文,仍然不免受五六十年代風氣的影響。正直是王信的標記。樊駿正直而近乎迂,王信則正直而執拗,都屬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優秀人物將他們的品質保存完好者,適應八十年代的學術環境還不難——那畢竟是有承有啟的年代;對此后變化了的學術風氣中的論文論著說“看不懂”,也出于一貫的誠實。當年得到過他們獎掖者,不能忘懷他們的古道古風,較之衡文,不如說更敬重其為人。
也曾遇到過知識水平甚低者,直接將《莊子》的《人間世》改為《人世間》。這樣的編輯將為作者改稿視為當然,編輯的職分所在。老舍曾說“改我一字,天誅地滅”,不便讀作玩笑。那可能更出于對擅改別人文字的嫌惡。尊重作者的表達方式,與其說基于編輯的職業倫理,不如說是一種教養。所幸一生遇到的編輯,尊重作者的居多。我不知道別人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幸運。
袁:錢穆說做學問的目的,在教人達于盡性盡才、天人兼盡之境。盡性盡才的前提是知道自己性之所近、才之長短。錢牧齋評袁小修文云:“小修有多才之患。”而小修亦復自云:“發揮有余,陶煉不足。”袁小修知病犯病,可謂“好文章我自為之”。“才華橫溢”或許是文士之幸,卻未必是學者之幸。據您個人的治學甘苦,如何才能逼近“盡性盡才,天人兼盡”之境。
趙:我真的不知道有這種說法,也就不曾懸為目標。我只是據自己的經驗,以為較之“創作”,學術更賴有積累,聚沙集腋,下笨功夫。我自知屬于中材;說自己素乏捷才,孜孜矻矻,絕對不是故作謙抑。學術是一份適于像我這樣較“鈍”的人從事的職業。顧炎武警戒潘耒“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這里的“末流”在明清易代之際當然有特指;但“中材涉末流”的警示對我仍然適用。以勤補拙在我,不是說辭。前面已經說過對文章一改再改,這里還要說,不能想象沒有點點滴滴、字字句句、片片段段的日積月累,能寫出任何可以看得過去的東西。已經面世的文字,無不賴有拼綴而成。間歇地,有短暫的“泉涌”“井噴”。更日常的,是“碼”字。將隨時想到的記在紙上,再用鍵盤“碼”在電腦上,反復修訂,直至發送出去,印成鉛字。
“鈍”也可以成為一種優勢:不茍做,不輕下筆,耐心地積累。能藏拙,可免于揚才露己。“才”本是造物所賜。造物從來吝于這種賜予。做學術,最不可恃的,是聰明,尤其小聰明。小聰明最經不起時間的銷蝕。我自己做學術的過程中偶爾像是有靈感來襲,寫得快意,似乎揮灑自如。回頭檢視,或許一無可取。至于時、運的湊泊,更是太難太難。
幾十年做學術,說不上高產低產。無論有怎樣的突發狀況,都盡可能依著自己的節奏寫作。我不“規劃”自己的人生,卻會有近期、中長期的小計劃,以便對自己的強制。一旦啟動,即不放棄。一九七八年進入專業之后,很少有機會將腦子騰空,享受一種單純的快樂。即使在行旅中,也會將偶爾所得記在隨身攜帶的本子上。卻又并不像別人想象的那樣惜時如金。縱然有預定的題目,也仍然會隨時分心關注與題目無關的信息,時政,社會新聞,“學術動態”,出版信息,影視評論,等等。與世界保持多維度的聯系,是習慣,也是生存的需要。自己的世界太狹小,有必要借助各種渠道,打破把我困在其中的墻。閱讀選擇卻一貫地挑剔。毫無阻力的閱讀是不可忍受的。對陌生的概念、知識的饑渴也始終維持,甚至腦補網絡熱詞,即使明知這些詞不會有多么長的壽命。
天道并非總是酬勤。選擇至關重要:基于對自己的可能性、潛能、極限的認知。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倘若有“未盡才”,往往系于外部環境、條件。八十年代之后,即使仍然有外在的限制,才未能盡卻更由于選擇中的盲點誤區。由旁觀者的角度,我會為熟悉的朋友惋惜。依資質而言,他們中有的人的確有未盡之才,所成就者本應當不限于此。
袁:從您的文字及與您的交往中,能感到一種清醒的“限度”意識,包括情緒的限度、概念的限度、一代人的限度、人我的邊界。但這種“限度”意識的背后,卻是您對學術境界、立身原則及內在體驗的極致追求。探究盡頭,是試圖超越此時此地此身的努力,倘若不是以世俗名利為驅動力,又是靠什么來支撐這場無休止的孤獨跋涉?魯迅借過客之口,說:“我只得走,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對您而言,催促您、召喚您往前走的聲音來自哪里?
趙:我的確有你所說的“限度”意識。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學術和寫作不曾遭遇過大的挫折,也由于對自己限度的清醒。別人以為的內斂,或許更因原本就較為向內,關注更在自我提升。突破了一點思維的障壁,找到一種貼切的表述,都是一樂。這種滿足無須與別人分享。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我的為己,自然與圣賢所言不同。
我習慣的,是“物來順應”的被動狀態。讀書寫作是生活方式,是此生適于我的生活方式,沒有對于其他什么的承諾。即使臨近了終點,也不會“與死神賽跑”,為了一項寫作而“燃燒生命”。即使不能為自己而活,也不想為他人為某種目標而活。平日里告誡小友的,是不必為學術犧牲什么,更無論“獻身”。我受不了那種夸張的悲情。盡管如此,仍然把大段的生命消耗到了學術/寫作上。莊禪關于文字之為“障”的思路極其智慧,只是終于不能徹底。說出來的不是禪。真的徹底了,就連“無言”也不必說,更不以文字行世。所謂的淡泊名利,不為“名韁利鎖”所困足矣,再多說就難免虛偽。情欲關系活力。無欲無求,去死也就不遠了。
至于不為讀書界的偏好而改變寫作方式,并非有意“高冷”,不如說出于習慣性的節制。一種書寫方式如若還有價值,就一定會為自己吸引甚至培養讀者——盡管這樣說或許被認為自負。一個鄭重的作者,其書寫方式是在生命過程中形成的,浸染了生命季候流轉的消息。如實地保存這些,或許才更是你之為你。任何為了迎合的設計、修飾都屬多余或徒勞。年輕的時候也曾有過文人夢。未必沒有想到出名要早。從事學術后心態已經大為不同。自己最初的學術作品印成了鉛字,不記得有過狂喜。出版的書到了手中,甚至會懶得打開,自己也對自己的漠然感到不解。早年的那種誘惑早已不再,“低調”也就無須努力。窮大半生的氣力做一件事,尚且做得破綻、漏洞百出,“硬傷”累累,哪里敢有大志向。“學不博,專不透”,啟功先生用以自嘲,其實對于我輩更適用。“博”,今生已不可能,即使拼命補課——何況并沒有必要。專,略有一點,對自己討論的問題還有一點發言權。斂抑收束,也因了一點自知之明吧。
不曾暴得大名,多少免去了名之為累。沒有讀網文的習慣,外界的毀譽也就隔在了門外。我知道自己的學術作品有受眾圈子,主要在專業人士、研究生中。不同于明星、公眾人物的有粉絲圈(“飯圈”),不必擔心“掉粉”。壓力從來更來自自己,而非外部。這種半隱逸的狀態,是職業對我的特殊賜予。不悔少作。未收入文集的文字,除少數幾篇外,只是因為沒有價值,無須災梨禍棗。不關心能否傳世:身后的事情與我何干?我們的文字禁得住時間者絕少。速朽是自然而然的。朽前曾多少使年輕學人獲益,朽后則肥沃了學術土壤。本來就是先天不足的一代,有這一點貢獻大可感到安慰了。
一邊寫作,一邊回望、自審;邊前行,邊檢視,省思,隨手記下千慮之一得。這種伴隨著反思的寫作成了我的習慣,或許也“極便后學”。我的確曾以此為年輕的學人說法,只是對方未必聽得進去,即使認可也未見得有意“踐行”。這是一個日益功利的時代,學術工作適用的是“投入-產出”的經濟效益的考量。
你看,說了這么多,也沒有回答你,那個催促、召喚往前走的聲音來自哪里。看來還得凝神聽一下,有沒有那個聲音。
袁:對純粹的學人而言,學術即人生。《艱難的選擇》扉頁上有段題詞:“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認識這個世界,同時在對象世界中體驗自我的生命。”把學術研究作為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一種方式,或許是許多人走上學術之路的初衷,但慢慢會忘記這一初衷,被學術體制所馴化。求真的學術是一道窄門,一條逼仄的小徑,回顧最初選擇的那道窄門,能否談談您在這條逼仄的小徑上體驗到的學術人生。
趙:我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經寫過一篇隨筆《學術——人生》,這種漫無邊際的題目,后來就不敢做了,今天更不知從何寫起。起步晚,不能不敏感于生理、思維能力的諸種變化。據我的經驗,你每一段時間都有那段時間的最大可能,問題在你是不是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機會。黃子平曾經說過“自己寫不過自己”,對我很適用。最終,是必然會到來的全面衰退。《論小說十家》之后不再有細膩的文字感覺;寫《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續編,不能回到寫正編的狀態;寫完了《想象與敘述》難以有旁搜博采的鋪張;考察當代史的后兩年,漸漸疲憊、麻木,不能如前那般“傾情投入”。看一些年前的隨筆,會驚訝何以有這樣的文字。你經歷的,是能量耗散的過程,情況正與年輕時相反。

《艱難的選擇》
趙園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回頭看,學術仍然是你最有可能自我掌控的職業。不直接面對受眾,是我所體驗的以學術為業的一大好處。你不必關心你的論文的引用率、點擊率,你著作的印數、賣相、銷量。不必像手工業者那樣要想到買主;不像競技體育那樣備戰數年卻只有一次證明自己的機會;不像舞臺劇演員依賴于現場的反饋;不像公司一類“職場”那樣競爭上崗,有隨時被炒的危險。你可以心無旁騖,面對你的題目,將一篇論文一部論著一天天做下去。盡管幾十年來,幾乎像一架寫作機器,滿負荷運轉,將別人用于休閑的時間也搭了進去。但自由、自愿與非自由、非自愿仍然不同。自由,也因為不曾感受來自“流行”的壓力。用自己的方式做,不關心最新趨勢、最熱門的理論。不以為必得“預流”;在潮起潮落的年代,“不入流”或許倒成了一種特色。這種狀態于我相宜。你可以慢工打磨,在自己擬定的方向上一點點掘進。偶爾欣欣然于意外所得,享有一份私有的快樂。既然不總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下,“淡出”也就毫不費力,順理成章,正像一個農夫或匠人因老因病放下手中的活計。如若有來生,或許可以換一種專業,即如在某地某處博物館做專業人員,工作內容相對更單純。我會想象自己每晚下班,走在入夜的城市街道,在臨河或臨海的酒店或咖啡館外小坐,看遙遠天際燈火明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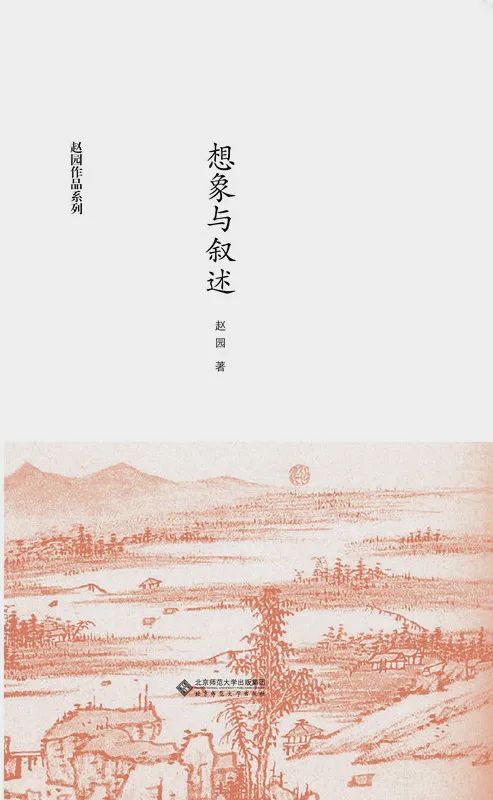
《想象與敘述》
趙園著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進入明清之際,分身乏術,有不得已的放棄。放棄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閱讀,放棄了跟讀輸入的外國文學、人文社會科學著作。此生錯過的自然遠不止此。比如錯過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流行音樂在大陸興起的那一時期,錯過了先鋒藝術在大陸的勃興,錯過了大量優秀的影視作品。錯過就是錯過,不可能找補,只能寄希望于來生。
袁:不管外在氣候如何變化,身邊還有幾位可信賴的前輩仍在嚴肅地思考、寫作,就會讓后來者覺得前面仿佛若有光。能否給那些尚在尋路的青年人幾句贈言,讓他們守住心里的微焰。
趙:為應對偶爾演講后青年學子題字的要求,曾經選了三條“語錄”備用:“致廣大,盡精微”(《中庸》),“以廣大之心裁物制事”(顧炎武),“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魯迅)。這的確是我喜愛的幾句,盡管沒有銘諸座右。在剩余的日子里,仍然會以此自期,或許也可以與年輕的學人共勉。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