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348年黑死病期間,薄伽丘的花園故事
羅伯特?哈里森 三聯書店三聯書情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薄伽丘絕非一位道德說教家。他并不特別關注人性的本惡或人類獲得救贖的前景。如果說他在前言里為《十日談》確立的道德目標終究是極為平常的,那是因為人之為人本來就是件平平常常的事。那場瘟疫也證實了這一點。做人意味著無法免遭不幸與災難,意味著時而感到自己需要援助、慰藉、消遣或啟迪。這種援助有著許多平平常常的形式,尤其是借助風趣的談吐、得體的舉止、故事的魅力,通過謙恭禮讓、對話交流、同伴之情和社交生活促使人類交往的領域更加愉快。給生活增添快樂而不是增加痛苦,這就是薄伽丘人文主義的首要原則。
那群年輕人從一個瘟疫橫行、道德淪喪的佛羅倫薩一時逃脫,并沒有對所謂“現實”產生任何直接影響。在臨界地帶的園林佳境里度過兩周后,故事的十位講述者又回到了一度置于身后的慘象之中。然而與此同時,《十日談》里的故事,如同為講故事提供環境的花園,畢竟還是干預了現實,哪怕此舉僅僅在于見證形式的幻化之力。一個個故事用各種敘事形態重塑了現實,讓原本被現實那無形無度的流程所遮掩的事物得以有形有致地顯現于世,宛如花園將目光引至園中景物之間的審美聯系。這是花園與故事兼有的幻術:它們幻化了現實,盡管看上去未曾給后者帶來絲毫改觀。
*文章節選自《花園:談人之為人》([美]羅伯特?波格?哈里森 著 三聯書店2020-1)。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John William Waterhouse
薄伽丘的花園故事(節選)
文 | [美]羅伯特?哈里森
人類文化起源于故事,人類文化的歷史從不間斷地講述著故事。我們能否想象人間沒有故事?沒有講故事的藝術?沒有故事來組織事件,給時間設立結構?假如你問我家在何方,昨晚的聚會上發生了什么,我的朋友為何心煩意亂,要回答你的問題,我多半得給你講個小故事。不論形式正規與否,講故事是人際交往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生活被編入故事,故事又編織成了生活,所以說交談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對敘事藝術的掌握。不讓這門藝術日復一日地作用于我們的人際關系,實為一樁憾事。
說得不錯,你答道,可是講故事同花園有什么關系呢?這個問題我們該去問西方文學史上最杰出的故事作家——《十日談》的作者喬瓦尼·薄伽丘。除了《十日談》,他還著有大量品質毫不次要的所謂次要作品。
薄伽丘的《十日談》(1350年)以極為雅致的、非教條的方式體現了真正的近代式伊壁鳩魯主義。據該書引言所述,在1348年的黑死病高峰期間,七位女郎和三個小伙子決定離開備遭瘟疫蹂躪的佛羅倫薩,退隱到周圍山間的別墅里;在那兒,他們打算以交談、漫步、跳舞、講故事、取樂等方式度過兩星期,同時恪守行為規范,不讓女士們的尊嚴受損。與瘟疫肆虐的佛羅倫薩的慘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莫過于等待他們的田園詩般的鄉間園林(《十日談》里的故事大都是由這十位年輕人在一處處園林中講述的)。在城里,市政秩序已淪為混亂無序,鄰里之愛已轉為鄰里之懼(鄰人如今代表傳染的威脅),親情的天然法則已讓位于人人為己的準則(許多人撇下患病的親人逃之夭夭,讓后者孤立無援地面對臨終的苦痛),原先謙恭禮讓、溫文爾雅的地方如今罪惡猖獗、神志癲狂。

這群青年男女表示,他們的目標是把怡人的田園景致帶給他們的快樂(piacere)增至最大限度。我們已經注意到,伊壁鳩魯式的享樂主義遠非解除自律或滿足欲望,而是一種需經培養方能形成的生活方式;有如一個花園,它的繁榮離不開秩序和規矩。“第一日”的“女王”潘比妮婭的話證實了這一點,出行后頭一天,她對同伴們這么說:“讓我們盡量歡樂吧——因為我們從苦難中逃出來,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呀。不過凡百樣事要是缺了明確的形式,就不會長久。”(薄伽丘,《十日談》,第25頁)接著,她把秩序和快樂這兩個概念聯系了起來:她希望“大伙兒愿意在一起多久,就會過多久秩序井然、快快樂樂、沒有恥辱的生活”。
在潘比妮婭的倡議下,這群青年人給他們愉快的活動設立了一個井井有條的結構。每天都有一位成員充當當日的“國王”或“女王”,負責作出用餐、午休、散步、唱歌、過安息日等方面的安排。最重要的是,國王或女王需指定當天故事的主題。根據計劃,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鄉居期間,大家總共講一百個故事。由于逗留時間恰為兩周,每周各有兩天因為過安息日的緣故不講故事,所以講故事的天數共計十天(《十日談》由此得名)。就這樣,大家給這兩星期的生活注入了一個“明確的形式”,這一秩序不僅確保了他們鄉居期間的快樂,而且為《十日談》一書的藝術構造奠定了基礎。
欲使快樂之感社會化,關鍵在于給它注入形式;欲使快樂之感持續穩定,關鍵在于讓它社會化。這一社會化過程馴化了無拘無束、自我中心的個人沖動,但并不要求人們壓制或舍棄自己的欲念(《十日談》里的故事大都與禁欲原則格格不入);正相反,它意味著讓快樂在社群秩序之中得到全面實現。在薄伽丘筆下,快樂無條件地帶有社會性,也毫不因此變得不“自然”。自然與社會并非勢不兩立,正相反,兩者是人的幸福事業中富于創意的盟友。一旦快樂既成全了自然本性的愿望,又滿足了社會性要求,人的幸福事業便如意大利式園林一般昌盛。《十日談》里的花園之所以是十位青年人共享愉悅生活的理想場所,原因之一就在此。那一座座花園以優雅的方式將自然與形式融為一體,成了遠不止一種意義上的“快樂之園”。讓我們來探究一下此種融合。

Franz Xavier Winterhalter
從薄伽丘的描寫可以看出,《十日談》里的花園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園林藝術仿佛共有某種審美特征,哪怕這僅僅意味著兩者同享某一淵源,或有傳承關系。后者在16、17世紀的意大利中南部興盛起來,過去幾百年中,不少優秀學者已對這門園林藝術作了深入精彩的探討。我不至于認為自己另有發現,而只想說在薄伽丘筆下的花園中,那些學者一定會認出自己研究的園林的某些典型特征,也就是這么一種造園風格:在這里,藝術既不支配自然(像凡爾賽宮園林那樣),也不刻意突出自然(一如盛行于18世紀英國的自然風景園),而是與大自然攜手共創一個既高度形式化又完全“自然”的富于人情味的空間——換言之,藝術以非正式的方式展示大自然的款款風物。
在此我想援引一位洞見精辟的評論家——伊迪絲·華頓,她撰寫的《意大利別墅與別墅園林》(Italian Villas and Their Gardens)一書至今仍是這一領域的一部經典。在題為《意大利園林幻術》的序言中,華頓寫道:“一天”,一位文藝復興時代的園林設計師從他的別墅露臺放眼望去,發現“環抱四周的風景被自然而然地包含在了他的花園里,兩者構成了同一款構圖的一部分”。如果說這一發現是杰出的意大利園林藝術的“第一步”,如華頓所言,那么“設計師的第二步是設法將自然與藝術在他的圖景中融為一體”。她接著評論道:
無論其他因素如何有助于引發迷人的總體印象,如果把這些因素逐個消除,在腦海中一一隱去那叢花卉、那片陽光、歲月賦予的那組豐富色調,便會發現在這一切背后潛藏著更深的和諧構思,獨立于任何偶然效果而存在。這并不意味著一座意大利式園林的設計方案同園林本身一樣優美。構成園林的各種相對恒久的材料——如石工石藝,常青樹木,湍瀉的水流或靜止的水面,尤其是自然風景的線條——都是藝術構思的一部分。但是這些風物在每一季節均以同樣優雅的面貌出現;不過,即便這些也只是基本方案的配飾。園林本身固有的美在于不同部分間的組合方式——在于那些相會一處的悠長櫟樹小道的線條,在于陽光普照的場地與林間清幽的樹蔭之間的交替,在于露臺和草坪的相對面積,或是一堵墻的高度同一條小徑的寬度之間的比例。在文藝復興時代的園林設計師看來,這些細節一處也不容忽視:他仔細考慮如何分配陽光與暗影,如何協調石砌建筑的直線外形與樹木起伏有致的曲線輪廓,正如他反復斟酌自己的整體構圖與周邊景致應持有何種關系。(華頓,Italian Villas and Their Gardens,第8頁)
如果細細品讀薄伽丘在“第三日”的引言中對一座花園的描寫(見附錄一),我們會發現他的文字朝著兩個相反的方向展開。一方面,作者在場景中安置了如此之多的動植物,致使花園被賦予了一種超乎寫實尺度的伊甸園特性。而另一方面,這段描寫稱頌了被華頓視為“意大利園林幻術”之精髓的那種“不同部分間的組合方式”與“和諧構思”,兩者的并列使花園的伊甸園特性成了假象。薄伽丘的文字強調花園巧妙的人為設計,這表明這座花園是人的作品,它的各種魅力源于人的匠心,它所處的環境始終受制于自然規律,無法免于衰老、災難和死亡。同樣在這里——尤其是在這里——瘟疫越過將花園像廟宇般隔離于世的墻垣,投下了它那長長的陰影。

Salvatore Postiglione
盡管這一花園囿于墻內,在《十日談》的讀者眼中,它仍不失為書中呈現的精心照料下的鄉間景致之精華。薄伽丘筆下的別墅、涼廊、花園、草地、湖泊和樹林組成了一種始終受制于人為設計構思的園林總匯(托斯卡納的風景至今依然大體如此)。我們若是不信一座花園的圍墻總是可以穿透的,不妨一88讀“第三日”的第一篇故事(見附錄一)。這篇故事把粗樸的馬塞多像十足的自然力那般送入了一所女修道院的高墻之內,在此,這位裝聾作啞的園丁將樂融融地去滿足九位修女的情色之欲。不論被圍在其中的是人還是花園,圍墻無法排斥自然,至多只能讓自然歸順于人的調理。
馬塞多無疑是一種自然力,不過我們可不能(像修女們那樣)被他擺出的那副粗陋的笨漢姿態給哄騙了。他的性欲多半是絕對“自然”、直截了當的,但他的行為和策略卻頗具匠心。其實,可以說他在諸多方面都對應于故事講述者所處的那座花園的設計師。也就是說,他深謀遠慮,制訂方略,按部就班地付諸實施,而整套計劃則服務于自然本性。如此行事的馬塞多也像預先播種、日后采摘勞動果實的園丁。
盡管馬塞多的出現給修道院的精神生活與情色生活帶來了不小的改觀,他的闖入卻并未導致無規無矩的混亂局面。正相反,在故事末了,修道院中的“力比多”能量得到了適度調控與合理分配,于是,這些能量既發揮作用,又不影響修道院原有的機構秩序。這篇故事最終頌揚了主人公們在給快樂注入“明確的形式”一事上表現出的足智多謀。從這個角度看,修道院的女院長與馬塞多一樣堪稱英雄(依照薄伽丘眼里的英雄主義標準),那項皆大歡喜的協議,正是馬塞多與女院長共同達成的。
如果說在基督教象征體系中,女修道院是修女與基督舉行神秘婚典的地方,那么馬塞多的到來使得修道院花園重新塵世化,它回歸了大地,向自然的欲求再度敞開。在此我們免不了注意到薄伽丘特有的精妙文思:“第三日”——《十日談》中最為“色情”的一日——開篇便影射但丁的《煉獄篇》(“太陽才從東方升起來,把鮮紅的朝霞映照成一片金黃”[《十日談》,第227頁]),而《煉獄篇》的高潮就發生在伊甸園中。薄伽丘對《煉獄篇》的影射無疑是隱伏的,它貫穿了整個“第三日”,起先便有馬塞多的故事在數字“九”上做的文章。在但丁眼里,“九”是最神圣的數字(三重“三位一體”位于一體)。我說薄伽丘將修道院花園再度塵世化,并不是在簡單地宣稱他以《玫瑰傳奇》那種性愛寓言的方式把花園變成了聲色的樂園,而是說他將修道院的情欲生活置于人的督管之下。繁盛的花園給修道院那獲得解放卻又循規蹈矩的性愛生活提供了貼切的寫照:在人的督管下,大自然的繁衍力得以興旺(修女們生下了不少“小修女和小修士”),盡管這一切都是在精心指導和控制下發生的。

Salvatore Postiglione
故事的講述者所在的花園歸功于人為設計,從這個意義上說,那處花園不啻為講故事提供了場景。事實上,在《十日談》里,花園與故事藝術之間存在一種更深更廣的相似性,因為從總體上看,薄伽丘的敘事藝術和文藝復興園林藝術依據了頗為相近的審美原則。我所指的不僅是《十日談》那精致的整體建構,比如它的敘述框架,一系列彼此呼應的主題,多種多樣的語聲,以及不同視角之間持久的互動。我所指的還有故事與花園之間的類似。一篇故事畢竟有如一座花園:它形態獨特,節奏明確,曲徑通幽,遠景連綿,奧妙重重,驚奇迭起,陰影朦朧,變幻無常,且與假想的邊界以外那“真實世界”相通相及。在薄伽丘看來,尤為重要的是,故事倘若編得好又講得好,它會令人愉悅。
不妨以馬塞多的故事為例。一種毫不張揚的匠心貫穿著它的直白風格,譬如,故事情節發展得有條不紊,詼諧的文風毫無避諱卻從不流于粗俗,基督教象征主義頻頻閃現,典雅愛情(特別是嚴禁引誘修女的戒律)得到幽默的諷刺,圣奧古斯丁關于人類言語起源的學說受到戲仿(他認為言語源自未滿足的欲望,而馬塞多因滿足過頭才開口說話),婚姻與園藝的雙關語屢屢回響。一旦注意到上述特色,我們便會發現這一切把文學工事和自然主義融為一體,正如意大利式園林——依照華頓和許多其他學者的觀點——融合了大自然與人為構思。甚至應當說,薄伽丘那常被人言過其實的“自然主義”與其說是一種宣稱自然本性統馭人類行為與動機的學說,不如說是一種獨到的敘事風格。薄伽丘著稱的、也理當以之著稱的那種精致卻不做作的風格——一種既明暢又復雜、既大膽又細膩、既通俗又博雅的風格——是把敘事藝術高度形式化的結果,而這一形式化的目的卻在于讓藝術歸化于自然。

Paul Falconer Poole
……
薄伽丘絕非一位道德說教家。他不是改革者,也無意充當先知。他并不特別關注人性的本惡或人類獲得救贖的前景。他從未以布道者的姿態訓斥讀者,向他們灌輸自己的道德、政治或宗教信念。如果說他在前言里為《十日談》確立的道德目標終究是極為平常的(作者希望借助他的故事為有需要的人消愁解悶),那是因為人之為人本來就是件平平常常的事。那場瘟疫也證實了這一點。做人意味著無法免遭不幸與災難,意味著時而感到自己需要援助、慰藉、消遣或啟迪。我們的狀況多半是平凡的,不是非凡的;依照薄伽丘的人文主義觀點,我們對他人負有的最低限度的道義責任,不在于為他指點救贖之道,而在于幫助他走完一天的路。這種援助有著許多平平常常的形式,尤其是借助風趣的談吐、得體的舉止、故事的魅力,通過謙恭禮讓、對話交流、同伴之情和社交生活促使人類交往的領域更加愉快。給生活增添快樂而不是增加痛苦,這就是薄伽丘人文主義的首要原則。它不是后世流行的那種“人定勝天”的人文主義(后者將自力更生的人類視為萬物之榮耀),而是以關愛他人為核心的民眾人文主(civil humanism)。(《十日談》的前言以“人”字開頭,并非偶然:“人之常情,是對不幸的人寄予同情。”[Umana cosa èaver compassione degli afflitti.])
值得重申的是,那群年輕人從一個瘟疫橫行、道德淪喪的佛羅倫薩一時逃脫,并沒有對所謂“現實”產生任何直接影響。在臨界地帶的園林佳境里度過兩周后,故事的十位講述者又回到了一度置于身后的慘象之中。然而與此同時,《十日談》里的故事,如同為講故事提供環境的花園,畢竟還是干預了現實,哪怕此舉僅僅在于見證形式的幻化之力。一個個故事用各種敘事形態重塑了現實,讓原本被現實那無形無度的流程所遮掩的事物得以有形有致地顯現于世,宛如花園將目光引至園中景物之間的審美聯系(見第五章)。這是花園與故事兼有的幻術:它們幻化了現實,盡管看上去未曾給后者帶來絲毫改觀。
如果說薄伽丘的故事藝術和他的人文主義倫理觀都與意大利園林設計美學相對應,那么,應當說他的“政治立場”也同樣與這一美學密切相關。雖然《十日談》一再頌揚給事物注入形式這一舉(不論此舉針對自我、言行,還是人際關系),但是該書也毫不留情地痛斥了那些欲對自然或下屬實施專制的暴君。在唐克雷迪(“第四日”第一篇故事)和瓜爾蒂耶里(“第十日”第十篇故事)這兩個人物中,我們目睹了暴政之欲的兩個最生動的化身。如果說理想的花園是自然在藝術的督管下欣欣向榮的地方,那么暴君則是欲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自然,從而征服和統治自然的人。從政治角度看,薄伽丘對專制政權的厭棄表現為他對佛羅倫薩的共和傳統畢生的忠誠,這些傳統讓自由與市政秩序并存。出于同樣的原因,那些由急于扼殺公民自由的區區暴君統治的意大利城邦令他深惡痛絕。他的友人彼特拉克力圖取悅于某些傲慢的君王,屢屢寄居他們的宮中,而薄伽丘則一貫拒絕權貴的捧場,始終忠實于共和式自由的理想。此種意義上的忠誠在《十日談》里處處可見,但它從不張揚,從不炫耀。應當說,《十日談》的字里行間帶給讀者的愉悅中,它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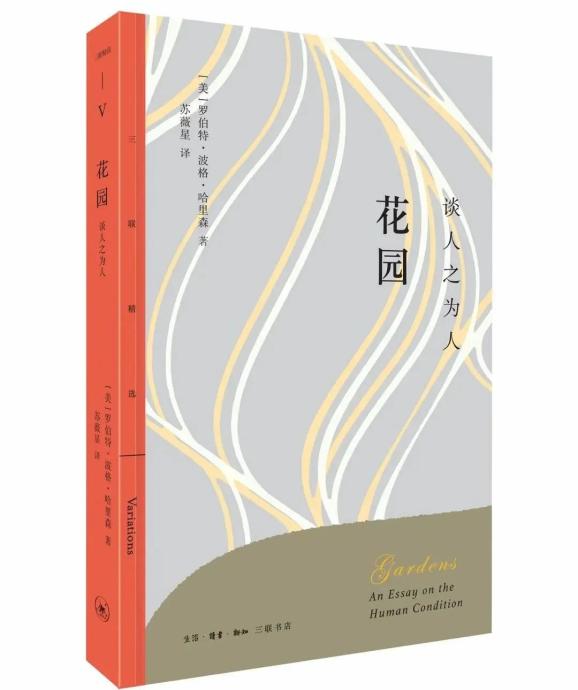
[美]羅伯特?波格?哈里森 著 蘇薇星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1
ISBN:9787108066305 定價: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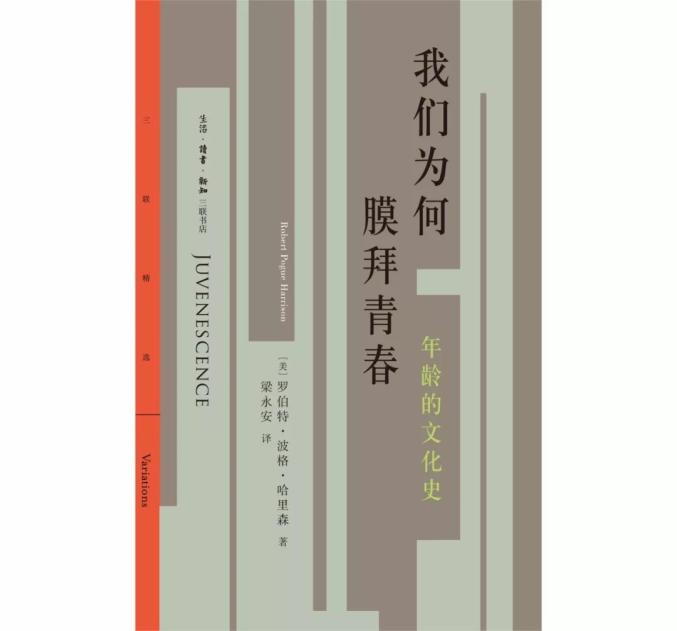
[美]羅伯特·波格·哈里森著 梁永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1
ISBN:9787108060426 定價:36.00元
━━━━━
原標題:《1348年黑死病期間,薄伽丘的花園故事》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