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真實影像|透過自我民族志的目光,拆解家庭空間中隱蔽的高塔
“家庭是一座高塔,按照年齡和性別分配角色和職責,構成一種必須遵守的等級和權力關系。”
外面作為廣場
“從小到大,我對她的印象,就是她時常都不在,都是跟她的女朋友在外面玩樂。我一直都知道,她跟朋友在外面,總是比待在家里的時候還要快樂。”這是紀錄片《日常對話》開篇不久的一段畫外旁白,來自導演黃惠偵。
女兒想要搞清楚為什么母親那么不喜歡待在家里。在訴說這段旁白的時候,黃惠偵的鏡頭似乎嘗試以特寫的距離貼近母親,但被母親面對她時的沉默推遠,只能在遠景的位置上旁觀母親的快樂(圖1)。影片讓我們看到了屬于母親的兩種空間:在家里,她寡言陰沉,在外面,她自由開朗。

圖1 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畫面中,黃惠偵的母親留著超短發、叼著煙,與幾個朋友暢快地打著牌,身邊坐著一位氣質很好的阿姨。隨著影片的展開,我們會意識到,她是母親的女朋友。母親交往過十幾個女朋友,但卻“不想”跟女兒共處一室。母親甚至一心想要遠離與女兒共同生活的親密居室,即便在廚房做好飯菜,也會出門坐到鄰居的牌桌旁(圖2)。母親的反常和疏遠不止于此:女兒問,如果我結婚了,你怎么辦?母親說,我自己一個人可以到處跑,公園就有地方睡。

圖2
母親想待在外面,可能是因為,在外面,她有能力支撐起一個空間,用自己的勞動養活兩個女兒,還能被社會上的人尊重。母親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在道場做法事討生活,在影片的回憶段落中,黃惠偵說到,從六歲開始就跟著母親“牽亡”。“牽亡”是一種臺灣民間的喪葬儀式,法師帶領著亡靈一路行經種種關卡走入極樂世界,要用密集的說唱口述來描述路途,其他人則用舞蹈、雜技或僅僅是站立注視來配合她對場景的說唱。
畫面中,做法事的母親是絕對的中心,周圍的人都專注投入到她的表演中(圖3)。宗教儀式賦予了母親一種作為拯救者的權力和權威,不僅拯救了亡者,同時也讓她有了一份有償工作,有能力負擔家計。跟著母親做“牽亡”的女兒覺得母親“很厲害”。

圖3
母親想呆在外面的另一個原因,也許是她在外面能交到很多女朋友,而且這些阿姨都說母親“很厲害”。黃惠偵給三位阿姨做了訪談(圖4-6),她們口中的母親很熱情:“在我姐姐的面前也叫我寶貝”;無拘無束:“心情不好的時候,就連摩托車也不讓我坐”;不僅花言巧語“很粘人”,而且追女孩子也很有策略:在公園里找理發的阿姨幫她理男生的發型,騎摩托車帶她去看歌仔戲,阿姨最后被她“掰彎”(注:從異性戀成為同性戀)的時候還說,“是因為遇見你阿媽才被愛沖昏頭”。
讓黃惠偵驚訝的是這些母親在她面前從未展現過的魅力、生命力和影響別人生命的力量,甚至有一個阿姨不僅跟著母親做“牽亡陣”,還心甘情愿地照顧她的兩個女兒。“不是厲害,是彼此互相喜歡”,母親的一句話道破了外部空間對于母親的意義:不僅是釋放自己的避難所,一個可以游刃有余加以調度、構建自己性別角色的舞臺,而且,或者說更是一個表達欲望的空間和快樂的源泉。

圖4

圖5

圖6
家庭作為高塔
作為自我家庭民族志,《日常對話》讓我們看到家庭空間對性別不平等結構的強化。居所意味著一種性別分工:男人的位置在外面,負責賺錢養家,而女人的位置在家庭,負責無償地看護、家務等再生產勞動。家庭對于女性而言,就像辦公室對于男性職員一樣,意味著性別化的責任。
盡管黃惠偵的母親在道場的舞臺上是絕對的中心,能夠用做法事的收入取代父親的位置負擔家計,但是她仍然需要回家。在外面有自主空間的女人看似反轉了性別上的權力結構,回到家庭空間,也要洗衣、做飯、喂養,繼續履行妻職和母職,不僅如此,母女還受到丈夫的暴力和控制,直到大女兒10歲時才獨自帶著兩個女兒逃亡。即便母親的性取向并非一個秘密,即便母親并非一個軟弱的人(她以“長那么大還要被人打”為恥),她仍然嫁給了一個嗜賭的男人,仍然會為女兒和外孫女做飯。在外面的開朗和在家里的陰郁,這些“反常”表現的原因,被母親的兄弟姐妹面對鏡頭時的反應所揭示。
重訪過去是為了在當下改變歷史的秩序。法國紀錄片作者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1925-2018)在制作紀錄片《浩劫》的過程中,為了搞清楚大屠殺中的普通人如何對待猶太人,帶著攝影機和當事人重訪過去的地點,讓回憶在碰撞中被記起和重演,從而有了在當下介入過去的可能性。回到本片,童年時的母親已經知道自己喜歡女孩子,為什么她還會嫁人生子?為了解開這個謎,黃惠偵也帶著攝像機和母親一起重訪北港老家。實際上,在外祖父母死后,她從位于鄉下的家庭空間里“出逃”,與家人幾乎沒有來往。借著祭奠先人的場景,黃惠偵讓我們意識到,在鄉土社會,似乎只有死亡才能改變女人和性少數者的處境:外婆曾因受不了外公的打罵,喝農藥自殺。相對而言,城市對一個同志媽媽來說就是“外面”,這里像是一個庇護所。
家庭空間不僅是一個舞臺,也是一種作用力,透過日常慣行構建和改變性別身份。飯廳的座次、供奉逝者的排位,都在強調異性戀父權制的價值觀。女人不嫁人、不持家,無論在空間中還是在社會中,都沒有身份。
在北港的家庭空間,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親人如何以沉默和有意遺忘來表達他們的態度,這是對于黃惠偵母親作為女人和作為同性戀者的雙重壓制。鏡頭中,黃惠偵向舅舅和姨媽逼問:你知道我媽喜歡的是女生嗎?三個人同時下意識地流露出反常的沉默和否認。平行蒙太奇的剪輯方法強化了三個人反應的不約而同,以及“不知道”的暴力性:一種比侮辱、打罵甚至斷絕關系還要有效的“施暴”(圖7-9)。在這個時刻,黃惠偵從當下進入過去:盡管母親從小就喜歡女生,但是所有親人都心照不宣地回避或否認,孤立無援的母親不得不嫁給賭博、家暴的丈夫。

圖7

圖8

圖9
家庭是一座高塔,按照年齡和性別分配角色和職責,構成一種必須遵守的等級和權力關系。對于結了婚的母親來說,家庭空間意味著她不得不履行的妻職和母職,即便這是一個錯誤。在鄉土社會,如果居室臟亂,其他人多半會責備家里的女人不盡責,保持居家整潔有序屬于傳統觀念對性別身份的編碼,這種慣性也被延續到了當代都市。即便黃惠偵的母親喜歡一個人自由自在地生活,也要在家里做了飯才出門。
不過,廚房也不一定在所有地點、所有時間都意味著性別不平等的生產。岡薩雷斯(Beatriz Mu?oz González)在2005年對西班牙的本土社區研究發現,家庭對于女性來說既是一種負擔和恥辱,也是一種滿足感的所在和庇護所。而本片在九十分鐘的時間里向我們呈現了母親在家庭空間中從沉默到釋放的轉變,揭示出對母職的拆解。
把職責轉變成關愛
《日常對話》可以說是所謂“私影像”的紀錄片類型,意味著拍攝者將攝影機鏡頭對準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通過攝影機的中介帶有距離地觀看自己和自己的日常環境、人際關系,從而獲得陌生或超越的視角,于是攝影機的在場帶有一種自我書寫與療愈的功能。
對于黃惠偵來說,與母親的關系構成了她人生的問題和答案,通過拍攝與母親對話也成為了一種觀察和分析自我的途徑。由于家庭的影響,幼時黃惠偵沒有得到正常的學校教育和文字語言的書寫能力,便攜數碼攝影機讓她可以通過一種獨特的語言來表達和溝通。1998年黃惠偵20歲時,曾成為臺灣紀錄片作者楊力州的拍攝對象,后來在社區大學學習到影像制作的基本技術以及社會學、人類學知識,對家庭空間的拍攝是她用影像來思考身份問題的實踐。黃惠偵讓我們看到了城市中的微觀領域和私密空間中的關系結構,以及攝影機的存在對自我的救贖。
《日常對話》中一個不斷重復的視覺母題是女兒和媽媽在廚房和飯桌邊的位置。在影片的開始,母親和女兒分別使用廚房和餐桌,彼此沒有交集。母親在廚房做菜后離開了家,女兒起床為自己的孩子煮奶瓶,然后坐到餐桌上喂孩子吃飯。我們不僅可以在這一組鏡頭的排列中看到母親的“冷漠”、母親和女兒的疏離,也可以看到兩種母女關系和母職執行活動的對比(圖10-13):優秀地履行著母職的女兒,希望自己的母親也能成為一個盡職的媽媽。

圖10

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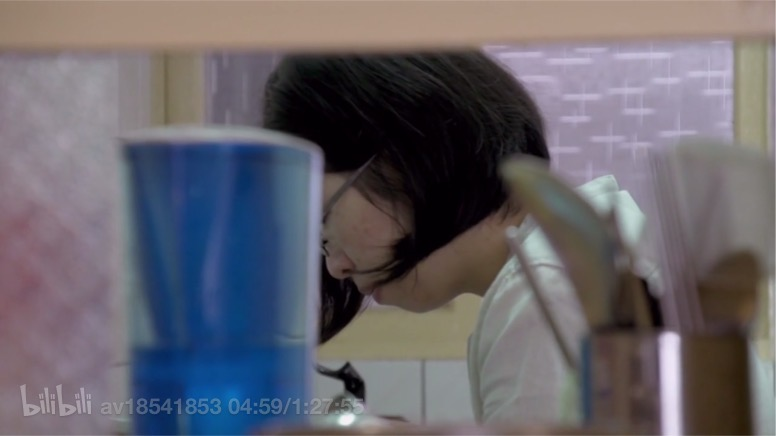
圖12

圖13
借助紀錄片的拍攝,母女產生了對話的可能,攝影機的在場讓母親不得不坐到桌邊,傾聽女兒講述自己的童年陰影、回答女兒的問題、描述和解釋自己的記憶(圖14)。

圖14
這帶來了紀錄片敘事弧線的高潮和轉折,當母女二人共享餐桌這個親密的家庭空間時,她們也在真正分享彼此的記憶、經驗、期待、情感的內在空間。于是共處一室不再(僅僅)意味著為了執行母職而“不得不”的行為,女兒和母親一起做飯變成一種為了生活本身而彼此協助、創造和關愛的自然而然的行為(圖15-16)。在影片接近結尾的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母女二人一起出沒于廚房和餐桌的景象,與影片開始的鏡頭序列形成了對比,講述著一種變化的發生:當職責被拆解的時候,高塔有可能變成廣場。

圖15

圖16
(作者徐亞萍系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真實影像” 每次聚焦一部紀錄片,試圖從非虛構的影像文本中還原城市記憶和拍攝者的思想實驗。)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