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和病毒相比,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場自然災(zāi)害
從“鉆石公主號(hào)”到全國進(jìn)入緊急狀態(tài),日本的疫情形勢逐漸惡化。截至13日,首都東京的確診人數(shù)已突破1300人,全國累計(jì)確診新冠肺炎病例7404例,其中137人死亡。
在防疫封鎖,惡劣的天氣狀況和接連不斷的訃聞下,正實(shí)施“外出自肅”的城市街頭也似乎也被低氣壓籠罩著。

3月29日的東京街頭,惡劣的天氣也讓街上人潮大量減少。 圖/美聯(lián)社
盡管4月7日傍晚安倍政府正式發(fā)表了“緊急事態(tài)宣言”,呼吁國民進(jìn)行配合,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但網(wǎng)友紛紛對此提出質(zhì)疑,“對于人身自由、交通運(yùn)輸沒有強(qiáng)制力的緊急事態(tài)措施,能發(fā)揮多少作用?”,不斷攀升的單日確診人數(shù)也引發(fā)了人們對政府防疫能力的爭議。

日本緊急事態(tài)將為期一個(gè)月,涵蓋東京都、神奈川縣、埼玉縣、千葉縣、大坂府、兵庫縣和福岡縣7個(gè)生效區(qū)域,實(shí)施時(shí)間為4月8日零點(diǎn)至5月6日。圖/美聯(lián)社
種種情況,不禁讓人想起9年前的日本。2011年3月11日這一天,當(dāng)一場史無前例的強(qiáng)震摧毀了社會(huì)秩序和日常生活后,幸存者依靠社會(huì)的集體意識(shí)和堅(jiān)忍意志渡過眼前的難關(guān),他們似乎一開始就對官方的救援不抱希望。今天的日本民眾看著屏幕另一頭的安倍,似乎也抱持著同樣的心理。

12日安倍在網(wǎng)上分享的一段居家視頻引發(fā)爭議,日本網(wǎng)友:“看了只叫人生氣,明明什么問題都還沒解決。”
(下文選自《巨浪下的小學(xué)》衛(wèi)報(bào)書評(píng):除了地震海嘯,日本的政治也是一場自然災(zāi)難 原文/堀田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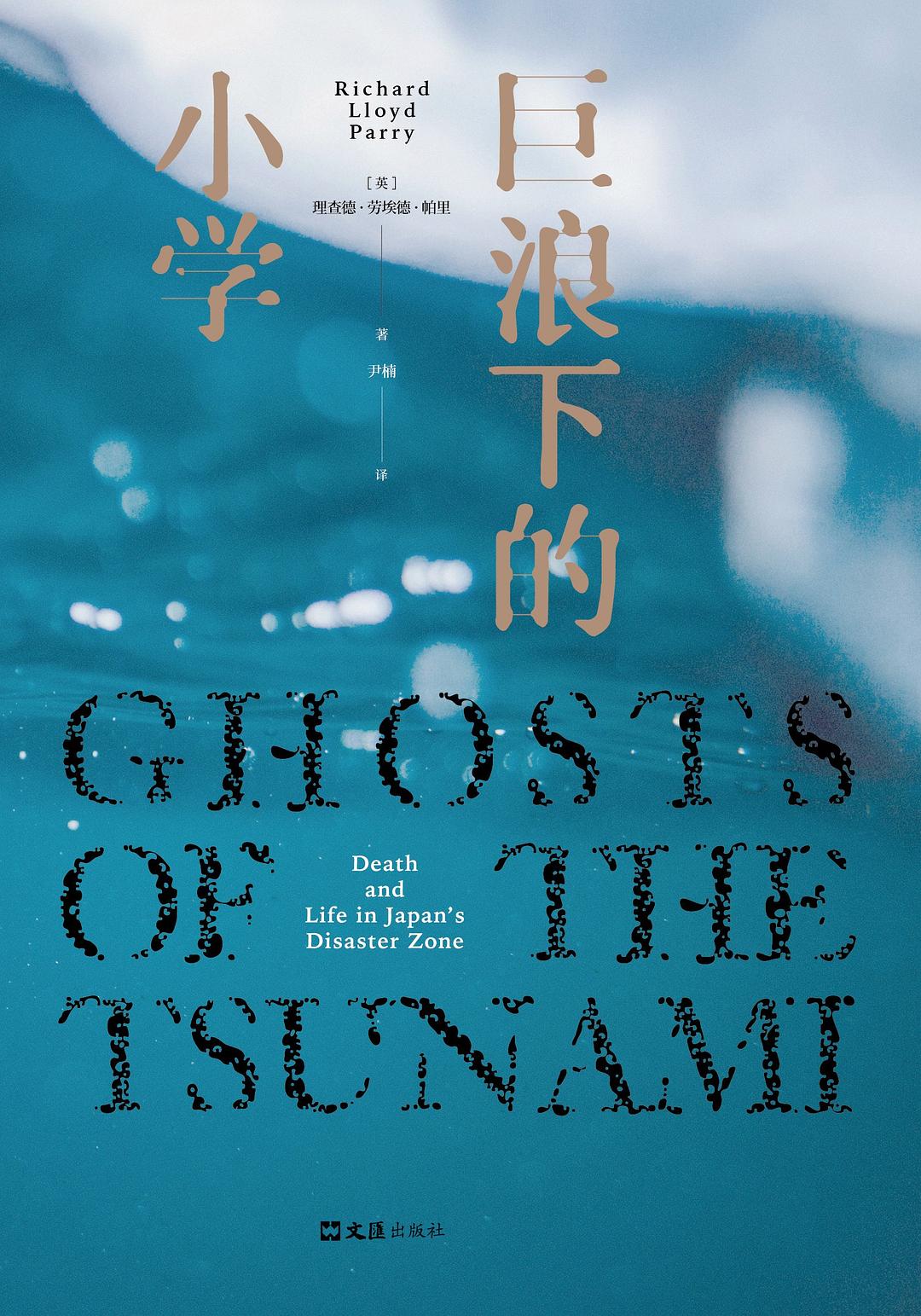
《巨浪下的小學(xué)》
作者: [英]理查德·勞埃德·帕里
出品方: 新經(jīng)典文化
在日本,糟糕的政治也被看作一種“自然災(zāi)難”,一種“普通人無法干預(yù)的集體的不幸”,只能“無助地接受它、容忍它”。
日本東北部氣候惡劣又遠(yuǎn)離日本中心,一直被看作整個(gè)國家的落后地區(qū)。伴隨這一看法,人們對東北部人民普遍帶有貶義的刻板印象——沉默寡言、冥頑不化,還有點(diǎn)神秘莫測。他們很少表達(dá)自己的心聲,往往咬緊牙關(guān)、壓抑情感,在陰郁的沉默中做著自己的事情。2011年3月,災(zāi)難襲擊東北部沿海社區(qū),伴隨9.0級(jí)大地震而來的,是海嘯和福島核電站反應(yīng)堆的泄漏。即使災(zāi)難發(fā)生,東北部人民仍十分隱忍、咬緊牙關(guān)堅(jiān)持到底的品質(zhì)令人尊敬。
有關(guān)災(zāi)區(qū)的新聞報(bào)道稱贊東北人民的堅(jiān)韌。許多幸存者失去了一切,卻表現(xiàn)出令人驚訝的克制。他們毫無怨言,在臨時(shí)疏散中心有序地安頓下來,排隊(duì)領(lǐng)取發(fā)放的食物,照顧體弱者和受傷者。旁觀者都認(rèn)為東北地區(qū)在應(yīng)對災(zāi)難方面非常成功。

排隊(duì)領(lǐng)取救災(zāi)物資
然而,理查德·勞埃德·帕里的書提醒我們,我們對這個(gè)地區(qū)及其人民先入為主的印象并不準(zhǔn)確。在災(zāi)后生活的有序表象之下,還隱藏著現(xiàn)實(shí)的其他方面。勞埃德·帕里是《泰晤士報(bào)》駐東京記者,他多次前往日本東北地區(qū),只為了解那里正在發(fā)生什么。最終,他向海嘯受災(zāi)地區(qū)投去充滿同情又發(fā)人深省的一瞥。這場海嘯造成的傷亡人數(shù)占當(dāng)天總傷亡人數(shù)(18500)的99%,是長崎核爆炸以來日本人員傷亡最嚴(yán)重的一次災(zāi)難。書中一個(gè)接受采訪的女人表示,他們不僅是生活發(fā)生了變化:“我是指我們腦子里有東西不一樣了。那天以后,每個(gè)人都出現(xiàn)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勞埃德·帕里試圖走入這些人的內(nèi)心世界,但相比于“出現(xiàn)問題”,他發(fā)現(xiàn)了許多不同層次的悲慟。他看到“每個(gè)人的悲傷都不一樣,由于每個(gè)人的損失不盡相同,悲傷也存在細(xì)微的差別”。能否盡快找到并安葬家人的尸體,也決定了人們悲傷的程度。而那些一直沒有找到家人尸體的幸存者,則開始尋求靈媒的幫助,希望能確定尸體所在的位置。

災(zāi)后的東北地區(qū)滿是幽靈,許多報(bào)道稱有人看見了幽靈。一些人認(rèn)為,這是不可避免的,因?yàn)檫@場海嘯帶走了許多人的生命,他們還沒準(zhǔn)備好放棄塵世的羈絆。到處都流傳著靈異故事:一個(gè)死去的女人去老朋友的臨時(shí)住所拜訪,并坐下來喝茶,離開后,她坐過的那張墊子都被浸濕了。一個(gè)出租車司機(jī)載了一位乘客,但他要去的地方早已不存在,而且在半路,司機(jī)便發(fā)現(xiàn)坐在后座的乘客不見了。
人們是否相信這些超自然現(xiàn)象并非重點(diǎn)。一個(gè)佛教僧侶驅(qū)散了許多死于海嘯的幽靈,他認(rèn)為,重點(diǎn)不是這些幽靈到底是真是假,而在于人們確實(shí)相信他們真的看到了幽靈。東北地區(qū)的“幽靈問題”變得十分普遍,大學(xué)的學(xué)者開始為這些故事編目,基督教牧師、日本神道教和佛教的僧侶也“不斷地被叫去驅(qū)趕怨靈”,這些幽靈在極端情況下會(huì)附上生者的肉身。
在勞埃德·帕里的書中,還有另外一類游蕩在災(zāi)區(qū)的幽靈——日本社會(huì)各個(gè)層次的政治失敗。從村子里的社區(qū)和當(dāng)?shù)毓賳T,到縣政府、中央政府,都沒能對災(zāi)難做出充分的反應(yīng)。大川小學(xué)就是這種政治失敗的最佳象征。如果將這本書看作一部構(gòu)思精巧的犯罪小說或心理劇,那大川小學(xué)的故事就是它的核心推動(dòng)力之一。
我不想過多透露這個(gè)令人著迷的悲劇故事,只想說在災(zāi)難發(fā)生當(dāng)天,有9所學(xué)校被海嘯襲擊,共75個(gè)孩子在學(xué)校喪生,其中的有74個(gè)就來自大川小學(xué)。這個(gè)喪生率令人困惑,家長想知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畢竟在警報(bào)發(fā)布和海嘯來臨之間,其他學(xué)校的孩子都有充足的時(shí)間撤到更高的地方。官方一直沒有給出統(tǒng)一的解釋,似乎也不愿徹查此事。在悲傷憤怒之下,一部分家長決定反擊,對市、縣政府提起訴訟。

家長的問責(zé)只換來冷冰冰的鞠躬與道歉
但這些家長還要面對一個(gè)極其特殊的歷史幽靈——一個(gè)強(qiáng)大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幽靈。在19世紀(jì)日本追趕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過程中,這一意識(shí)形態(tài)發(fā)揮了有益的作用。它將人民看作國家的公仆,那些批評(píng)官方的人或被看作制造麻煩的人,或被看作應(yīng)該受到排擠的自私的鬧事者。盡管在二戰(zhàn)中推行這一意識(shí)形態(tài)的官僚給日本帶來災(zāi)難,但這一幽靈卻仍然在飽受破壞的日本存活下來。勞埃德·帕里稱,在這樣一個(gè)集權(quán)主義的國家,糟糕的政治也被看作一種“自然災(zāi)難”,一種“普通人無法干預(yù)的集體的不幸”,只能“無助地接受它、容忍它”。最顯而易見的危險(xiǎn)在于人們不再發(fā)揮個(gè)人判斷的力量,這便造成了致命的盲從。書中的老人在海嘯警報(bào)發(fā)布后將車停在山上,之后又順從地走到山下的疏散中心集合,結(jié)果被海水吞沒,就是這種盲從的最好證明。有人會(huì)說,那些使東北人民成為模范疏散者的品質(zhì),如遵守秩序、寬容度高、不發(fā)牢騷等,也妨礙他們成為積極的民主公民。
然而,困難也可以激起一個(gè)人為自己的權(quán)利而戰(zhàn)的欲望。如今已鮮有人記得,歷史上的東北地區(qū)曾奮力爭取過民主。19世紀(jì)七八十年代,剛剛起步的日本公民社會(huì)正在考慮采用何種憲法, 經(jīng)歷了60年代內(nèi)戰(zhàn)在東北地區(qū)造成的貧窮、滯后和血腥戰(zhàn)敗的東北思想家進(jìn)行了一場草根辯論,他們討論了諸多社會(huì)話題,從是否應(yīng)該立女王,到新聞自由,再到如何讓東北這樣的落后地區(qū)融入日本社會(huì)。他們當(dāng)時(shí)辯論的許多話題與當(dāng)今社會(huì)仍然息息相關(guān)。
在所有由東北地區(qū)激發(fā)的民主運(yùn)動(dòng)中,《五日市憲法》仍然值得注意。這是一份1881年由東北人千葉卓三郎起草的憲法提案。一半內(nèi)容都與人民的權(quán)利相關(guān)。千葉在31歲時(shí)去世,而他的提案直到90年后才在一個(gè)無人留意的檔案中被發(fā)現(xiàn)。如今,東北地區(qū)以及整個(gè)日本都應(yīng)該在千葉這樣的改革者身上尋找變革的靈感。
堀田江理(Eri Hotta),生于日本東京,先后在日本、美國和英國接受教育,并先后執(zhí)教于牛津、東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領(lǐng)域?yàn)閲H關(guān)系,著有《日本大敗局:偷襲珍珠港決策始末》(Japan 1941:Countdown to Infamy)、《泛亞洲主義與日本的戰(zhàn)爭:1931-1945》(Pan-Asianism and Japan’s War 1931-1945)等。現(xiàn)居美國紐約。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澎湃號(hào)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