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傅高義:1958年一個(gè)美國(guó)人到日本做田野調(diào)查有多難

傅高義
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中期,我還是哈佛博士生時(shí),日本對(duì)我還毫無(wú)吸引力。
在我的論文導(dǎo)師弗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把我叫去之前,我從來(lái)沒有真的想過去日本。克拉克洪博士和她的丈夫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是當(dāng)時(shí)人類學(xué)和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杰出的學(xué)者。她把我叫過去時(shí),她說(shuō):“你應(yīng)該意識(shí)到自己視野太褊狹了,你從來(lái)沒去過海外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要客觀地看待美國(guó)社會(huì),就真的應(yīng)該去國(guó)外感受不同的文化。在你取得博士學(xué)位后,你應(yīng)該去另一個(gè)較美國(guó)有巨大文化差異的國(guó)家。”
另一位教授,威廉?考迪爾(William Caudill,威廉?考迪爾早在1950年就出版了一本比較日美社會(huì)文化的專著,之后研究興趣轉(zhuǎn)向心理衛(wèi)生,關(guān)注社會(huì)文化對(duì)人心理衛(wèi)生帶來(lái)的影響。他被公認(rèn)為是醫(yī)療人類學(xué)領(lǐng)域的奠基人。)博士和我聊了日本以及他在那邊的工作,并鼓勵(lì)我去日本做博士后研究。他還承諾,如果我去日本,他會(huì)帶我了解那邊的情況。顯然,日本是一個(gè)與美國(guó)文化非常不同的國(guó)家。
我給研究與精神病學(xué)基金會(huì)寫了一份研究經(jīng)費(fèi)申請(qǐng)書。正如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所說(shuō)的那樣:我打算以一名社會(huì)科學(xué)家的身份探尋跨文化的家庭與心理衛(wèi)生的普遍性問題。研究與精神病學(xué)基金會(huì)問我他們?yōu)槭裁匆Y助一位社會(huì)學(xué)家從事人類學(xué)領(lǐng)域的工作。好在最終他們還是認(rèn)可我的申請(qǐng)并同意資助我兩年。第一年是語(yǔ)言學(xué)習(xí),第二年是家庭采訪。
決定去日本后,我便參加了一個(gè)速成班,以熟悉日本與日本人。我開始坐在了解日本的課堂里,還請(qǐng)了一位日本學(xué)生有馬龍夫(他后來(lái)成為一名大使)做我的日語(yǔ)家庭教師,同時(shí)閱讀與日本相關(guān)的新書和期刊,比如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
一九五八年,蘇珊娜和我?guī)е暧椎膬鹤拥诌_(dá)東京羽田機(jī)場(chǎng)。從到達(dá)第一天開始,我便對(duì)這座今后兩年會(huì)在此安家的城市開始了觀察。
一九五八年日本的生活,與日后的逐漸變化相比,更簡(jiǎn)單,節(jié)奏也更慢。表面上,就我當(dāng)時(shí)所看到的景象,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日本將在二十世紀(jì)七十年代末崛起,成為世界上最成功、最具活力的經(jīng)濟(jì)體。當(dāng)時(shí)東京的大小馬路仍是泥土路。馬路上汽車很少,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進(jìn)口車。街道上除了公交和出租車,顯得非常空蕩。當(dāng)時(shí),出租車費(fèi)用根據(jù)車子大小分成六十日元、七十日元和八十日元三種,地鐵還只有銀座線。當(dāng)然了,山手線已開通運(yùn)行。蘇珊娜和我對(duì)日本鐵路系統(tǒng)印象非常深刻,因?yàn)榛疖嚪浅?zhǔn)時(shí),班次也多。
由于擔(dān)心地震,那時(shí)最高的建筑只有八層樓高。建筑公司也還沒有信心造更高的建筑。不過,很顯然,讓我們驚訝的是,在東京沒有看到任何被炸毀的建筑和瓦礫。前往日本途中,我們?cè)谟?guó)還看到了二戰(zhàn)時(shí)遺留下來(lái)的斷壁殘?jiān)6诌_(dá)東京后,城市已清理干凈,也許會(huì)在一些地方看到空地和閱兵場(chǎng),但見不到戰(zhàn)爭(zhēng)留下的瓦礫。
在日本的第一年,我們住在澀谷的一幢房子內(nèi),這是考迪爾拜托一位心理衛(wèi)生研究領(lǐng)域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幫忙找的,房子離他自己家很近。土居健郎是著名的精神病學(xué)家,寫過一篇名為《嬌寵:讀懂日本人格構(gòu)造的一把鑰匙》的論文。關(guān)于“嬌寵”(甘え)的概念,他解釋說(shuō):“這是將對(duì)方的愛或善意視為理所當(dāng)然,并期待對(duì)方能照顧自己的想法或情緒。”我們也非常幸運(yùn)能與土居健郎博士和他的太太成為鄰居。他們成了我們最好的導(dǎo)師,向我們解釋日本人一些難以為外人理解的態(tài)度和行為。

傅高義和土居健朗以及家人合影
我們每個(gè)月需要付二萬(wàn)五千日元的房租,按照當(dāng)時(shí)日元匯率(三百六十日元兌一美元)換算下來(lái),大概月租不到七十美元。然而,我們的日本朋友認(rèn)為,這個(gè)房租略微有點(diǎn)高:“可能因?yàn)槟銈兪峭鈬?guó)人,所以要價(jià)比較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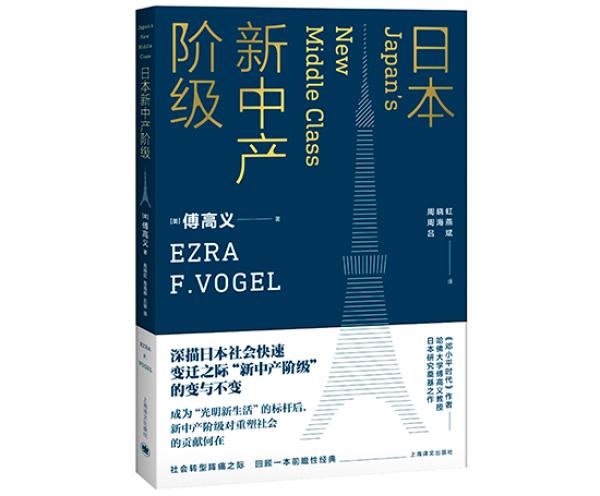
傅高義作品《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jí)》
我們住的地方與我們研究的日本家庭所居住的房子很像,正如我在《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jí)》一書中所描寫的那樣:
“所有的房屋都是未加粉刷的原木平房,環(huán)繞著精心設(shè)計(jì)的小花園,筑以高高的圍墻與外界相隔離。通常房子總有一面或兩面是向陽(yáng)的,安裝上玻璃移門,白天可以打開,讓陽(yáng)光和空氣穿透室內(nèi)。到了晚上,把玻璃門外的移動(dòng)木門關(guān)上,用以阻擋雨水、寒氣、昆蟲和盜賊。總的來(lái)說(shuō),建筑簡(jiǎn)潔樸實(shí),薄墻、尖頂、小窗戶,沒有地下室。每戶人家一般會(huì)有三到四個(gè)房間,房間之間用移動(dòng)紙門隔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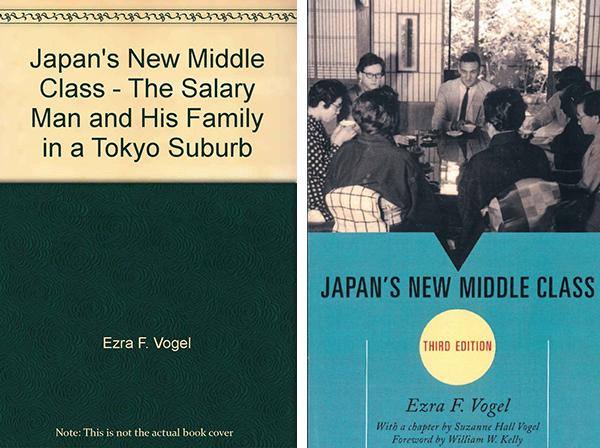
原版《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jí)》封面
我們的廚房非常小,地板又臟又舊,有一個(gè)用來(lái)煮食物的燃?xì)庠睢_@與我們以前在美國(guó)時(shí)的廚房形成鮮明對(duì)比,那兒有充足的儲(chǔ)藏空間、寬敞的食物料理臺(tái)。我們有電冰箱,但很多日本人當(dāng)時(shí)仍在使用冰柜(指用冰塊來(lái)冷凍食物的冰柜。)。
我們?cè)谌毡镜姆孔記]有中央供暖系統(tǒng),只能靠煤油加熱器和被爐取暖。取暖用的燃料非常貴。到了冬天,屋里很多地方讓人覺得冰冷。我仍然記得那時(shí)因?yàn)榧依镉幸粴q半的孩子大哭、四處亂跑而非常吵鬧,有時(shí)會(huì)去離家不遠(yuǎn)的圖書館。即使圖書館內(nèi)間或擺放著木炭火盆或炭鍋,每個(gè)坐在圖書館里的人還是都穿著外套,室內(nèi)也就十度上下。
我還記得被邀請(qǐng)去日本朋友家中,因?yàn)榕吕洌覀兇┲斓谋E瘍?nèi)衣,但是當(dāng)我們到達(dá)后,經(jīng)常很榮幸地被安排在靠近取暖源的位子。被當(dāng)作貴客的我們,因?yàn)榇┲E瘍?nèi)衣而滿頭大汗,反而希望能坐在屋內(nèi)寒冷一些的地方。
說(shuō)到取暖,我突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某個(gè)冬夜,我們臨時(shí)決定去土居健郎博士家拜訪。走到他家門口時(shí),發(fā)現(xiàn)他穿著外套來(lái)為我們開門。他告訴我們他正好要出去一趟。我當(dāng)時(shí)覺得他的舉動(dòng)非常奇怪,但我什么都沒說(shuō)。后來(lái)我才意識(shí)到發(fā)生了什么。土居博士想要省取暖費(fèi),因此晚上關(guān)掉取暖器穿著外套,他不好意思告訴我,所以當(dāng)我看到他穿著外套時(shí),只好假裝是剛穿上準(zhǔn)備出門。
我和蘇珊娜都要學(xué)習(xí)日語(yǔ),因此需要有人幫我們照顧兒子。考迪爾博士的太太先幫我們找了一位年輕女傭,我們叫她“幫傭”。后來(lái),出于政治正確的原因而改稱“家政婦小姐”,不能再以“幫傭”稱呼她。不過,自從勞動(dòng)力價(jià)格飛漲后,只有少數(shù)人能負(fù)擔(dān)得起用人。
考迪爾博士的太太幫忙找的女傭來(lái)自中產(chǎn)階級(jí)家庭。她想通過為我們工作而學(xué)習(xí)英語(yǔ),以便將來(lái)可以去美國(guó)學(xué)習(xí)。但是,當(dāng)她發(fā)現(xiàn)這個(gè)工作需要為一歲半大的小孩換尿布時(shí),覺得這個(gè)工作與她想象的非常不一樣。兩周后,她就辭職了。
隨后,我們又設(shè)法找了一位來(lái)自鄉(xiāng)下的年輕婦女,光子小姐。她非常高興能找到這份工作,并愿意承擔(dān)照顧我們兒子的責(zé)任。她住在家里的小房間,我們每個(gè)月支付她一萬(wàn)日元(三十五美元),包食宿。對(duì)此,我們的日本朋友再次感嘆:“你們付得太多了!我們比你們付得少多了。”然而,光子小姐非常投入地照顧我們的孩子,還幫助我們學(xué)習(xí)如何適應(yīng)在日本生活。
我們當(dāng)時(shí)的生活還是非常舒適的。研究與精神病學(xué)基金會(huì)每個(gè)月提供給我們五百美元補(bǔ)助金,按照當(dāng)時(shí)一美元兌三百六十日元的匯率換算,是非常大的一筆錢。每個(gè)月扣除房租和其他開支后,我們還能剩下很多錢。事實(shí)上,我剛成為博士后時(shí)的開銷,比我二十五年后作為一名正教授來(lái)日本,花得還更多。
非常幸運(yùn)的是,在日本的兩年中,我們沒有碰到重大困難。在我們赴日之前,還收到過關(guān)于如何在日本生活的小冊(cè)子。凡是參與富布賴特項(xiàng)目(二戰(zhàn)結(jié)束后,美國(guó)參議員J. 威廉?富布賴特主導(dǎo)了一項(xiàng)旨在將美國(guó)在海外剩余作戰(zhàn)物資出售后用于資助美國(guó)與世界各地教育文化項(xiàng)目的法案。之后相關(guān)教育文化資助項(xiàng)目也成為戰(zhàn)后美國(guó)軟實(shí)力對(duì)外輸出的重要象征。)的學(xué)者前往日本時(shí)都會(huì)收到。事實(shí)證明,這本冊(cè)子中的一些建議有點(diǎn)夸張了。比如,它告誡我們不要購(gòu)買一般的蔬菜,因?yàn)槿毡救擞眉S便施肥,蔬菜會(huì)被污染。因此,建議我們要去大型百貨公司地下商店購(gòu)買,那里賣的蔬菜使用的是化學(xué)肥料,吃了以后不會(huì)生病。
盡管我們被提醒要注意平時(shí)的飲食問題,但我們?nèi)耘f從附近商店購(gòu)買水果蔬菜。商店很方便,食物也都美味營(yíng)養(yǎng)。我們發(fā)現(xiàn),通常日本的衛(wèi)生狀況要遠(yuǎn)好于其他亞洲國(guó)家。比如,在日本可以直接飲用自來(lái)水,但在其他亞洲國(guó)家就不行。
我們最初碰到問題的主要原因還是對(duì)日語(yǔ)理解不夠。我記得我們經(jīng)常去附近的肉店買肉。不管什么時(shí)候過去,肉店老板總是把肉切成薄片,他認(rèn)為我們買回去是用來(lái)做壽喜鍋。盡管我已經(jīng)學(xué)會(huì)了日語(yǔ)“厚”的說(shuō)法,但當(dāng)我說(shuō)“切得厚一些”時(shí),老板也只是把肉片稍微切得厚了一點(diǎn)點(diǎn)。過了好幾個(gè)星期,他才把肉切成牛排的厚度。
那時(shí),日本的計(jì)量單位復(fù)雜得不可思議。重量單位,從過去的“匁(もんめ)”(“匁”為日本的和制漢字,相當(dāng)于中國(guó)的計(jì)量單位“錢”,即1兩的1/10。日本現(xiàn)行貨幣中,5日元面值硬幣的重量正好為1匁。)變成“磅”和“千克”。每換一個(gè)地方,當(dāng)?shù)厥褂玫挠?jì)量單位都不一樣。盡管我們已經(jīng)開始學(xué)日語(yǔ)了,仍然經(jīng)常很難判斷要購(gòu)買食材的體積或重量。
我們陷入與語(yǔ)言的斗爭(zhēng)之中。當(dāng)鄰居來(lái)做客,我們請(qǐng)他們喝茶時(shí),他們會(huì)說(shuō)“結(jié)構(gòu)(けっこう)”。我們知道“結(jié)構(gòu)”的意思就是“好的”,但仍不能分清這句話的意思究竟是“好的,那我喝一點(diǎn)吧”,還是后來(lái)才學(xué)到的“沒事,我不喝茶”。這種曖昧不清的語(yǔ)言經(jīng)常讓我們深感困惑。例如,如果我們邀請(qǐng)別人來(lái)家里,他們經(jīng)常會(huì)用含糊的語(yǔ)言表示“好的,沒問題”。我們花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才終于分清他們指的是“不,謝謝”“讓我考慮一下”或“我們會(huì)來(lái)的”,其中的哪個(gè)意思。
送禮也經(jīng)常是個(gè)難題。人們來(lái)我家時(shí)總會(huì)帶禮物,這是習(xí)俗。我們?cè)噲D了解送禮人的目的。他們是想表示友好呢,還是希望我們能幫他們做些什么?所以,不管什么時(shí)候有人送禮物,都會(huì)讓我們感到一絲煩惱。我們?cè)噲D退還禮物,但有時(shí)事情似乎有點(diǎn)失控,我們發(fā)現(xiàn)和送禮人的關(guān)系變得有些緊張而不自然。有時(shí),送禮反而成為建立開誠(chéng)布公的友情的障礙。在日本兩年的最后一段時(shí)間,我發(fā)現(xiàn)當(dāng)我們不再互換禮物,或者只是偶爾贈(zèng)送禮物時(shí),我和朋友的關(guān)系變得更放松自然。
第二年,我們搬到了東京郊外的千葉縣(市川市)。我們搬過去是因?yàn)槿毡拘睦硇l(wèi)生研究所建在當(dāng)?shù)匾粋€(gè)二戰(zhàn)時(shí)期的閱兵場(chǎng)原址上。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后,政府將軍事場(chǎng)所逐步改為醫(yī)院、學(xué)校和大學(xué)。當(dāng)時(shí),市川只有十萬(wàn)常住人口,沒有現(xiàn)代化的公寓。研究所的人安排我們調(diào)閱有心理失調(diào)兒童的家庭檔案。我不得不找一個(gè)人幫我看這些檔案,因?yàn)槲耶?dāng)時(shí)還不能很好地閱讀日文材料,大家可以想象我看完一卷檔案需要花多久的時(shí)間。
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并不希望我們親自采訪有心理失調(diào)兒童的家庭。不過,他們通過當(dāng)?shù)貙W(xué)校校長(zhǎng)為我們安排了六個(gè)有健康孩子的正常家庭,可以每周采訪一次。后來(lái)我們才知道,這六個(gè)家庭都熱衷于家長(zhǎng)教師聯(lián)誼會(huì)活動(dòng),并被告知,如果他們每周接待我們的采訪活動(dòng)就可以免于承擔(dān)一年的家長(zhǎng)教師聯(lián)誼會(huì)各項(xiàng)義務(wù)。在之后一年的采訪中,我們卻不得不對(duì)原計(jì)劃做出修改,原本的想法是由我采訪丈夫們,蘇珊娜采訪妻子們。結(jié)果卻往往變成,我們一起采訪妻子們和孩子們的時(shí)候,比采訪丈夫們的時(shí)候多多了。因?yàn)檫@些丈夫們的工作時(shí)間非常長(zhǎng),以至于很難約到采訪時(shí)間。
住在市川時(shí),我們打算像我們的日本鄰居那樣生活。即使很困難,我們也嘗試成為社區(qū)的一分子,卻始終被作為外來(lái)者對(duì)待。有一次我們邀請(qǐng)六個(gè)家庭來(lái)家里聚會(huì),想向他們展示,我們能以日本人的方式做任何事情,但后來(lái)發(fā)現(xiàn)讓他們失望了。母親們告訴孩子要去一個(gè)美國(guó)人家里做客,想要見到更多的美式生活方式。他們想親身見證外國(guó)人生活是什么樣的。我們?cè)趯W(xué)他們,他們卻想從我們這兒學(xué)西方的生活模式。我們開始了解他們,就像了解自己一樣,從他們身上開始逐漸了解日本人。
我漸漸意識(shí)到,被日本人完全接受的希望微乎其微,某種程度上我始終是一個(gè)外來(lái)者。一旦接受這樣的現(xiàn)實(shí),我會(huì)感到反思過去的想法可笑,也不會(huì)對(duì)此感到煩惱了。
不過再反思一下,最開始那幾天,日本人也會(huì)因?yàn)橥蝗怀霈F(xiàn)的外國(guó)人而不像平時(shí)那樣自在。我記得當(dāng)我走進(jìn)百貨公司時(shí),盡管我的基礎(chǔ)日語(yǔ)足以勝任日常對(duì)話,但有些售貨員只要一看到我,就會(huì)立刻叫來(lái)經(jīng)理或其他可以用英語(yǔ)對(duì)話者來(lái)應(yīng)付我。我是一個(gè)外國(guó)人,因此,我不應(yīng)該能夠聽懂日語(yǔ),同樣的邏輯是,也不可能理解日本人。
不過積極的一面是,沒有完全成為當(dāng)?shù)貓F(tuán)體或社區(qū)的一部分,讓我獲得更多的自由。我可以避免一些禮尚往來(lái)以及約束日本人的人情世故。
回首在日本的兩年,是我和蘇珊娜這段婚姻中最快樂的時(shí)光。作為社會(huì)科學(xué)家我們能很好地一起工作,花很多時(shí)間一對(duì)一地討論日本家庭。
至于蘇珊娜作為女性在日本社會(huì)的經(jīng)驗(yàn),那時(shí)女權(quán)意識(shí)或者女權(quán)運(yùn)動(dòng)即使在美國(guó)也尚未真正具有影響力,到日本的外國(guó)女性也沒有關(guān)注日本女性是否被不公正對(duì)待。實(shí)際上,蘇珊娜主要關(guān)心的是想出如何經(jīng)營(yíng)好一個(gè)家庭的方法,以及在一個(gè)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會(huì)中照顧好我們的兒子。
這里沒有讓蘇珊娜可以方便地找到她想要的食物的超市。為了買食物和日常必需品,她不得不去鄰家小店,并艱難地使用日語(yǔ)交流。
我想那時(shí)候從美國(guó)來(lái)的女性,無(wú)論單身還是已婚,都會(huì)遭遇很多適應(yīng)問題;與現(xiàn)在相比,當(dāng)時(shí)兩個(gè)國(guó)家在生活水準(zhǔn)上的差距要大得多。如果我們想要美國(guó)的藥物,就不得不去位于東京市中心有樂町的藥房購(gòu)買。我們也沒法經(jīng)常在鄰家小店中找到要買的東西,因此每到周日就不得不去尋找能買到那些東西的商店。

傅高義當(dāng)時(shí)的妻子蘇珊娜
蘇珊娜對(duì)日本女性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在日本的外國(guó)女性,比如那些跟隨丈夫到日本做生意的美國(guó)妻子。她們一般是在丈夫的公司內(nèi)見到日本家庭主婦,通常對(duì)日本主婦最深刻的印象是正式而拘謹(jǐn)。她們回到美國(guó)后,可能會(huì)和自己的朋友說(shuō):“呃,日本人很羞于開口。”
出于研究的需要,蘇珊娜會(huì)登門拜訪日本的家庭主婦,往往會(huì)度過一段很棒的時(shí)光。她很喜歡那些曾拜訪過的日本主婦。當(dāng)她們想要了解蘇珊娜的時(shí)候,非常放松開放。即使在四十年后,這些主婦中還有蘇珊娜最好的朋友。蘇珊娜從這些女性身上學(xué)到了很多東西:如何管教孩子,如何做出各色食物,如何調(diào)教自己的丈夫。我想,蘇珊娜將這些與她對(duì)話的日本主婦看作一面鏡子,可以從中看到她自己。不過無(wú)論何時(shí),只要她們的丈夫在場(chǎng),她們就拘謹(jǐn)?shù)枚唷?/p>
美國(guó)妻子可能會(huì)為日本妻子感到遺憾:“可憐的女人,她不能和她丈夫一起出去。”但是當(dāng)我太太和那些日本妻子交流時(shí),她們的說(shuō)法翻譯過來(lái)就是:“誰(shuí)要和他們一起出去啊,既拘謹(jǐn)正式又無(wú)聊,我還不如和自己的女性朋友們一起出門,更好玩。”在接觸日本中產(chǎn)階級(jí)家庭的主婦后,蘇珊娜對(duì)事情有了非常不一樣的看法。
其中一個(gè)原因是,日本主婦非常享受和蘇珊娜的交談,她們喜歡問她一些美國(guó)家庭的細(xì)節(jié)。主婦們非常有預(yù)見性地看到了一個(gè)全新的、更國(guó)際化的社會(huì)即將在日本逐步發(fā)展起來(lái),她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為這個(gè)更國(guó)際化的時(shí)代做好準(zhǔn)備。
因此,她們明確想要了解美國(guó)女性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提問總是一個(gè)接一個(gè)。她們會(huì)考慮這些給出的既定方法,是否能接受,能否適用于日本的相應(yīng)情境。
最后她們會(huì)想出自己的方法。面對(duì)這些深謀遠(yuǎn)慮的日本中產(chǎn)階級(jí)女性,蘇珊娜完全不覺得她們是受壓抑的,并認(rèn)為在日本這樣一個(gè)男人和女人起居時(shí)間不同步的情況遠(yuǎn)甚于美國(guó)、孩子和母親的關(guān)系更為親密的社會(huì)中,這些中產(chǎn)階級(jí)女性是非同尋常的社會(huì)組成要素。
某種意義上而言,父親更像一個(gè)只會(huì)在晚上和周末出現(xiàn)的遠(yuǎn)方客人,而家庭的核心群體是母親和孩子。
(完)

以上選摘自傅高義作品《日本還是第一嗎》,限于篇幅,略有刪減

傅高義作品《日本第一:對(duì)美國(guó)的啟示》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chǎng),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qǐng)澎湃號(hào)請(qǐng)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