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能的中國工廠
疫情爆發以來,全國日均口罩缺口高達2億個,從兩大石化公司和上海五菱這樣的國企,到私企富士康、比亞迪,多家企業開始跨界生產口罩,各大媒體也爭先報道。

全網報道“企業口罩轉型”
快速轉型可以說是中國工廠的專長。
1939年創刊的山東大眾日報就曾在抗日戰爭時期,建立商店、油墨廠、造紙廠,以供內需。抗戰中期,日軍大量封鎖根據地物資,并限制中方報紙的流通,大眾日報在內的多家報社都需要自力更生。大眾日報在1941年左右開辦‘利聚永’商店,并以當地獨特站銷往外地的方式,賺取資金,輾轉購買油墨、紙張等原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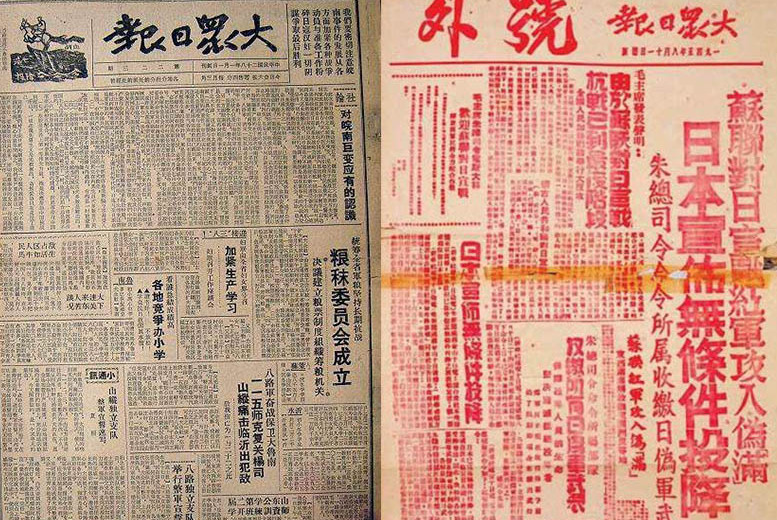
大眾日報舊刊
到了80年代,大量軍工廠面臨停產危機,被迫拓展新業務、二次創業。核工業504廠轉型生產雪糕,南京長江雷達制造廠生產電風扇,西安航空發動機公司改生產腎結石碎石機等等。

504廠雪糕本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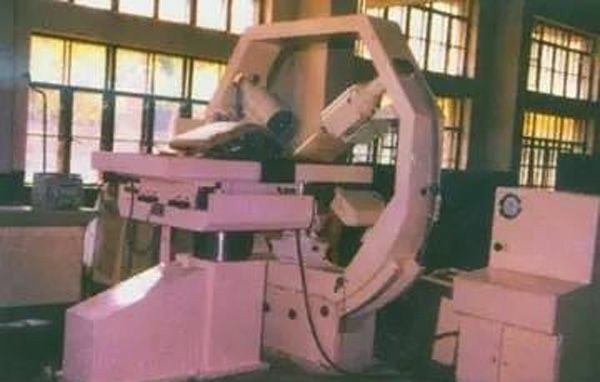
西安航空發動機廠NS15體外震波腎結石碎石機
之所以說這些“跨界”難得,是因為這幾個案例不光光是“上游變下游”這么簡單。也就是,不是像生產發動機的,改生產汽車這樣,利用自身的優勢,擴展到以已生產產品為原料的商品。簡單地說,這種難度大概類似突然讓一個碼農去演戲。
說到中國工廠,就不得不說剛剛獲得第92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美國工廠》,雖然名為“美國工廠”,但講述的是中國玻璃大王曹德旺的福耀集團在美國重開通用汽車工廠的故事。

電影《美國工廠》宣傳片
獨立電影人Steven Bognar和Julia Reichert所制作的《美國工廠》,記錄了2009年通用汽車公司GM關閉在俄亥俄州Dayton的流水線工廠后,世界最大的汽車玻璃廠商——福耀集團,將該廠收購,并于2015年左右招工、重新開廠。
“美國工廠”福耀玻璃(美國)FGA一開始由美國白人經理人所管理,中層管理者為中國調來的技術人員,工人則為Dayton本地各種族裔的低收入人群或曾經的中產階層。后期因曹德旺判定美國管理者無法達到生產目標,改聘任熟悉中、美的華人為FGA最高執行人。這也讓美國工人更加斷定他們是在“中國工廠”打工,而不是本土化的“美國工廠”。
影片最吸引人的,應該就是通過對美國藍領工人在中國人開設的美國工廠再就業的經歷,這期間所遭遇的文化沖突,而影射兩國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不同理念。要知道這部紀錄片的放映媒體Netflix奈飛,可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制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的合作伙伴。

左至右: 導演Steven Bognar,前美國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
導演Julia Reichert,前美國總統Barack Obama
美國本土媒體紐約時報、NPR、The Atlantic等,一邊倒地熱議著《美國工廠》所展現著人們對“自由”的向往。包括從福耀總部調職到Dayton的中國工人,看著美國廣闊土地時的感嘆;也包括美國工人為了實現自由民主,堅持要成立工會、保障個人利益。小編相信這是很多人的觀后感,不單是美國人,但同時,小編也看到原GM工廠會shut down有其必然性。
影片多處以中國人代表的中層管理者指責“美國工人效率低”,而美國工人抱怨“工廠不能保障安全穩定的工作環境”,設置了兩大對立面。中國人覺得要提高產能使工廠盡快盈利,而美國人覺得要在安全、有指導的環境下一步一步來。小編只能說,站在各自的角度,雙方都沒有錯。作為在中美兩國都工作過的人,小編贊同“大部分中國人更看重結果,大部分美國人更看重過程或進展 (紐約金融行業除外)”,這樣的說法。
小編個人覺得比較耐人尋味的一幕是,有一位中年女性白人工人 (抱歉請允許我在這里stereotype一下)吐槽說,“the Chinese supervisors don't even pat on my back”,這句俚語的換成中文就是“中國主管們都不拍拍我、鼓勵我”。大家看到可能第一反應是“什么鬼?又不是小孩子,還要拍拍?”就像華人總經理后來在片中提到的,多數美國人從小是被鼓勵著長大的。華裔小孩得了A-可能要回家跪鍵盤,而中產白人小孩得了D家長可以會說“好棒哦!及格了!下次會更好的!”
為什么強調中產白人呢?美國的其他少數族裔——黑人、阿拉伯裔等大多還是像亞裔這樣,盛產虎爸虎媽。上層白人急著進常青藤,底層白人比較少,我們之后會單獨寫一篇探討美國的階級。現在我們僅需知道的是,美國白人中產是占美國人口大比重的,他們也是生活在“美國夢想”American Dream里的那些人。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劇照
類似“鼓勵”這樣的小細節,逐漸聚積,最終激化了美國人所代表的工人和中國人所代表的福耀工廠之間的沖突。
比起提高自己的技能或效率,更多的工人為了實現在工廠的“自由”,保證自己可以不被逼迫生產額外的汽車玻璃,保證餐廳的微波爐是正常工作的,保證自己的薪水可以養家,他們選擇了上街游行,組織投票設立工會。小編并不是說他們有這些要求是錯的,反而小編覺得這是個人權益的一部分,但問題是“如果飯碗不保,談個人權益不覺得奢侈嗎?”
影片中的一位工人,因多次罷工并參加示威活動,最終被解雇,這時這位工人說道“如果知道自己可能丟掉工作、失去經濟來源,回到一開始,可能會再想想罷工抗議是否值得”。
可能有些人會說福耀不道德,或是不尊重美國本土文化,曹德旺也因為開除罷工的人、阻止工會設立,在影片播出后受到了外界的抨擊。客觀來說,工會這件事跟是不是中國企業家沒有太大關系,這只是典型的投資人理念,特朗普也不會想自己的公司有工會,因為對他們來說工會就代表罷工、代表生產停滯,每分每秒燒投資人的錢。
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人之初,性本?》中提到,善惡難辨,或者說善惡在生存面前不值一提,成人的世界就是這么殘酷。雇員有權游行,雇主便有權決定雇員去留,事關商業利益,就無法要求人人“圣賢”,在商言商,這也是商業規則。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上街抗議
中國因為人口基數龐大,競爭激烈,人人都要努力往上爬,不然就會優勝劣汰。
FGA初期,美國人帶領的管理團隊第一次到福耀總部參觀,被生產效率、工人間的密切配合度都震驚到。中國工廠比美國工廠工資低、安全保障低,但產量翻倍。
中美兩國的文化差異造就了兩種狀態,中國工人都這么拼,中國能成為制造大國也就理所應當。
美國經理參觀福耀廠這件事,也就觸碰到了小編個人認為《美國工廠》最大的一個bug,就是單向文化融合(one-way cultural adaptation)。指的是,當兩個擁有不同文化的個體、團隊或企業,需要合并為一體時,只有其中一方吸收對方的文化而進行內部調整,另一方表現出抵制的態度。這個復合詞是小編造的,查詞典應該是沒有,但意思是這個意思。
在《美國工廠》中,只有福耀努力適應美國文化,但美國工人不能接受中國的“福耀文化”。

福耀玻璃(美國)FGA美籍管理者參觀福耀集團位于中國福建福州總部的工廠
美國經理回到Dayton后,實行了中國工廠里班組、列隊的機制,但并沒有起到凝聚美國工人的作用。
美國工人一直吐槽中國人——說好了建設“美國工廠”,可是很多事情還是按照中國的來,但反之,他們是不是也拒絕被中國企業的運營方式同化呢?
盡管片中中美管理者都在強調“一個福耀”,公司文化而非中國或美國文化,工人也無法接受。
如果這僅僅是另一個美國公司的文化,美國工人對“同化”的反抗力是否就就小一些?種族歧視就又是另一個論題了。
如果一個美國企業家以中國人的方式提高產能,這可以被稱之為革新;而中國企業家以中國方式操作,就叫文化洗腦,有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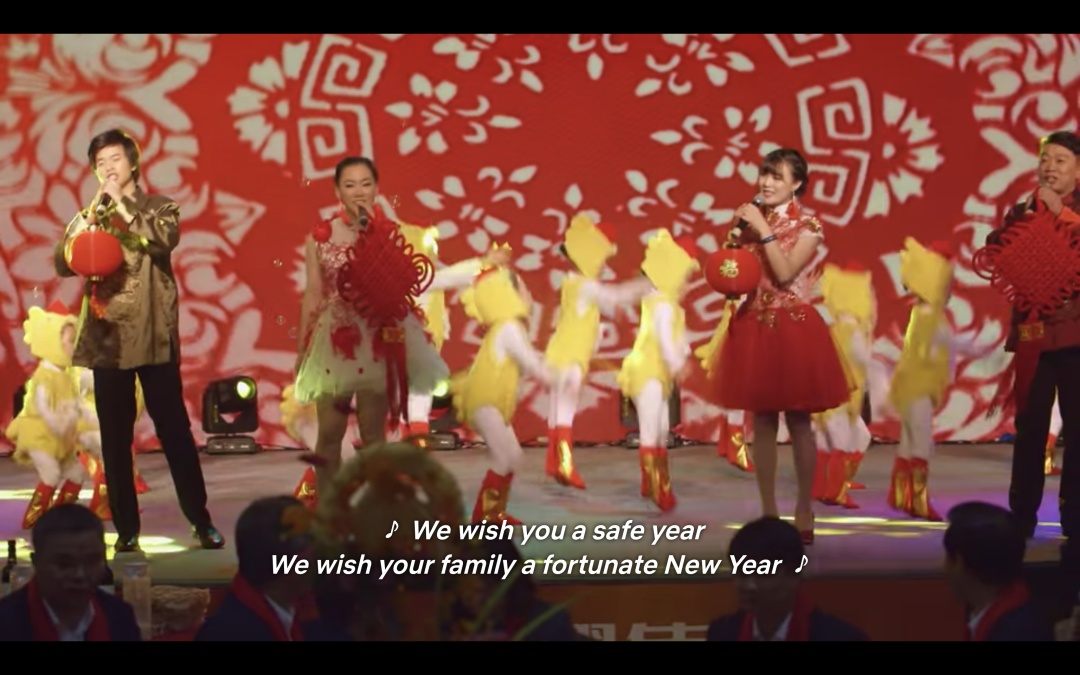
福耀年會(截圖自《美國工廠》)

福耀年會(截圖自《美國工廠》)

福耀年會(截圖自《美國工廠》)
之所以中國工廠的運營模式很難被西方人接受,除了文化差異,還有就是游戲規則。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所著《世界秩序》一書中說道,“中國幾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遵從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的國家,這也就解釋為什么中國強大而西方世界不服”。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來源于1648年歐洲各國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和平停戰協議,結束了歐洲諸國間幾十年的戰爭,也奠定了當代國際法的基礎。大家可能會想說,這跟經濟、政治也沒什么關系吧?之所以改稱其為體系,是因為在之后的幾個世紀,歐洲資本大國制定的商業、社會原則都深受《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影響。這就像儒學對中華文化的影響一樣,根深蒂固。
英、法等國殖民美洲、建立美國遵循的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日本、韓國這些東亞國家自明治維新后也逐漸被同化,因此中國可以說是獨樹一幟。雖然全球化、數字化及社交網絡的傳播,讓外國人對中國有了更真實的認識 (知道現在中國男子都不梳辮子了),但中國的“自成一派”,依舊是不被他國所廣泛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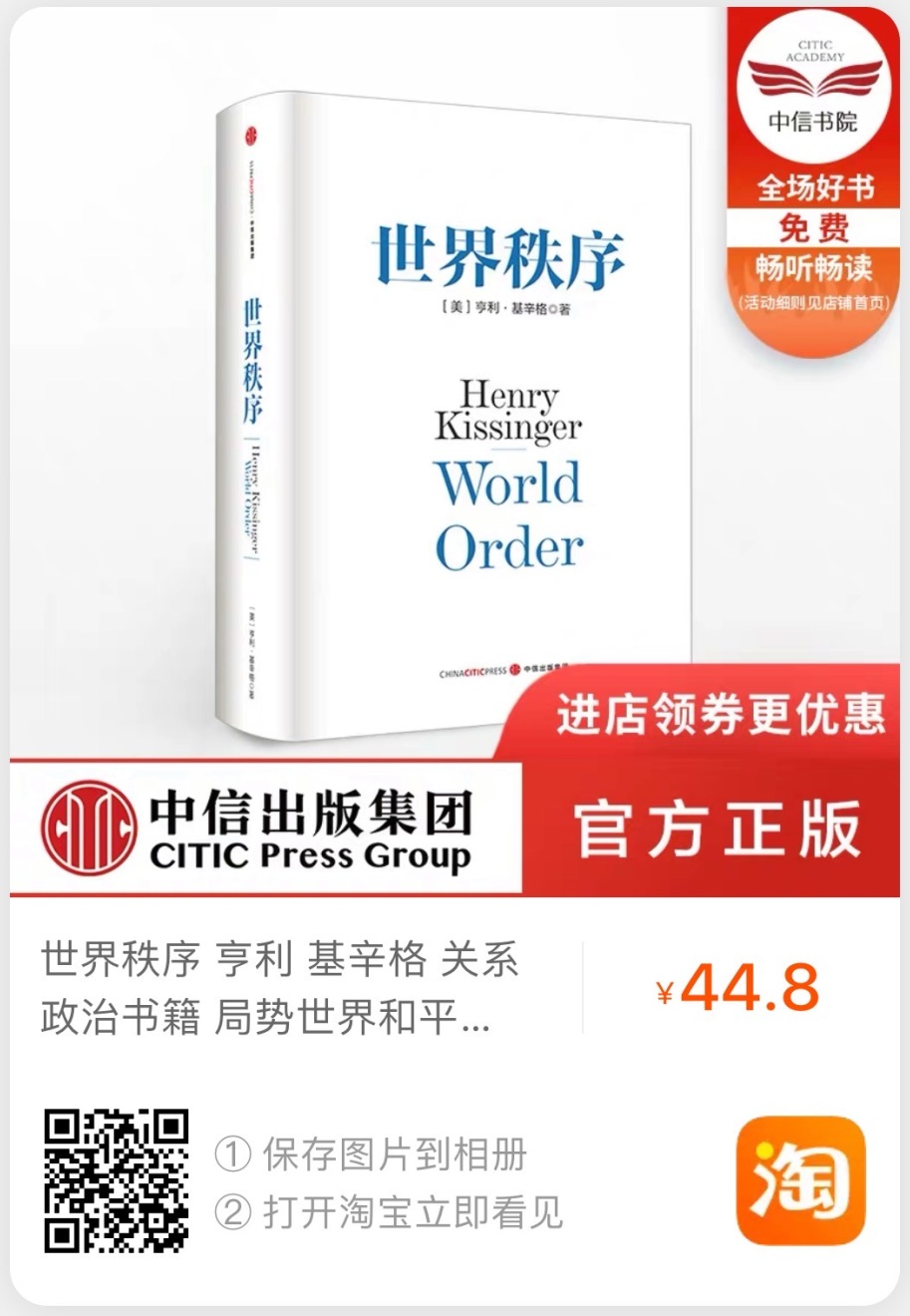
p.s. 小編良心推書,不收回扣,童叟無欺!
這就是為什么外國人經常想不明白,“哎?中國人怎么還能這么干?”
而大家往往對不同想法、思維模式,尤其是少數人的意見,是不接受的,就像我們上一期聊到的“現在社會的本質是少數服從多數”。
寫這篇文章也不是說小編有多“紅色”,反而是想表達,我們要在世界上被認可,真的還是“long way to go”——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為我們在用我們自己制定的規則,而這目前是不太被國際市場所認可的。
加上偶爾哪兒來個不法商人,賺快錢,搞得“中國商人”這塊牌子在海外難以立足。
追根究底,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外國人看到好多中國駐外人員一到國外就開始自己種地,可能會說“你們中國人好厲害啊!人人都會種地”,但他們可能不會想到曾經四萬萬中國人糧食短缺的艱苦歲月。就好像很多人看到猶太人會賺錢,卻忘了猶太人被迫流亡的幾千年。
歷史總是容易被遺忘的,但希望教訓不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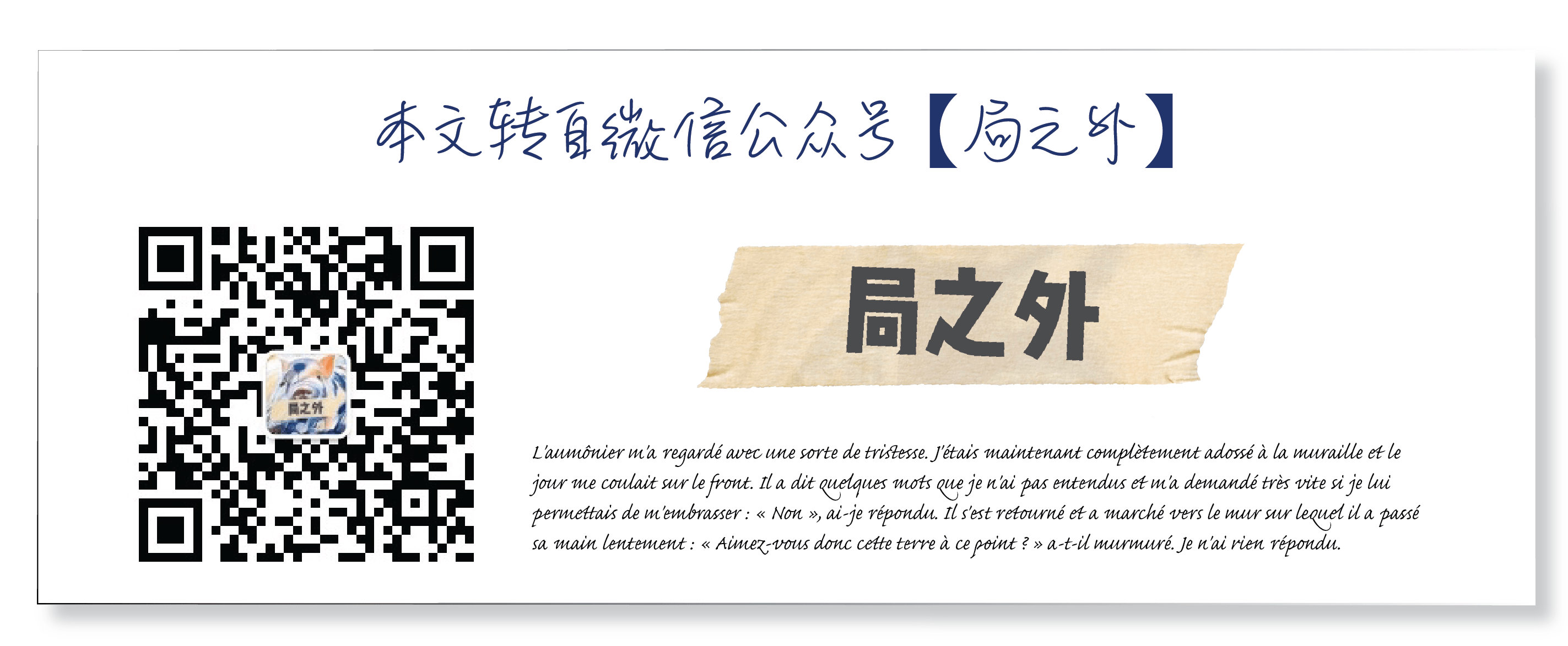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