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線上讀書會|張忌、弋舟:每當變幻時,尋找心安處
疫情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從前習以為常或忽視的現(xiàn)實接連出現(xiàn)。在這段變幻無常的日子里,我們要如何安頓自己的內心?
張忌和弋舟都是善于書寫日常的青年作家,他們一個偏愛煙火氣十足的生活現(xiàn)場,一個更加關注人物心靈與精神投射。等到疫情結束,兩人都最想去吃一頓熱氣騰騰的火鍋。
近日,他們接連來到中信出版 · 大方主題分享會,與讀者線上交流他們的寫作與生活、困境與日常。
如何書寫困境與痛苦
1970年代末,秋林被分配到鄉(xiāng)鎮(zhèn)一個偏遠的南貨店當售貨員。80年代末,供銷社來了一個新主任,將他調到縣供銷社當秘書股股長。秋林在90年代來臨的時候,似乎迎來了人生的一個高峰。但在這種光鮮背后,秋林固有的價值觀也在發(fā)生著劇烈的沖擊……

這是張忌新作《南貨店》里的故事。小說以江南城鎮(zhèn)的南貨店為背景,描述了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秋林以及他身邊人漫長而又跌宕的人生。
“人的困境是怎么面對自己。”張忌舉例,《南貨店》中有個馬師傅,從小跟著父親做生意。馬師傅所有的邏輯都是按照他父親的生意經來的,后來一旦他身邊的事物發(fā)展超出了肚子里的那盤生意經,那么他的困境就出現(xiàn)了。
《南貨店》里還有個男人,叫大明,他知道自己的老婆跟別人私通,但他不計較,甚至可以與老婆的情人坐在一張桌上吃飯。但就在吃一頓團圓飯的時候,老婆把酒壺里的最后一口酒倒給了另外那個男人。這一下,讓大明服毒自殺了。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我認為生死是最大的問題。但是從文學的意義上來講,我認為是活還是死并不是最重要的。”張忌說,“怎么樣活、怎么樣死才是最重要的,這是文學上的意義。”

弋舟說到,有的痛苦寫起來相對好理解一些,比如戰(zhàn)亂、饑餓,“但你不能因之就去否定那些人在不愁吃穿時的痛苦。譬如《紅樓夢》,如果站在前一個認知中,你壓根無從理解大觀園里那些男男女女的苦惱何在?所以人類恰恰在這點上跟動物區(qū)別開來,人類有巨大的精神要求。”
他提及張忌的《出家》與《南貨店》,認為這兩部作品都是在文學的層面上回答這樣的問題。“尤其是《出家》,我把它與余華的《活著》做過對比。《活著》中的苦難,相較而言還是容易理解的,因為它有著特別直接和顯見的原因——戰(zhàn)亂、動蕩。那么我們承平日久,但所有人的內心并非沒有痛苦,這時作家就有義務把人這樣的內心感受捕捉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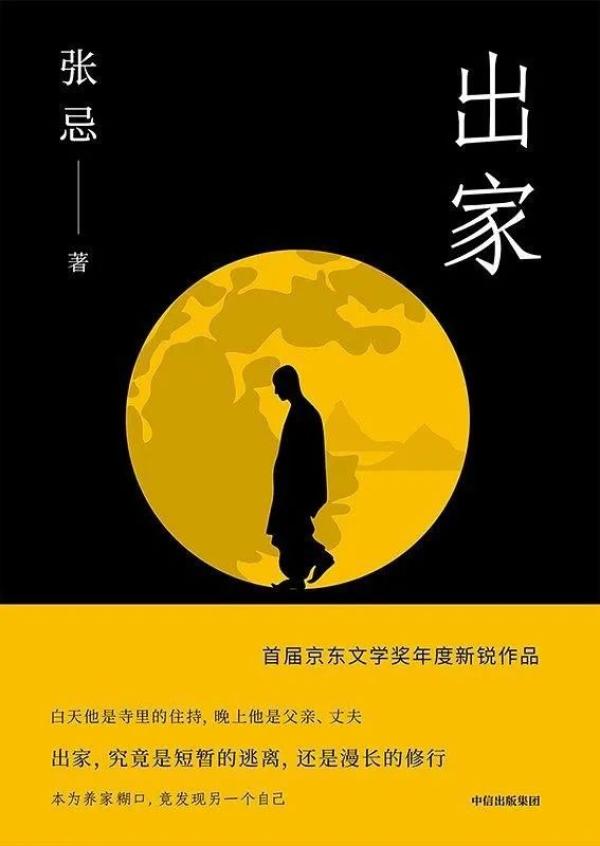
寫作源于生活,但生活不是作家需要專門觀察的目標
說起《南貨店》的起源,張忌說到了自己的爺爺。
“2016年我爺爺去世,我跟我父親聊,談到了我爺爺的父親。好像是一個下雨天,我爺爺的父親穿著蓑衣去余姚打官司,卻一直沒有回來。我父親也不是特別清楚后來的故事。”
就這么寥寥幾句沒有下文的對話,讓張忌有了一種特別奇妙的感覺:“從我開始往上到我父親,再到父親的爺爺,就變成了一幅畫面。一個身穿蓑衣在雨里走的人,去余姚打官司,從此就消失了。但是那些人,我的父輩和他同時代的人,還有那個時代,他們都在那個時代活生生存在過的,但最終卻以這種畫面的形式存在。”
張忌因此想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父母親人也都是陌生的,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其實局限于一個很窄的角度。再往大的方面去想,身邊的社會曾經是什么樣子?為什么變成這樣?到底經歷了什么?種種想法勾起了他巨大的創(chuàng)作欲望,于是有了這本《南貨店》。
在弋舟看來,生活可能不是作家需要專門觀察的目標,因為作家就身在其中,而且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一個又一個的事件,它本身就是人們一個又一個的感受。從這個意義上,作家擁抱自己的感受,捕捉自己微妙的情感變化,這其實就是生活本身。
他說:“作家的任務可能在于給予大家都司空見慣、習焉不察的生活現(xiàn)場某種精神發(fā)現(xiàn)——究竟什么地方出了問題?同樣一件事發(fā)生的時候,我們從這個事的背后看到了什么樣的精神感受?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存在主觀地、故意地將自己從生活中抽離出來,顯然也是無從抽離的。生活是完全沒有辦法去決定的事實本身,它就像一個大容器,只要你活著,你必定跟它發(fā)生千絲萬縷的關系。”
精神世界永遠提供人之為人的保障
寫完《南貨店》后,張忌最近沒有寫作,甚至想刻意離開文字一段時間。他看到梁鴻在微博寫下“和災難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顯得過于輕浮”,一時深有同感。
“覺得特別沮喪,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一開始會看看書上上網,沒多久就對什么都提不起興趣,這種感覺特別奇怪。其實我平時也不怎么出去玩,不大喜歡出門,但在這個特殊時期里就有一種特別大的沮喪,好像突然不知道做什么才是有意義的。”張忌感慨,以后回頭看這種感覺,可能也會具備某種價值。
弋舟同樣在這個假期經過了漫長的煎熬,努著勁兒想要重新恢復自己的秩序。他前兩天剛剛寫完了一個短篇,在《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之后跟中信大方簽下《庚子故事集》,“簽合同就意味著有交稿的日期。其實也從來沒有像這樣的時候,感覺寫作本身能夠給人帶來的那種支撐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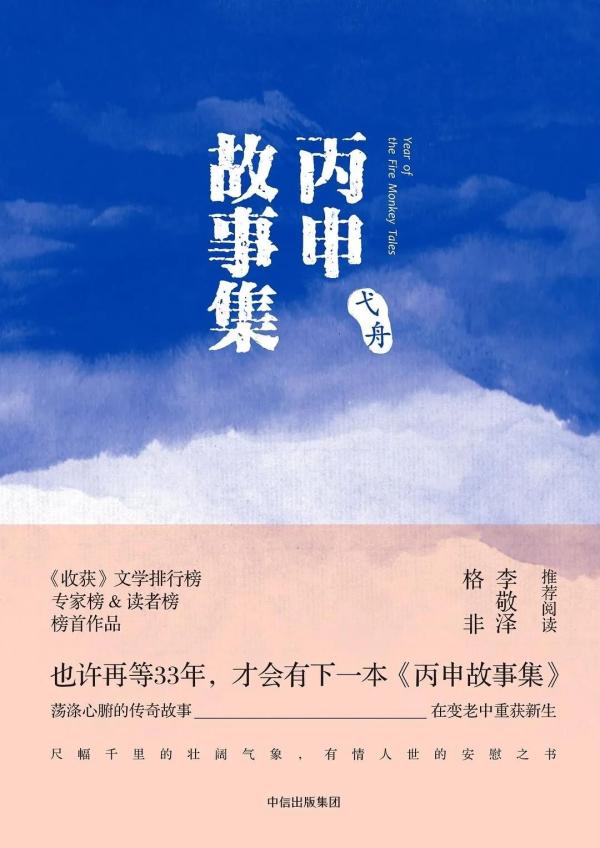
“面對疫情,我也會質疑文學的意義究竟何在,能起什么作用,自己的寫作是不是在一定意義上顯得淺薄和輕浮?但是當我努力重新回到文學的世界,還是會確認她的力量。”他告訴讀者,這樣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上也被反復證明過,比如在奧斯維辛,很多猶太人入獄時還帶著小提琴、文學書籍,“除了嚴酷的生活事實本身之外,人類始終不曾喪失過對于精神生活的依賴與追求。”
“在很大程度上,當我們對這個堅硬的世界無能為力時,唯一能給人以某種力量的,可能只能從精神世界里去尋求。比如現(xiàn)在短時間內暫時研發(fā)不出有效的抗疫藥品,這受限于客觀的科學規(guī)律,在這個時候,人是相當的無力。那你怎么辦?但那個極富滋養(yǎng)的精神世界,還永遠存在于我們人類物質生活的背后,給我們提供強大的人之為人的保障。”弋舟如是說。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