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歷史劇︱《切爾諾貝利》:文藝作品與公共史學
按:這是一篇“零零后”學生做的采訪,轉載自《復旦青年》第306期第7版,有改動。作者為《復旦青年》記者劉冠麟(復旦大學2019級中文系本科生),被采訪人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朱聯璧,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帝國與英聯邦史、民族與民族主義、全球史、公共史學。
2019年,HBO電視網推出了迷你劇《切爾諾貝利》,該劇講述了19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救災與科學家揭露事故原因的故事。這部僅有5集的歷史劇實現了口碑的爆棚,并在中國的年輕觀眾中引發了激烈的網絡論戰。部分網友認為這部劇思想深刻、符合歷史事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另一派則認為,這部劇站在西方立場上抹黑蘇聯。兩派觀點針鋒相對。
這部電視劇參考了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一書。阿列克謝耶維奇擅長紀實性文學作品,用與當事人訪談的方式寫作,以第一人稱記錄他們的真實經歷,她曾獲得20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但是在中國觀眾評價《切爾諾貝利》時,批評這部劇的一派言之鑿鑿地聲稱:有被采訪者起訴了阿列克謝耶維奇,認為她沒有理解自己在說什么,并且篡改了自己的話。其實這些起訴事件是針對《鋅皮娃娃兵》一書的,但阿列克謝耶維奇曾多次因自己的創作而被告上法庭,這也是事實。
公共史學在快速發展,同時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與歷史相關的文藝載體也在不同國家的受眾間快速傳播,從而產生新的碰撞火花。我們希望通過對朱聯璧老師的采訪,讓讀者們對以影視、文學等文藝作品為載體之一的公共史學能有更多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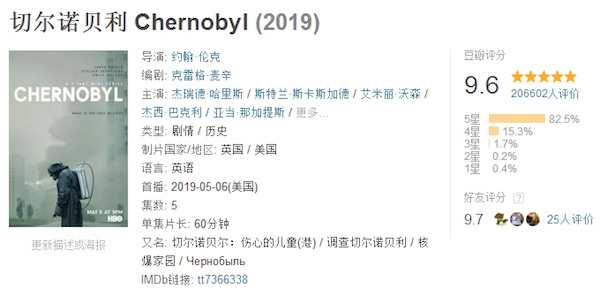
您可以簡要地介紹一下“公共史學”的定義、范圍和意義嗎?電視劇《切爾諾貝利》和紀實文學《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是否能算作公共史學的一部分?
朱聯璧:王希教授在《誰擁有歷史?美國公共史學的起源、發展與挑戰》中引述了不同時代對美國的公共史學的定義,可以作為理解這個概念的切入點。這篇文章是國內比較早的系統梳理美國公共史學的文章。你提到的電視劇和紀實文學都是屬于公共史學這一范疇的,在美國可以被細分到“文化史學或大眾史學”(cultural or popular history)這一類別。王希教授的論文提到過這一點。因為我自己只是對英國的公共史學稍微有點了解,你提到的電視劇是從HBO這個平臺推出的,可能還是要放到美國對公共史學的定義里來理解比較合適。
王希教授的文章中引述了美國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歷史系教授羅伯特·凱利(Robert Kelley)對公共史學的定義。她認為,“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公共史學指的是歷史學家的就業(方式)和在學術體制外——如在政府部門、私有企業、媒體、地方歷史協會和博物館,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領域中——(所使用的)史學方法。公共歷史學家無時不在工作,他們憑借自己的專業特長而成為‘公共進程’(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當某個問題需要解決,一項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資源的使用或行動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規劃時,歷史學家會應召而來,這就是公共歷史學家。”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出現的定義。王希教授認為,其中的“公共”既可以理解為“公共事務”(如政府部門和社區的決策、由納稅人支持的中小學歷史教學等),也可以理解為“公眾社會”(包括向公眾傳播信息和提供知識的媒體、電影、電視、出版業等),還可以理解為“公眾文化”(如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歷史遺址、紀念場所或公眾紀念活動等)。公共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運用歷史學家的知識與技能,在“公共領域”中發揮作用。而到了2007年,也就是公共史學在美國得到長足發展之后,美國的全國公共史委員會認為:公共史學是一場運動(movement),一種方法論(methodology)和一種方法(method),目的是“推動對歷史的合作研究與實踐”。公共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將“自己的特殊見識”以“易懂的和有用的”方式傳遞給公眾。盡管這個定義已經包括了大量可以被稱之為公共史學的實踐,但在參與公共史學的人而言,這個定義依然存在問題。
此外,從實踐的角度來說,各國公共史學都有解決歷史學博士生或研究生就業問題的目標,但同時也負責向整個公共領域中的不同群體還有專業的歷史學家提供公共歷史這種文化產品。在這個過程中,既滿足了大眾對歷史主題的文化產品的需求,也可能會沖擊學院派的歷史研究,豐富對歷史的解釋。
我個人認為可以借鑒王希教授的觀點來理解什么是公共史學及其包括的范圍。無論是從產出還是從人才培養來看,美國的公共史學確實發展最為成熟的,是理解公共史學的很好的切入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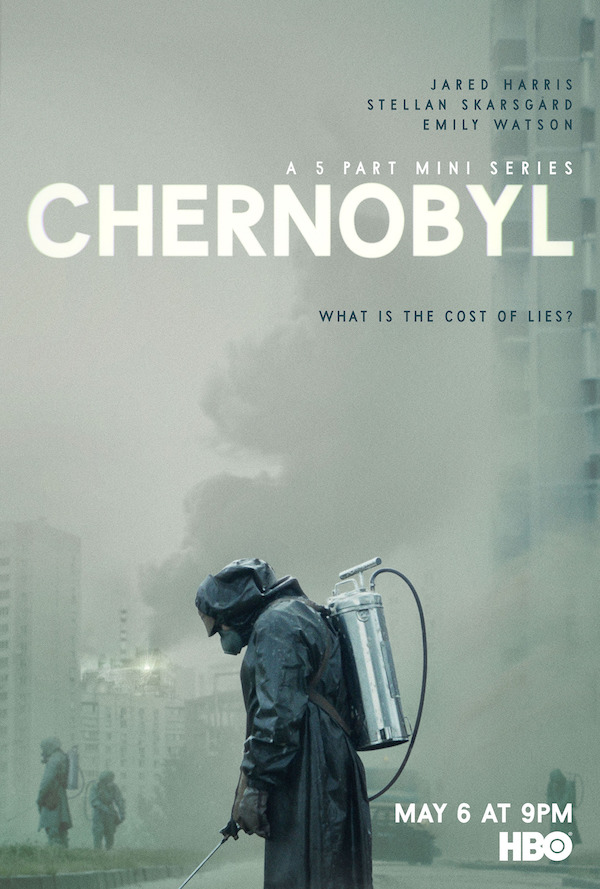
《切爾諾貝利》本身是一部電視劇而非紀錄片,這一點比較清晰;但是《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究竟是一部抒情性很強的文學作品,還是像作者她自己認為的那樣,是一種比較真實的、類似于口述史的作品?
朱聯璧:我想你這個問題關注的重點不在于《切爾諾貝利》這本書到底是文學作品還是歷史學作品,而是作品對歷史的呈現有多可靠。公共歷史學家是可以被培養的,美國英國都有公共歷史學的學位,獲得這個學位的人接受的還是歷史學的訓練,“求真”是書寫公共歷史的前提。但業內并沒有嚴格規定公共歷史的產品必須是“真實”的,畢竟到底什么是“真實”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再者,并非只有職業歷史學家才可以從事公共歷史有關的工作。有不少口述史研究者都有新聞從業人員的背景,阿列克謝耶維奇原本也是一個記者。她沒有獲得有關口述史的專門訓練并不意味著她的作品就不可以被歸入口述史和公共史學作品的范疇。她自己如果認為這是“真實呈現”,而其他人認為不是,也不能就說阿列克謝耶維奇是想寫“虛構的歷史”。并不是文體(小說還是口述史)決定了文本的可靠性,而是要從文本形成的過程來看到底是不是可靠的。對歷史研究來說,即便是不可靠的、完全主觀性的記錄,也不代表不能呈現歷史真實。探究其中的“不可靠”,或者是和其他的資料沖突的部分,可以獲得另外的對歷史真實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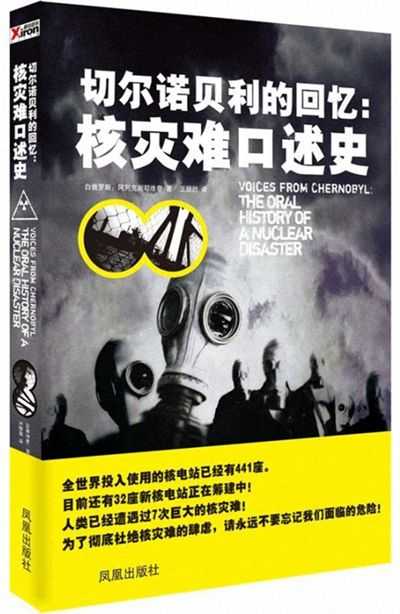
從阿列克謝耶維奇被受訪者起訴這一事件,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所謂的“口述史記錄”有時候和受訪者的本意有分歧。那么這種分歧是因為阿列克謝耶維奇堅持自己對于歷史的看法,在聲稱“紀實”的作品中投射自己的價值判斷,使得分歧出現;還是口述史記錄或者是紀實文學的記錄和寫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就會出現誤解、失真的現象?
朱聯璧:這些問題涉及到的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我建議你請教歷史系的陳雁教授,她開設了關于口述史的課程,你的問題應該可以在她這里得到更專業的解答。而就我對口述史非常淺薄和有限的理解,歷史文本都不可避免地帶有作者或創作者的主觀色彩。即便作者的目的是書寫“可靠、客觀”的歷史,寫出來的文本依然可能被讀者認為是“不可靠的、主觀的”。如何判斷文本是否可靠,可以看能不能經得起互證。口述史作為歷史研究的資料不應該是唯一的信息源,所謂“孤證不立”,必須要結合其他材料來看,找到一致和沖突的地方,再由寫作者甄別、解釋和取舍。這個過程得到的不一定是和文本直接相關的“歷史真相”,有時候歷史學研究者關注的是不同文本之間差異的形成過程中體現了怎么樣的歷史真實。而如果研究者只是想探究和文本直接相關的“歷史真相”,互證也不見得就能得到最可靠的結論。歷史研究只能無限接近歷史真實,但歷史真實的復雜性太大,很難有單個文本可以提供唯一可靠的“歷史真相”。甚至即便提供了,也會因為讀者的立場不同,認為那些表述是或者不是真相。
阿列克謝耶維奇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從專業的口述史的角度去評價她的作品,難免會被認為有不可靠的地方。再者,在她寫書的時候,是否參考了檔案,還是多數文本都是她對于采訪者的語言的闡釋,這些是不清楚的。就算她的方法是可靠的,也不見得就能寫出讓所有被采訪的人都認可的作品。說出一句話的人對自己表述的認知,和聽到這句話的人的理解本來就很難完全一致。但是否一定是聽這句話的人有意誤讀,就只有聽這句話的人才知道,甚至這個人自己也不知道。除了對語言理解的差異之外,被采訪人在說某些話的時候,也可能有隱匿和不誠實的地方。這些都讓口述史的資料很難輕松地提供真相。但這也不意味著就應該放棄口述資料。口述資料可以提供更多可以思考和討論的問題,幫助人們觀察到歷史的復雜和真實。
回到你的問題,阿列克謝耶維奇如果承認有意修改她所接觸到的口述材料,那么你可以說她是在杜撰。但如果她認為是可靠的,而其他人持否定觀點,也不能就簡單認為作者是篡改。所謂“誤解”和“失真”的前提,是存在一個唯一的可以被完美表述的歷史真實,但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語言可以提供非常多的信息,但所有被表述出來的文字,都是以犧牲更多看不見的歷史細節為前提的。歷史學研究者都會說自己愿意去追求書寫歷史真實,但很少有人有信心說自己所說的就是唯一的真相。這恰恰是現代的歷史學科的科學性所在。而作為一種文本,歷史學作品也是有文學性的。科學性和文學性對歷史作品而言不是相互排斥的、矛盾的特點,而是共生的、互利的。

《切爾諾貝利》這部電視劇的制作方是美國和英國,而它敘述的是發生在烏克蘭的、前蘇聯的歷史事件,偏重的也是對于蘇聯的體制和各階層的描繪。可以說它的制作方和描述的對象是分離的,并不是在描述自己國家歷史,而是在描述一個曾經與自己對立的他者。類似這樣的錯位,會給歷史敘述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樣的一種形式與自己書寫自己國家的歷史有什么樣的區別?中國觀眾對這部劇的評價呈兩極分化的形勢是否也與這種敘述上的錯位有關?
朱聯璧:你可以假定HBO的制作團隊依然帶有冷戰時代的思維模式,有先入為主的對蘇聯的負面認識,再帶著這個認識來制作影片。也可以假設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出現的作品,可以達到教育觀眾的目的,讓他們在認可這部片子的同時,認可背后的反蘇聯的觀念,從而強化對蘇聯的刻板印象,甚至將之提高到美國和英國的文化戰略的高度,也就是用盡所有機會展現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這并不一定是因為制作者不是蘇聯人造成的。從研究難度來說,一個當下的中國人研究中國古代史的難度和研究外國現代史的難度并沒有差很大。過去也是一種“異鄉”。一個人的國別不能完全決定這個人更擅長研究哪個國家的歷史。歷史書寫是否可靠,在于是否存在可靠的研究方法和充實的研究資料,是否有先入為主的結論,是否受到特定意識形態限制等等。一個人如果有可靠的方法和資料,能夠“論從史出”,那么只要語言能力許可,研究哪一國哪一段的歷史都是可行的,也可以寫出可靠的歷史作品。至于有些人在寫作自己國家的歷史時帶著情懷,又回到了上面提到的一點,歷史的科學性和文學性并不矛盾,取決于個體如何處理。當然,學者研究本國的歷史作品更為出色、數量更多也是很自然的,這和語言、資料上的便利有關,但并不是因為國籍限定了人的能力。持有美國籍的人也可能是在蘇聯長大的,哪個國家的歷史對這些人來說才是“本國史”呢?
中國觀眾對這部片子的質疑,可能是因為看到的內容和他們自己之前接觸到的材料有所不同,或者是和他們所相信的歷史事實不同。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不是國籍限制了人對歷史的理解,而是對資料和方法的掌握,影響了人對什么才是“真實”的判斷。
在中國觀眾激烈討論《切爾諾貝利》這一事件中,受眾,也就是觀眾,既不與制作方屬于同一國家,也不屬于歷史事件發生的國家。在這一事件中,觀眾是獨立的第三方。或者從更大的視野看,現在基于民族敘事的作品,其受眾不僅限于本民族的觀眾,很多其他國家的觀眾都會看到這部作品。即本來的目標受眾是本國觀眾,作品的實際受眾很可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這樣的趨勢是否會影響到“公共史學”的未來發展?
朱聯璧:歷史文化產品能對不同國家的觀眾產生吸引力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我不認為這會影響“公共史學”的發展。如果一個國家的民族敘事可以通過一個好的故事或者媒體得到其他國家的人的認可和喜愛,這只是說明了這個民族敘事的成功,僅此而已。
您曾經在論文里說:“在概念化的過程中,公眾史學產品的受眾同樣是公共歷史的施為者。創作者和受眾同時在歷史內,也在歷史外。受眾的多樣性,注定了他們對歷史的解讀,更確切說是‘再創作’的過程中,會帶入自己的經驗和認知。”我們看到中國觀眾對于這部電視劇有非常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是不是也受到他們本來的一些經驗和認知的影響,比如說可能中國觀眾內部對于美國和蘇聯的態度本來就有分歧?您是怎樣看這個問題的?為什么中國觀眾對這部劇產生這么大的興趣、強烈的爭論沖動呢?除了我們談到的兩點可能的原因之外,您認為還有什么其他原因嗎?
朱聯璧:觀眾對于電視劇的看法自然是會受到他們已有的經驗和認識的影響。中國觀眾對美國和蘇聯的看法肯定是很多樣的,但我覺得這部片子影響力比較大和劇拍得符合目前觀眾的口味,又選擇了重要的事件有關。不是因為這是美國人拍蘇聯的事就值得關注,而是因為這部劇確實吸引人看下去,讓人覺得有沖擊力。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和泰坦尼克號沉沒一樣,其實都是災難片。相比完全虛構的災難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是真實的災難,本身就是非常有沖擊力的,拍成片子自然會引發討論。相比20年前《泰坦尼克號》在中國引發的熱潮,《切爾諾貝利》的受眾面是非常小的,引發的討論實在算不上多。
HBO的團隊很擅長處理這種大制作的題材,雖然今年在《權力的游戲》上得到了不太理想的反饋,但《切爾諾貝利》還是很好地展現出這家公司對大眾需要怎樣的娛樂產品有非常精準的把握。關于這個事件,其實也有俄羅斯的連續劇,已經拍了兩季了,是一部科幻劇,基于歷史,但很多情節是虛構的。從豆瓣上的打分來看,給俄羅斯的連續劇打分的人加起來都還沒HBO這一季的人多。所以,即便是非常接近的題材,不同的公司來拍,能產生的影響差別就會非常大。
您認為,中國網絡上的這種激烈論戰,是否有助于中國觀眾對于這段歷史更深入的思考?這種爭論對觀看這部電視劇的受眾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朱聯璧:對于不了解切爾諾貝利爆炸事件、不了解核爆炸對人的影響的觀眾來說,看這部劇自然是能幫助他們了解這段歷史,但也只是這段歷史的一種呈現。是否了解就等于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歷史思考,這個我覺得挺難說的,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對一段資料有限的歷史進行“深入思考”的。
爭論很難說對受眾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很多人只是看劇后說兩句,更多人可能什么都沒說,那么爭論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這些在各種媒體上表達了看法的人,也不一定想著和不同觀點的人討論,所以你可能在豆瓣上看到兩個連續的帖子對這個片子有不同的評價,但這兩個作者可能就沒有要爭論的意圖,只是因為論壇的形式,讓你覺得他們好像在“爭論”。爭論是一群人有意識地在一個空間里面,就一個問題開展討論,有相互認可的評價方法,最終想要得到一個結論。但社交媒體上的各種帖子多數自說自話,沒有想要就一個特定的問題開展討論,也沒想要的出什么結論,形成什么共識,這些自說自話也不見得會對看劇的人有什么實際的影響。
我們應該如何客觀地看待這樣一種以文藝形式承載歷史敘事的表現形式呢?這樣的形式有哪些積極意義和局限性呢?
朱聯璧:什么算是客觀看待呢?用影片表達歷史的歷史已經很久了,這部劇只是無數劇中的一部,所以我個人覺得很難“客觀看待”用影片來展現歷史的做法。這就是一種文化產品,有需要,就有人會制作。作為多樣化的歷史呈現,對專業歷史學者來說也好也不好。好處是讓更多人了解了這段歷史,可能其中就會有人未來有志于從事歷史研究。壞處就是可能讓一些人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局限于他們所看到的影片,他們以后談論起切爾諾貝利核爆炸事件,談論的就只是他們在連續劇里看到的,而沒有進一步去探究這段歷史的復雜性。
更進一步,從中國的角度出發,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外國的歷史劇、歷史片?有人認為引進這些東西有助于我們開闊視野,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也有人認為這樣會導致一些人被洗腦,或者受到其他國家的一些立場的左右,使中國的年輕人喪失形成自己立場和觀點的判斷力。您是怎么看的呢?
朱聯璧:我覺得歷史劇就是一種文化產品,或者說是娛樂產品,最主要的功能是打發觀眾需要消磨的時間。也正因為是娛樂,所以不見得非要有什么學習的效果和目的,或者是對外國的歷史產生特定的理解和立場。如果看幾部外國的劇就能被洗腦,那這樣的學生為什么過去看很多國產劇沒有產生同樣的效果呢?如果有人因為看了劇就對特定問題有了根深蒂固的觀念,或對一段歷史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我覺得這個人可能本身就缺乏判斷力。中國年輕人是個高度復雜的群體,而絕大多數的外國歷史劇在中國不是公開上映的,有些會通過一些有流量的網絡平臺來展現,有些則只是在盜版網站上有片源。就算是一部豆瓣上有幾十萬人打分的外國歷史劇,但所有打分的人相比“中國的年輕人”這個群體來說,依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幾部歷史劇也只是他們接受的文化產品中很小的一部分。這批人在評述電視劇的時候,可能為了追求話題效應說點有爭議的話,但也不見得所說的就是他們的真實想法。我不覺得幾部外國歷史劇就能改變“中國的年輕人”的判斷力和政治立場。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