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圍爐夜話 | 從遠(yuǎn)方歸來,我們談起了“遠(yuǎn)方”


矗立在寧波三江口旁的雕塑“三江送別”,展現(xiàn)當(dāng)年寧波商幫為了生存外出經(jīng)商的場景。
矗立在寧波三江口旁的雕塑“三江送別”,展現(xiàn)當(dāng)年寧波商幫為了生存外出經(jīng)商的場景。


矗立在寧波三江口旁的雕塑“三江送別”,展現(xiàn)當(dāng)年寧波商幫為了生存外出經(jīng)商的場景。
矗立在寧波三江口旁的雕塑“三江送別”,展現(xiàn)當(dāng)年寧波商幫為了生存外出經(jīng)商的場景。
【編者按】
又逢一年辭舊迎新時。此刻不論你身在何處,相信都會與家人團(tuán)聚、和老友重逢。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家鄉(xiāng),你會有什么發(fā)現(xiàn)和感觸?難得的相聚,大家坐在一起又會聊些什么?
2020年新春之際,澎湃新聞推出“圍爐夜話”專題。區(qū)別于浮光掠影式的簡單記錄和宏大敘事,我們希望呈現(xiàn)的、似乎是碎片般的景象,但又意味深長,蘊(yùn)含著這個國家的另一些細(xì)節(jié)。
文 | 徐頌贊
編輯 | 俞詩逸
從“遠(yuǎn)方”歸來的浙江人
過年,對我家而言,是一年一度各種“遠(yuǎn)方”難得聚攏的機(jī)會。
我的家人和親戚主要分布在寧波、杭州、上海一帶,也有少數(shù)在廣東,甚至日本、歐美。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形成了一股強(qiáng)勁的時代浪潮,卷起早已躁動不安的浙江人,從東南一隅涌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形成了許知遠(yuǎn)所說的“第二次浙江潮”。
這次浙江潮,不再像19至20世紀(jì)盛產(chǎn)浙籍知識分子的文化潮,而是以商品經(jīng)濟(jì)和浙商群體為主要特征的經(jīng)商潮。從土地解放出來的千百萬浙江人,憑著敏銳的商業(yè)嗅覺,游走在天南地北。也只有短暫的春節(jié)是各地浙商的共識,讓他們暫時放下“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生活模式,紛紛回老家過年。
他們曾帶著對“遠(yuǎn)方”的想象,離開家鄉(xiāng),去他鄉(xiāng)和異國拼搏。每到過年,又從遠(yuǎn)方歸來。在這段時間里,無數(shù)的遠(yuǎn)方迅速相遇、交錯,形成碰撞點(diǎn),最后又各自散去,等待下一次的交匯。我對這些親朋好友們的“遠(yuǎn)方”非常有興趣——他從哪里出發(fā),去往何處,如今又從哪里歸來?在離去與歸來之間,他們又發(fā)生了哪些變化?這些問題,既關(guān)乎每位個體的人生歷程,也是改革開放后無數(shù)人匯成的時代故事,再進(jìn)一步,又何嘗不是人類普遍存在的生命追問呢?
你曾去往何方,又從何處歸來?
我最清楚的是我爸的“遠(yuǎn)方”。他曾是一位中學(xué)數(shù)學(xué)老師,后來因?yàn)楦鞣N事情下海,丟下了鐵飯碗,進(jìn)入了充滿風(fēng)險的市場經(jīng)濟(jì)浪潮中。我問他,為什么當(dāng)初不好好待在體制內(nèi)?現(xiàn)在會不會后悔?他不以為然,回答也很簡單——為了自由。為此,他曾從寧波闖到上海,后來又回到寧波。哪里有機(jī)會,就往哪里走。我發(fā)現(xiàn),這樣的敘述,也頻繁地出現(xiàn)于像他一樣的50后、60后身上。他們的“遠(yuǎn)方”,主要指向市場經(jīng)濟(jì)帶來的賺錢機(jī)會,以及掙脫體制而來的自由感。
不過,離去與歸來,并不總是凱歌嘹亮。尤其對于失意者而言,“遠(yuǎn)方”的意涵常會發(fā)生戲劇性轉(zhuǎn)變。前些年,姑姑因?yàn)樵趯幉ㄞk的工廠倒閉,曾經(jīng)身家千萬的她,在短短幾年之內(nèi)就從“富翁”變成“負(fù)翁”。姑姑小時候不喜歡待在學(xué)校念書,早早離家出去打拼。年輕時的她,視家鄉(xiāng)為束縛,視遠(yuǎn)方為希望,因而先在寧波一家小作坊當(dāng)女工學(xué)徒,然后一路做到上海一家大公司的管理者。小時候過年,我總看到穿著華貴的她,每次歸來都讓人有種“衣錦還鄉(xiāng)”的感覺。再后來,她帶著在上海的原始積累,回寧波創(chuàng)業(yè)辦廠。眼看著工廠從無到有、拔地而起,資產(chǎn)也漲到千萬,卻又在短短幾年之內(nèi),發(fā)生各種融資和貸款問題,最后化為烏有。以前開寶馬、住豪宅的姑姑,成了被債主圍攻的人。故鄉(xiāng)再一次成為她的負(fù)擔(dān),她開始重新望向遠(yuǎn)方。她聽聞有位熟人老板,在海南島辦的工廠需要副手,就直接去了海南,打算東山再起,如此一去便是兩三年。去年和今年,她都沒有回來過年,成了家族飯局里不在場的他者。人們談?wù)撍路鹫勂鹨粯哆b遠(yuǎn)的往事。當(dāng)然,人們也會順便談起附近沒回家的人——某某在深圳發(fā)財(cái),今年買了新房,不回來過年;某某破產(chǎn)躲債,上了黑名單,也不能坐飛機(jī),不清楚行蹤;某某去澳洲帶孫子,偶爾視頻電話,一邊調(diào)侃國內(nèi)霧霾的糟糕,一邊又抱怨國外生活的無聊……就在這張過年的飯桌上,人們的“遠(yuǎn)方”一再切換和重組。有時不得不讓人慨嘆,人生一世,究竟有多少人正在離去與歸來,究竟“遠(yuǎn)方”有著多少令人琢磨的涵義。
我有時特別好奇中國人的生活軌跡,感嘆這些軌跡的靈活、復(fù)雜和多變。他們離開了本土,沿著各自的方向,生長出不同的人生故事。在他們的人生中,“遠(yuǎn)方”曾是一種類似救贖的力量,以強(qiáng)大的引力,將他們抽離出自己生長的地方,移置到另一個地方。當(dāng)然,“遠(yuǎn)方”也有失效的時候,特別是當(dāng)人失敗,或者人到晚年,故土重新涌現(xiàn),“落葉歸根”的敘事再次興起。只有少數(shù)人能免于這場有規(guī)律的文化交響曲,有詩為證——且認(rèn)他鄉(xiāng)作故鄉(xiāng)。
當(dāng)然,我也發(fā)現(xiàn),中國人的“遠(yuǎn)方”,有時竟也顯得如此一致、單調(diào)和無趣。當(dāng)代中國人既不是安土重遷的農(nóng)業(yè)民族,也不是心懷四海的游牧民族,更像是在地球上游牧的農(nóng)民,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復(fù)刻已有的價值生活。這些生活往往很少跨越中國傳統(tǒng)的價值觀,僅是發(fā)生一點(diǎn)新變異,擦除一點(diǎn)新火花而已。就像我父親和姑姑那一代50后、60后的“遠(yuǎn)方”,更多指向賺錢、財(cái)富和經(jīng)濟(jì)自由。而像我這一輩的90后,心目中的“遠(yuǎn)方”,可能更多出于對“此處”的厭離。很多年輕人只知道要離開“此處”,但對于遠(yuǎn)方,卻時常是迷茫的。在和同輩人的一次交談中,我似乎發(fā)現(xiàn)了這種叛逆。
“遠(yuǎn)方”與“此處”
我有位親戚,也是同輩的90后。他家里富裕,父親是出名的老板。不過,這位兄弟本人因?yàn)樘煨栽缡臁⑿郧槊翡J,非常厭惡寧波本地流行的“經(jīng)濟(jì)至上主義”,很早就主動向家里要求申請留學(xué)。后來,他長期待在美國,很少回來。在一次網(wǎng)上閑聊中,我們都發(fā)現(xiàn)了彼此對“此處”的厭離,仿佛達(dá)成了一次心靈的共同聲明。但我也同時發(fā)現(xiàn),他對于“此處”的厭惡,并不等同于對“遠(yuǎn)方”的向往。因?yàn)椋绻晕镔|(zhì)生活而言,以他家的財(cái)力,在寧波一樣可以復(fù)制美國的生活方式。從精神生活而言,性情低調(diào)、獨(dú)來獨(dú)往的他,似乎也無法融入熱鬧的華人圈子,或者追求刺激的美國青年社交圈。最后,電子產(chǎn)品成了異國他鄉(xiāng)的知己,手機(jī)屏幕上的遠(yuǎn)方成了此處的生活。不論在“此處”還是“遠(yuǎn)方”,過的依然是一種“不在場”的生活。
對于成長于全球化時代的90后、00后而言,世界從未像今天這般,變得如此快速,又如此扁平——從前水火不容的國際關(guān)系正在變化,壁壘分明的文化結(jié)構(gòu)也處于快速重組之中。“遠(yuǎn)方”和“此處”的分裂,時常會加深人的焦慮。這種焦慮又通過電腦、手機(jī)和各類新科技產(chǎn)品被無限放大。而由這些新科技產(chǎn)品帶來的信息革命,比電視時代來得更加徹底。
相較以往,人們被卷進(jìn)了一個更深的“信息洞”里,無數(shù)陌生的、新奇的、有趣的遠(yuǎn)方,源源不斷地在這個洞里出現(xiàn)。只要打開朋友圈、翻看微博,人們的工作、社交、娛樂、教育,似乎都被打包裝進(jìn)眼球。這些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無限地?cái)U(kuò)展著人們對“遠(yuǎn)方”的想象。例如,最近新冠肺炎所引起的社會關(guān)注,遠(yuǎn)比十七年前的“非典”更加廣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手機(jī)的普及和社交媒體的信息普及。如今,就連最基層的鄉(xiāng)民,也能通過手機(jī)獲知有關(guān)“遠(yuǎn)方”的信息——很多人不知道地理位置的伊朗,也能從遙遠(yuǎn)的中東,直抵此處的飯桌,成為50后和90后爭論不休的話題。
牛津大學(xué)人類學(xué)系的項(xiàng)飚教授曾指出,中國人就像蜂鳥,永遠(yuǎn)在振動。這樣的生活,雖然看似生趣,但似乎常常讓一種模式成了意義的終極指向。人們的生活,失去了那種立體的、復(fù)雜的生趣,反而越來越變成處于“弦上的生活”。就像浙江人習(xí)慣性地把工作說成“做生活”,那種“閑不下來”的生活倫理,可以使他們在商業(yè)活動中取勝。然而,“做”了以后會如何,這樣的終極問題,卻是少有人思考的。
如今的中國,已經(jīng)從“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變?yōu)椤笆澜缰袊保瑥膩頉]有哪個時候,像現(xiàn)在這樣涌來無數(shù)的遠(yuǎn)方和海量的信息。人們在物理意義上的空間移動已經(jīng)更快、更廣,而在精神意義上的空間移動,卻顯得前所未有的拘束、慌張、膽怯。當(dāng)然,也從來沒有哪個時刻,像當(dāng)下的我們更加需要有關(guān)遠(yuǎn)方的哲學(xué)、遠(yuǎn)方的倫理學(xué)、遠(yuǎn)方的人類學(xué)……
我不由得想起魯迅說過“無窮的遠(yuǎn)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guān)”,這句話常被援引作為對“遠(yuǎn)方”和人類的關(guān)懷。但不妨回到1936年的魯迅身邊,看一看他更整全的語境和意義指向。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墻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jìn)行著的夜,無窮的遠(yuǎn)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guān)。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shí)了,我有動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這是魯迅逝世前一個月留下的文字,在這篇名為《這也是生活》,并收入《且介亭雜文》里的文章,可以看到魯迅不僅有“遠(yuǎn)方”,也有“此處”——那些具體的生活場景,那些讓他安頓身心的書和畫集,那些引起他遐思的夜晚。而且,不僅有此處的生活,也有“動作的欲望”——對于一位正在走向人生終點(diǎn)的人而言,他的自我實(shí)現(xiàn)和意義追求,也落實(shí)在生活的行動里。即便最后“又墜入了睡眠”,這又有什么呢?人的努力不正如滾動巨石的西西弗斯,不正如揮動翅膀的伊卡洛斯嗎?深深扎根于生活的行動,能讓分裂的“遠(yuǎn)方”和“此處”重新和好、得以共舞,再次開始新的創(chuàng)造。哪怕遭遇了失敗,那也是一種珍貴的意義,一種在“此處”和“遠(yuǎn)方”來回穿梭形成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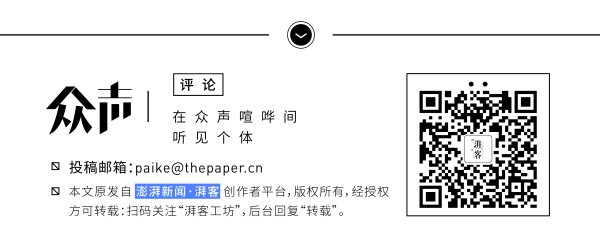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