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回訪|魏則西走后三年,留下的人還在用力地活著
【編者按】
“除非經由記憶之路,人不能抵達縱深”。
這句政治家的名言提醒我們,人活在時間的河流中,要理解現在,要從理解過去開始,而過去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未來。只是,一塊礁石、一處險灘、一波洪水都可能是命運翻轉的因素。
那些因為某起事件、某個人物、某次意外成為新聞主角的普通人,又會走向何方?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是否得到救贖?那些在風中飄的答案找到了嗎?
澎湃人物開辟“回訪”專欄,希望在更長的時間跨度里,留下他們的生命印記。
他們,也是我們。
“媽,我走以后,你們一定要想辦法再要一個孩子。”
2016年4月11日,魏則西躺在咸陽的家中,懸掛的氧氣瓶維系他微弱的呼吸。入夜,他讓父母關掉手機關上門,一家人聊了幾個小時。
這個飽受癌癥折磨的青年在次日清晨離開了人世,留下關于“人性最大之惡”的叩問。
三年之后,魏則西的遺愿實現了。2019年中秋節的前一天,“魏則西父母通過試管嬰兒手術重獲一子”的消息傳遍了互聯網,這個滿是創傷的家庭等來了些許寬慰。
但就像逝去親人留下的恒久遺憾,那些直接或間接地卷入這場風波的人們,還在承受綿延的傷痛和不安。他們擔心被遺忘,也在努力地活下去。
故去
魏則西被安葬在陜西咸陽的一處公墓內。從路口走到墓園正門約有200米,腳下是一條狹長筆直的水泥路,隔絕了馬路上的塵囂。
墓碑位于墓園左側一處僻靜清幽的園子里,四周草木茂盛,正面銘刻著“愛子魏則西”的字樣。

1994年出生的魏則西在20歲時被查出患有滑膜肉瘤。求醫期間,他曾在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接受生物免疫療法(DC-CIK),未見療效,還貽誤了治療時機,最終早逝。
墓碑后記錄了他短暫的一生——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品學兼優,經史子集,了然于胸,談笑之間,代碼寫就。”
在昔日同學的印象里,魏則西是一個“為未來而活”的人,夢想考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入硅谷,成為計算機領域的“大神”。
然而,他在舊時光里故去。“如果你還活著,這會可能已經在美國了吧?”一位網友在魏則西的微博下留言道。
在魏則西的母校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每一棟教學樓都顯得肅穆威嚴,背著書包的學生腳步匆匆,出入各自的實驗室。魏則西的同學們畢業后各奔東西,輔導員也轉至其他學校。關于他的記憶正日漸遠去。

“印象變得模糊。”魏則西昔日的班長楊小天(化名)說。但他總記得,第一次見到魏則西的情形,很親切,絲毫沒有陌生的感覺。當時,魏則西因病休學一年后重新入學,楊小天幫他辦理手續。魏則西告訴楊小天,休學期間,他還在寫數據結構的程序。
后來回想起來,楊小天才明白,魏則西為什么那么積極刻苦。大概經歷了一場大病,他更感到時間寶貴,想努力抓住眼下的東西。

新生
位于咸陽的西北國棉一廠,始建于上世紀50年代,是新中國第一家國營棉紡織廠,曾經鼎盛一時。
如今,繁華落盡。從老舊的家屬院正面進去,是一條直通到底的水泥路,生銹發黑的暖氣管道在半空中縱橫交錯。
居民樓排列在道路右側,魏則西家的老房子是最深處的一棟。1994年2月18日,大年初九,他出生在這里。25年后,小區里的人已經不大記得這個孩子的名字,但一提起魏海全的外號,他們都想起來了。
“這個孩子從小就愛學習,不要大人操心,不像別人家的那么調皮。” 一位70多歲的老人在單元樓下回憶道。
她并不清楚則西得病的事,“那可能是他們搬走之后了吧。”她也不知道魏則西有了弟弟的消息,“哦,這樣啊,那太好了。”
外人一句輕描淡寫的祝福,魏海全夫婦聽來也許會百感交集。
失去獨子魏則西的那一年年底,魏海全的妻子開始吃中藥調理身體,她雙側的輸卵管已經堵住,自然生育希望渺茫。在當地婦產科醫院,再也找不到比她年紀更大的婦女了。
夫婦倆開始嘗試試管嬰兒,“如果老天爺賜一個,我們就留下。”魏海全此前接受采訪時說道。
第一次取卵之前,他給妻子連打了9天促排針,每天打6支。為了讓藥力充分地進入身體,他們一遍遍地按摩、熱敷,希望都寄托在這小小的卵泡上。

3次取卵,得到5個卵泡,形成2個健康的胚胎后,最終移植還是未能成功。
魏海全和妻子不得不開啟新一輪的備孕,一年后,終于等來了新生命。魏海全說,這是老天在眷顧他們,新生兒帶來“笑聲和希望”。
過去三年,他們夫婦無法淡忘喪子之痛。
“母親幾乎每天都把魏則西的照片拿出來翻一遍……她流著眼淚,對著照片上笑吟吟的魏則西絮絮叨叨地說話,一面還開著兒子生前的手機錄音,翻來覆去地播放著那一小段魏則西關于治療計劃的語音備忘錄。”《每日人物》的一篇報道寫道。
現在,他們搬離了老家屬院。新入住的是一幢簇新的小區,小區空地擺放著幾張乒乓球臺,每到周末都有老人帶著孩子過來練球,有人推著嬰兒車在一旁圍觀、閑聊,輕松愜意的樣子。
這是否也會成為魏海全夫妻今后的日常?

被遺忘
魏則西走后一個月,她的母親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自稱是癌癥患者家屬,“你們得了那么多賠款,給我們一點嘛,我們沒錢看病”,他在電話里說。
“誰給我們一分錢了?”魏母氣得掛斷了電話。他們當時不僅沒有得到賠償,也沒有收到道歉。
沒有等到道歉的,還有許多跟魏則西一樣被誘導接受DC-CIK療法的病人。
“三年半了,你是第一個(關于生物療法后續)給我打電話的人。”37歲的河北邯鄲人崔鵬(化名)對澎湃新聞記者感慨道。他的母親2015年11月10日去世,兩個月前,她曾在武警二院接受過生物療法。
回想起來,崔鵬覺得母親走得冤。
1999年,崔鵬初中畢業,母親被查出罹患非霍奇金淋巴瘤,醫生告知時日無多,但母親依舊陪伴了他十多年。真正困擾母親的,是放化療后出現的肝硬化腹水癥狀。
膨脹的積液把她瘦弱的身體撐得鼓鼓的,連睡覺都不能平躺。每兩個月,她就要去醫院抽取腹中的積液,針頭扎得密密麻麻,每次花費一萬多元。
這期間,母親不停在網上尋醫問藥,直到2015年夏天,她注意到了一種叫“生物免疫治療”的療法。也是通過網絡搜索,她聯系到北京武警二院的醫生郭躍生,在網頁自帶的聊天窗口里,對方向她“科普”什么是生物療法,并表示“治愈率高達94%”。
母親詢問兒子的意思,但崔鵬也是第一次聽說。他私下里上網去搜,一看“醫院是正規的部隊醫院,醫生還上過央視,應該挺靠譜吧?”崔鵬沒有指望母親能徹底治好,但凡能讓她減輕一些痛苦的法子就值得一試。
崔鵬理解母親的心情:想給他多帶幾年孩子,減輕點家里的負擔。看上去非常神奇的“生物療法”點燃了她的希望。
崔母自己曾是護士長,她覺得這個郭醫生的話理論上說得通,母子倆很快便坐上了去北京的動車。
在武警二院,他們見到的第一個醫生叫李志亮,“瘦瘦的高高的,戴著金絲眼鏡,穿著軍裝”,李也是魏則西當時的醫生。隨后,他們又在二樓見到了郭躍生,身穿白大褂,內搭軍綠色襯衣和深綠色領帶,和電視上的形象一模一樣。
郭躍生給了他們一本《腫瘤生物技術病例集》,書中夾了一張光盤,上面寫著“多細胞生物治療”、“科技之光”、“治愈腫瘤的希望”,以及大大小小電視臺的臺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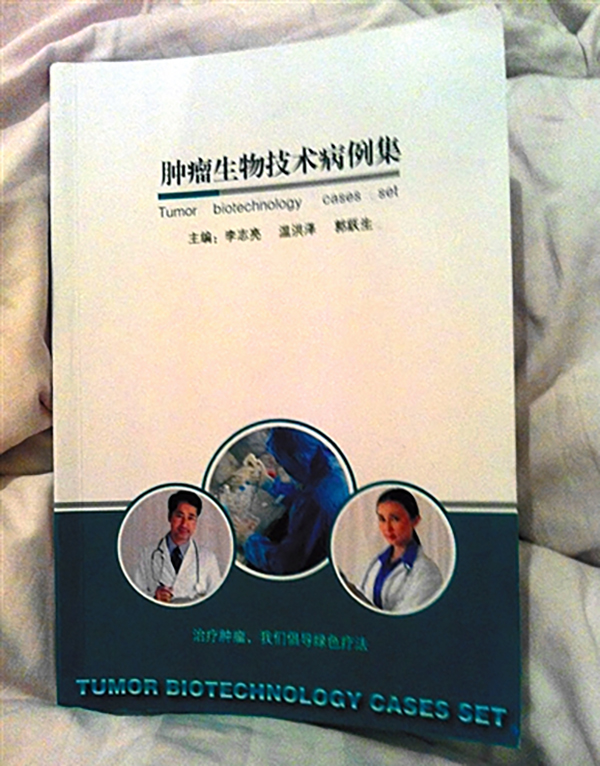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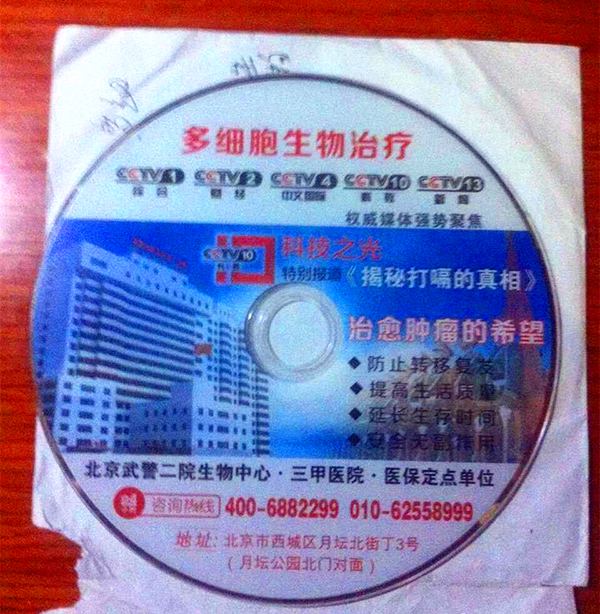
和先前談到的“治愈”不同,此時郭躍生稱,接受生物治療后,崔母的肝硬化保證3-5年不會復發。
崔母當天就在醫院辦理了住院,并于第二天抽血用于細胞培養。根據治療方案,幾天后崔母將接受手術,把培養好的細胞從大腿動脈輸向病灶器官,進而發揮療效。
整個過程花費4萬多元,歷時十多天,晚上崔鵬就睡在醫院走廊里,等待天明。
他沒有想到,兩個月后,等來的是母親的“不辭而別”。
“我不服”
去世的前一晚,崔母對兒子說自己很冷,無論是喝熱水還是吃藥都不管用。救護車把人直接送進了搶救室,之后再也沒有醒來。
醫生初步分析崔母的死因是,多器官衰竭,具體原因需要做尸檢。崔鵬拒絕了,他說不想母親再挨刀受苦。他也沒有告訴醫生,母親做過生物治療,如果沒有這次意外,半年后,他們還打算去武警二院復查。
崔母死后的第二年,魏則西的事件披露了出來,崔鵬傻了眼,“渾身都涼了”。他問自己,我是不是被騙了?
崔鵬當即就買票去了北京。當時,武警二院的大門已經被封鎖,只留下一個人進出的通道,有人把守。看到這情形,崔鵬僵在那,不知道何去何從。

中國軍網發布的消息顯示,武警二院于2016年5月4日起全面停業整頓;5月9日晚,由國家衛計委等部門組成的調查組稱,武警二院存在科室違規合作、發布虛假信息和醫療廣告誤導患者等問題,對涉嫌違法犯罪的醫務人員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但崔鵬還想要個說法,哪怕是一句道歉。兩個月后,他帶著母親的病歷又一次來到武警二院,在附近一處辦公室做了登記。一位工作人員對他說,這個事還要等,回頭有消息打電話給你。
“這一晃三年了,什么都沒有。”崔鵬說完,沉默良久。
那一年里,他多次往返于邯鄲和北京,海淀區法院門口的律師事務所他都咨詢過,但得到的回復大體一致,這個案子打不了。
其中一位律師都提筆準備記錄他的情況,但猶豫了一下又放下了筆。“年輕人,回去上班吧,你媽這個事情來找的人挺多的,比你花錢多的人也有,但是這個官司是個消耗戰,就算贏了也不劃算。”
后來崔鵬在律師的建議下來到調解部門,仍然是登記、等電話。他也試過把自己經歷發上微博,但信息總是發不出去。
整個2016年,崔鵬過得極為艱難。那是失去母親的第一年,從那時起,他再也沒去過大姨家,因為母親和大姨長得很像,他看到大姨就會掉眼淚。
下半年,他丟掉了汽車4S店經理的工作。在去北京治病之前,他買了新房,貸款還了一半,如今新房也賣了,他和父親、妻兒擠在6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至今還欠著銀行幾萬元。
爭議“免疫療法”
曾經熙熙攘攘的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如今門庭冷落。大門上方的金屬字樣已被去除,柵欄門緊閉,只留下一條窄縫,一位快遞小哥從縫里擠了出來,顯示這里還有人居住。
當被問到醫院情況時,坐在門口的保安擺擺手,說原來的醫院早已關閉,如今這里是軍隊所屬,有家屬在里面居住。
而當年生物診療中心的五位醫師也清空了自己的微博賬號,不知去向。
2016年5月,國家衛計委(現為國家衛健委)緊急叫停醫療機構在細胞免疫治療方面的臨床應用,僅允許其作臨床研究,不得開展收費治療。同年12月,國家食藥監局(CFDA,現為國家藥監局)發布了《細胞制品研究與評價技術指導原則》(征求意見稿),首次明確提出將細胞免疫治療產品納入藥品監管。
但對于DC-CIK這種細胞免疫治療技術,當年調查組并沒有定性。北京大學醫學部免疫學系教授王月丹表示,對于接受這種治療的患者而言,沒有定性意味著索賠沒有依據。
2017年4月,國家衛計委回復澎湃新聞稱,從免疫治療中的CIK療法多年的臨床研究和應用來看,盡管可以使患者總生存期顯著延長、生活質量明顯提高,但是該療法存在細胞制備質量參差不齊、特異性不強、個體療效差異大等問題,同時存在器官損傷等副作用,還不具備進一步廣泛臨床應用的條件,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一年后的10月,2018年度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授予了美國科學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科學家本庶佑,以表彰他們發現了抑制免疫調節的癌癥療法,最終引出了PD-1/CTLA-4抑制劑等免疫藥物的產生。
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免疫學研究所所長董晨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介紹,“免疫療法目前存在一些爭議,主要在于一些人把DC-CIK療法等同于免疫療法,這是不準確的。免疫療法可能是未來人類戰勝腫瘤的一個重要武器,但就國內來講,臨床研究還比較薄弱,人類對自身免疫系統和腫瘤免疫治療的理解至今仍只是冰山一角。”
“螞蟻菜”的抗爭
“螞蟻菜”沒有見過魏則西,但兩人的命運隔著生死產生了某種聯系。
2015年底,當時的百度“血友病貼吧”吧主“螞蟻菜”發現,吧內多了一位官方吧主劉陜西。而眾多病友指稱,劉陜西并不是所謂專家,而是“醫療騙子”。
不久后,“螞蟻菜”被撤換并禁言,精品帖也被大量刪掉。他意識到,血友病吧被“賣”了!
憤怒、失望、悲傷,種種情緒包裹著“螞蟻菜”,他寫下了一篇“血是什么味道”的帖子,轟動網絡。
這是“螞蟻菜”的一次“抗爭”,對手是商業巨頭。
他贏了。2016年1月12日,百度宣稱所有病種類貼吧已經全面停止商業合作,只對權威的公益組織開放。同年2月,新吧主劉陜西起訴“螞蟻菜”侵犯其名譽權,后于9月撤訴。
三年過去,他做回四川攀枝花人張建勇,41歲,家庭教師。生活沒有太大的波瀾,除了身體越來越差,他更頻繁地注射凝血因子——血友病人由于體內缺乏凝血因子會過度出血,目前尚無治愈方法,只能終身注射。
小時候,他嘴里破了一個瓜子尖尖那么小的傷口,卻流血流了一個月,差點休克。更讓他“惱火”的是內出血——關節里的積血導致滑膜增厚,壓迫血管,同時還會腐蝕骨骼導致變形,無法長時間行走。電動輪椅成了他買過的東西里性價比最高的一個。
“打針”嵌入了他的生活,近兩年,他有時一周只打一次,也時常一周兩三次,每次都還不是足量注射。
長期打針導致他的血管萎縮得厲害。9月的一天,他的父親扎了10次才把針扎進他的血管,破了之前8次的記錄。現在,他“抗爭”的對手是時間。
人到中年,泥沙俱下。他說2018年大概是“最艱難的一年”了——家人接連生病住院;做了19年家庭教師發現,學生越來越難招,家長的要求越來越高;自己的精力和時間又不夠用,貼吧、論壇輪軸轉,還要幫著照顧孩子。
“這大概就是中年危機吧。”他苦澀地笑。
“活著”
但他還是樂觀的,聊起天來滔滔不絕。電話那頭不時傳來嬰兒的啼哭,他抱歉地說道,女兒出生還不滿一年,他還需要幫著妻子照顧。
因為有了頭胎的經驗,他擔心孩子出來后他太過勞累引發腦出血,便跟妻子說去注射凝血因子。誰知剛走出病房,妻子就被推進產室,等他打完針回來,小女兒已經出生了,沒能第一時間抱上讓他有些遺憾。
他很愛孩子,這也是他選擇做家庭教師的原因。
他每天一早起來,送大女兒去幼兒園。他坐在電動輪椅上,女兒坐在他腿上,一路上他給她講故事,聊天談心,這是他最享受的時光。
到了下午,他開始備課。20多個學生,從小學到初中,分晚輔和興趣班,他教孩子正直和勇氣,就像自己當年面對龐大的百度時那樣,但這些往事他從沒跟家長和學生提起過。


他懂的東西很多,但受困于這副身軀,許多夢想無法實現。
前不久,有個學生考到了綿陽,臨走前他在留言簿上寫道,“張老師,我要用我的眼睛幫你去看這個世界,用我的腳去幫你丈量這個世界。”
他見識過“死亡”的模樣:五彩的光芒,黑洞式的拖拽……那是瀕死反應。
所以他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工作到夜晚,送走學生們后,還要打開電腦處理病友和網友的問題。“我是一只螞蟻,一只行走在人間的螞蟻,一只勤勤懇懇永不放棄永遠向前的螞蟻。”他的微信簽名寫道。
他對很多人說過,自己和魏則西最大的區別在于,他死了,“我還活著”。
“如果說還有點理想,我希望生命像流星一樣,在夜空中長一點、亮一點……”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