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82年生的金智英》風靡背后,是無數名字被抹去的女性
原創: 傅適野 GQ報道

那么我們就從命名的角度梳理幾部小說和非虛構作品吧。女性在不被看到的無名、共同生命體驗凝聚的集體之名,到彰顯個人的自我命名中掙扎,并與這種掙扎相伴。
···············
?
一個名字和許多名字
1982年4月1日,她出生于韓國首爾某醫院婦產科;身長50厘米,體重2.9公斤;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家庭主婦,她有個大自己兩歲的姐姐和小自己五歲的弟弟。一家人連同奶奶一起生活在33平米的平房內。
她叫金智英。是韓國作家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筆下的人物。六七歲時,她因偷吃了弟弟的奶粉被奶奶訓斥。初中時,她在偏遠地方補習成為男同學跟蹤的對象,回家后卻遭到父親的指責,“為什么要和陌生人說話,為什么要穿那么短的裙子?”

全職家庭主婦意味著永無止盡的家務。同名電影10月份在韓國上映,開篇就是密密麻麻的有關家務的鋪排。金智英在自己家收拾垃圾、吸地板、分門別類地整理孩子的玩具,然后到婆婆在釜山的家中做飯、洗碗,早晨起來繼續摘菜、削蘋果,接受婆婆送的圍裙禮物,表現出很開心很喜歡的樣子。
只有在晚上四五點鐘太陽落山的時候,金智英能站在陽臺上,在夕陽的余暉中發一會兒呆。可這段全天中最為輕松愜意的時光,很快就會被孩子的哭鬧聲打破。她回到客廳,繼續投入周而復始的繁瑣的家務和育兒工作中。
這就是金智英和她的生活,實際上她恐怕并沒有電影中扮演金智英的演員鄭有美那么精致美麗。她平庸、普通,放在人堆里看不見。

男孩偏好、陌生人跟蹤尾隨、職場性騷擾,書中這些女性再熟悉不過的場景和遭遇,讓金智英成為千千萬萬女性處境的縮影——她們時常被忽視、被抹去名字。接受媒體采訪時,趙南柱表示為了“象征性地展示世界如何抹去女性的名字”,她特地刪除了金智英丈夫以外的所有男性角色的名字。正如女性通常被冠之以誰的母親、誰的奶奶等諸如此類的稱呼,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一書中,男性都沒有名字,他們都是“父親”、“學長”、“上司”、“弟弟”。
這是作者趙南柱對于性別不平等的一種反抗。這樣的安排參考了電影體系中表述性別不平等的指標“貝氏測試法”(BechdelTest)——在一部電影中,是否有兩個以上的女性擁有姓名,且她們之間有沒有產生過對話,以及這個對話是否和男人相關。事實上很多電影都不符合這個看似簡單的、能夠輕易達到的標準。基于此,趙南柱在書中嘗試把男性人物的名字隱去,用一種反諷的方式體現整個社會對于女性的忽視。
有趣的是,趙南柱坦言,回看自己作品時,她意外地發現她在寫作中也時常不自覺地把女性的名字變成她們扮演的角色,以婆婆、媽媽這種方式書寫。在修改書稿的過程中,她才給女性角色起了名字,而那些名字——無論是金智英還是美淑——都是在韓國十分普遍的女性名字。
?
從Emily Doe到Chanel Miller
女性無名,不僅出現在日常生活中,也出現在一些更為極端的狀況里。
2015年1月,當時22歲的艾米麗·多伊(Emily Doe)在參加斯坦福大學兄弟會派對時遭遇性侵。喝完啤酒和伏特加后,她到戶外小便。在2019年的回憶錄《公開我的名字》中她這樣回憶這段經歷:“當時我百無聊賴,放松自在,喝醉了,并且極度疲勞,我離家不到10分鐘的距離……在那之后我的大腦就一片空白了,我斷片了。”兩名學生在派對場所外面的垃圾箱后面發現了不省人事的艾米麗·多伊。
恢復知覺時,艾米麗·多伊人在醫院。她的頭發里混入了松針,她的內褲不翼而飛,而她的陰道里還留有被侵犯的殘跡。她被審視、被檢查、被拍照。然后她意識到,自己被強奸了。
整個經過,一部分來自于她在醫院得知的消息,另一部分則來源于網絡。在那里,她被描述成一個“失去知覺的女性”,而實施強奸的,是一名叫布洛克·特納(Brock Turner)的游泳運動員。他有名有姓,有照片,有具體細致的背景故事。而艾米麗·多伊只是一個不知名的女性,一個“被害者”。在警方的報告中,她沒有名字:“他聲稱他在地上親吻了受害者。他脫掉受害者的內褲,把手指伸進她的陰道。他也撫摸了受害者的胸部。”
在《公開我的名字》一書中,作者這樣描述這一具有毀滅性改造能力的經歷:“原有的生活離我而去,新的生活就此開始。為了保護我的身份,我被賦予了一個新的名字:艾米麗·多伊。”
在艾米麗·多伊這個化名之下,她開始上訴,她在網絡上發布了案件的訴狀,引發了種種討論。在這個過程中,她因為事發時喝醉,不是“完美受害者”而飽受攻擊。一名特納的前同班同學在一封寫給法官的信中表示,“我很確定她和特納在派對上就已經打情罵俏,相約一起離開”,并暗示因為一個醉到不省人事的女性的指控就將其同學認定為強奸犯,是不公平的。
最終受理此案的法官判定特納性侵罪成立,檢察官要求處以六年刑期,而法官以過長刑期會對特納造成嚴重影響為由,最終判了六個月監禁,并緩期執行。
四年后,《公開我的名字》一書出版。在書中,作者告別化名,將自己的真名香奈兒·米勒(Chanel Miller)公之于眾。“名字”,是理解這本書的核心。這一舉動意味著剝離她被賦予的面具,袒露自己,袒露這個真實鮮活的名字下面存在著的有血有肉的個體。她不是受害者,不是被強奸者和被侵犯者,不是在斯坦福大學醉酒的不知名女生,她叫香奈兒·米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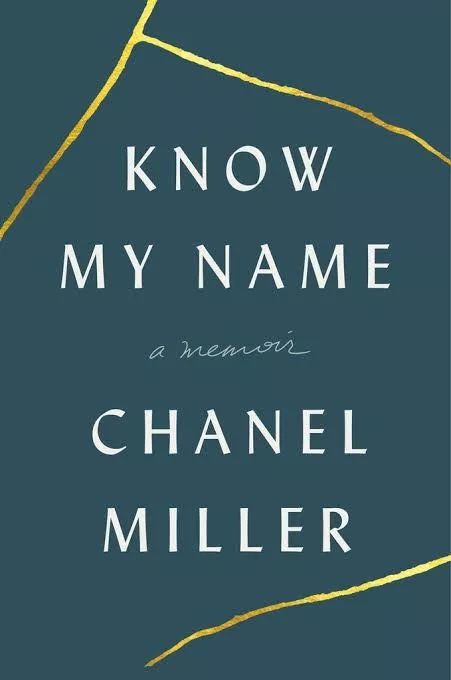
在為自己命名的同時,她選擇隱去其他人的名字。在書的開篇她這樣寫道:
“在這個故事里,我將會稱呼陪審團為陪審團,法官為法官。這些名稱在這里是為了彰顯這些人的角色。這不是一個私人控訴……我相信我們都是多維的存在。而在法庭上,被扁平化、被塑造、被貼上錯誤的標簽、被中傷都是有害的,所以我并不會對他們做同樣的事情。我會使用布洛克的名字,但事實上他可以是布拉德或者布羅迪或者班森,這都不重要。重點并非他們單個個人的重要性,而是他們的共性,所有讓一個破損的系統持續運轉的人們的共性。”
“不給他們命名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為我自己命名。”
日本記者伊藤詩織在《黑箱:日本之恥》一書中也描述過類似的經歷。2013年,伊藤詩織在紐約大學讀本科,結識了日本TBS電視臺駐華盛頓分局的局長山口敬之。之后二人斷續有一些郵件往來,談論工作事宜。2015年,一次會面時,伊藤詩織在洗手間暈倒,醒來時卻發現山口重重壓在她身上。她意識到,自己被強奸了。

她對這個始終纏繞在自己頭上的標簽感到不滿。“‘受害者’不是我的職業,也不是我的人設。”她在書中這樣寫道,“不是稱其為‘受害者A’,而是讓他們作為真實的、有名字的、有面孔的人登場,豈非能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影響?”
當性侵犯案件發生時,法律機構經常會隱去受害者的名字。這當然是保護受害者的善舉。這些公布自己身份的受害者,也可能會付出一定的代價。她們的名字永遠和某件性侵案聯系在一起,在一些仍對她們報有惡意的人那里,她們暴露了某種可供攻擊的方面。但從無名到有名,這是她們充滿勇氣的反抗。
正如《紐約時報》有關《知道我的名字》的書評所言,“《知道我的名字》是一種矯正行為。在書的每一頁,米勒都讓自己變得立體,從受害者或者艾米麗·多伊回到香奈兒·米勒。”
也正是通過一次次具體的名字指認——不管是香奈兒·米勒還是伊藤詩織,她們承擔了個人代價,去讓女性個體經驗擁有被講述的空間。
?
從金智英到《她的名字是》
34歲那年,金智英患上了產后憂郁癥。她開始用很多不同女性角色的身份說話,有時是自己的母親,有時是過世的朋友、社團學姐車勝蓮。
中秋節時,金智英跟著丈夫回婆家,吃完飯后,她用母親的口吻跟親家公說話:“只有你們家人團聚很重要嗎?既然你們的女兒可以回娘家,那也應該讓我們的女兒回來才對吧?”
通過“被附身”,假借他人之口,金智英說出了自己的壓抑與不滿,似乎只有這種人格分裂式的方式,才賦予她言說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因為她是妻子、是母親、是兒媳,所以她要盡善盡美,一絲不茍,不能犯錯。
這種對于女性的苛責,也是趙南柱創作《82年生的金智英》的初衷。2014年年底,在韓國互聯網上爆發了有關“媽蟲”的討論。“媽蟲”是英文“mom”和韓文“蟲”結合而成的詞匯,用來貶低無法管教在公共場合大聲喧鬧幼童的年輕母親。這些年輕母親被視為丈夫的“吸血鬼”,不出門工作,依附于丈夫。而她們為育兒付出的情感和體力勞動,卻無人在意。

趙南柱意識到,女性在當下韓國社會中面臨的諸多問題。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網絡上分享自己因性別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從初中生到高中生,從母親到女性創業者,趙南柱收集、瀏覽了這些素材,并將它們揉進金智英這個人物里。
正如女性主義研究學者金高蓮珠所言,追求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是這本小說最特殊之處。也正是因為這種普遍性,這種面目模糊的形象,讓每一位讀者都有了進入角色與之共情的可能性。從金智英到金智英們,讀者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代入、聯結、共情,形成一個以性別為基礎的情感共同體。
接受GQ報道采訪時,趙南柱表示,她并非將金智英的“分裂”想象成一種病狀,而是希望借此凸顯女性之間基于理解的關愛和安慰。“女性之間可以體驗到那種不安感和恐懼感,當對方陷入危險的時候,當對方不能為自己發聲的時候,我想站出來為她發聲。”女性之間的理解是基于她們共同的性別和類似的生命體驗,而這種共情自有其生命力、爆發力和創造力。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之后,趙南柱又創作了《她的名字是》。她采訪了60幾位女性——從9歲的孩子到69歲的老奶奶,并以這些女性的故事為藍本,寫了這本小說。

正如書中一位女性所言:“我依然年輕,斗爭尚未結束。”
?
當小說照進現實
當女性開始覺醒,開始形成共同體,然后呢?如果女性的聲音是一種源于內部的聲音,是一種不甘于汲汲無名的生長性力量,它能夠沖破性別壁壘,沖破結構性和制度性的不平等,進而抵達整個社會嗎?它能夠生成并且培養一種新的性別生態嗎?它能夠不僅限于文學作品中塑造的如《使女的故事》般惡托邦的警示性想象,刺入現實社會嗎?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作者趙南柱并沒有提供一個光明的充滿希望的結局。故事的最后,敘述視角從金智英轉向了她的精神科醫生,一位四十多歲的男性。在接觸金智英的過程中,他產生了諸多同情和理解,也因為意識到自己妻子的付出犧牲和育兒背后的辛酸陷入深深的自責。

這樣的安排反映了趙南柱在性別不平等問題上的立場。她曾談到,我們經常借助讓男性代入和想象的方式,促使他們產生共情,例如“想想如果受歧視的這位女性是你的母親、妻子、女兒”,但這種方式有其局限性,因為性別問題并非依靠個人善意就能解決。正如她在《她的名字是》一書中不斷傳達的,“女性個體的奮斗是不夠的,學校、公司和社會也應該努力”。
雖然小說沒有光明的結局,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本書引發的討論和行動已經遠遠溢出了文本本身,也遠超出趙南柱的預期。它開啟了小說照進現實的一種可能性。《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在韓國出版后,兩年內在韓國就銷售了100萬冊。
它的讀者既有如韓國總統文在寅、韓國前國會議員魯會燦這樣的政客,也有女團少女時代成員秀英和娛樂節目主持人劉在石。受到這本書的啟發,韓國勞動社會研究所出版了82年生女性勞動的實情分析報告書,一名檢察官在揭發自己被性騷擾的經歷時引用了小說內容,“82年生的金智英法案”作為首爾市涉及雇傭的性別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公共政策被提出。同名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也被搬上銀幕,引發熱議。
相比小說,電影的改編光明、積極、充滿希望、也充滿了公開表達的力量。當再次在公共場合面對“媽蟲”指責時,金智英沒有像電影開篇那樣默默走開,而是選擇正面還擊,走到發出這樣指責的男性面前,質問:“你認識我嗎?你為什么說我是‘媽蟲’?你對我有多少了解就隨意評價我?你知道我經歷了什么,遇到過什么樣的人,心里又是怎么想的?要不我也評價評價你?”
諷刺的是,在影片中,金智英的丈夫被刻畫成一個近乎完美的丈夫——對妻子表示支持和理解,在職場上以高性別覺悟的形象出現,在妻子想要外出工作時主動提出申請育兒假——但上述種種都是一種象征性的好。實際上金智英的痛苦、探索、思忖、轉變都是由她自己以及她身邊的女性同伴完成的。從電影一開始鋪排出的綿密繁瑣的家務到金智英無數次在夕陽中望向窗外,她的丈夫始終是缺席的。即便最后那段為了彰顯稱職父親的接孩子放學并詢問孩子晚上要吃什么的橋段,和金智英在片中付出的繁重勞動和照料相比,簡直微不足道。

更加諷刺的是,一個象征性的熒幕好丈夫形象,已經在現實中博得了眾人羨慕,引發了一眾公眾號的集體高潮,“能有一個孔劉這樣的丈夫,還有什么不滿意的。”這恰恰反映出現實中男性在家庭的缺位和女性處境的艱難。
在電影中,金智英已經可以稱得上幸運。她有氣氛和睦的原生家庭,有支持她并且反思自己性別特權的弟弟,有身體力行支持和踐行女權主義的姐姐,也有疼她愛她在家庭內部反對丈夫重男輕女思想的母親,還有支持她幫助她的好姐妹和上司,在生病時也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支付心理咨詢的費用。
即便如此,金智英還是覺得無力,覺得生活無望,沒有出口,自責為什么自己把生活過成了這樣。
現實中那些女性呢?因不堪忍受長期網絡暴力而選擇自殺的韓國女星崔雪莉和具荷拉呢?因出演了《82年生的金智英》這部電影而被網民抵制謾罵的鄭有美呢?那些在父權制幽靈依舊盤旋的韓國財閥和資本的夾縫中生存的女性藝人呢?被沱沱踩在腳下毒打的忍受屈辱、在站出來勇敢發聲后還被詰問為何不早點離開的宇芽呢?被蔣勁夫暴力對待的日本籍女友中浦悠花和烏克蘭女友Julieta呢?
這些女性的遭遇和困境恐怕無法依靠小說和電影來解決。但小說和電影提出問題,并開啟一個可供討論和訴說的空間,就已經邁出了積極的一步。
在采訪的最后,趙南柱暢想了一種女性生活的最佳狀態:“希望社會不要因為我們身為女性而對我們做出評價,而是把我們當成一個個實實在在的人,與性別無關。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希望每一個女性都可以在一個無關性別的條件下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那就是最好的樣子。”
看完本期推送
你有什么話想說?
在評論區留言吧
撰文:傅適野
編輯:靳錦
視覺設計:二水
運營編輯:二水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