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祝淳翔:柳雨生與小報
兩年之前,幾乎每日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翻閱紙張泛黃發脆的民國小報,搜尋并過錄唐大郎的各色詩文。忙里偷閑,偶然發現在一張知名小報《力報》上,橫空出世一位“超然”,自1945年2月起持續寫稿,題材起先與周越然的類似,“多為中外性學筆談,后也離題改聊舊劇,談相面,旁及讀書感悟、文字考證、文學評論之類”。后來謎底逐漸揭曉,超然果真不是什么無名之輩,他正是淪陷區文壇騰踔恣肆,長袖善舞的柳雨生。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雖說柳雨生在主編《風雨談》月刊時,采取新舊并舉,兼容并包的錄稿政策,刊物上也常有包天笑、程小青等舊派文士的作品,但他終究屬于“正統派”文學陣營,與小報界被普遍目為鴛鴦蝴蝶派的文人們,似乎并無交集。他究竟是如何與小報界的文士們打成一片的呢?此外,他有沒有在別的小報上也如法炮制?甚或用過別的筆名?……總之,當時專注于揭示超然的真身,對于這種種的疑問,均涉入不深。
最近,在逐日翻閱《中華日報·中華副刊》時,發現柳雨生在1944年9月28日《中華副刊》所撰《雨生小報》,竟以小報筆法寫了三節內容,并配有簡短的代序,通篇讀來,每一節都可獨立成篇,著實精彩紛呈,大有考證余地。

先來看文前的“代序”:
每日讀報皆讀大報,讀得頭痛,遂喜覽其副刊,副刊非每日可看,遂看小報,以迄于今亦積歲矣。不佞為小報作文,始于十余年前《晶報》,錢芥老晤時猶復詢之,后亦屢為他報涂鴉,興到為之,時作時輟。今寫此數則,以實“副刊”,顏曰雨生小報,推此用心,固不止于謀遮眼而已矣也。
原來柳氏曾為《晶報》撰稿,也與該報元老錢芥塵熟識,語氣中透出一股擺老資格的味道。而此時寫此數則,究其用心,想必是在向當日小報界的同仁輸誠吧。
該文的第一節“為小報作文”,如此袒露心聲:
某報,俗所謂小型報也,為小報作文,通常不免“有失正統派文人”之誚。然此實無意義。……若周先生啟明,戰亂前即常為北平《實報》撰小品,體裁一類后日之《看書偶記》《藥堂語錄》,讀之開卷有益,掩卷有味。馀如徐凌霄一士兄弟隨筆,亦獨步南北,專研掌故文史故實者。南方所見,舊時不必論矣,近如某報之曼翁,其秋星閣筆記式之短文,又何一不清峭有極致。專以小報為肆詬罵揭隱私者,不免為一孔之見也。惟小報文字,其事不外政海秘辛,今已不多見,再則為社會風尚,名人動態,極確正而饒意趣者蓋亦甚尠,最后遂及飲食男女之私,以及劇壇掌故,銀幕消息,浸假而至市井土語,艷側佚聞,不免逐于俗陋。惟忙人之所閑,其尤善者,雖小道必有可覯,君子弗棄,而閱眾轉自超越大報,若某報諸文,時有妙緒,流傳之廣,亦無遠弗屆也。
某報,當指《力報》。據九公(蔣叔良)在《小型報內幕》的第七段“小型報的最近趨勢”里披露,為了扭轉頹勢,擴大銷量和影響力,力報方面“轉變方針”,延請海報系人物(指黃也白)擔綱編務。至10月16日,《力報》即以醒目黑體大字刊登預告:“二十日起,以嶄新姿態與讀者相見”,其中所附36位新作者名單中,柳雨生赫然在列。此后便以本名點綴其間。
說實話,一向務實的力報社長胡力更無疑看重的是黃氏的人際關系網,而在后者廣大的作者群中,當然少不了年富力強的柳雨生。柳氏以北方的周作人、享譽南北的徐凌霄一士兄弟以及南方包天笑(曼翁)等人都曾替小報供稿為例,推崇褒獎之余,強調小報雖稱小道,卻“君子弗棄”。于是給自己重新“出山”,擺出充足的理由。此外,柳雨生還儼然將小報內容分出等級,第一等是“政海秘辛”,繼而“社會風尚、名人動態”,再次則為“飲食男女、劇壇掌故、銀幕消息”,卻將“市井土語,艷側佚聞”貶為末等。這也許會讓小報界的主將們感到不適的。
接下來的一節則為“張愛玲與平秋翁”:
張平二公,近為稿費及其他寫稿不寫之細事,爭怨于報端,蓋逾旬矣。二公以文字之交之姿態言之,皆為愚之友人,且皆不時常晤面。日昨友人晶孫招宴于其事務所,到者予且、黎庵、亢德、江楓、關露等多人,而秋翁亦應邀來臨。閑談之間,不佞首以二公和解之議進,而江楓主纂《雜志》,社中出小說《傳奇》,亦與此事不無景響,遂群起詢之江楓秋翁,二君亦首肯。惟事不宜遲,病宜速治,雜志社似應于最近期內,商得當事二公同意,遍邀海上不分新舊文士,共襄盛舉,往事如煙,況際茲離亂,此等事大可一笑置之,矧雙方又或不過略有誤會,一經名法家如予且黎庵等排難,張平二君又烏得不點頭相喟耶?
此前,一直不大清楚作為兩人共同的朋友,柳雨生在張愛玲與平襟亞爆發矛盾,在報上爭訟互斗時的態度。從上面這段文字,分明可見柳雨生的立場了:他似乎并不想分辨是非曲直,只想在朋友們的共同勸解之下,盡快息事寧人。找的理由亦冠冕堂皇。觀其行文,則一派典型小報風格,確實是浸淫多時,故能與之融為一體。
末一節“某書店”:
某書肆,其名與保險及印刷公司三輪車公司同,實為愚輩所營書肆之省稱,其本名為“某某書局”,以局字不及店之響亮,友人率多以某某店稱之。其店亦在所謂文化街之四馬路(福州路)晝錦里口,左與中央,右接世界書局為鄰。店舊為四如春面館,今停歇,改建以來,觀者咸謂其式甚類東洋料理店。今知其不然。緣某某書局,舊有其名,實友邦熱心人所辦,出版華文東文書籍,址在小沙渡路,與同名之印刷所毗鄰。然華文所出無幾,而所刊畫報亦旋刊旋輟,今俱廢矣。不佞有志文化,而無力出版,又乏貿遷經驗,聞舊店停頓,有意改組重盤,遂與陶亢德兄等謀諸有資力友人,杭育杭育而有心擺一個精神食糧攤之議。其攤創立于本歲六月,迄今亦逾季矣。亢德固善擺精神食糧攤者,過去所創之宇宙風社、亢德書房、人間書屋,績業自在眾口間。今合辦此書店,立業之始,即著力推銷新舊文學書籍雜志,兼及文化教科書。至本版新書,如知堂、紀果庵、予且、陶晶孫、楊之華、楊晉豪、路易士、丁諦、譚正璧諸君所作小說散文,已先后付梓。雖規模甚小,紙張困躓,而入室也清幽,磚地低落寸許,置有書桌煙缸及諸色新書,供讀者咀嚼,書皆偏于文藝及一般文化,無干燥乏味,店友皆讀書,無惡聲惡顏之弊。亢德亦有心人也。愚文即排日成于“店”中,因以為顏,并略述其梗概。
開篇寫得甚為風趣,故意打著啞謎,深怕讀者不知道在說太平書局,這抑或是在模仿小報上的某人,也未可知。這段記述其目的還是在做宣傳,先是點明書局的方位,包括新址、舊址,又是怎樣引入新的管理者,承前啟后。所謂“友邦熱心人”即指日人名取洋之助,等柳雨生請來陶亢德合作之后,此人退居幕后,書局的業務遂亦發生了不小的變化。還將書店的布局、陳設及店員情況公之于眾,也令陌生讀者一目了然。
客觀地說,該書局的創辦,在豐富讀書人的精神生活方面是不無貢獻的。如愛書人周炎虎《買書漫談》(《文史》第3期):“在紙貴上海的時代,陶亢德柳雨生兩君竟在文化街經營書店。陶君對于出版編輯已是此中老手,我于他編輯的刊物,都有收藏,是他的一個忠實讀者。這次陶君經營太平書局,我有一點貢獻……”
多年以后,許覺民在一篇回憶文章《孤島前后期上海書界散記》(《收獲》1996年6期)中也提到了這家書店:
孤島消失后,福州路上頓見蕭索。有的書店雖然也開著,但出售的圖書經過清理后已少有特色,宛如一個個被盜匪洗劫后的人沒精打采地蹲在那里一般。不久,福州路上開設了一家名“太平書局”的,主持者為落水文人陶亢德,這書店門面不小,構筑的樣式有點日本色調,一望即可知是敵偽辦的。這書店的出版物以文學讀物為主,表面上看來還并不十分可憎,大約正是一種文化懷柔政策的表現。
仔細想想,倘若抹除其日資背景,太平書局出的書,如周作人、紀果庵、金性堯的散文,凌霄一士、瞿兌之的掌故,譚惟翰、潘予且、丁諦等人的小說,哪一本不是經典名作呢?可嘆的是,兩年后陶柳雙雙被判入獄,辦這一項文化事業,也成為罪名之一。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可謂身陷囹圄悔也遲啊。
柳雨生現身《力報》,是在1944年冬。次年4月2日,他以超然筆名撰《一鞠躬》,述及曾先后兩次登上力樓拜訪同文:
難得到有名的“力樓”來拜訪朋友,雖然欣仰已久。去年有一天來候黃也白先生,在座見到白玉薇女士及鳳三先生,雖值冬寒,居然譚得滿室生春。事后就想常趨力樓,終因俗務羈絆,今年方才第二次,為了友人譚惟翰先生要拜望也白兄,鄙人忝居引導,又會見了鳳三及勤孟先生。還有許多位,聞名已久,如雷貫耳,人去還是初識,或僅晤面數次,沒有深談,不過我從旁看到他們的談笑及忙碌情況,心里也深覺得力樓是一座有趣味的地方。
然而同文于報間有所回應的,似乎只有柳絮、鳳三和勤孟。如柳絮撰《〈 撻妻記〉讀后感》(《力報》1945.1.7),對集中篇什略作點評。鳳三《超越二公》(《力報》1945.3.2),記不久前的“元宵文藝沙龍”,與超然同席。勤孟《謝柳雨生》(《力報》1945.3.30)也憶及元宵“萬象廳文藝聯歡會”上第一次見到柳,“后月馀,柳偕譚惟翰先生登力樓,余識之,因道仰慕之忱,共談片刻,意實未暢也。翌日,承贈《撻妻記》及舊著《人物風俗制度叢談》各一冊。”并附信毛遂自薦,欲參與小型報同文義演。終因細故未能如愿。
無獨有偶,在另一份城市小報《大上海報》也出現了超然的“蹤跡”。分別為:《十一點》(1945.5.25)、《記撻妻記》(1945.5.26)、《末梢與根塞》(1945.5.28)、《李又全》(1945.5.29)、《夏日之春》(1945.5.31),其中的四篇或多或少與性有關。《撻妻記》是柳雨生的一本短篇小說集,作者在報攤上見到此書再版,“心里有一點兒喜悅”,便寫短文抒發感想:“這本書中,記戀愛式的故事,如《香侶島》《栗子書》是一組的,《夜行人》和《霧》又是一組的,它們都沒有傳統式的故事的氣氛。這樣的寫法,也許可以算是不好的,可是我在寫它們的時候,卻的確把我這些虛構中的人物看得很神圣。”
這幾篇隨筆之后,似乎停頓了一個月,復因潘勤孟于7月1日發表一篇《太平書局座談會》,援引柳雨生、陶亢德、吳江楓、周班公及其本人對于小型報的回顧與前瞻。其中引柳雨生的話,說李士群死事真相,是小型報絕好材料,但至今沒有看到。此事其實極敏感,私底下的話怎可公開?為了免遭物議,超然遂于次日撰《“太平座談會”補》,以往年小型報喜記名人軼事為由,作了一番解釋工作。大致上算是應付過去了。7月7日,又撰《“一日三價”辯》,為《風雨談》雜志隨行就市、一日三變的價目作出申辯。
無意中,讀及1945年6月28日《大上海報》上有篇署名秋翁的隨筆《長戚》,又于次日印出“更正”,稱前一日《長戚》一文“系深翁所作,為手民誤植秋翁”。這不尋常的舉動引起了我的注意。該文錄有一段日記,其中提及陶亢德與蘇青:
日記這個東西,不記它是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按天記敘,隔了一些時候看看,倒也真有意思。本年一月五日星期五,我的日記有著這樣的話:“上午在書肆。午間,亢德加菜宴同人,因前生一女,伙友曾送賀禮也。蘇青來談,至四五時而霜老亦來。六時許,相偕小酌于二馬路同華樓,食二蚶子,醉蟹一,大魚頭豆腐,白蹄,燒菜心,又酒飯,共九千余圓,四人分攤。興猶未闌,又去某某咖啡館小坐,霜老請也。屋內甚暖,有柔暗美。惟食客大多‘醉翁’,亦有制服軍人,男女雜沓。今日亢德勸予勿長戚戚,宜坦蕩蕩也,甚可感”。
之后,作者大嘆苦經,絮叨著大時代的悲歡離合之類的話……我所感興趣的是,這個深翁又是何方神圣?從其交游圈子來看,我很懷疑這也是柳雨生(如1944年12月25日創刊的《語林》刊有柳雨生《幼學記》,提及這年夏天與陶亢德、蘇青在跑馬廳的一家小館吃飯閑聊),于是拈出吳商《淪陷日記》(刊《好文章》三集,1948年11月出版。按吳商即柳雨生,可參見宋希於相關考證)同一日的日記作一比對:
上午到肆。午間,浩兄加菜宴客,因前生一女,伙友曾送賀禮也。莊女士來談,至四五時,霜兄亦來。六時許,霜,宛,君浩及余相偕小宴于二馬路同華樓,食二蚶子,醉蟹一,大魚頭豆腐,白蹄,燒菜心,又酒飯,共九千余元,四人分攤。余與君浩,胡,莊諸君久不聚食,無所不談,亦自快意。然苦中作樂,是苦是樂耶。
幾乎驚人的一致。《淪陷日記》中被改寫的君浩即陶亢德,莊女士、宛,當即蘇青(本名馮允莊),皆可一一對應。霜,估計是《雜志》編輯吳江楓(筆名霜葉、霜廬)。
循此,又找到深翁在《大上海報》所撰的《記蔣孟麟》(1945.6.29)、《小功之察》(1945.7.2),以及以同一筆名,卻刊于《力報》的《康長素之兩極端》(1945.7.3)、《鉆穴之官》(1945.7.6)、《異術》(1945.7.7)和《飲食男女》(1945.7.8)。細讀之,便可知曉柳雨生當時的所思所想,以及生活近況。
回過頭,來說說《大上海報》的背景。楊嘉祐《半個世紀的上海小報》披露:“《大上海報》是《中華日報》經理顏某號稱‘集資’所辦。……顏某辦此報,不向偽新聞處申請登記,而是借用停刊較久《大上海報》的登記證,編輯撰稿人都是聘用小報界人士,也有留在淪陷區知名的作家。”顏某即顏加保,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中對他有所描述。此人是鐵桿汪派,先是跟著林柏生在香港辦《南華日報》,宣揚汪的主張。后來汪系《中華日報》在滬復刊,顏加保擔任營業部經理。抗戰勝利前夕,此人官運亨通,被任命為偽安徽省稅務局長,又辦過鈣奶生食品公司,估計撈到不少錢。以至于抗戰結束后,能安然逃往香港,據說就是花錢買得自由身。那么楊嘉祐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呢?則輾轉從陳青生先生處打聽到,楊氏即《大上海報》主編楊赫文的本名,作為親歷者和當事人,自然一切心知肚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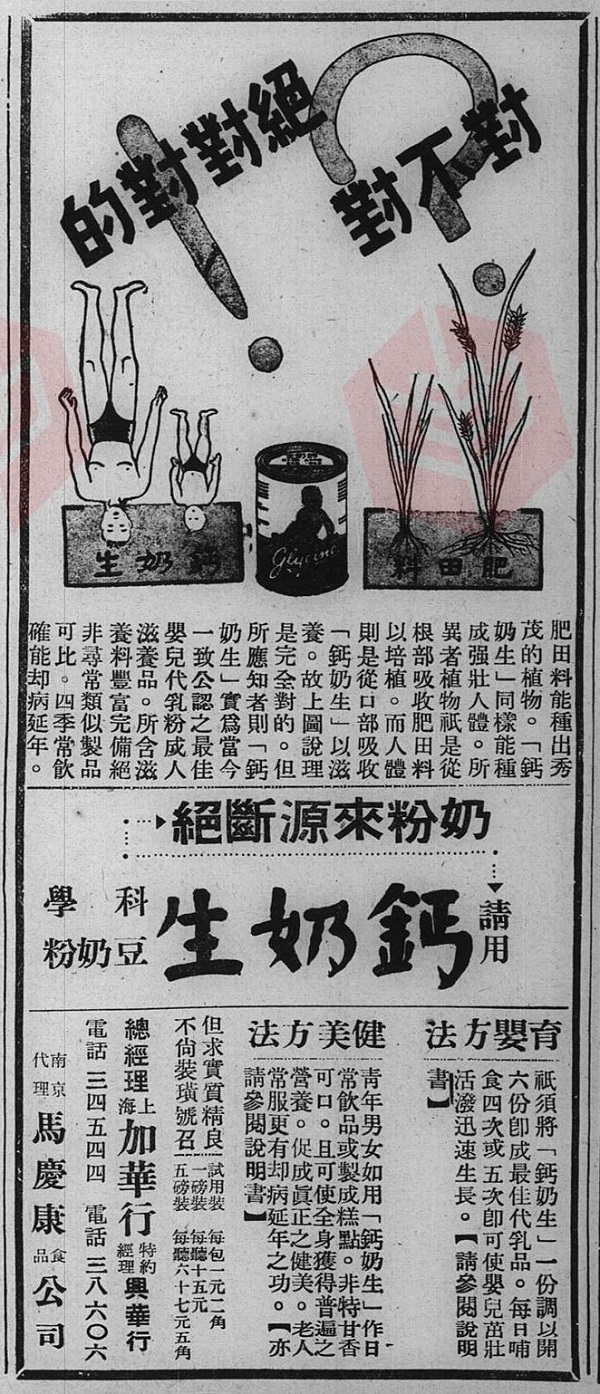
中華日報》上的鈣奶生廣告
不妨再說說《風雨談》上柳雨生還用過兩枚偶一為之的筆名,相關線索都來自小報。
1945年6月30日,《力報》與《大上海報》分別有兩篇報道,均談及即將出版的《風雨談》。其一為玉茹《蘇青的近作》,文中寫道:“昨天筆者偶去訪友,看到七月號的《風雨談》校樣,原來是出的夏天生活專號,這是很刺激的‘噱頭’。一看文字,果然是十分精彩,有予且、越老、超翁、譚惟翰、何若、路易士等十余位名家執筆”,接著稍微例舉了幾篇文章梗概,并于篇末煞有介事地道:“還有一個秘密,我這里不妨吐露一點出來,該期中還有一篇很幽默的文章,也可以說是‘小報論’,卻是謔而不虐,饒有妙趣,里面談到阿毛哥、曼翁、夷白諸公的大作。文章是寫得很溫柔敦厚的,作者也是文壇上頗有名的一位,至于究竟是誰,愛讀文章的‘閱眾’,卻何妨猜上三猜!”這里所提的“小報論”,當指《西窗讀報談》,署名賓客。通讀之,發現文章第二段,也是從大報談起,繼談其副刊,終及于小報,雖詳略不同,但這思路與《雨生小報》的“代序”有異曲同工之妙。又鑒于“閱眾”一詞原是周越然的口頭禪,后來也為超然所模仿、借用,且柳氏文章素被目為“得溫柔敦厚之旨”,故這位在《風雨談》大談小報的“賓客”(意指小報界的“外來戶”),分明就是編者柳雨生。
另一篇是黑老夫《蘇青、顏潔、張愛玲》:“《風雨談》自改大型以后,新舊作家時有佳作刊布,這一期出的夏天生活專號,稿子至十七篇之多,除了避暑一類的散文外,還有蘇青的談夏天的吃,超翁的談夏天聽戲……”作者在《風雨談》七月號雜志出刊之前,已知曉內容,想必見過校樣,故與《力報》上發文的那位玉茹為同一人。我猜他很可能便是力報社編輯黃也白。“超翁的談夏天聽戲”,所談即《聽戲》,署名則為“老鄉”。
換言之,柳雨生為使“夏日生活專號”贏得讀者青睞,刻意避免兩次出現自己的名字,索性用了不為人知的兩枚筆名“賓客”“老鄉”。真是用心良苦了。
柳雨生說十幾年前就已經在替小報寫稿,時間上有所參差,似有托大之嫌。今查得柳雨生曾以“予亦”筆名在《光華附中半月刊》寫稿,時在1933年。作為高中生,他筆頭甚健,作品題材亦十分廣泛,有書評、隨筆、詩經試譯,甚至還有獨幕話劇。等考上了北京大學,他利用業余時間,“跟著一班弄戲劇治詞的朋友們在一塊兒,抽暇也寫一點談論舊劇的文章”。這些文章,如“彤齋劇話”(彤齋,是柳雨生的書齋名,多次見于文后注記,有時也署為:彤齋予亦)按期登載在《北平晚報》和《民聲報》上,“彤齋劇談”登在《立言報》,直至七七事變發生而止。回滬后,“偶有所書,輒付《十日戲劇》”。之后,才為《晶報》撰寫“彤齋戲語”專欄,時間則已經來到了1938年7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