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韓柳文研究法》:翻譯家林紓的另外一面
林紓最家喻戶曉的成就是翻譯,但是他一生著述宏富,尤致力于古文的評(píng)點(diǎn)與寫作。唐代韓愈與柳宗元提倡古文運(yùn)動(dòng),在文學(xué)史上影響深遠(yuǎn),其文章被后世奉為典范。林紓所著《韓柳文研究法》,遴選韓柳佳作一百四十余篇,逐篇剖解其文理與技巧,集中呈現(xiàn)了他在民國(guó)初年尖銳文化沖突的背景下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認(rèn)識(shí)。本文系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劉寧為新近整理出版之《韓柳文研究法校注》(低音·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9年11月)所寫的序言,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刊發(f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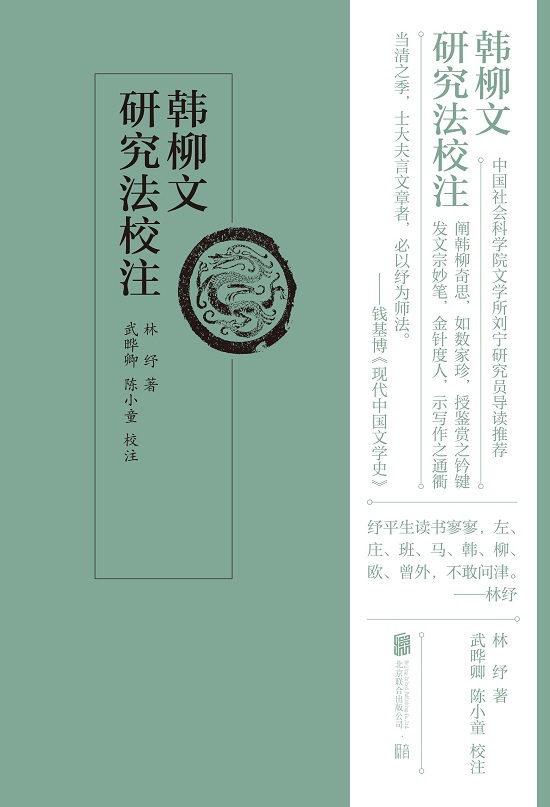
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hào)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林紓最家喻戶曉的成就,是翻譯二百多種外國(guó)小說(shuō),風(fēng)行海內(nèi);然而在近代文化史上,他還有許多重要的建樹,其中作為古文家,在新舊文化轉(zhuǎn)關(guān)之際,為延續(xù)和發(fā)展古文傳統(tǒng)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尤其值得關(guān)注。對(duì)于古文藝術(shù),他既有抉發(fā)文理的理論思考,又有體悟文心的篇章點(diǎn)評(píng),前者的代表作是《春覺齋論文》《文微》等著述,后者的代表作則是《韓柳文研究法》和《左傳擷華》。韓柳古文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歷代品評(píng)者眾,林紓這部《韓柳文研究法》自出手眼,對(duì)理解韓柳古文極有裨益,因此自問世至今,一直是閱讀韓柳古文難以繞開的津梁。
韓愈是古文宗師,林紓對(duì)韓文極為推重。在《左傳擷華》中,他說(shuō):“天下文章,能變化陸離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馬、一韓而已。”對(duì)于韓文,他沉潛鉆研,傾注了極大的心力,在《答甘大文書》中,他回憶自己的學(xué)韓經(jīng)歷:“仆治韓文四十年,其始得一名篇,書而黏諸案,冪之。日必啟讀,讀后復(fù)冪,積數(shù)月始易一篇。四十年中,韓之全集凡十?dāng)?shù)周矣。”林紓晚年曾反復(fù)勸勉后學(xué),讀古人書要“神與古會(huì)”,要“涵而泳之”,“泳如池沼澄碧,魚鳧上下,自在悠游于中;涵如以巾承露,浸漬全幅使透”,又說(shuō)“讀文須細(xì)細(xì)咀嚼,方能識(shí)辨其中甘辛”(《春覺齋論文》)。他對(duì)于韓文的研讀,顯然就是如此全身心地沉浸濃郁。
由于寢饋甚深,林紓自己的古文創(chuàng)作也被韓文潛移默化。1901年,他以文名被聘為北京金臺(tái)書院講席,從此由閩入京定居。不久又任五城中學(xué)堂國(guó)文總教習(xí),其間與桐城古文大家吳汝綸結(jié)識(shí)。吳稱贊林紓的古文“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林紓《贈(zèng)馬通伯先生序》)。這一評(píng)語(yǔ)非常接近北宋蘇洵對(duì)韓愈文章的評(píng)價(jià):“韓子之文,如長(zhǎng)江大河,渾浩流轉(zhuǎn),魚黿蛟龍,萬(wàn)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蘇洵《上歐陽(yáng)內(nèi)翰第一書》)可見,在吳汝綸看來(lái),林文深有得于韓文之精髓。
這部《韓柳文研究法》初版于1914年10月由商務(wù)印書館印行,林紓此時(shí)已六十二歲,剛從北京大學(xué)去職。全書選評(píng)韓文60余篇、柳文70余篇,應(yīng)是在其北京大學(xué)授課講義的基礎(chǔ)上整理而成,當(dāng)時(shí)京師大學(xué)堂的課程,多以某某研究法命名,此書的命名應(yīng)該是受此影響。書中具體的選評(píng)方式,繼承了古文的評(píng)點(diǎn)傳統(tǒng),但內(nèi)容則多有獨(dú)到的思考,不僅反映了林紓數(shù)十年沉潛韓柳文的所得,也體現(xiàn)了入京后復(fù)雜文化學(xué)術(shù)沖突對(duì)他的觸發(fā)和影響。林紓早年即醉心古文,他博覽群書,中年后對(duì)以韓愈為主的八家之文以及《左傳》《史記》《漢書》等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和桐城派的古文旨趣頗為接近,但林紓并未有傳續(xù)桐城派的自覺意識(shí)。入京后,他與桐城派吳汝綸、馬其昶、姚永概等代表人物頗為親近,他甚至向吳汝綸表達(dá)了希望能居門下受業(yè)的愿望。1906年他受聘任教于京師大學(xué)堂,與當(dāng)時(shí)同在大學(xué)堂任教的章太炎產(chǎn)生矛盾,錢基博提到當(dāng)時(shí)“大抵崇魏晉者,稱太炎為大師,而取唐宋,則推林紓為宗盟”(《林紓的古文》)。由于章太炎一派的排擠,林紓不得不于1913年從北京大學(xué)去職。無(wú)論是與桐城古文家的親密,還是與章太炎一派的矛盾,都強(qiáng)化了林紓對(duì)桐城派所主張的以唐宋古文為核心的文章傳統(tǒng)的認(rèn)識(shí)。雖然他一直不認(rèn)為自己是“桐城派”,而且明確主張“桐城無(wú)派”,反對(duì)用狹隘的派別來(lái)框定桐城諸子的成就,但桐城派對(duì)其古文思考的影響,在入京之后無(wú)疑是日趨深刻的。這部《韓柳文研究法》就體現(xiàn)出這種影響。
桐城派主張“文道合一”,“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重“義法”、講“雅潔”。所謂“義法”,方苞認(rèn)為“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又書貨殖傳后》);意謂文章內(nèi)容要合乎儒家之義理,行文要講求法度。所謂“雅潔”,就是為文以儒家倫理之道為本,立意雅正,語(yǔ)言也不能蕪雜枝蔓。這些文章宗旨,都鮮明地體現(xiàn)在林紓對(duì)韓柳文的解讀之中。北宋秦觀稱贊韓文“鉤莊列,挾蘇張,摭遷固,獵屈宋,折之以孔氏”,林紓認(rèn)為此語(yǔ)頗為不妥:“韓文之摭遷固,容或有之;至鉤莊列,挾蘇張,可決其必?zé)o。昌黎學(xué)術(shù)極正,辟老矣,胡至乎鉤莊列?且方以正道匡俗,又焉肯拾蘇張之余唾?”林紓認(rèn)為秦觀被韓文的“海涵地負(fù)之才,英華秾郁之色”所炫惑,沒有看到韓文“信道篤、讀書多、析理精”;因此,林紓論韓文,始終堅(jiān)持以儒為本。
在藝術(shù)上,林紓高度贊同北宋蘇洵對(duì)韓文“抑絕蔽掩,不使自露”的評(píng)價(jià),認(rèn)為“蔽掩,昌黎之長(zhǎng)技也。不善學(xué)者,往往因蔽而晦,累掩而澀……能于蔽掩中有‘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所以成為昌黎耳。”在林紓看來(lái),韓文的汪洋縱恣,并不表現(xiàn)為外在的駁雜,而是內(nèi)在的豐富,因此韓文的創(chuàng)作一定是經(jīng)歷了深入的錘煉淘洗,絕非率然的隨興所至,他說(shuō):“吾思昌黎下筆之先,必唾棄無(wú)數(shù)不應(yīng)言與言之似是而非者,則神志已空定如山岳,然后隨其所出,移步換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窈曲折,使入者迷惘;而按之實(shí)理,又在在具有主腦。”
林紓對(duì)韓文的解讀,正是用力于揭示韓文抑遏蔽掩、淘洗錘煉中的光芒;而其詮評(píng)的入手處,則是分析韓文的法度,其中又尤其關(guān)注韓文文體的特點(diǎn)。他論韓愈《原道》不僅“理足于中”,而且“造語(yǔ)復(fù)衷之法律”。行文有法,可使學(xué)者“循其途軌而進(jìn)”。又論《進(jìn)學(xué)解》,認(rèn)為此文“本于東方《客難》、揚(yáng)雄《解嘲》”,孫樵以其行文奇警而將其與盧仝《月蝕詩(shī)》相提并論,是不恰當(dāng)?shù)摹S秩纭稄堉胸﹤骱髷ⅰ肥恰吧w仿史公傳后論體”。這些都體現(xiàn)了辨體的努力。林紓對(duì)古文文體特點(diǎn)多有精妙的論述,如論“贈(zèng)序”之特點(diǎn):“愚嘗謂驗(yàn)人文字之有意境與機(jī)軸,當(dāng)先讀其贈(zèng)送序。序不是論,卻句句是論,不惟造語(yǔ)宜斂,即制局亦宜變。”又論“祭文體本以用韻者為正格,若不駕馭以散文之法,終覺直致”。這些文體之論,都頗為新警深刻。
在此基礎(chǔ)上,林紓進(jìn)一步觀察到韓文法度中的新意,規(guī)矩中的千變?nèi)f化,如論韓愈之書信:“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結(jié)構(gòu),未嘗有信手揮灑之文字。熟讀不已,可悟無(wú)數(shù)法門。”又論韓之“贈(zèng)序”如“飛行絕技”,無(wú)人可以企及。《韓柳文研究法》最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對(duì)這些無(wú)法之法的解讀。他或言韓文語(yǔ)言之妙,“在濃淡疏密相間錯(cuò)而成文”,又論《說(shuō)馬》之“馬之千里者”五字,是于行文幾無(wú)余地可以轉(zhuǎn)旋之處,忽然叫起,“似從甚敗之中,挺出一生力之軍”;論《畫記》“文心之妙,能舉不相偶之事對(duì)舉成偶,真匪夷所思”;論《重答張籍書》“辯駁處無(wú)激烈之詞,自信中含沖和之氣”;《送齊暤下第序》則是“篇法、字法、筆法,如神龍變化,東云出鱗,西云露爪,不可方物”。
這些精妙的體悟,是林紓繼承桐城而又更為豐富開闊之處。他對(duì)桐城“義法”,從“性情”和“意境”兩個(gè)方面加以拓展,認(rèn)為“義”要融會(huì)為一種作家內(nèi)在的精神人格,形成豐富的精神性情,這種“性情”是文章的根本——“文章為性情之華”“性情端,斯出辭氣重厚”。對(duì)于 “義法”之“法”,他沒有將其泥定為具體的起承點(diǎn)畫,而是從“意境”的角度加以闡發(fā)。在《春覺齋論文》中,他標(biāo)舉為文“應(yīng)知八則”,皆文法綱領(lǐng),首揭者即為“意境”,提出“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不能造境,安有體制到恰好地位”。義法之法,即是“意中之境”,“境”的形成當(dāng)然要綜合多種因素,而其所以形成之本又在于“意”。這就為悟入古文妙境,尋繹文章無(wú)法之法,打開更豐富的空間。“桐城三祖”中的劉大櫆和姚鼐,從推重音調(diào)和藝術(shù)風(fēng)格的角度來(lái)豐富對(duì)文法的認(rèn)識(shí),而林紓對(duì)文法的討論,則綜合了這些傳統(tǒng)而更為豐富靈活。
《韓柳文研究法》另一個(gè)很值得關(guān)注的特點(diǎn),是韓柳并論。柳宗元雖名列八家之一,但后世古文家對(duì)柳文頗多爭(zhēng)議,特別是桐城派如方苞等人,論文取法韓歐,多有抑柳之論。林紓并未受此束縛,他自述精研“韓柳歐三氏之文,楮葉汗?jié)n近四十年矣”(《答徐敏書》),力主柳宗元“為昌黎配饗之人”。
林紓雖然突破了桐城派對(duì)柳文的偏見,但他解讀柳文的視角,還是與他解讀韓文一樣,淵源于桐城的文法傳統(tǒng)。唐代劉禹錫論柳文:“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古來(lái)論柳文者眾,林紓獨(dú)以此語(yǔ)為知言,甚至說(shuō)“雖柳州自道,不能違心而他逸”。對(duì)于柳文的語(yǔ)言,他認(rèn)為“用字稍新特,未嘗近纖;選材至恢富,未嘗近濫;麗而能古,博而能精”。從思想上講,柳宗元精通佛理,林紓對(duì)此有意加以忽略,“集中六、七兩卷均和尚碑,不佞昧于禪理,不能盡解,故特闕而不論”,又“柳州集中有‘序隱遁道儒釋’一門,制詞命意固有工者,然終不如昌黎之變化。且釋氏之文逾半,從略可也”。可見,無(wú)論從藝術(shù)上,還是思想上,林紓論柳都滲透了桐城的“雅潔”旨趣。
林紓對(duì)柳文藝術(shù)的詮評(píng),就其方法,與評(píng)韓并無(wú)二致,也很善于揭示柳文文體特色,發(fā)抉其篇法、章法、字法之妙,如對(duì)《封建論》開篇立一“勢(shì)”字的分析,對(duì)《段太尉逸事狀》“氣壯而語(yǔ)醇,力偉而光斂”的討論,對(duì)永州山水記用字精微的品味,都值得細(xì)細(xì)體會(huì)。
林紓讀柳文,最值得關(guān)注的,是對(duì)韓柳文命筆異同的對(duì)比,例如“昌黎《碑》適是學(xué)《尚書》,子厚《雅》適是學(xué)《大雅》,兩臻極地”“(韓愈《柳州羅池廟碑》)幽峭頗近柳州,如‘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此三語(yǔ),純乎柳州矣。柳州勍峭,每于短句見長(zhǎng)技,用字為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為人人筆下所無(wú),昌黎則長(zhǎng)短皆宜。自‘民業(yè)有經(jīng)’起,‘出相弟長(zhǎng),入相慈孝’,純用四言,積疊而下,文氣未嘗喘促,此亦昌黎平日所長(zhǎng)”。這些看法,也都很值得細(xì)細(xì)體會(huì)。
馬其昶為《韓柳文研究法》作序,稱林紓將自己平生對(duì)古文的甘苦所得,“傾囷竭廩,唯恐其言之不盡”。在此書出版數(shù)年后,林紓就卷入了與“五四”新文化人的論戰(zhàn),為延續(xù)古文命脈而大聲疾呼。1917年2月8日,他在《民國(guó)日?qǐng)?bào)》上發(fā)表《論古文之不當(dāng)廢》,稱“夫馬、班、韓、柳之文,雖不協(xié)于時(shí)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學(xué)之,……必有一二巨子出肩其統(tǒng),則中國(guó)之元?dú)馍杏写嬲摺薄_@部《韓柳文研究法》集中呈現(xiàn)了他在民國(guó)初年尖銳文化沖突的背景下,對(duì)作為中國(guó)文字之祖的韓柳文的深入認(rèn)識(shí)。在古文的文化藝術(shù)價(jià)值重新引發(fā)關(guān)注的百年后的今天,這部書值得給予更充分的關(guān)注和探討。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