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吳雅凌讀《我不可告人的鄉愁》︱一半比全部值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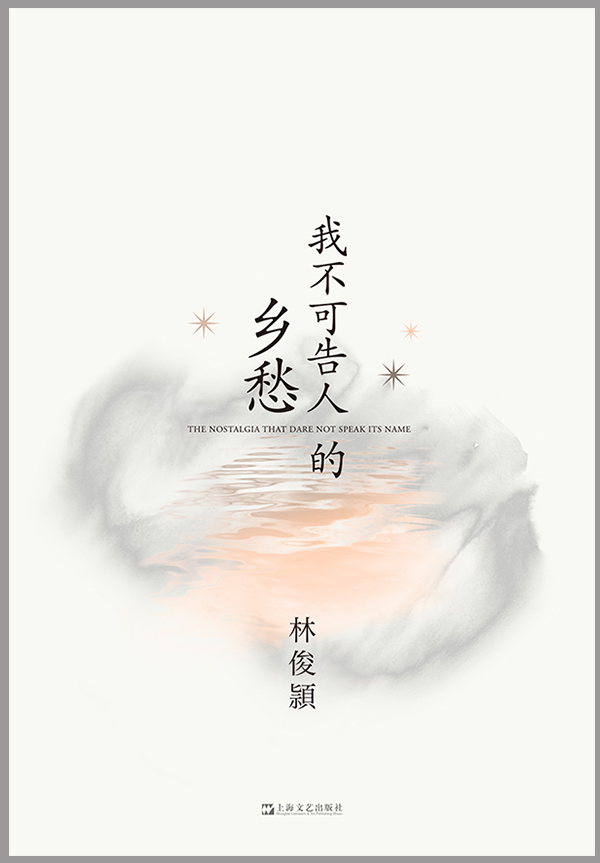
一
6月在南方。人最好學樹的模樣。沉默中郁郁蔥蔥,向雷雨敞開,交遞看不見的氣息。
每天下午放電影。新浪潮,不新了。五十年前的電影,人到中年才看出滋味。那一代年輕人在電影里奔跑,犯罪,在愛中孕生,絕對地不要命。戈達爾的《輕蔑》,一群電影人拍荷馬史詩,有人中途死了。李維特的《巴黎不屬于我們》,一群年輕人排演莎士比亞,狀況連連。《瘋狂的愛》換成拉辛,有人入戲要自殺和殺別人。顧不得奧德修斯們的古早苦難,他們在電影里追逐什么比性命更要緊的東西。
我來講安德洛瑪克神話的古今版本。Andro-mache,名字里頭有“人”有“戰爭”,太硬的女人名啊,什么樣的命運才壓得住?從荷馬到新浪潮,特洛亞亡城女子的蹤絲千年不散。原本想到李維特的《瘋狂的愛》,重看才發現,阿蘭·雷奈的《廣島之戀》真正是安德洛瑪克的現代故事。那個從戰爭中活下來的女子,死了愛人,被勝利的人們剃了頭,游街囚禁,趁夜出奔,從此無故鄉。某日在廣島,也許是那間茶室依稀有故國河水的光影流轉。她突然地推案而起:啊!啊!我曾經多么年輕!
工作坊上,眾人認真地聽,也不解地問:為什么要去說荷馬?
6月太張狂,到7月落一身皮疹。南方故鄉的樹叢和蚊蠅在我的身體留下殷紅的斑點,謎樣的地圖標記。夜里難寐,把林俊頴的小說一字一句念成鄉音。是因為艱難,各方面的難,才慢慢地讀進了心里。那些游離在口說和書寫之間的男男女女,如魂影的夢,蒸騰汗水和淚水的氣味,滋潤痛癢難耐的皮肉和靈魂。現代文學是與日常瑣碎的血肉相連的筋絡。不病感覺不到存在。不通,痛了,有了掙扎和自我關照的迫切,遂在文學的鏡像中浮顯所謂詩意的慰藉。讀著讀著,我也依稀去了從前,阿伯坐在大厝的彩描嵌瓷門廊下打盹,茶桌上的收音機幽幽地唱南曲。
白天我以長衣長褲維持體面,黑夜獨自面對“我不可告人的鄉愁”:一半是難以捉摸的荷馬,一半是漸漸生澀的泉州話。6月的文章寫寫停停,在7月尋找到它的另一半。
二
毛斷阿姑十七歲就見了世面。從斗鎮林家老厝去扶桑國。船上遇同鄉少年書生,生平頭一回被稱呼“密斯林”。他帶她看櫻花,念詩給她聽,在粉白花簇下私定終身。
毛斷,modern的諧音。全斗鎮的姑娘數阿姑最摩登。第一個出洋“食咸水”,彼時斗鎮無汽車,伊已識得車油味。第一個自由戀愛,未過門與翁婿出雙入對徹夜不歸。在大街媽祖宮前聽他宣講“安娜琪”姑娘,眸子宛若兩粒含情的彗星。
斗鎮林家盛極一時:“某家族所有,阡陌相連到天邊,雀鳥飛毋過。”四兄喜讀古冊,六兄偏擅刺繡。毛斷姑丈頭一回上門,連過幾關。大門的長工,灶腳的廚娘,六兄守花房,四兄坐大廳,一厝長幼之后,終得見佳人,“一身絲絨長衫白皮鞋,點了胭脂,那匹絲絨值一牛車的稻”。八兄還鄉,攜新娶的明子,模樣和名字一樣皎潔。是夜原配八嫂上吊未遂。日子過不下去,還得過。這是古早人的正氣清揚。那一日,八嫂燒了八兄的離緣書,聽見明子在水邊唱:人生短短,少女啊緊去戀愛吧……從不唱歌的八嫂在眾人面前和了起來。“兩人面容一烏一白,月娘的正面反面。”
古早的理想國,盛時如“瓊花開”。
林厝兄弟開自動車行,放電影,辦演講比賽,逛宮口夜市。中元普渡,夜游賞花,放留聲機給雞鴨聽,不亦樂乎。好時光若有神助。彼時林家老厝的每個角落都有神在。黃金時代鎖住的封閉空間,“仿佛一個磁場,杜絕所有外力的干擾,除非厝內的人決心行出去”。林厝如此,斗鎮如此,整座島嶼亦如此。
彼年大厝真鬧熱,八兄的兄弟一陣一陣來,若回光返照,之后就開始空襲,是啊,米國來空襲,糖廠彼上嚴重,聽講一粒無爆開,當初的少年和人走去看。四兄念,危險。等到欲暗,大厝毋敢點電火,少年入門,一聲若臭火潐味,將我攬得未會喘氣。
繁花的鄉愁字句只是故事的一半,少不了那樣坦坦然的不能釋懷。多年后,毛斷阿姑夜夜對著一疊舊相片,“用夢話的腔調”絮說當年,“伊次次講古的版本不同款”。好似《伊利亞特》中的女子,說不盡故國的浩蕩河流,王城的華美宮殿,說不盡翁婿帶聘禮來迎娶的風光,說不盡最后一次拉他的手,喚他的名,不讓他出城去打仗。
毛斷阿姑是遺腹子,做夢在一場大霧中得見父親。一個半世紀前,林厝先祖渡船到斗鎮,也似這般起大霧。開篇題為“霧月十八”(18 Brumaire)。是夢醒方知啊!“老父一世人用舊歷過日”,而她,人生的寒露霜降,一場秋的政變不容分說正在蕭瑟潛行。
三
《我不可告人的鄉愁》不止乎毛斷阿姑一人一生,而是記錄百年來臺灣社會流變的種種側影。書分九章,兩條線,并行前進。二四六八章講林厝故事,一三五七章講“我”離了職場,不為建商文案,改為死者寫祭文,引入若干人物事略。古早的和現代的,閩南語和漢語,本省人和外省人,漳泉械斗和藍綠風云,相互交叉呼應,滲透糾纏。其中一二章“駱駝與獅子的圣戰”和“霧月十八”,講紛爭里的生成。三四章“萌”和“瓊花開”如題,講青春的萌動花開。五六章“鉆石灰燼之夜”和“理性國的煙火”是全盛圖景,翻過去了,七八章塵歸塵土歸土,各自回歸死亡,一股扭成末章,主敘毛斷阿姑的喪禮,末章名與小說同名。生而開花,盛極必衰,死后復生,全書謀篇結構宛如生命四季,生生不息。
書中兩個平行世界的唯一交集。我與毛斷阿姑相遇,同伴見是老婆婆,“看我一眼,下一個客戶目標”。整本書確是作者為毛斷阿姑寫下的可以用古語念出的長祭文!
林家老厝三代敗落。六兄長子生第四代萌少女(見“萌”章),夭折在十七歲,正與當初毛斷阿姑出洋同年。彼時“大厝跟鬼屋沒兩樣了”。毛斷阿姑在老厝和臺北來去,來時與萌隔壁,少有交集。只除了萌日夜笙歌的所在名曰“安那其”,叫人恍惚是否毛斷姑丈當年夢成真。
唯一一次,周日我睡到下午醒來,滿屋子亮晃晃,她獨自在客廳里,手指間夾著一支煙,她迎視我的出現,眼睛澄亮,一下子她沒了年齡,沒有了所有衰老的跡象,沒有了怨念折磨的重量,飽滿而輕盈,引我直直走進那雙瞳的光的隧道。那是我與她共有的秘密。
秘密不能說,能說的只有歲月推陳的繁花。比如萌來不及遇見“我恨你恨得夜不能寐”的那個人。又比如毛斷阿姑的那個人自是毛斷姑丈。心思不在家熱衷新世界的他終于留下一封信,渡海參軍去了。從此生死兩茫茫。再見時,阿姑只剩一只骨灰壇子,他活成禿頭老朽,癱在輪椅里,趕赴一場遲到的告別式。
毛斷阿姑聽慣《陳三五娘》。喬裝的陳三遲早會出現在五娘家的大厝前喊:有人欲磨鏡嗎?“戲臺頂戲文內的古早人,無論經過怎樣的艱難,總是要團圓。”但戲歸戲。母親叫毛斷姑丈“浮浪曠”,游手好閑之人。臨終有言:“嫁著彼浮浪曠,有嫁若無嫁,仙也(阿姑正名為林玉仙)的房間得替伊留。”阿姑孤身到老,沒能如五娘隨陳三一路私奔還鄉,“大厝是伊一世人的監牢”。
小時候我隨阿伯去看戲,印象最深是結尾。夜奔的盡頭,“仰望天空烏云散,一輪紅日上天來”。戲中人突然一聲歡喜喊:前面就是往泉州府的大路。在戲里聽聞家鄉名,真稀罕(后來才知戲文里明明是“往福建”啊)。小說里林厝祖先來自泉州,不但阿姑沒能如愿做五娘,渡海回鄉也是老父未竟的終生夢想。
她們都是陳三五娘的毛斷后人。阿姑、萌、寶妹(見“鉆石灰燼之夜”章)。萌若活著,或許就成了寶妹?寶妹亦是“小漢姑”,經歷豈非是毛斷阿姑的翻版?寶妹得知羅杰“死訊”,一如毛斷阿姑當年相信姑丈不在了。只不過相隔半世紀,一個為革命,另一個為資本。
書中那位馬戲團小姐在啃尼采的書,不知有否讀到這一句:“存在的永恒沙漏將不停轉動,你在沙漏中,只不過是一粒塵土罷了。”(《快樂的科學》第341條)
四
怪胎惠子(見“有錢人不死的地方”章)現身,“楔形的一道黑影”,讓我想到戈達爾的電影《筋疲力盡》。貝爾蒙多扮演的小混混叼著煙,墨鏡,歪帽子,張口頭一句就說:“我是傻帽,非如此不可。”
本章講有錢人庫瑪,卻是“夜叉投胎轉世”的惠子叫人過目難忘。
惠子一身圍裙,提一桶消毒水,坐在小吃店門口抽煙,想象中很難與當年的吸毒少年——“鴉片之后開臺第一代毒蟲”掛上鉤。可是他張口講自己的故事,不動聲色仿佛講別人的故事,頓時露了本相,“渾身一種野放、浪蕩感”,“一臉骨棱棱的青森鬼氣”。小時被大姊關進雞籠讓老鼠咬,七個禿鷹姊姊輪番折磨中風老父,母親沒下過廚煮過一頓飯,喜歡的女人當眾用力羞辱他……“他想并且期望一覺醒來父子倆雙雙變成蟲”,惠子用卡夫卡的修辭做了他自己故事里的異鄉人。
某種程度上,自開篇第一句起——“當然,他記得他們盛年時所有的大夢”,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都在做自己故事里的異鄉人。而這算是現代鄉愁故事的另一半的核心所在吧。《盛夏的事》中有句引言:“老年時,任何地方看來都是異鄉。”半個世紀前出洋歸來的斗鎮青年早早有感同身受,只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只有在茲,伊更加覺得遙遠,陷入一種似是而非的困境,進兩步退三步,閉塞的家鄉人,天真又固執,激發了伊說服眾人看世界的熱情。伊樂于做一個故鄉的異鄉人。落雨的暗暝,商家攤頭的電火映在積水路面,一片水晶琉璃,柴屐咔噠咔噠,雨光若白鐵,只有在彼時,伊以為人在他鄉,長出逍遙的翅膀。
加繆寫“異鄉人”(常譯為“局外人”),比新浪潮電影早十八年。默爾索張口頭一句話說:“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十八年后,戈達爾電影里的人不提媽媽了。他偷車,偷錢,偷姑娘的心。殺人,被殺。毫無動機的殺人,如道德法庭一再強調,沒有悔恨,沒有反思。加繆在小說末尾強加給異鄉人一種精神升華,一次與世界的和解。在戈達爾的鏡頭下不這樣了。他背后中槍,在巴黎街上逃命,到十字路口倒地,吐最后一口煙,做最后一次鬼臉,用一句辱罵的話和心愛的姑娘告別,再伸手給自己合上眼。
所有傳世作品都值得問一句:從頭到尾,那人的靈魂深處究竟發生什么轉變?
電影里的轉變發生在第五十六分鐘。戈達爾扮路人甲,向警察告發路過的主人公。面對帥氣無敵的貝爾蒙多,戈達爾活像狄俄尼索斯身旁的薩圖爾,這神來一筆支撐起電影的黃金天平。對力量的控制,完全基于天才的均衡感。當年那批年輕人得益于新技術(便攜攝影機,高感光膠片,同步錄音……),興高采烈走出攝影棚,拍攝夜景,讓演員即興發揮,把自然噪音看得與對白同等重要……一種新影像書寫傳統就此生成。他們渴望打破成規。他們也說,移動鏡頭是道德問題。他們發出不和諧音時,何嘗不受益于拼命想要打破的東西呢?而我們,學會從現代電影文學引經據典乃至踐行某種生活方式的幾代人,我們如何接受輪到我們的拷問?
本來講庫瑪的死,先死的是惠子。沒人知道他病重,到死他還在關心別人“生命中最不堪的痛最深的怨”。講故事是一種療救。惠子不僅講出自己的故事,也讓別人講出她們的故事。又或者,一心呵護他人的傷口也就忘了自己的疼痛。惠子赴死如“苦修僧侶做完最后的功課”,并且修行到只剩一種執念:“愛是朝生暮死的蜉蝣,不能重生與再現。”(256頁)
五
“一半比全部值得多。”
讓人費解的古訓不是嗎?柏拉圖卻欣賞赫西俄德的這句話(《勞作與時日》,40),在《理想國》(466b-c)和《法義》(690d-e)兩篇對話中重復援引。不必多說這與當下生活的諸種價值判斷何其相悖。但我發現,至少在最值得關注之處,這句話持續地有魅力,不妨學柏拉圖的樣子連念兩遍。
我以此理解小說中單數篇章和復數篇章分別搭建的故事世界。一邊越是暗淡,另一邊越是絢爛,如此相生相和,相依為命。“我”的故事從盛年大夢(一章首)說起,直至一句耐人尋味的結語:“只要活著就好”(七章末)。毛斷阿姑的故事一樣地從做夢開始(二章首),到夢醒結束(八章末),首尾相銜,朝向過去和未來循環發生。
夢醒的霧月秋日,毛斷阿姑從一場大病死里逃生,出門聽見遠來的聲音,“來也來也,漫長等待中的人將將欲出現了”。忍不住想那漫長等待中的人究竟是誰?“恨得夜不能寐”的毛斷姑丈?“云霧中的一尊天將”馬太神父?也許是伊繡圣像咬破指尖以血染心的耶穌?還是用母語書寫如此溫柔地擁抱“我不可告人的鄉愁”的作者,如唐諾的文章標題,“把小說念給祖母聽的林俊頴”?
小說中的“我”與毛斷阿姑會面后,突然僅此一次地提到“我父母的長子”,儼然是《盛夏的事》的敘述人筆調在“追憶他那些年的歡樂時光”,特別是“夏天的合音”那一輯,又特別是《遙遠的長夏》那一文。
六
鄉愁神話是死而復生的儀式。每一次告別如赴死,每一次靠近死亡才知呼吸的綿長。世代的安德洛瑪克口耳相傳一個共有的秘密。大多數時候,秘密的力量無關知不知道,而與往往比知道更瑣碎因而也更艱難的生活本身有關。我以此理解杜拉斯為《廣島之戀》寫下的開場話,強迫癥似的被反復重復的一句話:“你在廣島什么也沒有看見。”
在廣島,一對陌生男女的赤裸身體扭抱交纏在一起,像兩只干涸的魚用口水濕潤彼此的傷口。記憶的潮水洶涌而來,讓人坐立不安,想要大聲叫嚷,在陌生的街巷徹夜游蕩。電影中的女人伸出鋒利的指甲,拼命掐進愛人的皮肉,記憶中她也一度這樣絕望地做了愛的獻祭,死摳地牢的墻,再貪婪舔掉指尖的流血。一頭靈魂受驚的獸,游離在不同世界和時間之中。
鄉愁神話不只是讓從前的人再活一次,還是當下的人掙扎想要安頓自己。神話的安德洛瑪克從荷馬詩中走出來,在文字時空中輪回轉世,一遍遍地經歷“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從小亞細亞到希臘,從維吉爾到拉辛,從波德萊爾到新浪潮電影,從口傳方言到文字書寫,從毛斷阿姑到無數講故事的“我”。
連續幾天去醫院輸液。那么多生病的人,素昧平生,過分親密地擁擠在同一病室,個個似波德萊爾詩中“被遺忘在孤島的水手”,或那只逃出籠的天鵝,“蹼足擦著街石,白羽毛拖在糙地上,張嘴在無水的溝邊,煩躁地在塵灰里洗翅膀”。波德萊爾想象困在城市中的天鵝想念故鄉的湖。走出醫院,我忍不住抬頭看天。梅雨之后的城市,被高樓遮蔽的天,卻難得是“嘲弄人的藍得殘酷的天”。我在心中默想林俊頴小說里天鵝的唯一“現身”:“我眼前一直徘徊著那人工蜘蛛俠掛在大樓外,風吹起攬著他的繩索成一弧天鵝頸項。”
真的。一半比全部值得多。一半比全部值得多。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