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這位才華橫溢的海軍少將,因何在戰時突然服毒自殺?
原創: 蒹葭從風 我是科學家iScientist
作者:蒹葭從風
編輯:Yuki
1894年11月16日,威海劉公島,淺灘上伏著北洋海軍的鐵甲艦鎮遠號,身上滿是彈孔、凹槽和火痕,像頭飽經滄桑的巨鯨。

夜色淡去,太陽照常升起,很快有人發現了異樣。楊副管駕帶人沖進住艙撞開艦長室,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
“瞳孔極度縮小,皮膚濕冷,呼吸抑制……典型的嗎啡中毒,可是太晚了,抱歉,我已經無能為力。”劉公島病院的英國醫生格衛齡檢查完嘆了口氣。桌上有一只空碗,底部有些許黑色塊狀物,那是還沒有溶解的鴉片。
北洋海軍左翼總兵、鎮遠艦管帶(艦長)林泰曾,在125年前那個深秋清晨服鴉片自殺,時年42歲。


北洋海軍的左翼總兵軍銜相當于今天的少將,職權位列海軍第二;鎮遠是清政府僅有的兩條鐵甲艦之一,為國之重器,類似今天的航母。林總兵自殺前不久,中日甲午海戰剛剛暫告段落。國事維艱,海軍高官突然自盡,無疑讓低靡的戰勢、疲敝的國命雪上加霜。一時間軍內嘩然,朝野震驚。
林總兵自殺的消息成為熱議話題,有人說他是因兩天前鎮遠觸礁過于內疚,也有人說他是自證清白駁斥通敵謠言,還有說他是對戰勢失去信心,更有甚者翻出之前種種八卦,說他為人膽小怕事[1]……不知是否受輿論影響,最終官方調查結果是:“林泰曾向來膽小,想因疏忽,內疚輕生” [2]。
膽小輕生,成為林泰曾的蓋棺定論,一直影響至今。
但林泰曾是中國第一代海軍著重培養的三位英才之一, 做船政學生時就“歷考優等”,被譽為“閩省學生出色之人”,而后選派留學、接艦回國、接手營務、初創海軍、訓練巡航……順利完成一個個重要任務。借用中國心理學家編制的軍官大五量表MOVPS[3]請一些在近代海軍史方面的資深研究者對他進行人格-崗位適應性的評估,發現他擅長組織、協調和管理,同時在軍事指揮才能方面表現優秀。
誠如李鴻章所謂的“向來”膽小,為何還費盡心思將他調入自己麾下?當時自殺用鴉片泡酒,但鴉片溶解度差,達到致死劑量且要喝上一壺,而且味道難喝得讓人想死,哦不,是難喝得讓人都不想去死,比如后來戰敗前自殺的劉公島護軍戴宗騫就要別人補藥,定遠艦管帶劉步蟾自殺過程持續到次日中午。林泰曾從服藥到死亡僅2個小時,可見他求死之心之決絕。死都不懼,算膽小么?
事出蹊蹺,還是來回顧下他自盡前的幾個關鍵軌跡:
事件 1
戰前,猝不及防的一枚標簽
1894年6月20日,林泰曾作為北洋艦隊分遣隊司令,奉命率鎮遠、超勇、廣丙三艦前往朝鮮仁川等地巡航[4]。很快,他發現戰爭的步伐無法阻擋,于是立即向上司李鴻章發電報申請支援。
然而李鴻章心里一萬個不想打仗。作為風頭正勁的洋務權臣,一旦開戰家底都得賠光,因此一直積極尋求列強對日本的外交牽制。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正好利用這種心態,一面增兵一面釋出和平信息。李鴻章越是怕輕舉妄動成為日本出兵的借口,手下那群將領越不安生:這邊海軍的林泰曾請派魚雷艇,陸軍的葉志超嚷著大舉增兵,這關頭不省心的朝廷還送來一份四百里密諭,“籌戰”“欽此”等字眼讓李鴻章頭大了好幾圈。
不明真相的林泰曾一門心思從戰事出發,幾次三番地請求支援備戰。結果……


受了委屈的林總兵倒沒有消極怠工,而是根據形勢率艦隊轉移牙山,以此為據點巡航偵查,直到他獲得了日軍大舉增兵仁川的消息。而這時,牙山通往李鴻章所在地天津的電報已經阻斷,而自己作為分艦隊司令,得為手下的一眾艦長和軍艦負責。

日本戰爭文學家小笠原長生的小說中引述戰后繳獲的林泰曾日記,提到了林泰曾事后的反應:“嗚呼。泰曾一介武夫耳,才拙識淺,但憂國家知無不言。既傅相已有成算,何敢再言戰?唯有謹待傅相之命而已。”[5]
武將在清朝地位低下,但晚清建立的第一支高學歷、職業化海軍,已經擺脫了傳統的鄙陋印跡,那些留英留美的海軍軍官更是以精英自居。林泰曾作為此列中人,此時卻自貶自嘲“一介武夫”,可見備戰熱情徹底涼了。與此同時,那枚“膽小張皇”的標簽卻越發顯眼,李鴻章后來批評丁汝昌都會拉他來溜:“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遁走……中西人傳為笑談。”
當時“中西人”的八卦熱情不亞于今天的吃瓜群眾,成山頭電報委員報告的“林泰曾海上遇日艦逃竄事件”說得有鼻子有眼,仿佛他當時親臨現場。這個故事從一群洋人那傳到了林泰曾老同學、時為盛宣懷秘書的羅豐祿耳中,遂展開調查,結果查無此事。但造謠一張嘴,辟謠跑斷腿,事已至此,林泰曾跳進黃海也洗不清了。
事件 2
海戰正酣,艦長卻精神失常
1894年7月25日,中日豐島海戰爆發,李鴻章調停避戰的希望徹底破滅。在此之際林泰曾申請辭職,氣頭上的李鴻章斷然拒絕并放狠話:再提不干就砍了你。林泰曾只得繼續留崗,直到那場決定了中日兩國國命的大東溝海戰爆發。
1894年9月17日下午,鴨綠江口外的黃海海面濃煙滾滾,炮火如雨,沖天水柱此起彼伏。當中國艦隊先期失利,接連損失了致遠、經遠等巡洋艦后,局勢全都系在兩條鐵甲艦上。旗艦定遠在北洋海軍右翼總兵、管帶劉步蟾的指揮下如中流砥柱抵抗著日艦瘋狂的圍攻,然而在鎮遠艦的指揮塔中卻是另一番景象。

鎮遠艦幫帶大副、美國洋員馬吉芬(McGiffin)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道:
“我不斷地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從我下方的指揮塔里傳出……我驚訝地發現這竟是我那尊敬的艦長發出的!他正跪倒在地,以極快的語速用中文喃喃自語——祈禱著,或者說一邊祈禱一邊詛咒著——每一發炮彈擊中軍艦時他就像狗一樣嚎叫起來。只要我還活著,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幕景象和那種聲音。” [6]
一位參戰的中國海軍軍官盧毓英也印證了此事:
“大東溝之役,林驚惶無措,故置濃酒作長飲大醉,而卜于戰臺之下,所有調遣悉讬其副駕帶楊用霖之身上,備諸死具如迷藥洋煙之類。” [7]
好在鎮遠有一位非常出色英勇的副艦長楊用霖,代替艦長全權指揮,挽救了軍艦并改寫了戰局:關鍵時刻鎮遠連發兩枚305mm炮彈命中日本旗艦松島,其中一枚開花彈引起松島彈藥庫的嚴重殉爆,致船上四分之一成員傷亡,武器系統、液壓舵輪嚴重受損,不多時便集結艦隊撤出戰場[6]。若非如此,林泰曾這次瀆職的后果可能難以估量。


事件 3
老司機“科目二”失敗
1894年11月14日黎明,威海灣和劉公島夾峙的西北口傳來一聲巨響。鎮遠艦龐大的身軀劇烈顫抖,向左傾斜。經驗豐富的指揮官們立即啟動損管措施:堵漏、抽水、關水密門……然而海水還是源源不斷漏進了彈藥艙、帆艙、煤艙、鍋爐艙及水力機艙。
據后來的調查報告,事故原因是鐵甲艦在魚貫入港時,前面定遠七千多噸的身軀產生巨大的分水壓推偏了浮標,導致后面的鎮遠艦對航道判斷失誤,擦過靠近劉公島一側淺灘的礁石,致左舷艦底裂壞擦傷達8處之多。

大東溝海戰已損失了數條巡洋艦,兩條鐵甲艦成了清政府最后的威懾力量。其中一條竟在節骨眼上出了嚴重事故,更糟的是,日本陸軍即將在旅順登陸,鎮遠無法前往唯一擁有干塢的旅順港修理。
那天的入口指揮的是管帶林泰曾。他作為中國第一代海軍軍官的佼佼者曾戰勝地中海的颶風、印度洋的無補給航線、蘇伊士運河的淺窄河道以及朝鮮海岸的暗礁險灘,最后卻栽在了往返多趟的劉公島北口,而且那次返港只開出了8節航速(1節=時速1海里≈時速1.852公里)。家門口低速觸礁,不和老司機倒車入庫失敗一樣么?以至于事故上報后李鴻章的第一反應是,難不成林是……故意損壞?
雖然最后的調查證明了林總兵的清白,但關于他膽小輕生的論調卻成為他永久的身后之名。
林總兵病情剖析
那么,林泰曾為什么會在戰前出現如此嚴重的問題?不到3個月時間,他從穩健忠謹的分艦隊司令,變成一個精神運動性激越的戰斗應激者;2個月后出現抑郁癥典型的“三低”(情緒低落,思維遲緩,意志減低。)“三無”(無用、無助和無望)“三自”(自責、自罪和自殺)特征,是他有性格缺陷,在戰斗中變得膽小抑郁,還是另有原因?
戰斗應激
乍一看,林泰曾失常的行為很像某種戰斗應激。
戰斗應激(combat stress reaction, CSR)是當前常用來評價軍人在戰斗或非戰爭軍事行動中經歷壓力性事件后反應的軍事心理學術語。關于戰斗應激,歷史上因認識程度不同產生過不同名稱。一戰時被稱作“炮彈休克”“戰爭神經癥”或“Da Costa綜合征”等。這些術語在二戰時仍被大量使用,直到越戰時才逐漸統一為戰斗應激。海灣戰爭期間,包括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在內的一系列癥狀都被囊括在戰斗應激反應的范疇。[8]
戰斗應激反應可分為六大類型:軀體、認知、行為、情感、過失性及適應性的癥狀。如果對號入座的話,林泰曾基本崗位技能喪失,語速加快,是戰斗應激的行為癥狀;焦慮、易激惹、歇斯底里,是典型的情感癥狀;嚴重的挫敗感提示出現了認知方面的癥狀;無視自己的艦長身份,放棄指揮并訴諸麻醉品和酒精,已經上升到嚴重的過失行為。
不過,戰斗應激的高頻人群是年輕、低階且未見識戰陣的士兵。林泰曾雖也是第一次經歷大海戰,但畢竟不是對海戰一無所知的新兵。他從少年時就接受的系統海軍教育,對海戰的慘烈有充分的心理預期,然而癥狀卻比普通士兵嚴重;普通的戰斗應激患者屬于急性心理應激障礙,85%在三天內通過休息會好轉[9],而林泰曾的癥狀持續性加重,直到又一次重大事故。

根據經典的戰斗-逃跑(Fight-or-flight response) 行為學模型:動物面對應激原通常有兩種選擇:要么逃避要么反抗。但有意思的是,經過抑郁造模的大鼠面對尾懸、電擊、強迫游泳等應激原等,往往呈現出不抵抗不逃避的麻木行為[10],這時很難界定它們到底是勇敢還是膽小。
人的情況本質上類似。海戰中諸多官兵不懼死傷頑強應戰,毫無疑問可謂勇敢;也有人臨陣脫逃或當縮頭烏龜,如濟遠艦管帶方伯謙、鎮遠艦駕駛大副王珍,這是無爭議的膽小。而林泰曾的行為和這兩種都不一樣,更像類似抑郁模型動物那種精神障礙。那么,是什么引起了林泰曾的精神變化呢?
非戰斗壓力
戰斗應激反應通常很復雜,許多案例表明并非單純的戰斗壓力引起。輿論壓力是不可忽視的一項。中國古代長平之戰,一個反間計幾乎奠定戰局;甲午戰前的負面輿論最終也產生了莫大影響,這件事追蹤起來還有些耐人尋味。如今史學界證實當年日本間諜在戰前活動相當猖獗,就連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都與日本間諜石川伍一牽連不清。這層關系對林泰曾事件起到什么作用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關鍵時期某些勢力蓄意挑釁激惹高階軍人引誘他們出現過失行為,是一項軍事心理學范疇的常規操作。
軍人的承受力有時無比堅韌,但有時可崩于纖毫之間。1996年,時任美海軍作戰部長的布爾達(Jeremy Boorda)四星上將在辦公室以手槍自戕。他是一位參加過越戰和波黑戰爭且功勛卓著的軍人,也是美國二百多年來唯一從水兵成長為海軍總司令的傳奇軍人,自殺原因僅僅是因為被媒體質疑不具備佩戴“V字勛章”的資格。

軍人的職業特征決定他們重視榮譽甚于生命,這恰恰成為他們的軟肋。布爾達上將自殺事件引起美國國防部的高度重視,啟動了以軍事心理學為基礎的各軍種的自殺預防計劃和相關研究。來自美軍醫學機構的各項數據顯示,軍人自殺案例中被診斷為抑郁情緒、人格障礙或適應不良的比例常超過90%。[11-12]
林泰曾又是什么情況?
關于抑郁性人格的研究十分駁雜,早先認為固執、沉默、敏感、做事一絲不茍、童年失去父母、從小根植提高家庭社會地位的志向、D型人格(具有消極情感、社交抑制特點)等特征與抑郁癥發病率有一定關聯。作為林則徐侄孫的林泰曾出身名門、自幼父母雙亡、家境艱辛并肩負中興家族的使命、平日“性沉默,寡言笑,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上述特征竟然全中;然而,另一些與抑郁癥負相關的人格特征,如隨和、責任心[13]等,有“待下仁恕”“存心慈厚”“性行忠謹”之譽的林泰曾也都擁有。事實上,今天關于抑郁性人格的論調格外嚴謹,過去認為的許多特征如今都不被認為是抑郁癥的預測因子。所以僅憑史料中林泰曾呈現的人格特點還真無法得出他是否容易患抑郁癥的結論。

他的情況,更可能是一系列外界因素,包括頂端困惑和奮斗目標坍塌造成的心理障礙。從史料中看到,林泰曾和同學們剛從船政學堂畢業時曾有豪言壯語:“從今而后,要去對付颶風,控制狂浪,窺測日星的行動,了解暴風的規律……讓最可怕的困難變成平易、最險惡的情況成為靜謐……我們的愛國心將不減少”,多年以后,他卻在日記中自嘲為“一介武夫”,挫敗極強地感嘆報國無門,如此天壤之別真有些諷刺。林泰曾字里行間透出的是:我原以為自己成了國之干城,哪知到頭來還是一介武夫,為國備戰不遺余力,誰知主帥和朝廷卻各懷心思。袁世凱三電乞歸,葉志超推諉責任,我兢兢業業反成了“膽怯張皇”“畏日遁走”……報國無門,罪由我起,活著夫復何益?林泰曾空懷職業軍人的責任感,以及一腔報國之志,卻因清政府的昏聵無能和領導的輕率誤判,成了一己私利下的炮灰,豪情壯志化為心灰意冷和無助絕望。
酒精、麻醉品濫用
最后,造成他病程的加速的除了戰斗、非戰斗壓力外,很可能還有一個原因。
1770年英國皇家海軍開始給西印度艦隊的水手定量配給摻水的朗姆酒或威士忌,標志著皇家海軍開始正式減少麻醉品依賴的努力。嗯,你沒看錯,這是皇家海軍旨在降低官兵酒精濫用的努力,因為那些家伙之前都直接喝烈酒。
過去軍隊的酒精-麻醉品濫用是個普遍問題。美國內戰中酗酒和吸食鴉片司空見慣,越戰期間34%的士兵吸食過大麻,50%的人服過海洛因。軍人面臨著平民不會遇到的巨大壓力,這種生活方式本身就是酒精和麻醉品濫用的誘因。

北洋海軍同樣沒能解決這一問題,導致林泰曾能夠“置濃酒”“備諸死具如迷藥洋煙”。洋煙是鴉片,迷藥或許是麻醉劑,甚至可能是當時已經開始使用的古柯堿。可以試想,林在情緒低落時沾染上這些東西以至沉迷,在那個時棘人困之際,加速了他的精神狀況的惡化。
林泰曾是否膽小恐怕還會繼續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精神上的完人,面對戰爭的人永遠都充滿不確定性。林泰曾少將的自殺事件過往已久,就算不能像布爾達上將那樣對軍事心理學產生推動力,如果能成為一個小小的史鑒,就是翻這筆舊賬的意義。
本文感謝海軍史研究者陳悅、方禾、吉辰、李嫣、李玉生、劉烜赫、劉致、呂望舒、隋東升、孫建軍、王鶴、張黎源的支持。
作者名片

參考文獻:
[1]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中日甲午戰爭(下)[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2]李鴻章全集(25)[M],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p172.
[3] 王芙蓉, 張亞林, 楊世昌. 軍官職業人格量表的初步編制[J].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006, (03):224-6.
[4]孫建軍. 鎮遠艦長林泰曾在韓觀察覆命書箋注[J]. 大連近代史研究, 2010, 7: 44-72.
[5]田漢. 關于中國海軍的幾個問題·林泰曾[J]. 海軍整建月刊, 1941(民國三十年), 1(12): 5-6.
[6]李·馬吉芬 著,張黎源 譯. 他選擇了中國[M].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13.
[7]孫建軍 整理校注. 北洋海軍官兵回憶輯錄[M].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16
[8]陳悅. 中日甲午黃海大決戰[M]. 臺海出版社. 2019.
[9] Carrie H Kennedy, Eric Zillmer. Military Psychology: Clinical and operational applications [M].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2, 2nd New edition.
[10] Castagné V, Moser P, Roux S, Porsolt RD. Rodent models of depression: forced swim and tail suspension behavioral despair tests in rats and mice. Curr Protoc Neurosci. 2011;Chapter 8:Unit 8.10A.
[11] Trent LK. Parasuicides in the Navy and Marine Corps: Hospital admissions, 1989-1995. (Techical Document 99-4D). 1999, San Diego, CA: Naval Health Research Center.
[12] Ritchie EC, Keppler WC, Rothberg JM. Suicidal ad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Military Medicine, 2003, 168, 177-181.
[13] Jenkins EN, Allison P, Innes K, Violanti JM, Andrew ME.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Police Officers: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ity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J Police Crim Psychol. 2019 Mar;34(1):66-77.
歡迎個人轉發到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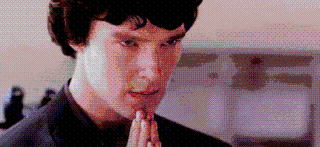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