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荷蘭人在日本的經(jīng)驗:“歐洲崛起”并非所向披靡
本文選摘自《公司與將軍:荷蘭人與德川時代日本的相遇》,[英]亞當(dāng)·克盧洛著,朱新屋、董麗瓊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5月出版。經(jīng)授權(quán),澎湃新聞轉(zhuǎn)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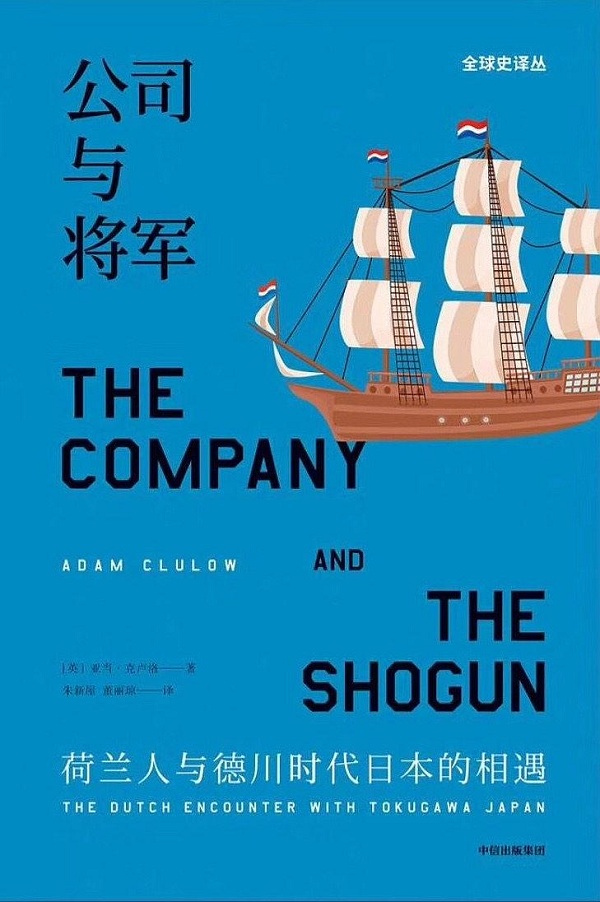
以上兩種關(guān)系類型中的一種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這種關(guān)系中逐漸積累權(quán)力,直到它能夠決定雙方訂約的條件,以此來獲得更具主導(dǎo)性的地位。這種類型主要包括印度尼西亞的政權(quán),如馬塔蘭、萬丹和望加錫,它們都在17世紀開始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強大競爭對手,但最終以一種從屬地位被納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帝國中。韋紐斯和芬克的著作顯示,盡管在這一過程中荷蘭東印度公司遭受到頻繁的(有時是毀滅性的)挫折,但在整個侵略性擴張的漫長時期,不論是在馬塔蘭、萬丹,還是在望加錫,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地位仍然成功地不斷上升。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爪哇中部的馬塔蘭君主的關(guān)系——在前面的章節(jié)已有簡單討論——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權(quán)力的緩慢增長提供了典型例子。馬塔蘭在阿貢蘇丹(Sultan Agung,1613—1646在位)統(tǒng)治時期,幾乎要征服巴達維亞,后來卻被迫變成一個越來越從屬的角色,到1677年唯有依靠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事支持才平定了內(nèi)部叛亂。同一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另一個競爭對手——萬丹港口的政權(quán)影響力與日俱增,后者最終于1684年被迫簽署一個單方面的條約,承認荷蘭總督的權(quán)威。
巴達維亞與位于南蘇拉威西(South Sulawesi)的戈瓦(Gowa)蘇丹或望加錫蘇丹之間的往來有著相似的軌跡。16世紀晚期,蘇丹作為一支商業(yè)和新興的軍事力量崛起;至17 世紀上半葉,蘇丹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最持久的對手,它有能力召集成千上萬的軍隊,把望加錫城變成了一個日益繁榮的中心,其規(guī)模之宏大,堪比歐洲的都會城市。160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望加錫開辦了一個工廠,但雙方關(guān)系卻迅速惡化。雖然荷蘭人被迫于1615年撤退,但是隨后的沖突斷斷續(xù)續(xù)地持續(xù)了五十多年,雙方爭奪的焦點主要是對貿(mào)易的控制。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勇敢地嘗試通過為包括葡萄牙人在內(nèi)的外來貿(mào)易者提供庇護所,來建立起對珍稀香料的壟斷權(quán);望加錫正是在規(guī)避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這種限制的過程中才繁榮起來的。事實上,望加錫的統(tǒng)治者曾大肆抗議:“真主安拉創(chuàng)造了大地和海洋。他在人們中間分割大地,海洋為大家所共有。從未聽說過任何人可以禁止通航。”
巴達維亞充分利用武器優(yōu)勢,尤其是通過強勢的外交部署和軍事設(shè)施,來回應(yīng)蘇丹的挑戰(zhàn)。為獲得貿(mào)易控制權(quán),荷蘭東印度公司曾通過一系列的信件和派遣使節(jié),與繼任的蘇丹建立了雙邊關(guān)系,這些蘇丹把荷蘭總督看作是一個擁有自身權(quán)利的獨立政治行動者,而且同時作為“所有土地與堡壘、大大小小的船只,以及所有荷蘭臣民都在其庇護之下”的統(tǒng)治者。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勸說未能產(chǎn)生效果,于是很快訴諸武力,正如它在日本的行動一樣,派出船只襲擊在望加錫海域的葡萄牙船只,隨后又于1653年、1660年和1666年發(fā)動了對蘇丹的一系列戰(zhàn)爭。最后一次戰(zhàn)爭最具決定性,1667年哈山努丁蘇丹(Sultan Hasanuddin,1653—1669 在任)被迫簽署《本加亞條約》(the treaty of Bungaya),實際上把望加錫變成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屬臣。
在為掌控關(guān)系主動權(quán)而發(fā)動的三次戰(zhàn)爭期間,荷蘭東印度公司逐漸施加壓力,直到它能夠?qū)ζ湓?jīng)的對手實施絕對的影響力。然而,這種類型的關(guān)系遠非標準模式,因為在其他類型的關(guān)系中——荷蘭東印度公司被迫做出讓步,甚至處于更危險的境地——也有著數(shù)不清的例子。后一種情況涉及的對象十分廣泛,包括了早期近代亞洲一些最重要的政權(quán),如中國的明朝和隨后的清朝、印度的莫臥兒帝國、波斯的薩非王朝,以及暹羅的大城王國,所有這些政權(quán)都動用了遠遠超過荷蘭東印度公司所能聚集的軍事力量,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只能甘拜下風(fēng)。毫不意外,巴達維亞和這些政權(quán)之間所發(fā)展的關(guān)系也就隨之改變。比如最明顯的差異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某些情況下能成功地建立起持續(xù)性聯(lián)系,而與一些政權(quán)的關(guān)系則更多是斷斷續(xù)續(xù)的。
例如,在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關(guān)系是間歇性的,從未成功地建立起一種持續(xù)性關(guān)系。事實上,它想要在中國統(tǒng)治邊緣鞏固自己地位的兩次嘗試都以軍事敗退告終——1624年荷蘭人被一支明朝艦隊從澎湖列島擊退,166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旗幟被鄭成功的軍隊在臺灣推倒。中國有著如此大的規(guī)模和威力,即使在其國內(nèi)動亂頻繁和內(nèi)部政權(quán)瓦解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從未處于一種擁有決定性話語權(quán)的地位,但它總是利用大憲章第35 條中授予的使用武力的權(quán)力,揚言進行某種出其不意的襲擊。因此,如前所述,16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對中國宣戰(zhàn),決心利用其船堅炮利來迫使明朝官員開放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占領(lǐng)澎湖列島之間的貿(mào)易。盡管這些策略在東南亞十分有效,但是在恐嚇中國官員時卻遠沒有那么有用。荷蘭人意識到中國官員打算顯示其勢不可擋的軍事力量。事實上,巴達維亞戰(zhàn)役的結(jié)果之一是吸引了中國沿海官員的全部注意力,他們陸續(xù)召集軍隊準備驅(qū)逐澎湖列島上的荷蘭人。因此,公司第一次與中國明朝建立聯(lián)系不是以落腳臺灣而是從臺灣撤退為結(jié)局。
明朝覆滅以后,荷蘭東印度公司面臨著一個更為復(fù)雜的政治環(huán)境,它不得不處理與兩個相互競爭的中國政權(quán)——一個已控制絕大部分中國大陸的清政權(quán),以及一個實際上在鄭成功治下的海上政權(quán)——的關(guān)系。處理與前者的關(guān)系,公司的首選工具是官方使團,多個荷蘭使團被派往北京,帶著荷蘭總督的信件和禮物,希望結(jié)成軍事聯(lián)盟以期獲得商業(yè)讓步。正在此時,荷蘭東印度公司面臨著來自鄭成功的日益嚴峻的威脅。鄭成功正致力于將臺灣變成一個反清戰(zhàn)爭的基地。轉(zhuǎn)折點來臨時,就如1624年一樣,中國統(tǒng)治者——在當(dāng)時情況下指的是鄭成功,決定不再容忍荷蘭人的存在,聚集了大批軍隊將他們從大員的堅固陣地中驅(qū)逐出去。結(jié)果,荷蘭東印度公司又一次遭到潰敗,盡管它從未在中國軍隊的襲擊中占據(jù)過優(yōu)勢地位,但是這一次從事實上結(jié)束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中國海岸的存在。
暹羅的情況恰恰相反,荷蘭東印度公司成功地建立起了與大城王國(1351—1767)的持久關(guān)系。從1608年在暹羅開設(shè)工廠,到1765年的150多年時間里,雖然有過偶爾的間斷,但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持續(xù)在那里開展活動。這種關(guān)系的長期存在主要取決于與大城朝廷的相對良好的關(guān)系,大城朝廷很熱情地與荷蘭人往來。巴哈旺?欒斯爾皮(Bhawan Ruangsilp)的論著,是對荷蘭人在暹羅的最好研究之一。她認為巴達維亞和暹羅國王之間發(fā)展出了一種伙伴關(guān)系,盡管她也謹慎地指出這種關(guān)系一直是有條件的。處在這種關(guān)系中心的是雙方頻繁的外交往來,首先是暹羅君主與奧蘭治親王,然后是與巴達維亞,使團定期往來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與大城首都之間。荷蘭東印度公司不僅被看作一個商業(yè)和外交伙伴,而且被當(dāng)成一個有價值的軍事同盟;正因為這樣,荷蘭東印度公司利用外交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實際上,暹羅國王在與敵人或叛亂下屬的各種戰(zhàn)役中,曾多次向荷蘭官員尋求軍艦協(xié)助。
與在中國的情況一樣,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未能夠?qū)﹀吡_發(fā)號施令,其雇員將暹羅描述成一個“著名的強大的王國”,但是它打算采取強勢行動,并利用必要的工具來迫使大城對一些關(guān)鍵問題的政策有所轉(zhuǎn)變。最明顯的是1663年,巴達維亞認為——引用欒斯爾皮的話——一系列“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暹羅國王之間累積的問題,都應(yīng)按照它的條件得到解決”。為此公司選擇了一種老掉牙的策略——軍艦封鎖。從1663年11月到1664年2月,公司的船只封鎖了湄南河,抓獲暹羅帆船,直到國王對巴達維亞的要求做出讓步。雙方簽訂了一個條約,根據(jù)當(dāng)時荷蘭人的報道,“ 出于對荷蘭東印度公司威力和武器的懼怕與敬畏”,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贏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讓步。這一短暫卻十分有效的戰(zhàn)役,其總的影響是將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暹羅的關(guān)系重新調(diào)整到一個對巴達維亞更為有利的位置。

上述簡略討論把我們拉回到日本,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日本的經(jīng)驗的問題。當(dāng)然,巴達維亞與德川日本之間維持了兩個多世紀的持久聯(lián)系,與它在中國所發(fā)生的間歇性交往有著明顯的不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暹羅也成功建立了一種持久性的存在,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例子與和大城王國所建立的關(guān)系也幾乎毫無相同之處。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日本幾乎很少看到欒斯爾皮所描述的有條件的伙伴關(guān)系的證據(jù)。相反,這是一種絕對的不平等關(guān)系,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其中被迫處于一種一貫的從屬地位。盡管這部分是因為德川幕府相對強大的力量,它是早期近代亞洲強大的政權(quán)之一,但只是指出這一事實并不能解釋為什么事情會發(fā)展成它們所呈現(xiàn)的那樣。通過關(guān)注在17世紀——也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強勢擴張階段,荷蘭東印度公司和德川政權(quán)之間發(fā)生的所有一系列沖突,本研究試圖為此提出解釋。
1609年抵達日本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是一個帶有企業(yè)和政府雙重屬性的混合組織。因此它來日本時不僅帶著船只和商品,還帶著一種源自大憲章并且決心要予以執(zhí)行的統(tǒng)治權(quán)。荷蘭東印度公司隨后對外交、暴力以及主權(quán)的權(quán)利維護,引發(fā)了與幕府的一連串沖突。在這些沖突中,諸如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否能與幕府將軍建立高層次的外交關(guān)系,是否有權(quán)在日本海域或針對日本貿(mào)易伙伴實施海上暴力,以及是否有權(quán)在大員宣示絕對主權(quán)等,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幕府將軍之間的關(guān)系,我已經(jīng)表示過,大體上是確定的。雖然是以不同的方式,但在每種情況下都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而非德川政權(quán)被迫放棄立場,從其對應(yīng)有權(quán)利和統(tǒng)治特權(quán)的堅持上做出退讓。這個過程一旦完成,荷蘭東印度公司就失去了它在亞洲其他地區(qū)理所當(dāng)然采取的手段。
在暹羅,比如1663年發(fā)生在湄南河的事情,一個陣容強大的使團或精心策劃的海上戰(zhàn)役就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機會,然而這種調(diào)整性的武器在日本是不存在的。1632 年的例子很明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決定采取非常措施,為了恢復(fù)與日本的關(guān)系,將一位高級官員彼得?奴易茲引渡到日本。荷蘭官員在這一時期的許多評論也能證明這點。例如,1638年12月,荷蘭總督明確解釋了公司在日本的策略:“切勿惹惱日本人。若想要得到一些東西,你必須等待適當(dāng)?shù)臅r機與機會,并且必須抱有極大的耐心。他們不喜歡被人反駁。因此我們將自己變得越不重要,假裝成卑微、低下和謙遜的商人,只為他們的愿望而存在,我們就能在他們的土地上獲得越多的喜愛與尊重。這是我們從長期的經(jīng)驗中得來的……在日本,再怎么謙遜都不為過。”
在荷蘭聯(lián)合省,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也支持同樣的觀點。在著名的1650年通令中,十七先生談到日本問題時,認為“除了使這個傲慢、宏大和嚴謹?shù)膰以诟鞣矫娑紳M意之外,我們給官員們沒有其他訓(xùn)令”。董事們堅持,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應(yīng)該“帶著謙遜、卑微、禮貌和友誼”,絕不能去命令德川政權(quán),而是應(yīng)該一直服從它的愿望。
荷蘭東印度公司為此失去了使用它在亞洲其他地區(qū)所依靠的有效工具的機會。但是事情絕不僅僅這么簡單。在日本的荷蘭人以某種方式融入日本的內(nèi)部體系,這與大城的例子截然不同。去觀察巴達維亞在兩次不同的軍事行動中向暹羅國王和后來的德川將軍提供的支持,就可以看出這種區(qū)別的意義。從1633 年開始,暹羅的巴薩通(Prasatthong)國王(1629—1656年在任),通過許諾有利可圖的貿(mào)易特權(quán)來換取軍艦支持,試圖引誘荷蘭人加入反對其臣屬國帕塔尼的戰(zhàn)爭中。這些請求最終奏效了,荷蘭東印度公司于1634年派出一支小型艦隊參加了軍事行動。盡管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參與所產(chǎn)生的實際效果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巴達維亞愿意提供援助,為荷蘭人贏得了一系列新的特權(quán),極大地改善了他們在暹羅的處境。三年之后的島原戰(zhàn)役,其情形則完全不同。荷蘭人并非因為許諾回報被卷入戰(zhàn)爭,而是受制于他們自己的言辭與過去的承諾,不得不自愿作為幕府將軍的國內(nèi)屬臣參與鎮(zhèn)壓叛亂。
兩次戰(zhàn)役的差異說明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幕府將軍的關(guān)系其性質(zhì)截然不同。在日本,荷蘭東印度公司被馴服,受限于一個自我設(shè)定的屬臣角色,承擔(dān)了一系列的附帶責(zé)任。不論是省督還是總督,荷蘭人盡管有著明顯的異域性,卻放棄了他們代表一個強勢的外部力量的權(quán)利,轉(zhuǎn)變成了國內(nèi)屬臣。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們作為日本國內(nèi)屬臣的一部分,服從于一種量身定制版本的參勤交代制度;被要求承擔(dān)軍事服務(wù)(直接地或以提供情報的形式);在接受幕府將軍的法律權(quán)威(至少與某些犯罪有關(guān))時,被迫放棄一些關(guān)鍵權(quán)利(最明顯的是與實行海上暴力有關(guān));像其他屬臣一樣,被迫在呈遞炫耀性展示品時扮演自己的角色。這是一個將會變得越發(fā)熟悉的角色,年復(fù)一年地扮演這一角色,直到表演與現(xiàn)實的邊界變得十分模糊。至于荷蘭人是否是真正的屬臣,抑或只是扮演著屬臣的角色,這些問題基本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行動事實上已經(jīng)像是幕府將軍忠實的仆人,構(gòu)成為幕府將軍服務(wù)(hōkō)的單獨組成部分——正如在《通航一覽》中所顯示的那樣,在德川幕府的秩序中,荷蘭人擁有與眾不同的身份。
這項研究并不是要記錄荷蘭人在日本的歷史,而是要關(guān)注在這段歷史中產(chǎn)生的一系列沖突,旨在追蹤一個社會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荷蘭人被迫去適應(yīng)并在德川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這些沖突幾乎毫無例外地是在有利于日本的情況下得到解決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德川將軍的關(guān)系不完全是典型性的,這一點應(yīng)該很清楚;但是它也并沒有脫離歐洲人在亞洲更為普遍的經(jīng)驗,它不應(yīng)當(dāng)被看作一個在日本范圍之外的無甚相關(guān)的歷史局外人。盡管存在這樣一種理解趨勢,即關(guān)注直接殖民化發(fā)生的地方,或者歐洲在其中產(chǎn)生最大影響的關(guān)系,比如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馬塔蘭、萬丹或者望加錫之間的關(guān)系,但這些并非常態(tài),更常見的劇目是歐洲人在其中努力掌握他們與亞洲打交道的主動權(quán)。毫無疑問,沒有什么可以比荷蘭人在德川日本的遭遇更好地證明這一點。
如果我們跟隨彭慕蘭、王國斌等人的著作,接受在早期近代時期亞洲政權(quán)的持久權(quán)力這一事實,那么很明顯,更好地去記述歐洲人被納入亞洲秩序這一長期的融合過程,是歷史學(xué)家義不容辭的責(zé)任。荷蘭人在日本的經(jīng)驗表明,歐洲在亞洲的立足點并非一貫是從孤立的貿(mào)易商棧轉(zhuǎn)變成城堡基地,最后變成完全的殖民地。事實恰恰相反,強大的亞洲政權(quán)的存在,意味著即使是最強大的歐洲組織也會被一個它們無法逃脫的牢籠所限制。日本給在亞洲的歐洲企業(yè)制造了一個象征性的死結(jié),一個完全受到遏制的場所,因此為那些認為“歐洲崛起”始于1492年或1497年的探險遠航,并在隨后幾個世紀里伴隨著無休止的戰(zhàn)鼓所向披靡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價值的對比。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