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訪談|魯西奇:區域,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法
魯西奇教授二十年前的舊作《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修訂再版,在此書中,他從地理環境與人類活動探尋漢水流域地區貧困落后的歷史原因,洞察到了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的某些側面,并逐步形成了對這個世界及其歷史過程的一些認識和認識的方法。然而近二十年來,他也在不斷反思區域研究及其方法,努力探索突破或彌補區域研究局限性的路徑。世界上各個區域的疊加,并不是世界;各個區域的歷史,固然是人類歷史的“局部”,但絕不“就是”人類歷史。如何從區域研究走向“人”的歷史研究,魯西奇教授真誠分享的治史經驗將給我們不少啟迪與思考。

江田祥:欣聞《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一書近來再版。此書是您第一部學術著作,二十年后它又修訂出版,藉此機會,請您回顧一下當年此書的寫作背景與學術思考。這本書并不是基于您的博士學位論文,而是博士畢業之后完成的著作,請問當時您撰寫這本書是出于怎樣的契機呢?
魯西奇: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漢魏六朝時期長江中游地區地名移位之探究》,是跟著石泉先生做的,問題、研究理路與基本認識,都是從先生那里來的。雖然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特別是受了很好的研究方法的訓練,對一些具體問題,形成了一點自己的認識,但視野、材料與認識的局限也很明顯。博士畢業后,我開始嘗試著走自己的學術道路。在此之前,從1992年起,我參加中科院成都山地所陳國階先生與武漢測地所蔡述明先生主持的“漢江流域資源調查與開發”的調研項目,在十堰、安康、漢中等地區跑,取得了一些感性認識,并有機會向從事山地與湖泊研究的老師們學習,較多地受地理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影響。石先生研究的重心,也在漢水中游地區,特別是襄陽—宜城平原與南陽盆地、隨棗走廊地區;而且先生也特別強調歷史研究與地理學、考古學方法相結合。所以,當我向先生匯報,想把以后研究的重心放在漢水流域、而且想側重于運用地理科學的分析理路與方法時,石先生與李涵老師都覺得很好,給了很多鼓勵。這個方向就定下來了。
江田祥:最近我又重讀這本書,記憶深刻的是此書開篇的第一段話:“地理環境常常并不甘于僅僅充當舞臺,而是不時地參與演出,成為演員,甚至設計或改變劇情的發展。所以在很多時候,地理既是歷史這出戲的編劇,又是導演和演員,還是劇情的組成部分”,這本書是以漢水流域為區域對象分析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演進模式,探討地理環境與人類活動的關系,請問您是如何走上歷史地理研究之路的?
魯西奇:跟著老師讀書,老師是做歷史地理的,就做了歷史地理,所以,可以說是老師領著走上了歷史地理研究的路吧。進了門之后,才去想自己究竟要做什么、適合做什么、做這些有什么意義,給自己的生存與努力尋找理由與意義,然后磕磕碰碰地走自己的路。走著走著,回頭一看,發現離自己本來設想的路有些偏離,甚至離得很遠,慢慢地,也就忘記自己本來設想的路了。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正在迷“年鑒學派”(現在也迷的)。這本書,深受布羅代爾《法蘭西的特性:空間和歷史》、《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影響。這些好的議論,大抵都是在各種閱讀中受到啟發,結合著自己的一些思考,而做出的。當時我才三十出頭,其實沒什么深刻的思考,認識也很膚淺。現在讀起來,都覺得有些好笑了。
“年鑒學派”強調地理所塑造的空間結構及其特性,對于人類歷史進程及其所表現出來的總體結構的形成與變化,具有重要的意義。我雖然深受這些論述的影響,但出發點其實有些不同。我最初在漢水流域跑,就是到秦巴山區,那里生存環境的惡劣、社會經濟的落后、老百姓的無助,深深地打動了我。所以,我討論漢水流域的人地關系,是為了回答,這些地區是為什么會如此貧困落后的?我當時試圖在地理環境與人類活動方面去尋找原因。后來,我可能更著意于從政治與社會方面探究原因,而不是從地理條件與當地人的經濟生產活動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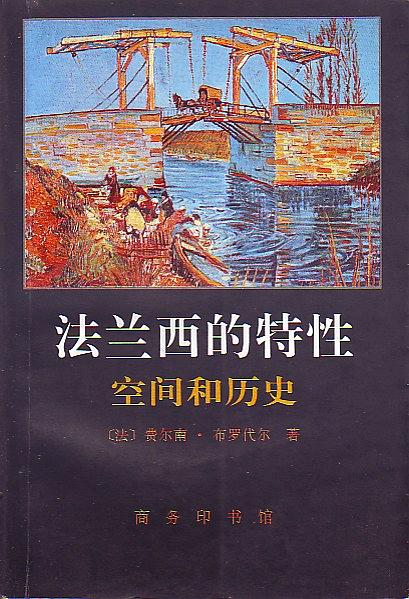
魯西奇:1990年前后,中科院地學部提出的地學研究重大課題中,有一個“區域鏈”的系統研究,強調對一個區域系統各部分間的相互關聯與影響機制展開研究,以全面認識區域人地關系的結構、特質及其演化規律。“區域鏈”觀念的提出,可能與侯仁之先生有關系。石先生改做歷史地理,是向侯先生請教的。所以,我也很注意侯先生那邊的研究趨向。那幾年,跟著從事山地與湖泊研究的老師們學習,并和他們一起跑,自然而然地,就會注意到河流的上、中、下游之間,不同層級的支流之間,以及山地、丘陵、平原湖區之間的差別、聯系,以及它們是如何形成為一個整體的系統、系統內部又是如何分化的,等問題。所以,把漢水流域作為一個整體或一個系統,對我來說,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立場。一直到后來,我才會去追問,漢水流域是一個整體或一個系統嗎?如何論證在某一個歷史時期,漢水流域是一個具有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一致性”和“內聚性”的區域呢?在寫作這本書時,我還沒有這個意識。我在研究之先和過程中,都預設了“漢水流域”的整體性或“一致性”。
我知道近些年學術界關于“歷史流域學”、“流域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設想與討論,但沒有太多關注。“流域人類學”,還第一次聽說。“水域史”與“海洋史”,雖然從根本上說,也是以“水”或“海洋”界定的區域,然而其所追求的目標或學術訴求,應當有所不同吧,我不能太確定,或者說還不太明白。

同時,“區域”觀念及其思想方法,是地理學(至少是傳統地理學)研究與認識世界的基本觀念與方法,它構成了地理學的基礎。如何研究區域,地理學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并且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中。區域的內聚性、中心—邊緣理論、地方感、地方認同乃至地方性知識等概念與研究理路,都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地理學提出來的,或者與地理學有著密切的關聯。人類學的“社區”觀念與方法,較之于地理學的“區域”與“地方”,更強調人在空間范圍內的感知、認同與聚合,使它具有更為豐富而深刻的“人”的內涵與意義。我在這本書里的研究,受地理學“區域”觀念及其方法的影響比較大;后來這些年的思考與研究,受人類學“社區”觀念與方法的影響比較大。最近這兩年,我又比較關注政治學對于空間特別是區域間關系的討論。我的研究,受這些學科相關觀念與研究理路的影響,并努力將它們融會起來,試圖形成自己清晰、明確而相對穩定的研究路線。可是,一直到現在,我也還沒有能夠形成這樣的研究路線,仍然在摸索中。最終能否形成這樣的思想路線,我對自己并不太有信心。

魯西奇:是的,后來的這幾本書,都是本書的延伸與深化。很明顯,我的研究,是從地理出發的。在《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中,我著重地理的因素及人地關系的總體考察,落腳點是在地理上的(那時候,我還是想做一個地理學者的)。《河道變遷與堤防》和《城墻內外》兩本書,處于過渡階段,是從較為單純的地理考察,向人為的地理要素(堤防,城市及其形態)方面擴展,重點是看人類所“制造”或“生產”的地理事物,這中間強調了“人”,但落腳還是在“地”上。《漢中三堰》以及同時期發表的有關江漢平原垸田水利的幾篇文章(后來都收在《長江中游的人地關系與地域社會》卷三中),就有了很大不同,是從水利工程設施(堰渠與堤垸)這種人類“制造”或“生產”的地理事物出發,看“制造”或“生產”它們的過程中以及其后所形成的社會關聯。這中間,“人”及其“社會”既是“制造”這些堰渠、堤垸的主體,又不同程度地“依靠”這些水利設施而生存、交往與發展,并形成其較為獨特的社會關聯。這些研究的落腳點,就不在“地”上,而在“人”與“社會”上了。因為研究“社會”,我又把“制度”的因素引進來,開始觀察王朝國家的鄉里賦役制度與土地制度,是如何與人們為了生存與發展而形成的“水利組織”相互利用、滲透與融會在一起的。《長江中游的人地關系與地域社會》的卷三“江漢平原的水利社會”,本來和《漢中三堰》是一本書(《堰渠與堤垸:漢水流域的水利與社會》),當年由于某種原因,拆開了。把它們合在一起看,能夠更明白我的研究理路的發展。關于鄉村聚落的一些觀察與思考,也是把村落看成為人類的“制造品”或“生產的產品”,并在這個人類“制造品”或“產品”的基礎上形成、發展、運作其社會關系、組織的。通過人類“制造”或“生產”的地理事物,去看人及其社會關系,從而把地理、人與社會聯系起來,并在這一過程中強調“制度”的作用,是我這些年比較重要的研究理路。

江田祥:近十幾年,您逐步將研究區域從漢水流域延伸到中國南方地區,特別是濱海地域,并提出了“中國歷史的南方脈絡”的研究理路與初步設想,請問研究區域、問題意識的變化對您后來的學術研究思路有怎樣的影響,您對區域研究、地域社會研究的方法與路徑的認識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魯西奇:我做了很多年漢水流域歷史地理與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大家也把我看作是區域歷史地理的研究者。其實,我一直在問自己:你做的這些研究,真的有意義嗎?就漢水流域而言,雖然我大致弄清了其歷史進程的基本軌跡、結構與某些特征,可是,我并沒有能夠回答我最初開始研究時提出的問題:漢水流域,特別是其上中游,為什么如此貧困?因為,漢水流域的問題,其實并不在漢水流域。就中國歷史而言,我從漢水流域,看到了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的某些側面,也初步形成了自己對這個世界及其歷史過程的一些認識和認識的方法,可是,我并沒有能夠形成自己的歷史觀念與方法論,甚至未能形成對中國歷史的總體認識。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研究的局限。立足于經驗主義的研究,很可能并不能形成對歷史進程、方向及其動力的把握。換言之。世界上各個區域的疊加,并不是世界;各個區域的歷史,固然是人類歷史的“局部”,但絕不“就是”人類歷史。通過對區域或地方歷史的精細研究與把握,可以加深對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的認識,但任何試圖將基于區域或地方歷史研究而得出的認識普遍化的努力,都可能是危險的。一方面,我認識到區域、地方或地域社會,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研究領域,而且相關的研究確實饒有趣味,又頗具挑戰性;但另一方面,我開始在思想方法上,去反省這些研究及其方法的局限性。
我試圖突破或彌補區域研究的局限性的辦法,最初是努力擴展研究區域。我曾設想把研究對象從漢水流域擴展到長江中游地區,但很快認識到區域范圍的擴大或區域的轉換并無意義。然后,我試圖轉換研究理路,把關注的重心,不是放在區域歷史進程本身,而是放在其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上,加以考察。“中國歷史的南方脈絡”的理念和研究思路,就是在這一思考背景下提出的。近十年來的研究,也是在這個理路下展開的。在這十年里,除了在南方地區的考察,只要有機會,我也盡可能在北方地區跑。其實我內心深處開始懷疑自己的這個理路——真的有一個“中國歷史的南方脈絡”嗎?師友們經常鼓勵我,可以圍繞這個“南方脈絡”或“南方道路”多做些工作,甚至是“打起旗幟來”,可是,2015年以后,我卻很少再談這個話題,原因也就在這里。
事實上,我已經慢慢地離開了“區域”,走到了“本質主義”的路子上來。雖然我還在做區域研究,但無論是“南方地區”,還是“濱海地域”,都只是我試圖探究人類某種生存狀態時“被選擇”的一個地點或地方,其本身的歷史進程與特性,固然要探討明白,卻絕不是我的目標。我希望探究的問題,實際上是人在某種具體的生存環境中的生存、交往、認知與思想及其表達方式,亦即人在不同狀態下所展現出來的人的本質或“人性”。當我寫那篇《人的歷史與人的歷史學》的時候,至少有一位朋友,敏銳地注意到我的本質主義傾向。當時我自己并沒有清楚的認識到。近兩三年來,許多老師系統地闡述人(個體的人、人群及其組成的社會)在歷史進程中的主體作用與意義,我才逐步地明晰,自己真正關注的,其實并不是人在歷史中,而是人的“歷史性”——人的本質的一個重要方面。我真正試圖探究的問題,乃是不同區域(地方、地點或地區)的人,在不同的時期,是怎樣表現出其“人性”(“個人性”與“人類性”)的,又是在歷史過程中,怎樣不斷改造、發展其“人性”的。“歷史的人”或“人的歷史性”意味著“人”與“人性”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并發展的,因而不同時空下所表現出來的人性是千差萬別的;而千差萬別的人性表現,卻在歷史進程中貫穿著一種根本性的“人性”,并不斷發展、完善“人性”,這就是對同類的認同和關愛。

魯西奇:有本書能夠再版,還是很高興的。寫這本書的時候,還很年輕,也比較急,認識也不深,表達也不精致。當年,廣西人民出版社能夠全權出版,就非常了不起了,但畢竟印的很少。社科文獻出版社提出希望重版這本書時,我本想大改的,其實我很看不起當年的自己,怎么寫得這么爛?但一動手,就知道不行。畢竟二十年過去了,我早已不再是當年的我了。如果大改,那就得完全重寫。靜下心來再看看,也發現自己這些年,其實也沒什么進步,很多想法,在這本書里,都有影子了。所以,最后就出了這個修訂本。
我想和相關專業的碩博士同學們說一句,我一直設想做一個小流域的綜合研究。前些天寫了今年六月參加北大文研院隴東寧南考察的個人報告,只寫了一條小河的考察記,是流經今寧夏彭陽、甘肅鎮原兩個縣的茹水河(蔚如水,葫蘆川)。我知道,要是選擇一個范圍適當、資料豐富的小流域,綜合使用地理學、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的資料與方法,一定可以做出很好的研究來,甚至可能在理論與方法上取得一些突破性的進展。但這樣的選題,其實很難做,最現實的困難是短期內無法發表論文,所以,又不建議做。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