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諾獎作家托妮·莫里森:離婚后,她開始寫愛,寫背叛
原創:Lens

年輕時,莫里森并沒有想過成為作家。她那時在大學里任教,27歲時和一位建筑師結了婚,先后生了兩個兒子。但這段婚姻只持續了六年。
離婚時,第二個孩子還在肚子里。
此后,她再也沒有結婚。
有人指,莫里森是為了對抗離婚后的孤獨才開始寫作的。她回應道,“可以這么說,雖然它簡化了現實的復雜。”

在很長的時間里,她都有朝九晚五的工作,獨立撫養兩個孩子。她感慨過,男作家們從來不用考慮這些。
她開始寫作也不是為了賺錢——在那個時代,她還沒聽過有像她這種出身的女性靠寫作成名的事兒。
她是感到了有些東西非說不可,有些答案她必須要去尋找。
在諾獎(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致辭時,莫里森說,文學會創造意義,讓語言沉思,”語言能保護我們“:
“告訴我們做女人是怎樣的,我們才會知道做男人是怎樣的;告訴我們什么在邊緣移動,在這個地方,沒有家是怎樣的,離開了熟悉的家四處飄游又是怎樣的;告訴我們生活在城鎮的邊沿,無法忍受你的陪伴又是怎樣的……”
01
“讓我重新開始吧,
看一看做成年人是怎樣一回事。”
莫里森受父親影響很大——父親只是個焊工,卻很善于講民間傳說和鬼故事。
父親很聰明,負責任——為了養家,換過很多份工作。
他總是對莫里森給予肯定,有些夸獎莫里森都懷疑自己身上是否具有。
這種愛,讓莫里森在當時黑人被歧視的環境中成長時,沒有過自卑。
只是到了中學、要談戀愛時,她才強烈地感受到歧視和不公。她也沒有逃避,她知道反抗的力量就在自己身上。
莫里森說自己從不在乎失敗,但很在乎男人們要聰明、“要知道得更多”。就像她的父親那樣。
她的前夫很聰明,但“他對自己的生活知道得更多,而不是對我的生活。”
因此,她果斷提出了離婚:“讓我重新開始吧,看一看做成年人是怎樣一回事。”
單親媽媽的生活不會太好過,尤其在那個時代。
但莫里森對可能的失敗做好了準備。
離婚后,她立刻去找了一份在蘭登書屋的工作,并帶著孩子搬了家。

工作之外,莫里森沉浸在寫作中。
但只能在孩子們入睡后寫——她不能為了自己的追求,犧牲了孩子們的生活。
天亮之前,莫里森就爬起來,給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后開始寫。
久而久之,她覺得自己在早晨時腦袋才會最清楚,最有自信,太陽落山后,自己的創造力就會被收走……
這種習慣變成選擇,一直延續到去世。

“我是那么忙碌。只知道我再也不會把我的生活、我的未來托付給男人的隨心所欲了,公司里的或是外面的任何男人。他們的判斷跟我覺得我能做的事情再也不會相關了。”在《巴黎評論》的訪談中,她如此總結離婚后的生活,“離婚而有孩子是非常棒的解放。”
02
“我總是在寫背叛”
她的第一本書《最藍的眼睛》,花了五年寫完。發表時,她39歲。
故事靈感來自于她小時候認識的一個黑人小女孩,她祈求上帝給自己一雙藍眼睛——因為“藍眼睛”是一種別人認可的美。
這雖然是一個黑人話題,但更是受到排斥的人失去自我的故事。他們活在別人的目光里,從來沒有看到過自己,直到幻想出一個自己,祈望有奇跡出現來讓自己解脫。
這個小說當時印了2000本,評價不高。莫里森也只拿到很低的報酬。
直到1993年,也就是她獲諾貝爾獎那年,該書再版,她在后記里寫道:
“贏回它的發表尊嚴,足足花了25年。”

寫到第三本小說時,莫里森才確信這就是她生活的中心。
“書不寫完我從不簽合同,因為我不想把它變成家庭作業……我寫書不簽合同,如果我想要讓你看,我會讓你看的。這跟自尊心有關。”

辭職幾天后,坐在自家門前的碼頭上,看著寧靜的河水,她開始感到急躁。想了很久都找不到有什么煩心事在困擾自己……
回到家中細細品味這種憂慮甚至恐慌,她才豁然開朗:
“我感到幸福,享受著從來沒有過的自由。這種感覺太離奇了。不是狂喜,不是滿足,不是過度的歡愉或成就感。是純粹的喜悅,一種確定的對游手好閑的預期。”
就是在這種感覺里,莫里森開始寫作《寵兒》——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探究“自由”對女人意味著什么。

她的這些主題,別人說永遠都是關于愛。她說,“我點頭,是的,但也不對——不全對。其實我總是在寫背叛。愛的天空,背叛是閃電,把天空撕開讓我們看清楚。”
03
女人的友誼:
“我們必須被教育成彼此喜歡”
作為單親媽媽的日子里,莫里森有幸身邊有些親密的女性朋友。
她們那時彼此住得不遠,結成一個互相依賴的小團伙。當她必須寫一些東西時,她們會幫她帶一會兒孩子。
她也寫了很多和女性友誼有關的故事。
”對于很大一部分女性來說,女人的友誼被看作是一種次要的關系。男女關系是主要的。女人,你自己的朋友,一向是男人不在時的輔助關系。因為這樣,才有了整個那一群不喜歡女人和偏愛男人的女人。“莫里森說,”我們必須被教育成彼此喜歡……停止彼此抱怨、彼此憎恨、爭斗,停止和男人一起譴責我們自己。“

她的第二部小說《秀拉》就寫了兩個一起長大的女人:一個叫奈爾,按部就班地生活;另一個叫秀拉,選擇放縱地生活,尋找一個個情人,又將他們一個個拋棄。
在這種觀念差異下,兩個閨蜜友好但不再親密。
最后,秀拉在孤獨中臨死之時,奈爾去探望她。兩人誰也無法證明自己的選擇是更好的……
很顯然,這不只是50年前兩個黑人女性面臨的矛盾,今天的我們,也依然時時處在類似的掙扎里。
莫里森后來的《愛》,也是寫了兩個玩伴:克西斯廷是來自富裕家庭柯西的孫女,留心是窮人家的女兒,她們卻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但柯西娶了留心,小玩伴成了她的小祖母,克西斯廷不能接受,和留心絕交后離家出走。
多年之后,走投無路的克西斯廷又回到家中,和留心生活在一起。但彼此憎恨。直到留心死前,兩人才敞開心扉,最終實現了和解——但這一切來得太晚了,她們已經付出了一生作為代價。
《秀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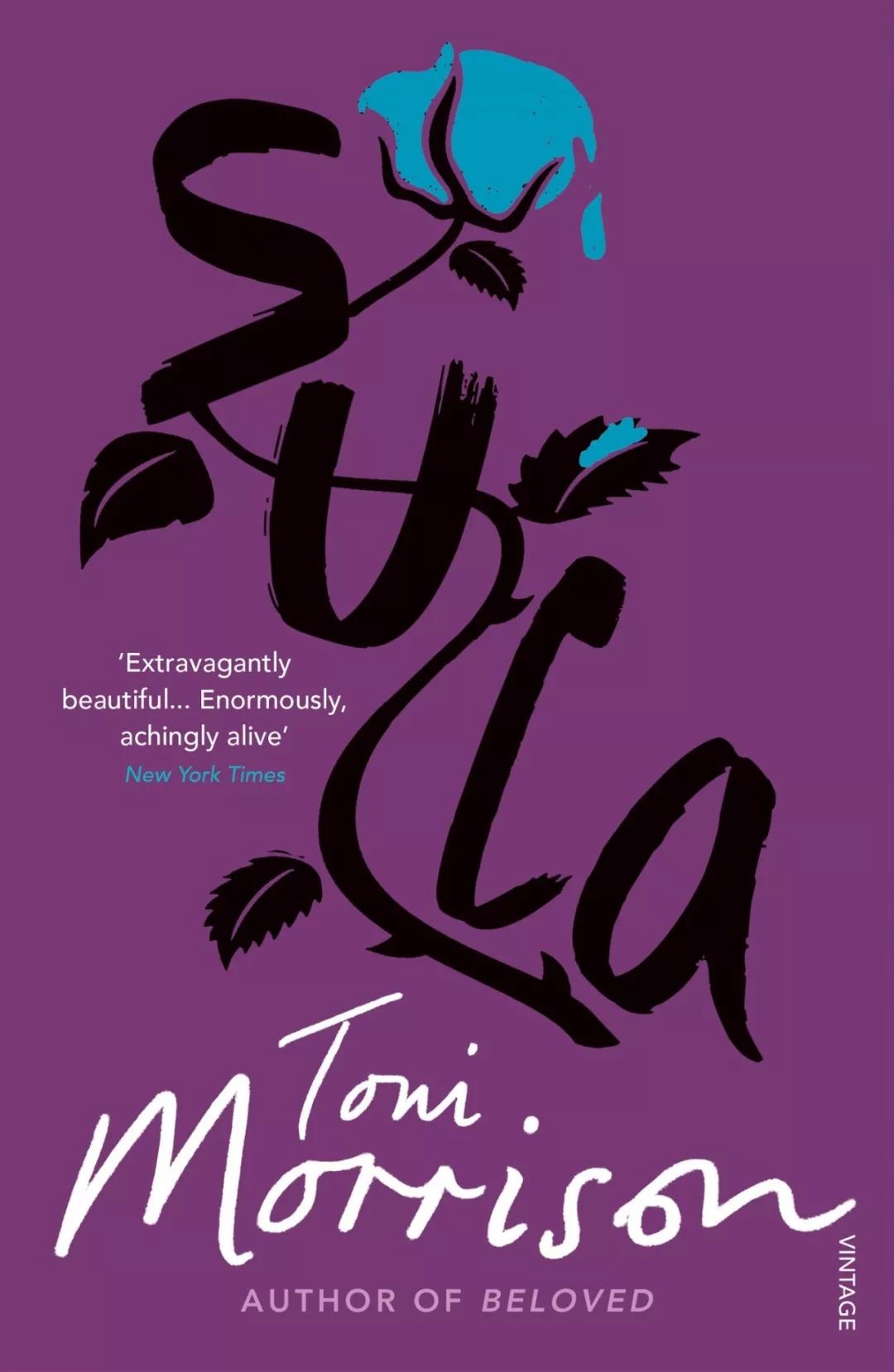
“在所有的老太婆都和十幾歲的男孩睡過之后,在所有的年輕女孩都和她們醉醺醺的叔叔睡過之后……在所有的狗干過所有的貓、倉庫上的每一個風向標都飛下屋頂壓到豬身上之后……那時就會有一點剩余的愛給我。而且我知道那會是什么滋味。”
“他們將是她所愛的一切。然而這種愛如同在火上熬得太久的糖漿,成了又硬又甜的一灘泥,粘在鍋底刮不掉,只剩下甜味。”
《愛》

“像友誼一樣,仇恨不僅需要身體上的親密,還需要創意和努力才能維持。”
“給她們一個相互聯系的理由,或許能明白舌頭有多寶貴。”
“男人的記憶是最短暫的。所以他們總要照片。”
“他們不懂那真正的、更好的、損失最小的、彼此都受益的方式。那樣的愛需要智慧,輕輕柔柔,無依無傍。”
04
傷痕累累的愛
莫里森的很多小說是關于愛,包括那些被命運摧殘、被生活傷害后繼續選擇的愛。
醞釀十年、寫了三年的《寵兒》是尤其震撼的一部。
故事講一個女奴塞絲,生活在絕望之中,為了不讓兒女重復自己做奴隸的悲慘命運,而將最小的女兒殺死,下葬時取名”寵兒“。
塞絲一直活在愧疚之中,而“寵兒”的冤魂則在家中肆虐,造成一系列悲劇,后來還以少女的肉身還魂,繼續難以饜足地向塞絲索取著愛,不擇手段地擾亂母親剛剛回暖的生活……

奧普拉回憶說,當年她還沒讀完《寵兒》,就難抑激動地飛到紐約,通過報警查到莫里森的電話。
見面后,奧普拉泣不成聲地問,“你是如何寫出這樣的作品的?我可以把它拍成電影嗎?”
這就是后來的電影《真愛》,奧普拉自己出演了塞絲一角。
還有很多愛是給予孩子的。
《紐約客》有一篇拜訪莫里森的文章,里面提到有一年她的家中著火,因為是寒冬,消防員噴出的水結了冰,一些珍貴的東西被毀,比如她的部分手稿。但最讓她惋惜的,卻是孩子的成績單——說到它們再也不會回來時,她的眼里充滿了淚水。

莫里森對孩子的世界十分珍視。她晚年和兒子斯萊德一起寫了系列童書。其中,《大箱子》就來自斯萊德9歲時的一個想法。她以此提醒大人:要傾聽孩子的心聲,不要以愛的名義去綁架孩子。
4年前,她又推出一本小說《孩子的憤怒》(God Help the Child),寫的是童年對人生的影響。
故事里的母親,對女兒十分嚴厲,認為這樣才能讓孩子在惡劣的環境中學會堅強,“我做了對她而言最好的事。”
而為了贏取媽媽的關注和愛,女孩撒謊傷害了另一個人,長大后也給自己披上看似強悍的偽裝……
這也是很多原生家庭里發生過的殘酷。
“即便你認為自己的童年非常完美,我仍懷疑其中總有那么幾滴毒藥。你可以忘記它,但有時,它會在你血液里留下一絲痕跡,決定你如何回應別人,決定你如何思考。”莫里森寫道。
《寵兒》

“到一個你想愛什么就愛什么的地方去———欲望無須得到批準———總而言之,那就是自由。”
“還有一種孤獨四處流浪。任你搖晃,絕不就范。它活著,一意孤行。它是一種干燥的、蔓延著的東西,哪怕是你的腳步聲,聽起來也仿佛來自一個遙不可及的地方。”
“愿意的話,他們摸得到它,可是千萬不要摸,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碰了,一切將不會安然如故。”
《爵士樂》

“他對她的死非常在乎,傷心得要命,可他更在乎的是他的記憶可能再也想象不出那種親昵了。”
“知道什么時候去愛,什么時候放棄。要是不知道的話,到頭來你會失去控制,或者被身外的什么東西控制住。”
“特雷斯先生看著你的時候,兩只眼睛是不一樣的。每一只有每一只的顏色。一只眼睛悲哀,讓你看見他的內心,一只眼睛澄澈,看見你的內心。”
“從葬禮上跑回家后,‘我愛你’偏偏是維奧萊特不能忍受的聲音。她在屋子里踱步的時候盡量不去看它,可那鸚鵡看見了她,透過窗玻璃微弱地叫了一聲‘愛你’。”
《恩惠》

“在你之外。空蕩一片。我身上感到饑餓的不是胃而是我的眼睛。用多少時間都看不夠你的動作。”
“在這種地方做女人,就是做一個永遠長不上的裸露傷口。即使結了疤,底下也永遠生著膿。”
《所羅門之歌》

“很多人對我的死活只是感興趣,但他是關心。”
《孩子的憤怒》

“只有成為母親,你才會發現自己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你對待孩子的方式,會深深地影響他們,他們可能永遠也無法擺脫”。
《最藍的眼睛》

“愛絕不比施愛者更美好。邪惡的人以邪惡的方式去愛,殘暴的人以殘暴的方式去愛,軟弱的人以軟弱的方式去愛,愚蠢的人以愚蠢的方式去愛。一個無拘無束者的愛絕不是安全的。被愛者得不到任何饋贈。唯有施愛者占有自己愛的饋贈。”
“這片土地對某些花卉來說,生存條件太過惡劣。某些種子無法獲得養分,某些植物不會結果,當土地決意展開殺戮時,我們默許了,說什么受害者無權生存。當然,我們錯了,然而這無關緊要。已經太晚了。”
06
常掛在嘴邊三個詞:
“不”“閉嘴”“出去”。
莫里森的作品看似沉重,其實充滿樂觀。
”我知道這個世界傷痕累累,流血不止。盡管不要忽視它的痛苦很重要,但拒絕屈服于它的惡意也至關重要。“

語言會被權力利用,“在可敬的愛國主義的裙衣下蜷曲著法西斯主義的根須”;語言會“煽動”,被人屠殺并屠殺別人;“將會有更多迷惑人心的偽經驗主義語言被巧制出來,把有創造性的人們禁錮在卑微和絕望的牢籠之中。”
而這,正是她選擇文學的理由。讓語言沉思,去反抗權力和規訓的戕害。
“只有作家才能深刻地理解創傷,才能把悲傷化為意志,化為敏銳的道德想象力”。
她還說:“作家的生活和工作不是人類的禮物,而是必需品。”
所以,在晚年,她還一直在不斷地寫。這是她的武器。
幾年前,在一個采訪里,她說自己的心理年齡是23歲,“一個剛剛好的時候。”
去世后,她的家人在聲明里說,“她寫作時最自在。”

她還取消了和老東家蘭登書屋簽下的自傳約定:
“我在普林斯頓教創意寫作時,就對學生們說別寫那玩意兒,別寫你那點微不足道的人生”。

影片略過了那些獎項、榮譽,也沒有雕琢她堅韌而勤奮的履歷,甚至沒有去講她辛苦養大的兩個孩子——她的次子幾年前患癌去世了。
里面呈現的,只是一個喜歡抽煙的老太太,坐在霞光之中,神采奕奕地談著話。
窗外靜靜流淌的,是已經陪伴她幾十年的哈德遜河。
曾經,閑下來時,她很喜歡坐在門廊上,花去一整天看著光線變化,聽著河上傳來的風聲和水聲……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