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們該如何讀懂勒克萊齊奧?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對于小說的定義,真的相信,好的小說家都是魔法師,好的小說都是寓言性的小說。勒克萊齊奧的所有小說幾乎都是這樣,作為個體的故事,一切顯得匪夷所思,然而,作為人類命運的探索,一切卻又令人膽戰心驚。在小說結構上,勒克萊齊奧至少在創作的初期表現出與新小說的某種親緣性,可是阻止他最終成為新小說人物的關鍵因素,也許首先是語言。喜歡他,因為他也是一個相信詞語力量的人,并且,完美地體現了這份力量。和女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男作家總是更傾向于尋找某種絕對的力量對充滿悖論的小說世界進行幻覺式的澄清,使得悖論在這個迷人的空間里被暫時懸置。這就是為什么女作家往往會呈現出迷人的悲傷姿態,而男作家卻往往能夠呈現令人向往的力量。

勒克萊齊奧
勒克萊齊奧在語言上的探索并沒有走得像羅布-格里耶或薩洛特那樣遠,他的語言標準、規范而優美。優美到在翻譯時要讓人心焦的地步,唯恐找不到合適的詞語和意境。這或許和他在雙語環境中長大有關。在兩個語言世界猶豫和選擇的人往往會對語言本身表現出一種更為積極和肯定的構建愿望,希望維持某一類語言中特有的因素。不知道勒克萊齊奧是不是出于這樣的原因,他對于傳統的挑戰僅僅到消減傳統小說的要素為止,甚至,在八十年代之后的小說創作中,連對傳統小說要素的挑戰也已經不再那么激烈了。他在八十年代以后創作的小說已經有了真正意義的主人公,并且,有了歷史背景襯托之下的所謂故事。雖然,小說仍然保留著現代小說的某些特征,比如說復調——我們借用昆德拉的語匯——比如說情節和人物的相應淡化,比如說敘事時間鏈的截斷和錯位,但是,完整的敘事者視角,完整的故事,開始和結束,這些似乎是傳統小說所著眼的因素較之其青年時代的小說創作有明顯的增加。
也就是說,勒克萊齊奧進入中年之后,在小說主題和手法上出現了轉向。如果說從《訴訟筆錄》開始,一直到《洪水》、《戰爭》、《逃遁書》,小說在勒克萊齊奧的筆下是對現代文明的一種質疑和否定,從八十年代以后,勒克萊齊奧卻趨向于一種肯定的寫作。轉變當然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勒克萊齊奧去到南美,并且沉浸于有別于西方主流文明的其他文明相關。創作于1980年的《沙漠》Le désert,第一個中文譯本譯為《沙漠的女兒》,2008年勒克萊齊奧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版本更名為《沙漠》。將視線轉向了北非沙漠的“藍面人”,這一轉變看來也吸引了評論家的目光,因此,小說獲得了第一屆保羅·莫朗獎。
肯定的寫作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尤其在今天這個時代。在小說領域,包括在小說以外的領域,減法無論如何都比加法好做。尤其,我們愿意相信小說家的使命就是對世界產生懷疑,甚至質疑已在的“合理”,就是不“媚俗”——用昆德拉的小說概念來說。
肯定的寫作所要求的,是信念。勒克萊齊奧在一次訪談中曾經談起過十八歲的時候,他讀薩特、加繆、莫里亞克的專欄,談到那個時代的“介入作家”相信可以憑借文字的力量改變世界——我們稱之為“理想”——憑借一本小說,憑借一組專欄文章就改變世界。然而法國的當代文學是絕望的文學,是一點點把我們曾經相信的東西毀滅掉的文學。現實的世界坍塌了,可是文字的世界并不能用來替代現實的世界,因為它也是不完整不完美的,因為它在描述現實世界這座廢墟時,自己本身竟也幾乎成了一座廢墟。不能夠聽憑這個世界這樣坍塌下去,我們應當做點什么,這是勒克萊齊奧在日臻成熟之后所體會到的作家的使命感。因而在八十年代之后,我們清楚地看到,寫作對于勒克萊齊奧來說,既非逃避之地——逃避個人的,情感性的深深的悲哀——亦非試驗之地,而是一磚一瓦的構建之地,是給人以夢想、以希望的構建之地。
八十年代的這次轉向讓勒克萊齊奧脫離了六十年代群、七十年代群甚至是八十年代群作家,因為他選擇的逃離方式是獨一無二的: 南美世界的史前文明。他翻譯出版了——這在西方也是第一次——兩部南美的神話傳說,并且開始在未來的小說創作里,在面對現代物質世界經歷了焦灼和欲喊無聲之后,開始精心構造一個他所向往的童話世界。因為這已然是一個令人絕望的世界。或許,四十歲以后的勒克萊齊奧終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吧。他對南美土著世界的發現和迷戀幫助他及時地抽離,逃脫了流派(以及歸屬于某種流派之后,有時不得不表現出的極端與夸張)的規定,永遠在尋找“真”的路上。
隨著主題的轉向,勒克萊齊奧的文字也顯得更加美麗、流暢和輾轉,充分顯示了標準法語的魅力。他的句子開始變長,筆下世界的色彩更為艷麗,能夠給讀者以充分的感官享受。
《流浪的星星》一開篇,是這樣一段戰爭前的幸福:
在夏日的灼熱里,在這碧藍的天空下,她感到有那樣一種幸福,那樣一種盈溢了全身,簡直——叫人有點害怕的幸福。她尤其喜歡村莊上方那一片綠草萋萋的山坡,斜斜地伸往天際。
碧藍的天空,耀眼的陽光,濃密的綠色草地——我們在這樣的語言里的確能夠感受到,原本我們有一個純凈而美麗的世界,在我們不懂得仇恨,不懂得利益,不能夠感受到物質世界的存在之時。
很有意思的是,和這個物質世界相適應、能夠展現這個物質世界的斷裂、疼痛的語言文字往往也是斷裂而疼痛的。唯美的語言竟然還是在童話,或者神話里,在我們已經遺忘的傳奇里。
真的拒絕了抒情和浪漫,真的拒絕了理想與熱情,就像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里所說的那樣,輕就是真的美麗嗎?世界被消減為廢墟之后,有的小說家還是不忍,承擔起尋找和建構的工作。

昆德拉
勒克萊齊奧的工作,就好像是要在這座廢墟里建造一座童話的城堡,用的是美麗的詞語磚石。(盡管出現轉向,勒克萊齊奧仍然使用的是詞語,而不是傳統小說中與理性的思維邏輯世界保持一致的話語。)后來他曾經簡單地描述過對寫作的根本看法,他說,作家要做的就是,到鄉村去,就像一個業余畫家,帶上筆和紙,選擇一塊沒有人的地方,嵌在群山間的山谷,坐在巖石上,久久地看著周圍。看好了之后,就拿起紙筆,用詞語把所看見的一切描繪出來。因為找到了家,八十年代以后的勒克萊齊奧的創作變得尤其穩定,曾經淡化的人物和故事開始慢慢地在他的小說中找到了位置。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幸運地逃過流派規定的勒克萊齊奧曾一度被貼上新古典主義、新新小說或是新寓言派的標簽。古老的印第安文明和神話給了他形式,從而也給了他靈魂的居住地。1985年,他出版了《尋金者》,次年,又有了《羅德里格島游記》。
1992年,他出版了《流浪的星星》。這是一個講述回家的故事。什么是家?對于猶太人來說,他們的家園在哪里?次年,對南美大地充滿感情的他出版了一本傳記《迭戈與弗里達》。1995年,他出版了講述自己外祖父家故事的《檢疫隔離》。在世紀末,他又相繼出版了《金魚》、《歡歌的節日》、《童年》等作品。這位雖然不能被納入任何流派,卻已經成為法國現代文學不能略去的一頁的作家至今已經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作品涉及小說、散文和翻譯。
但是,如果說我們談到了勒克萊齊奧中年之后在創作中出現的主題和文風的轉向,我們卻不能忽視另外一點: 一個堪稱偉大和重要的作家再有轉向與變化,也必然會顯示出作品的整體性。這整體性既是主題性的,也是文風上的。發現南美的世界或許是勒克萊齊奧幸運的起點,幸運,或者說是命。然而一切都是從對這個技術高度發達的西方現代文明社會的懷疑開始的,后面的轉向并沒有改變這個根本的前提: 速度,豐富的物質真的給我們帶來了幸福嗎?而在這樣的社會里,我們的情感何在?我們的家園何在?我們的災難又究竟源自何處?為什么在高度發展的物質世界里,人類永遠避免不了似乎是遠古神話就已經奠定下的悲劇模式?西方現代文明社會已經如同巨石一般橫亙在世界的中央,堵住了歡愉的生命的通道,我們該怎么辦?
于是他向后退去,退一步,一方面是為了看清楚這個吞沒自己的世界——或許,這也是相信語言世界的人所必然做出的舉動吧。而另一方面,退一步,竟然心甘情愿地退到了一種史前的文明里,“大洪水”到來之前的那個人與自然、環境和平相處的狀態。這種狀態,想象中的非主流文明還為我們保留著,雖然,我們幾乎都知道,這種狀態必然,并且已經遭到現代文明的毀滅性的吞噬。
在勒克萊齊奧的身上,我再三使用“童話”這個詞,我想,他和我一樣明白,其實他逃遁其中的史前文明并不存在,南美或者非洲的美麗原始世界說到底在今天的社會里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世外桃源。于是我們又要回到我們在緒論中的話,所謂“用文字的性感來對抗生存的死感”的問題。而我也是在閱讀之中,尤其是在這一年的閱讀之中,漸漸明白一個道理,其實或許人類的誤區就在于一直在尋找著什么。尋找美麗,尋找愛情,尋找家,尋找真實。可是,神話所奠定的模式就已經告訴我們,尋找注定了“永遠在別處”的悖論。是在尋找的過程中,我們有了《流浪的星星》里的這首詩:
在我彎彎曲曲的道路上
我不曾體會到甜美
我的永恒不見了
然而有一天,有人對我說,如果真實是一種構建呢?如果它可以是一種構建,童話就是它的外衣,它的居所。勒克萊齊奧所創建的世界,就是用美麗的詞語蓋了一座與現實隔離的透明屋子,在現實的存在廢墟之中,它是那么耀眼,給每一個相信文字力量的人以安慰和避處。因為它的完整和堅固,它不會破碎,它所包裹的真實也不會破碎。勒克萊齊奧完成了那首題為《天真的預示》的詩歌。詩里的最后一句說——把永恒在剎那之間收藏。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記憶是痛苦,未來是虛無,語言這種經歷現時的唯一方式可以為我們提供不再心碎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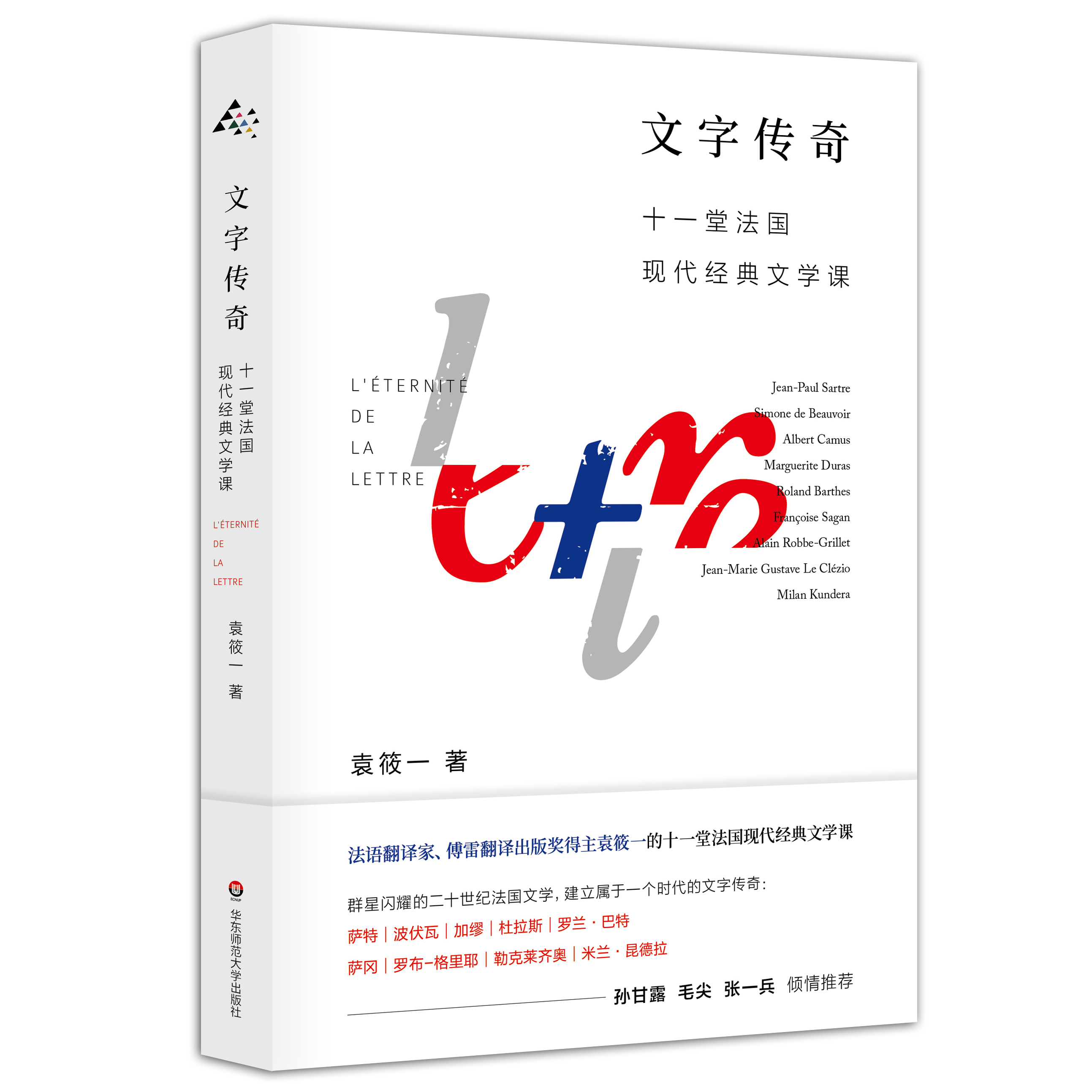
本文節選自《文字傳奇:十一堂法國現代經典文學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5月版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